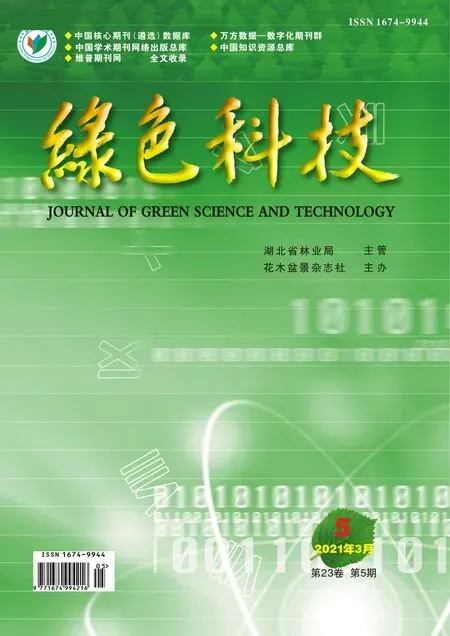近20年国内文化景观研究进展
张俊玲,刘佳辉,潘 婷
(东北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1 引言
随着西方学界对于人文地理学科的理论探索以及在认知层面不断深化,“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在19 世纪末由德国学者施吕特尔第一次提出,他将景观的形态看作为文化的产物[1]。20世纪20年代,文化景观的研究从概念的提出开始逐渐扩展,并且美国人文地理学者苏尔(Carl.O.Sauer)不拘泥于传统的人文地理研究方法,成立了文化景观学派。他借用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视角,从以往单纯地研究自然地理,开始转向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探讨不同文化对景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化景观的兴起是在1980年之后,由于后现代思潮以及新文化地理学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对文化的概念不再局限于静态的结果中,他们认为文化是动态的并且存随着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变化。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已经从传统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过渡到经济、政治领域,希望从多个视角获得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将历史城镇景观纳入其研究的视野。同时文化景观逐渐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在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被正式确定,它代表着一种内涵更加丰富、维度更为宽广的遗产范畴[2]。对20年文化景观的研究历程进行综述,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国内不同学者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发展历程以及研究领域分类。
2 研究数据及方法
在2000年之前对于文化景观的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以文化景观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仅为171篇。从2000年之后,文化景观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从2000~2020年,以文化景观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高达768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占957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8篇,硕士学位论文939篇。国内外会议发表123篇;报纸期刊发表6772篇;国内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起步于1985年,本文总结了国内文化景观近20年的研究历程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以“文化景观”为搜索词进行检索搜集文化景观的期刊文献,对检索出的文化景观期刊文献以作者进行首次归纳分类研究,得出不同作者团队的研究方向。以年度发表期刊文献脉络为第二主要研究线索,得出文化景观研究方向的发展历程。在2000年之前国内学者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处于初探阶段,相关期刊文献数量较少。总结了国内对于文化景观研究的发表期刊文献数量,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文化景观发展逐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2000年至今,学者对于文化景观的关注度增加,是什么引起了学者对于文化景观研究的关注,通过对每年发表期刊进行归纳解读,得出国内文化景观研究四个时期内的研究重点,也得出了文化景观受到关注的原因。
3 文化景观内涵演变
3.1 地理学范畴
查阅景观这一词汇的来源,发现其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原本的意思是指美好的风景、事物,随后景观在地理学的语境下被赋予了学术概念。1986年德伯里在《人文地理学:文化、社会与空间》一书中认为“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所有可辨认出的改变,包括对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3]。
3.2 景观学范畴
1925年,美国学者苏尔发表了文章《景观的形态》,其中将“文化景观”定义为“特定的文化群体在自然景观中创造的格局,是具有丰富时间层次的人类历史,体现了传达场地本质的人的价值”;苏尔的学生怀特认为景观离不开人类的活动,景观是由人类活动层层叠加而来,在每一个阶段都会表现出人所造成的影响,他将此称之为“相继占用”理论。
3.3 遗产学范畴
199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将文化景观纳入到遗产的范畴,其中明确了文化景观与人之间的强关联性,它不仅仅指人在自然中生存所呈现的文化性,也指人类为了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大自然改造的过程以及结果,由此反映出来的景观。1994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指出:文化景观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4]。也就是说文化景观在遗产学层面已经逐渐受到认可,而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
4 文化景观的研究历程演变
4.1 文化景观的总体研究特征
4.1.1 论文数量及期刊分布
总体上,1980年代国内开始展开文化景观研究,到1995年文化景观期刊论文数量呈现不断增多趋势。这说明文化景观在国内不断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从侧面印证文化景观的学术潜力巨大,也暗含着相当多值得挖掘和丰富的问题。在1995年之后,随着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文化景观的相关论文数量也持续增大,研究包括遗产保护、文化景观保护、文化景观判别因子等方面。与文化景观相关的论文大多发表在《风景园林》《中国园林》《世界建筑》《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等20多种期刊上。
4.1.2 基金来源
所发表的论文中,基金来源主要是国家级基金、省/市级基金、高等教育基金及其他基金四大类,其中受到国家级基金资助的占比最多,高达76.3%,尽管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支持,文化景观的研究仍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较多,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论文成果占比高达55%。另外,具有省科学基金支持的论文成果有15.1%,具有教育部基金支持的论文成果有4%。
4.1.3 研究团队
对研究文化景观的科研团队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文化景观是以韩峰、王向荣、王云才、单霁翔和俞孔坚近等40位学者为首的研究团队为主,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景观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进行探讨。如韩峰团队侧重于文化景观的内涵以及文化景观的遗产保护的研究,总被引频次最高,其研究成果对文化景观相关研究影响巨大。李和平团队侧重于探讨文化景观的类型的分类标准以及其对它们的评价机制。王云才团队则更多的研究文化景观的地域性,因地制宜地研究文化景观保护策略及文化景观地演进方向。学者们的研究有其自身的优势,为文化景观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
4.2 国内文化景观研究内容分类
4.2.1 文化景观概念的引入与热点问题
步入21世纪,国际上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成果日益丰满且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国内也开始切入到文化景观的研究中。首先是韩锋、单霁翔在深入了解国外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背景之后,提出了中文语境下的文化景观概念,这对于后面的学者进行再研究有很大的价值。韩锋具有先进的理念以及相当的国际视野,她先后编译了麦琪·罗的《〈欧洲风景公约〉:关于“文化景观”的一场思想革命》[5]、路易奇·扎赫日的《文化景观与自然纪念地》[6]等一系列国外学者对于文化景观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这极大地方便了国内学者对文化景观的初探,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2010年,单霁翔在其著作《走进文化景观的世界》中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推动了国内将文化景观作为遗产对象的广泛研究工作[7]。
4.2.2 文化景观类型划分及评价研究
在概念引入、明晰的同时,李和平等深入分析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文化景观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的文化景观的类型进行划分,分为设计景观、遗址景观、场所景观、聚落景观和区域景观[8]。王毅根据《操作指南》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67处文化景观进行分类,并探讨每一类文化景观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其中的10条标准使用情况[9]。
4.2.3 文化景观的地域性探索
在文化景观的概念引入与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基于不同地域的特色对文化景观的地域性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保护策略研究和实例分析。
王云才等提出了保护传统地域文化的重要调控机制[10,11],另外他还利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提出了地域性文化景观的保护模式。在文化景观保护实例研究方面,赵荣、司徒尚纪等人开展了具体区域的文化景观研究并发表著作《陕西文化景观研究》《广东文化地理》;李和平、肖竞等人将视角着重在历史村镇的文化景观保护方面,更加具有地域性[12,13];而国内早期对于文化景观案例的探索则是苏黎杰和郭晓[14,15],他们分别选取北京和武汉两个城市,对文化景观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
4.2.4 乡村文化景观
王云才等提出了以“大地叶片:细胞机镶嵌体”的概念模式、“水系紫脉”的传统文化遗产廊道和“生长的细胞体”[16,17]。
在村镇文化景观的实例研究上,宋霞[18]对河南小城镇中的乡村的痕迹,及其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风土民情交织的景观演进过程作了分析;张海霞[19]以平遥古城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放问卷以及访谈等形式,对所得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并绘制专题地图,对当地的文化景观的梳理以及旅游开发情况有很好的总结。
4.2.5 文化景观遗产相关研究
4.2.5.1 文化景观遗产发展动向及趋势
韩锋在[20]《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国际新动向》中以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了国际遗产的发展动向以及中国文化景观在遗产保护领域的机遇,在《亚洲文化景观在世界遗产中的崛起及中国对策》中提出中国文化景观需要在空间上和类型上进行深入地基础研究,为全面建构景观战略体系打好基础;李晓黎等分别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类型发展趋势前瞻及其动因解析》《文化景观、历史景观与城市遗产保护——来自美国的经验启示》中浅析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类型以及保护发展趋势[21,22]。
4.2.5.2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
单霁翔在《实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中描述了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保护观念的变化进程;朱强、李伟在《遗产区域:一种大尺度文化景观保护的新方法》一文中描述了美国是如何通过遗产的角度对文化景观进行保护,引出我国如何在较大的尺度下完善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体系[23];邬东璠、庄优波、杨锐在《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及其保护探讨》中通过对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的重新认识提出了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管理的思考[24]。
4.2.5.3 文化景观遗产地域研究
在文化景观遗产发展趋势以及保护的研究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考虑如何将中国特有的地域性融入到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中。钟福民、王林、高悦发表的《论江西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以赣南地区为例》《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要素探析——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洋浦古盐田文化景观遗产的现状问题与保护对策》等文章都是以个案来探索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构成以及问题策略等问题。谭波的《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的居民认知特征——以浦市古镇辰河高腔为例》提出了对于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策略[25~27]。
4.2.6 文化景观研究的技术方法
在文化景观体系概念保护等方面都已经具备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上,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上,许多学者进行了探索,能为文化景观的研究提供可靠数据以及技术支持。
一方面,刘沛林等人在研究中巧妙地借助生物学上“基因图谱”的概念,通过深入研究各聚落的景观区系的“文化基因”,最终建立起“景观基因图谱”,直观地展示出不同聚落景观区系的演化过程以及它们的关联性;另外他们还建立了景观基因图谱平台,并分析了平台构建中的技术难点以及解决方案,提高了景观基因图谱分析的效率和科学性。另一方面,GIS的运用也极大的提升了古村落文化景观的管理水平。邓运员等人论证了GIS技术代替传统管理手段的可行性,并试图以凤凰古城为例加以解释。
5 讨论与结论
虽然文化景观在西方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且在文化景观的概念、类型、保护手段等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通过对文化景观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发现近20年国内的文化景观领域在韩锋、王云才、王向荣等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在文化景观的概念、类型及评价、地域性探索、乡村文化景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技术手段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目前我国文化景观的研究正处于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内特色,积极进行深入探索的进阶发展阶段。
回顾文化景观在我国的发展过程,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学者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状,在国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视角等,比如旅游发展、公众参与、地域特色、政府规划等相关领域。因此,在探讨我国文化景观的发展研究的同时,应当结合国内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发展与保护研究。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在未来的研究中,新技术新方法新数据的运用对研究成果的提升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