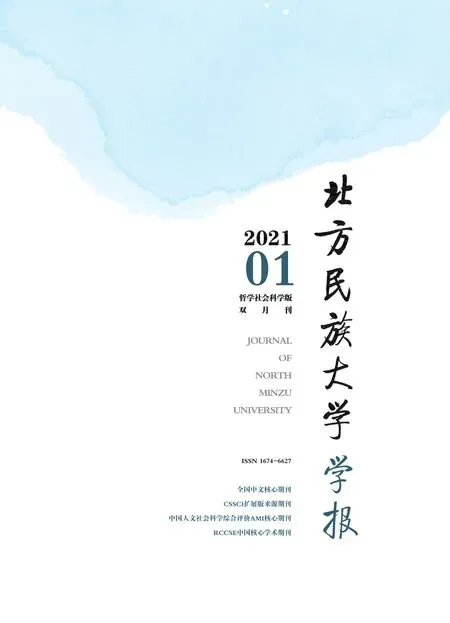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
——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
刘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和方向,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场域。事实上,“共同体”已然成为破解当今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实践路径。而关于“共同体”的经验研究及理论思考,国外学界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如何将国外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所用”,使之成为我们研究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参照工具,是一个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
谈及西方的“共同体”理论,很多学者可能会追溯至1887年出版的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Tönnies)的著作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国内学界一般将这部著作译为《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Gemeinschaft”因此一般译为“共同体”[1](1)[2],也译作“共同社会”[2]“社区”[2][3](285)或“社群”[4]。问题在于,孕育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共同体”理论能不能或者说多大程度和意义上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当今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引入和消化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变迁和经济社会转型,开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本文拟对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进行揭示,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提出一些个人浅见。
二、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及其在西方学界的传播与发展
1887年,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出版了《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书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基本结合类型:共同体和社会。“在滕尼斯看来,无论是经验水平上的社会纪实,还是理论水平上的应用社会学,都需要一个概念体系。并且,这种概念体系还不是一般的概念分类,而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东西,即滕尼斯的标准概念(normal concept)。建构滕尼斯的纯粹社会学的标准概念就是社区(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3](288)
在罗马以后的传统欧洲,“国家”及与“国家”相对的“社会”长期不发达,人们主要生活在“自然形成的”而非“政治性的”较小群体中,如家庭、氏族、村社、教区、行会、采邑、自治市镇等[5]。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整个市民社会时代”提出了“共同体”理论,或者说一种“小共同体”理论。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主要在原生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里实现,这种群体具有家庭、宗族等血缘关系;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里实现,这种联合体即是一种村庄、城市等的地缘共同体;它也可能在思想的联合体里实现,这种联合体是一种如友谊关系、师徒关系等的精神共同体。总之,这种“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地缘以及共同记忆的基础上。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是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而且是浑然有机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在人类发展史上,作为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这种结合类型早于有的放矢建立的“社会”类型[1]。
在滕尼斯的体系中,“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小范围的,而“社会”的整合范围要大得多[5]。“社区”(即“共同体”)以共同意志、成员的非个体性、社区利益支配、信仰、道德和习俗、自然团结、共同财产为特征,而社会则以个人意志、成员的个体性、个人利益支配、原则、时尚和风尚、契约交换、私人财产为特征[3](293);“社区”(即“共同体”)是在情感、依赖、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密切联系的有机群体,如亲属关系(血缘共同体)、邻里关系(地缘共同体)、友谊关系(精神共同体)等,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3](292);自然意志缔造了社区(Gemeinschaft),而理性意志则产生了社会(Gesellschaft)[3](294)。
有些学者认为,传统乡村是一种通过口头传播来传递其文化内容的共同体。这种传播不依赖于文字、书籍等中介,总要涉及直接的人际接触。由此,传统乡村成为一个大家能够互相见面、互相认识的“共同体”或“社区”,而“共同体”或“社区”对个人的压抑主要在这一层次发生[5]。
自《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出版以来,该著在西方学界即有广泛的传播,而滕尼斯本人使用的这两个德文词,即这部作品的两个核心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翻译也存在不小的困难和争论。
1940年,美国人C.P·卢密斯第一次将这部著作从德文译为英文时,未能找到对应的词,只将此书的标题译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1955年在英国出版英译本时,标题被译为“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社团)”;1957年芝加哥大学重版C.P·卢密斯的译本时,才将标题定为“Community and Society”。自此,“Community and Society”成为英语世界的通常译法,尽管依然存在很多争论[3](291)。例如,英语世界中也存在“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的英文译法[6]。这种翻译方式,即用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来翻译Gesellschaft(社会),与滕尼斯所针对的“身前身后的整个市民社会时代”是相符的,因此,这种翻译也有其道理。一般而言,英语学术界多把德文概念Gemeinschaft(共同体)译为Commune(公社、村社)或Community(社区)。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社会”的理想类型,不仅启发后人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研究的类型学传统,也在启示后人不断推进“共同体”理论研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与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folk-urban),贝克尔(H.Becker)的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sacred society-secular society)等即为其中的重要体现[3](295~296)。
需要指出的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是对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一种重要解构,也是一种重要发展。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的基本特征在于:低度的分工,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约束性法律占主导地位,低度的个性,特殊的规范性模式上的一致是重要的,社区对越轨者进行惩罚,较低的相互依赖,是原始的或乡村的。而有机团结的特征在于:高度的分工,微弱的集体意识,复原性法律占主导地位,高度的个性,抽象的一般的价值上的一致是重要的,专门化的社会控制机构对越轨者进行惩罚,高度的相互依赖,是城市的与工业的[3](251)。
机械团结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的一些“不发达”社会的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它通过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诸多个体凝结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团结“来源于相似性,它将个人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3](251)。
与机械团结不同,有机团结是由发达的社会分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所决定的,其典型代表是近代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联结形式下,分工导致的专门化,增强了个体间的相互依赖:一则,分工越细致,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依赖越深;二则,每个人的行动越专门化,个性越鲜明,越能摆脱集体意识的束缚,“正是分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原来由共同意识承担的角色”[3](252)。
对比来看,滕尼斯的共同体或者“小共同体”,指的是传统的乡村、小群体,人们之间关系密切,人们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保持着相同的习俗,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人们之间的依赖性较低,社会高度一致,社会靠传统文化力量来维持。但在涂尔干看来,这种“千人一面”的群体生活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基于社会分工的近代工业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机体,属于有机团结。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价值观和信仰日益多元化,社会就像有机体一样被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体为社会整体服务,社会中的个体虽然是独立的,但不能脱离社会整体。“与后者(滕尼斯)对传统社会(社区)田野牧歌般的怀念不同,迪尔凯姆(涂尔干)清楚地意识到了有机团结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292)
三、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引入与创新
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概念的引入,与英语世界中community概念的引入和中文语境中“社区”概念的提出有着复杂的“交集”关系。经细致考证,丁元竹认为,“‘社区’这一中文概念源自英文community,由费孝通建议译为‘社区’,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集体认同采用。吴文藻是倡导社区研究第一人,是以社区研究为风格的‘社会学中国学派’奠基者。community在中国翻译历经‘基本社会’‘地方社会’到‘社区’”[2]。此外,丁元竹还明确指出,20世纪30~40年代,德语世界中的Gemeinschaft和英语世界中的community在中国的传播有交汇,但Gemeinschaft不是“社区”思想的主要来源[2]。吴文藻当时是把德文Gemeinschaft翻译为“社区”,有时还称其为“自然社会”,称之为“纯理的社区研究”[2]。燕京大学社会学派在“基本社会”“地方社会”的基础上,赋予community(社区)更加明确的空间意义——这是它的最大贡献——并使其可以在实地研究中操作,也使其与Gemeinschaft有所区别[2]。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最先将英文‘community’成功地译成‘社区’的费孝通,在这里却没有遵循英语世界的译法。他将这对概念传神地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3](291)。
需要指出的是,Gemeide作为德国社会最基层组织层面的组织形式,与源自拉丁语的commune(Kommune)有语源和词义上的叠合关系,所以,从commune到Gemeinde再到英文的作为社区的community,这一线索的翻译和理解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是把这个意义上的community译为汉语的社区,则应该是一种较大的创造和发展。事实上,Gemeinde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译法,就是作为基督徒基层团体的“团契”。在一个以基督徒为人口基本构成要素的欧洲社会,最基层的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其实来源于早期基督宗教历史的“团契”。笼统说来,commune和德语中的Gemeinde可以视为同一个概念,没有矛盾和抵触,在欧洲语境中不至于引起大的歧解。在德文原有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Gemeinde,已经很难简单用中国的礼俗社会来表明——礼俗社会强调的是社会层面或者共同体的传统意涵,而这种传统要素在德语中更多指向原初的基层宗教共同体。此外,礼俗社会体现了“传统性”,却无法传达Gemeinde的“基层性”,这也是一个问题①笔者曾就德文Gemeinschaft的汉译等相关问题向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杨煦生教授讨教。此处见解来自杨煦生老师给笔者的邮件回复(未刊)。这里对杨煦生教授的无私惠赐深表感谢!。
总之,由于Gemeinschaft并不等于Gemeinde,由此造成了滕尼斯“共同体”概念和理论在引入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界的时候,必然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
从国内学界来看,不少学者关注了community在中国学界的运用和发展,即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社区”(community)思想——通过“有形社区”的有血有肉的素描来把握社会或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的方法及其机理运用到中国学界[2]。这些学者认为,这种通过实地研究理解当下社会事实的方法,与滕尼斯通过历史和理论建构来重新发现传统——人类共同体的传统,也重新发现历史的方法相比,是不同的[2]。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派与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是分别演进的,无论是具体到人还是当时的学科分类,都还不能完全视为一回事[2]。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费孝通先生是英文community(社区)、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等有关概念的重要引入者和翻译者,为这些概念的中国化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社区研究典范《江村经济》不仅开创了社区研究的新范式,呈现了与当时凌纯声、芮逸夫《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7](169)②一方面,《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本极其完整的科学民族志,它“具有典型民族志书写的内容与章节,而且其描述至为精详生动,所以一直成为中国民族学者从事田野调查与撰写报告时之圭臬”,另一方面,它“没有说明赫哲人是适应怎样的生活环境而创造出文物和制度的,更没有把赫哲人的各种文化现象置于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使人们无法了解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也无法了解其各种制度对社会有何影响或作用”。、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7](171)③《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虽然包括风俗习惯、乡村娱乐、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状况等的调查和描写,但是这个调查和一般的社会调查一样,仍是一种静态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定县人民的社区生活及实际活动,仍未获得十分亲切的认识。等民族志或地方志不一样的田野叙事方式④《江村经济》则把当地人的经济社会生活置于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加以考察,使人们了解到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具体联系,了解了其各种制度对社会的影响或作用,真正了解到当地人活生生的社区即“共同体”生活。,“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8](17),而且构建出一种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乡村共同体类型,为推动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以及涂尔干的“机械团结”论和“有机团结”论的发展,尤其是为推动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体现了“共同体”研究从规范探讨(normative)层面转入经验探索(empirical)层面的重要意义。
对于《江村经济》学术贡献的研讨已有很多,本文主要就《江村经济》在创新滕尼斯“小共同体”理论中的特殊贡献进行揭示。《江村经济》不单单开启了费孝通先生自己长期持续关注的“小共同体”研究,而且是我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小共同体”研究的先声和重要代表作。
第一,不管是德文语境中的Gemeinschaft,还是英文世界中的community,与其他很多学术概念一样,事实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中文概念与之对应。费孝通先生用“社区”或者“礼俗社会”来翻译,为从中文语境充分理解community和Gemeinschaft等学术概念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从community和Gemeinschaft所展示的一种“小共同体”的内涵来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深刻细腻地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面临外在工业社会强烈冲击的一种“小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如何有效组织起来,谋求新的出路和发展的艰难探索,体现出了与community和Gemeinschaft相同的“小共同体”范畴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
第二,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小共同体”是这样一种“村庄社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8](25),“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8](20)。
第三,滕尼斯和涂尔干所纠结的社区和社会,谁是机械联系、谁是有机联系的问题,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个体权利与群体生活关系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中转换为面对“外部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小共同体”内部如何基于传统生计和生活方式的调适而更为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问题。
第四,与涂尔干对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进行“倒置”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家庭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这种原生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小共同体”进行描述,揭示了乡村社区内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洞察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8](20)。
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都处于社区(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的连续统当中,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社区因素不断减弱、社会因素不断增强的过程,而非社会替代社区的过程[3](296)。滕尼斯、涂尔干、费孝通在“小共同体”研究问题中具有前后相继的承接关系,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在推动“小共同体”研究中更具现实意义,有着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和创新价值。
费孝通先生的“聚焦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体”思想,在其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强调和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一旦城乡分离,他们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自给自足可以达到一种安全,但代价是生活水平的降低和回到更为简单的生活中去,这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方法”,“城乡在生产和消费上的互补……根本问题是如何将都市和城镇转变成可以维持自己的生产中心而不用去剥削乡村。对于乡村来讲,问题是如何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或专门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乡村和都市同等重要,应该携手合作,但是变革的动力来自都市。最为根本的是,传统城镇的特点是应从一群寄生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生产社区,人们可以找到除了收取高利息和高地租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换句话说,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土地改革”[9](99~10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共同体”是滕尼斯等一代人为了回应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城市化等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而进行的社会理论构建,是滕尼斯为自己所期望的社会变化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经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的连续性和自然法则的想象,表面上是对过去历史的社会形态的描述,实际上隐含了滕尼斯对理想状态社会的期待[2]。相比之下,从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所展示出的“小共同体”思想来看,《江村经济》并非在展示一种理想的社会类型,而是以一种实践和行动的方式在探求“小共同体”的现实出路和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强烈的“志在为民”的现实关怀。虽然《江村经济》表现出了与community和Gemeinschaft相同的“小共同体”范畴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但《江村经济》又明显超越了community和Gemeinschaft所探寻和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图景。
基于上述综合分析,从学理发展的意义上看,本文认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为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
除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调查与研究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引入人文区位学和功能学派理论后,展开了很多社区或“共同体”意义上的调查与研究:林耀华先生对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乡黄氏宗族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调研,杨懋春对他的家乡山东台头村——一个中国老农业区的家庭生活、村内冲突、庄稼种植和孩子游戏等有关中国乡村生活各方面进行调研,李有义对山西徐沟县农村的社会组织进行调查,蒋旨昂对北京附近的卢家村进行细致调查,陈礼颂对福建澄海县的一个以陈氏宗族为主的杂姓村落宗族结构、家族结构、宗族与家族的功能、亲属称谓、婚丧习俗进行调研,黄迪和许仕廉对北京清河展开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婚姻、亲属关系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7](167~185)。这些研究,虽然具体的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差异,但都体现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在社区研究或“小共同体”研究中共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是当时社区研究或“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代表。可以说,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为西方“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的当代意义
滕尼斯基于“身前身后的欧洲市民社会时代”提出了一种“小共同体”理论:社区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涂尔干基于社会分工,将此“倒置”过来,认为集体意识强的社区属于一种机械团结,而基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价值观和信仰日益多元化的近代工业社会才能形成有机团结。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先生基于当时中国乡村面对外在工业的冲击如何谋求出路的现实考量,提出了“聚焦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体”思想,从经验实证角度发展了滕尼斯的“小共同体”理论。诚如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揭示的道理:原生理论只有在广泛传播和不断创新中才能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10]①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在2020年10月28日《民族研究》2020年编委会工作会议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试论诠释学与藏传佛教中国化》,对本文此处的见解有重要启发,特此致谢!。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聚焦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体”思想和城乡互补发展的思路,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基于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一体发展规划,对于今天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社会,人口流动的幅度和范围日益扩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深,城乡一体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一种超越“小共同体”的包容城乡在内的地域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和建构过程之中。尽管“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二元划分已经难以描述和概括今天的发展态势,但是费孝通等学界前辈积极引入国外“共同体”理论并使之中国化的创举,依然是新时代“共同体”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参照。
另外,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推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对于理解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亦有重要意义。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需要借鉴和吸纳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费孝通先生等前辈学者在西方“共同体”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和重要表率。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世界民族研究的重要推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1]强调印刷技术对于塑造民族“想象”的作用,将族群和文化认同的建构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4]。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民族主义建构论的困境,反映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叙述困境[12]。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是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重维度的民族社会实践研究及理论升华①需要另文专论,此处不再展开。,与过于强调话语分析和理想类型建构的西方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滕尼斯、涂尔干、费孝通等所形成的“小共同体”学术发展脉络,尤其是费孝通等前辈在推动滕尼斯、涂尔干“小共同体”理论发展中的贡献,事实上也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切实推动世界民族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需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小共同体”以及“地域共同体”进行专题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千万个“小共同体”及“地域共同体”组成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发生于这些“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型构之中,而很多民族互嵌社区就是由这些“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来体现的。这些众多的“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织基础②相关的深入探讨,需要另文专论,此处不再展开。。在此意义上讲,费孝通先生等前辈学者在西方“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中所做出的贡献,对“小共同体”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不仅有益于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有助于推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深入的理解。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相关的概念分析、理论探讨,需要大数据、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更需要诸多的微观经验个案研究。事实上,任何一种研究范式乃至系统理论的提出和创新发展,任何一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知识考古意义上的概念诠释、宏观的理论分析,以及大数据、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也需要细部微观的经验案例研究。在“小共同体”理论的引入和发展中,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一方面结合中文语境,对德文Gemeinschaft、英文community进行了翻译和解释,提出了“共同体”“社区”等新的中文学术概念,另一方面,也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基于诸多案例和经验研究,不断推动“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目前来看,国内学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中,政策分析、理论探讨、统计分析居多,而案例研究,尤其是基于长时间深入田野调查的微观经验研究偏少。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主要以微观案例的方式来切实推进“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对于反思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创新发展的研究方法亦有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