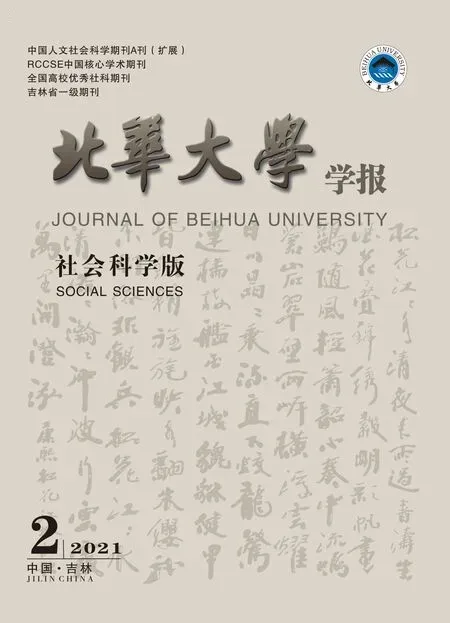孔子对西周以来传统“德”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李德龙
引 言
“德”是先秦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动态演变过程。从《尚书》《诗经》等早期原典文献的记载来看,西周初年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们,在深刻反思前代尤其是殷商政治兴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出于论证周革殷命合法性的政治诉求,赋予了“德”较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将“德”视为周王膺受天之大命、开创巩固基业的根本。周初统治者所反复强调、大力宣扬倡导的“德”虽然已经具有了道德(主要是政治美德)的意蕴,但更多的价值指向则是诸多有利于保民惠民养民的施政举措和政治行为,这些善政懿行应当成为以周王为代表的统治者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并通过“礼制”之创设将“德”加以制度化。因此,“德”的外在行为约束意义在周初乃至整个西周时代的“德”观念中占有主导地位,“德”所蕴含的内在心性道德意义尚不明朗,从“德行”层面去理解体会西周的“德”观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思想实际。[1]
在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晚期的较长历史时段中,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动摇及人文思潮的兴起,人们对“德”的体认也逐渐超越特定的政治层面,向着更具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方面延伸。与之相对应,“德”观念大致呈现出内面化、抽象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周初之“德”所蕴含的理性和道德因素在既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积蓄和丰富起来,使“德”的内在意义获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渐压倒其外在意义。孔子生逢春秋末世,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失范现实而痛心疾首,他秉持着“吾从周”的文化价值取向,将周公视为自己心中的偶像,以继承和弘扬周公的“德”“礼”思想为己任。但孔子由贵族而下降为平民的身份转变,使之与同时代的贤大夫们所论之“德”有着不同的思维视角。上述两方面决定了孔子关于“德”的思想中,既有对传统之“德”的充分继承,也有结合时代特征而进行的转化和超越,而这种超越恰恰顺应了西周以来“德”观念内面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并使“德”最终完成了向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的皈依。本文即结合《论语》中孔子关于“德”的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一、孔子之“德”对传统的继承及新意蕴
《论语》中“德”字共出现40次,其中有5例不是出自孔子之言,分别是曾子在《学而》中所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楚国狂人接舆在《微子》中所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子张和子夏在《子张》中分别讲的“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此外,《宪问》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此句中的4个“德”字可以较明确地理解为“恩德”“恩惠”的意思。除却上述所举,通览《论语》中孔子关于“德”的言论,我们未见他对“德”的内涵有明确而系统的阐释和界定。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孔子也较为注重教导弟子们从外在的“行为”层面去践行“德”的要求,“德行”科即为孔子对学生进行施教的4项重要科目之一,颜渊与闵子骞在此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在治国的政治实践中,其“德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为政》中的这两句话: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这里,孔子所指明的只是以德治国将会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以及“德治”相较于“刑治”而具有的优越性。尽管对于“德治”的具体施政举措,孔子在此未做条理式的罗列,但我们可以通过他对“问政”的解答来领会之,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如下诸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路》)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不难看出,孔子把端正名分、居位不厌倦松懈、忠心执行政令、推举贤能、施恩惠取悦百姓、做事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等各项举措,都视为以德治国的应有之义。诸如此类的德政条目在《论语》中还多有涉及,如《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应该说,上述孔子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发问者所提出的具有“德治”意蕴的各项举措及行动指南,在《尚书》《左传》《国语》中也是屡见不鲜,这既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治学态度的彰显,同时也是对西周以来“德”观念中所蕴含的政治理性的继承和发扬。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述而不作”并非是对历史不加反思的全面继承,而是寓“作”于“述”之中。西周以来的政治家们对“德”的关注与强调,多是站在政治功利的角度,把“德”视为一种为政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来申说的,那些较为宽泛的各项德政举措,对执政者虽具有一定的外在约束作用,但在“礼崩乐坏”“诸侯力争”的时代背景下,已显得苍白无力,孔子认为传统之“德”对于春秋乱世而言只是治标不治本。为此,他在继承传统“德”观念中政治理性因素的同时,又认为其与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德”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故而发出了“知德者鲜矣”的感叹。如果说西周以来传统之“德”关注的是统治者外在的德政实施,那么孔子之“德”则是突出强调统治者内在的道德自觉,如: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为上者的道德示范和价值引领,统治者自身必须要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意识,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道德人格来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品行端正的有德者、好德者身居高位,才能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进而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不难看出,较之传统的“德”观念,孔子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德”的精神实质上,而非那些泛泛的各项德政举措,没有政治主体的道德觉醒为依托,再好的德政举措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孔子所宣扬的以德治国“就是通过最高政治人格或政治主体的德性和德行,来赢得民心,从而达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目标。”[2]
也正因如此,孔子强调政治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是个体的道德水准,而非昔日的贵族血统和阶级出身,这就大大拓展了“德”的覆盖面,使之成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要求,从而彻底改变了西周以来“德”被统治者垄断的局面。历史表明,“德”所面向的对象范围和涉及的领域越广泛,“德”就会日益超越特定的政治层面,沿着精神层面而内向发展,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道德方面延伸。孔子本人尽管在政治上终生不得志,但仍秉持着“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不问出身贵贱地广收门徒,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教学大纲,循循善诱地教导弟子们进德修业,旨在培养一批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正人君子,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来实现自己的“德治”理想,因为孔子坚信君子能够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这种对传统政治之“德”的视角转换,大体上奠定了儒家德治思想的体系架构和理论基础。
孔子在《述而》篇中曾讲过“天生德于予”,对这句话理解得正确与否,牵涉到孔子关于“德”的思想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德”从何而来?是出自于上天还是源于人的心灵深处。《论语》中孔子谈及“天”或“天命”的话主要有如下诸例: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
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据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天”在孔子那里仍是具有最高主宰意义的至上神。(1)如冯友兰先生说:“孔子所谓天,乃一有意志之上帝,乃一‘主宰之天’也。……若天为有意志之上帝,则天命亦即上帝之意志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任继愈先生也认为:“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将天命视为冥冥中的最高主宰。……人的生死寿夭和富贵贫贱都受天命决定,天命主宰一切。”(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孔子天命观的是孔子在《阳货》中所言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句话,这里的“天”无疑指的是自然之天。吕绍刚先生把《论语》同《周易》《春秋》结合起来,经过细致对比考索研究曾深刻指出:“孔子讲的‘天命’,是指整个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言,它既包括自然界的规律,也包括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3]“天”在孔子的心目中只是客观自然的认知对象,并没有“最高主宰”的意味。倘若“天”真的能主宰人生的命运,那么孔子何以把自己的为人总结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他在《为政》篇中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正是对自己一生“下学而上达”之道德践履历程的自我表述,五十岁的“知天命”是孔子“对自己的性,自己的心的道德性,得到了彻底地自觉自证。”[4]“天生德于予”不能证明孔子在理念上仍然认可人之“德”源自于天,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在面对桓魋欲加害于自己的威胁时,借用传统观念中的“天”之名,以表达自己坚定的自信和超然态度。“德”既然不是天之所赋,那就需要人的主观修为,对此,孔子站在世俗人道伦常的角度提出了先事后得、学思结合、内省反思、持之以恒等一套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高度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在修德成德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高扬人的道德理性自觉,强调人应当把对德的追求视为一种自觉的精神需求。
综上所述,孔子承袭了传统之“德”原有的理性化因素,对有利于恢复礼乐文明的德政举措给予肯定的同时,又把重建稳定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完美道德人格上,形成了异于传统的道德思考形式。与先前的政治家们论“德”方式明显不同的是,孔子更加关注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其追求个体德性完美的道德理想,赋予了“德”以新的时代意蕴。
二、孔子“仁”的学说是对传统“德”观念的超越
在《尚书》《诗经》中“仁”字即已零星显现,但其内涵与孔子所论之“仁”相去甚远。(2)“仁”字在今文《尚书》中只一见,出自周公之口:“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金滕》)在《诗经》中共两见,分别为《郑风·叔于田》:“洵美且仁。”《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对这3例“仁”字的解释,可详见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从《左传》《国语》的记载来看,“仁”在春秋时期已经是较为常见且重要的道德条目之一,被统辖于“德”的范围之内,《左传·僖公四年》庆郑所言“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可为其证。对于“仁”的具体所指也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左传·成公九年》的“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一》的“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等。
“仁”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远远高于“德”的出现频率,这既表明孔子是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发现而非创造了“仁”,也说明“仁”经过孔子的发挥后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故《吕氏春秋·不二》中有“孔子贵仁”的说法。孔子把“仁”从隶属于“德”的众多子目中拣择出来,通过对“仁”的学说之建构,完成了对“仁”的抽象,“仁”是“德”的参和与超越,[5]这是孔子对传统“德”观念进行超越的根本表征。
在《论语》中孔子同样没有对“仁”的内涵作出全面而系统的概括,当弟子们向他“问仁”之时,孔子分别予以了不同的解释,其详如下: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细加推敲,上述这些因人而异的回答实际上是孔子在向弟子们宣扬求仁得仁的方法,并非对“仁”这一概念本身所作的诠释。金景芳先生认为孔子对“仁”的最精确的解释,当属《礼记·中庸》中孔子答“哀公问政”所说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者人也”是说“仁”的产生及“仁”的适用范围都只限于人类;“亲亲为大”是说尽管仁的适用范围是全人类,但“亲亲”最重要。因为“亲亲”是“仁”的起点与原动力。[6]朱熹对“仁者人也”的理解为:“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7]这表明,“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之规定,是以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为根本的推己及人的泛爱。故孔子在《泰伯》中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弟子有若在《学而》中也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仁者人也”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哲人们开始真正把“人”自身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来探讨人的价值问题。尽管孔子很少谈及人性问题,更没有明确地说“仁”为人之本性,但“仁”乃人心人情固有之理是“仁者人也”这一命题的应有之义。孔子的仁学思想为儒家的心性哲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并由此拉开了诸子百家关于人性问题论争的序幕。
孔子之前的“德”一般是统摄诸多具体德行的综合性概念,但在《论语》中孔子打破了传统的做法,以“仁”代“德”,并把“仁”改造成为包罗众多具体德目的总德。如: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
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阳货》)
“仁”在孔子这里已不再是从属于“德”的次级德目,而是上升为集所有品德于一身的抽象概念,诸如刚毅、勇敢、恭敬、宽容等道德德目,只是“仁”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有“德”未必有“仁”,但有“仁”则肯定有“德”,“仁”的层次和境界要高于“德”。在《公冶长》中子张认为楚国的令尹子文和齐国的陈文子,在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高尚的官德和操守,具有超出常人的道德涵养,可以称之为“仁”了,但孔子认为他们只是分别具备了“忠”和“清”的政治美德,还未达到“仁”的标准。又如在《宪问》中原宪曾向孔子发问道:“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如果一个人能够克服争强好胜、自我夸奖、怨天尤人、贪得无厌这些坏毛病,可以算得上是“仁”人了吧?孔子的回答是:“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可见,孔子对“仁”的标准把握得极其严格,“仁”出于“德”而超越于“德”,“仁”是个体完美道德人格的象征,人在修为的过程中具备某种道德品质并非难事,但若想企及“仁”的境界绝非易事。孔子不仅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对于他自己也认为不够格、不敢当,故在《述而》中曾向弟子表白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虽说“仁”的境界非常高远,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却也并非高不可攀,孔子在《颜渊》中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能否达致“仁”的境界,全凭个人的主观努力程度而非外力作用。有了强烈的自信心和坚韧的持久力,辅以正确的切实可行的修养方法便可成为仁人,《雍也》中讲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即为此理。
综上所述,孔子所讲的“仁”是根植于人类血缘亲情之上,以孝悌为起点,符合人的本性与心理的“爱人”,同时“仁”又是人在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后方能具有的完美个体人格。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的仁学思想有4个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的构成因素,即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这4大构成因素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故孔子仁学思想的整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实践理性”。[8]孔子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把探索社会失范的根源转向了人本身,将外在规范约束的他律转化为内在人之仁心的自律,从而为人们的尊礼守礼提供了道德自觉的保障。他所热衷的“德治”实质上就是“仁治”,这就将政治理想的诉求安顿于对个体完美道德人格的向往,有了“为仁由己”的道德自觉、“杀身以成仁”的道德意志、“能近取譬”的求仁方法、“下学而上达”的修养工夫,人们就能在道德生活中不断重新审视、超越自我,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融入对“成仁”的不懈追求中,这就是曾子在《泰伯》篇中所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不计利害得失、无所畏惧的对至善之“仁”的热烈追求,显然超越了充斥着浓郁政治功利色彩的传统“德”观念。
结 语
虽然孔子一生都是以传统历史文化的坚定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宣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徐复观先生曾把他的“述”归纳为三大特征:“一是从过去的特定事项中,找出富有普遍性的共同准则;二是把外在的形式,转化而为内心的德性,使其成为人格成长的表征,并使形式因受到德性的批判而不致归于僵化;三是通过他个人的人格上的体验与成就,而把传统的观念推进并提高为高深的根本原理。”[9]孔子对“德”所作的叙述,就是在充分继承传统“德”观念的基础上,悄然无息地寓“作”于“述”当中,以价值转化的方式构建起了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体系的主体框架。孔子通过对人之仁心的发现,顺应了西周中晚期以来反复酝酿的“德”的内面化趋势,开始将“德”植入人心。前孔子时代的“德”“礼”等思想观念经由“仁”的诠释而呈现出异样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孔子被后世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从外在的、强制的天启之“德”和形式之“礼”引入了“仁”的内心自律。[10]孔子改变了西周以来传统之“德”从属于政治的局面,把“德”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概念,“德”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经由“仁”的诠释,内在意义上的 “德性”意蕴已较为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