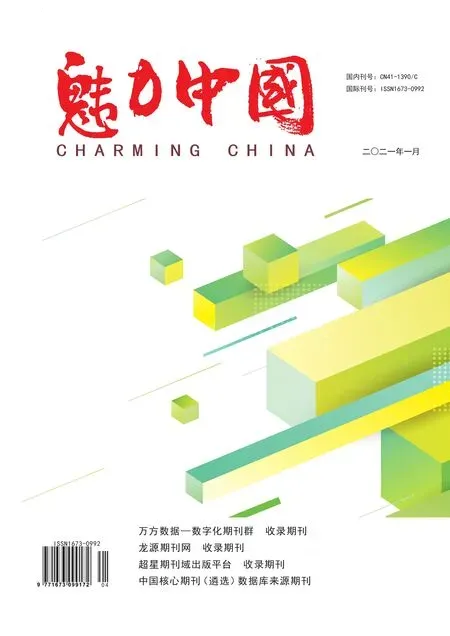漫谈舞台美术设计的特征
王群博
(濮阳市戏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河南 濮阳 457000)
舞台美术设计,以前常常被人们称作舞台设计师。在前不久有人提到戏剧设计师这个称呼,有把握可以认为他指的是舞台设计师,即设计舞台布景(通常还包括戏剧服装)的人,而随着演出的实物装置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原来有一位设计师总揽的舞美任务就逐渐解体成五种主要的设计功能:布景、服装、灯光、化妆和音响。随着戏剧演出对技术的要求日高,这些不同的设计任务就由各司其职的设计师单独承担了。
纵观戏剧设计的历史,也能给人一种启示。早在古典时期,演出中的实物设计基本上并不存在。古希腊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纯建筑性背景前演出,演员穿传统所规定的服装,戴着几乎千篇一律的面具;中国戏曲的雏形“优孟衣冠”、以“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说中的“傩戏”,也是如此;舞台设计是根本不需要的。舞台设计不受重视,也可以从这一事实获得证实;亚里斯多德在按照重要性为次序而列举的戏剧要素中,把“形象”排在第六位,也即最后一位。跟随着希腊之后出现的罗马戏剧,就现在可以确认的,对戏剧设计也很少改进。罗马人也利用标准的正面建筑作为演出背景,稍微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也用十字架来表现磔刑场面。罗马拟表剧的一个残本中提到一组布景:舞台上一条河,有九个裸体的“蛮女”在水中沐浴嬉戏,这究竟是一台真的布景,或者仅把歌舞场(它在当时显然是相当普遍的)充水,则很难确定。
到中世纪时期,有所发展。我们有关现代戏剧的设计观念,可以从中世纪找到根源。虽然中世纪的演出风格和表现方法与今天的舞台迥异。但其时对布景和服装的重视已十分普遍。中世纪演出中用于表现不同地点的布景其宏伟壮观,是显而易见的,就当时的技术水平说,场面也尽可能做到逼真。即使在当时辚辚驰过英国乡村的彩车舞台上,也有证据说明倡演连本戏的行会间的竟争导致产生了一些观赏场面的技术和舞台布景:正在抽芽并迅速长大的树木、喷水的井,还出现坐在金色御座上的神仙。当时多数演出服装华丽多彩。有些服饰已趋向规范化,如犹大戴红色的假发,穿黄色长袍;蒙恩升天者穿白色服饰;受罚入地狱并在地狱门口跳跃不息者则黑衣裹身;圣母玛利亚穿蓝色服装。我们还知道彼拉多和希律王服饰华丽,手执金瓜棍。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明显地存在大量的设计工作。
文艺复兴时期,特别在意大利,拓宽了舞台设计的思想,赋予它以绘画性再现的概念,这种概念一直流传至今。例如:1508 年在费拉拉上演的一出阿里奥斯多的戏。就用了一套透视布景,来表现一组“房屋、教堂、塔楼、花园”的风景。以后的演出,还出现了庭柱、塑像、神坛、寺院。我们还被告知,这样做是为了“使街道看上去能象真的,每样东西都做成了浮雕,而通过绘画艺术及完善的透视技巧使一切都更引人注目。”
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还可以从萨白蒂尼的著作中,看到制作布景的技术,如“如何使海使豚及其它海洋怪物出现,并且边游水边喷水”“如何使河水湍流不息”“如何分割天空”“如何使一片载人的云彩笔直地落到地面”,以及如何使云彩按一定角度降落的种种细节。
带有镜框台的现代舞台,其原型在1618 年形成于帕尔玛⑤的法尔纳斯剧场。自从这个剧场建成以后,几乎所有舞台设计都致力于镜框舞台所提供的写实的可能性。产生镜框舞台的准确来源至今尚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某些意大利著名画家转行搞舞台设计,导致了使画框适应于舞台。但这种假设还缺乏具体根据。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当职业剧团在一个简单的(与古希腊、罗马相比较而言)建筑物前的伸出舞台上演戏时,他们的舞台设计要比中世纪在写实方面倒退了一步。从一些剧团的舞美财产清单来看,他们对写实布景也作过有限的努力。但只字未提舞台“设计师”。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设计工作,和演出中的其他部门相似,是由全团共同负责,而不是某个人的专门任务。这并不是说舞台设计在英国完全不受重视。事实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伊尼果·琼斯⑥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设计师之一。他为设计埋头苦干,尽管他的创作主要是为宫廷做假面具,而不是为商业性剧团服务的。
17 至18 世纪,由于越来越多的戏剧在镜框台口后面演出,从而要求布景写实,演出者开始感到有必要在现有写实的基础上实现换景。这样,从勃南森林转换成邓西嫩城堡内景就必须在视觉上交待清楚。这就要求有所改进。开始时对迅速有效的换景能力要比对舞美设计的要求更为迫切。为此,人们提出了若干方案,它们都要求改变传统的设计观念。侧片滑槽式装置利用木料和帆布做成可移动的折角侧片,通过两侧的滑槽来回滑动,车杆式装置是一种机械设备,通过可以在舞台地板的槽空内移动的立杆来换景。有的剧场还把背景和侧片设计成可以飞吊的景片,通过升降景片就可以迅速换景。
之后,整个19 世纪和20 世纪,从大体上说舞台设计的变化主要在方式方法方面,而不是在布景类型方面。如:电力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戏剧照明,可靠、有效地扩大了照明效果,但照明的基本原理并无很多变化。直到近年出现了灯光设计师,才真正改变了演出照明的概念。
戏剧设计的历史十分复杂,一本书也无法充分阐明,更别提一篇文章了。也许了解这一领域的最好方法还是看看各主要部门的设计师都做些什么,特别要注意这个领域有些什么要求。
美国的李·西蒙生曾下过一个定义,把舞美设计师称为“从事于解释工作的集体中的一个成员”,意思是说:舞美设计师的职责在于和导演及其他设计师一起,共同提供一个综合的、视觉的演出,这种演出依赖对剧本内容的恰如其分的解释。也就是说,舞美设计师要创造一个符合导演构思、适应演员表演的特殊需要(确定入口、出口等)、并和灯光及服装设计师的想法协调一致的物质环境。
舞美设计师需从艺术角度认真研读剧本,从演出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哪些是演员上下场和完成剧本要求的所有动作必须的特殊手段),同时从纯主观的艺术要求出发(努力理解或“感知”剧本所表现的情绪和气氛),仔细地进行分析。在与导演以及其他舞台设计同行磋商的同时,舞美设计师逐渐形成既给观众以审美愉悦,又符合演出实际需要的设计方案。
在完成了设计,跟服装、灯光设计师取得协调,并征得导演同意后,舞台设计师就面临着把设计方案体现于舞台的许多实际工作。
我认为,学术研究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变革创新的重要条件。但是,在这一方面,历来就有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舞台美术是一种实践性的学科,不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而我认为,舞台美术实际上是处于戏剧学、美术学之间的一种领域,其创作正处于文学与造型之间,它的各种关系又处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之间,它的研究很直接地联系着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前端问题。在艺术风格急速变革的时代,学术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艺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两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理论研究是根植于实践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真知,这些观点都是不错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实践可以有这样两种情况,有一些实践是创新性的实践,或者可以称为创造性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是艺术创作真正需要的实践。因为这样的实践具有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的创造性特征,也就是具有艺术的不可重复性。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实践,这就是重复性的实践,也就是不断地以相同的或近似的材料,相同或近似的手段去进行重复性的生产活动,这样的重复性实践也是一种实践,当然也会有成果,然而那也许仅仅是一个产品,而这样的产品的重要性本性是与艺术相悖的。我们作为从事艺术创造的艺术家显然需要的是创新性的创造性的实践,而不是那种只能产生产品而不能萌发艺术的重复性实践。创造性的实践和重复性的实践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认为,差别就在于我们创作实践中有没有是真正来源于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的学术研究。研究与实践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所谓研究就是创造新知,开掘新域。研究就是创新。不创新、不创造就不是研究。研究是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的。总之,存在重复性实践而不存在重复性研究,重复性的工作就不是学术研究,这或许是实践与研究的不同之处,也是我们需要在实践中重视学术研究的缘由之一。舞台美术的研究领域是有极为明显的独特性。以大型新编历史故事戏曲《许穆夫人》的演出为例(张士芳编剧、导演,河南省滑县大弦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充分说明这一点。张士芳同志在《〈许穆夫人〉导演阐术》中把《许穆夫人》的形象种子定为“黄河”,我也反复研究了剧本,反复研读《〈许穆夫〉导演阐述》,《〈许穆夫人〉导演阐述》指出:“许穆夫人生活的中国春秋时期(此需考证),但戏曲不是搞历史研究,我们把它定为中国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列国纷争、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社会的转型期、卫灭复兴等。许穆夫人生长在黄河边,是黄河水滋养了她的高洁品格:才华盖世,多才多艺,文武双全。为了光复卫国,隐忍了巨大的‘夫妻情、母女情’。黄河的怒涛和静静倾泻时水下的激流飞湍,在许穆夫人身上得到了诠释”。坚定了“黄河”作为全剧“形象种子”的认识。把这一“形象种子”运用到了舞台各部门使全剧有了一个大的升华和飞跃。
舞台美术是深奥的,复杂的,需要深入的研究;舞台美术是独特的,需要专门的研究。舞台美术始终应该是注重创作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