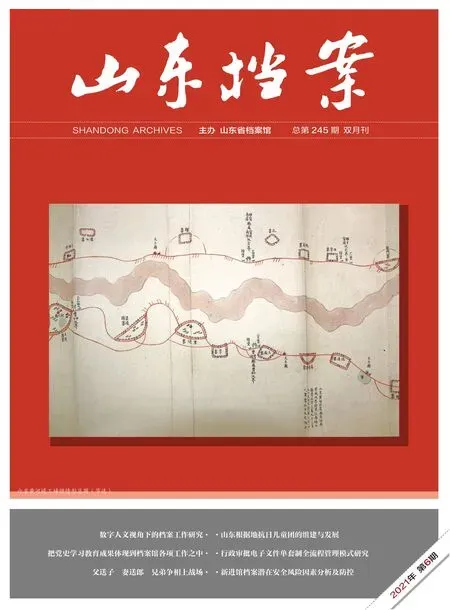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工作研究
文·林静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跨领域议题,早已被确立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前沿热点。近来颁布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人文,推动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的融合,积极借助数字人文工具,推动档案工作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强化数字人文在档案深层组织和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来说,数字人文作为一种理念和技术,其集中凝聚的有关高程度的资源依赖性、强便利的技术工具支撑、有深度的跨界协作、高标准知识生产与组织等特质,不仅能够引导档案馆将档案转向档案资源,并且能够推动档案作为一种资源,从数量增加转向质量提升,推动档案服务从“文件级”深入到“数据级”,满足当前用户对档案服务的多元化、知识性和交互性需求[1],从而为破解当前我国档案馆和档案工作的瓶颈性问题提供新思路。
一、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数字人文与档案馆工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档案工作与数字人文共享相同的旨趣,档案作为数字人文的资源,可以为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信息支撑。另一方面,数字人文可以为档案工作提供指引,创新档案工作发展的方向。
(一)共享保障人类信息的有效获取与查询的共同旨趣
纵观学术发展,人文研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对机构馆藏(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自由获取利用。档案馆的出现是为了保存人类原始记忆以便日后利用,其根本旨趣在于保存人类集体记忆的存取与利用。尤其是业界和学界不断提出档案馆和档案工作社会化和档案利用的社会化开发以来,档案的信息资源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档案工作相比,数字人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更高层次对人类信息有效获取与查询的保障,其产生的目的与人文学者进行研究时对依靠资源供给方式的创新需求密不可分[2]。这一目标成为数字人文研究与实践发展的主要导向并引导它不断定义自身。例如,就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和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国内外倾向将数字人文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方向阐释为:构建数字人文服务体系,营造数字人文生态和以需求驱动满足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两大方向。从这一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数字人文和档案工作天然共享相同发展旨趣——保障人类信息的有效获取与查询,而且通过当前大型数字人文项目,如威尼斯时光机、北京记忆等具体项目来看,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的这种天然联系就显得更为直接。
(二)档案资源是数字人文的基础性内容资源
数字人文的实质是从技术上创新信息资源的供给方式,以构建一个数字生态,满足人文学者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档案资源始终都是数字人文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源。据相关数据统计,当前美国70多家数字人文机构所开展的项目中,起码有35%以上的数字人文项目是以档案资源作为主要基础资源的。换而言之,数字人文研究和项目实践需要依靠各类档案资源。例如,1990~1994年的美国记忆项目,该项目基于用户需求角度,直接使用档案馆通用著录标准对美国的历史文献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进行历史史实的构建和还原。除此以外,还有浙江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古画数字记忆项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文化科研中心的911数字档案馆项目、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GWonline项目、斯坦福大学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大革命数字档案馆项目、达特茅斯学院的达特茅斯越南项目等。在这些项目中,最基础和根本的数字资源多来自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机构,数字人文仅仅作为资源供给方式和技术而存在,在资源组织和呈现方式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而档案资源是作为数字人文工作的基本内容资源[3]。
二、数字人文对档案工作的影响
数字人文的兴起给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促使人类信息资源供给方式创新发展。对于以保存人类集体记忆为存在价值的档案工作来说,数字人文能够促进档案工作实现服务和技术互补,实现档案工作的创新发展。
(一)数字人文推动档案组织工作的优化升级
从档案整理和收集工作来看,数字人文可以为档案工作的集成化提供借鉴。例如,“the Venice Time Machine”项目就是将威尼斯国家档案馆的地图、手稿、乐谱等档案进行系统加工组织,把不同类型相同主题的档案整合到一个框架内,以动态可视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历史面貌的复现主要是通过过去历史档案数字化、档案著录工作来实现的。在档案数字化方面,数字人文项目和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无疑可以为档案数字化的工具和动力提供更多的支持,能够将原来尘封或很少使用的历史档案重新集合重组,根据用户的需求组合起来,推动档案组织工作的转型;在档案著录工作方面,数字人文首先从组织主体层面能够将社会大众纳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展档案著录主体,如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就采取众包思路,通过在网络和线下招募社会志愿者对盛宣怀手稿档案进行抄录识别著录,实现盛宣怀手稿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和组织利用[4]。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档案著录工作的主体,既能够推动档案组织工作的公众性,也能够发挥图书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得到一致好评。其次,数字人文项目中关联数据的引入也能够帮助档案馆将不通类型的档案整合,将具有关联性质的档案连接,形成一个庞大的档案体系,在解决档案资源孤立、封闭的档案孤岛和档案冗余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
(二)数字人文推动档案保管工作的创新转型
首先,数字人文能够强化档案工作的有效保管。在数字人文项目中,档案往往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形成一个数字化的档案馆,原有档案作为底本被保存下来,用户可以通过数字档案馆或数字人文项目平台进行资料利用,从而替代原有档案文件的使用,因而能够强化档案的保管功能。例如,普林斯顿韵律数字人文项目对档案馆1569~1923年期间出版的数千篇韵律作品进行数字化,并提供免费开放服务,减少了原来作品的使用,提升作品的寿命;其次,数字人文还创新了传统档案保管的存储方式。在数字人文下,数字人文仓储能够帮助档案馆对档案知识本体进行揭示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智能化、针对性的档案服务,从而满足需求者高层次的档案利用需求。例如云南省档案局先后完成了13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的民族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图书、民族服饰、乐器等进行汇总,形成一个多类型、针对性的档案资源仓储。
(三)数字人文项目推动档案利用的社会化服务
目前,我国许多档案馆都构建了“两微一端”的档案新媒体平台,旨在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推送信息,推动档案开放,提高档案资源的利用程度,增强档案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功能。但这种单向推介方式也存在资源挖掘深度不够,服务方式单一的问题[5],很难满足专业用户档案服务需求,也很难推动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服务的社会化进程[6]。但是,在数字人文环境下,数字人文具有明显的需求驱动,以人文学者需求为中心提供资源服务。档案工作引入这一理念,能够促进当前档案服务工作的社会化进程,解决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众多数字人文项目所开发的工具包具有明显的优势和价值。例如,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工具集”。该数字人文工具包能够为用户提供多种服务工具,包括参考工具、检索分析工具和关系勘探工具,如中西历转换、清代中国文官官职表查询、度量衡单位换算系统、THDL契约文书买卖角色分析等。这些工具一方面能够为用户提供多种服务,满足用户的不同和需求;另一方面,这些工具是建立在对档案资源的深度挖掘之上的,兼顾了专业性用户研究需求和社会大众兴趣和生活需求,具有明显的社会化服务倾向[7]。
三、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工作的创新路径
(一)重视打造档案人才的数字人文素养
数字人文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构建档案人才数字人文素养培养体系,必须将数字人文融入档案教育,培养具备数字人文素养和档案素养并重的人才。为此,首先要将数字人文融入档案学教育体系,将数字人文知识作为档案学核心知识能力,以选修课或必修课的形式固化数字人文知识在档案学知识中的作用;其次,可以设置数字人文专业学位,并将数字人文方向作为招生方向,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了相关探索,设立了专门的数字人文学位;再次,注重档案馆当前工作人员数字人文素养的培养,如以数字人文专题讲座、学期教育、档案工作坊等进行培训教育。最后,依托图书馆、档案馆等已经深入开展数字人文实践的机构进行合作,如美国西蒙斯学院档案与保存专业就要求学生要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机构中实习,去学习实践数字人文。
(二)打造特色的档案数字人文中心
搭建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运行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是目前国内外的普遍做法[8]。档案馆应当主动开放可供利用的人文、历史等档案信息资源,如文本档案、拓片、书画、古器物、典籍等档案资源,并采取跨界合作方式,联合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背景的专家,成立数字人文中心、研究室、工作坊等组织,打造共同交流平台,推动我国档案的数字人文创新。例如,我国在2015年成立数字人文中心,致力于数字古籍、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运作与研究。这种档案馆和数字人文专家共同组成的档案数字人文中心,一方面推动了数字人文在档案馆场景中的落地,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彰显档案服务社会的使命价值。
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为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档案工作需要积极创新发展,要以数字人文和档案工作社会化开发和利用为契机,以档案资源的数字人文项目实践为抓手,推动档案组织工作的优化升级、档案保管工作的创新转型、档案资源利用的社会化服务,以提升档案人才的数字人文素养和打造具有特色的档案数字人文中心为策略,推动档案工作更好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和保障人类信息资源的有效查询与获取,进而彰显档案工作在数字人文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