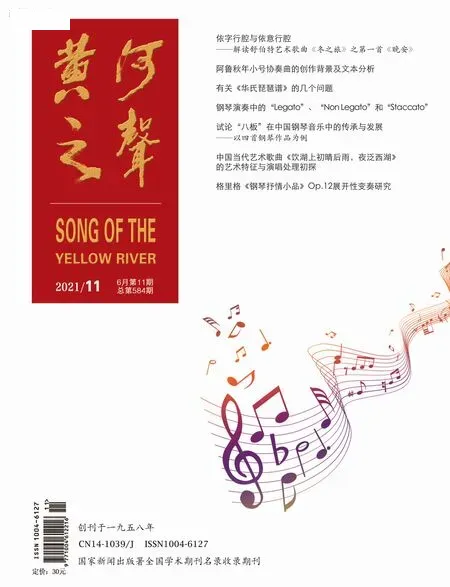咏叹调《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的演唱探究
徐宁泽
一、《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背景介绍
歌曲《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是由李井然作曲、王韦民编剧的中国经典民族歌剧《启明星》中的一首咏叹调。《启明星》是根据蒙古族的故事改编创作的民族歌剧,故事发生在1770年清朝乾隆年间,土尔扈特蒙古族部落的同胞们为摆脱俄国沙皇政府的压迫,维护民族的独立自由,部落首领“握巴锡”领导民众进行武装起义,决定举族东迁,在途中逃过沙俄的重重阻拦,进行千里的长途跋涉,最终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回归祖国的感人故事。戈桑和阿珠是歌剧《启明星》中的关键人物,推动着剧情的发展。阿珠是一个坚贞、勇敢的女人,为了心爱的戈桑,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则是女主人公“阿珠”在剧中的咏叹调,这是一首由女高音演唱的咏叹调,选自歌剧的第三幕,戈桑本是东归的先锋,可以与心上人阿珠一起回到祖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料内奸却借阿珠之手将毒奶酒敬给了戈桑,导致戈桑中毒身亡。阿珠在得知自己被迫杀害了心爱的人——戈桑之后,悲痛万分,失去心爱的人的痛苦,无法回到祖国的绝望,和对内奸的痛恨夹杂在一起,演唱了这首咏叹调。随后阿珠追随戈桑自刎而死。
二、演唱时角色形象的塑造
想要完整地表演一首歌曲,所需要准备的前期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即要对所演唱的作品进行一次“解剖”,首先要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意图;音乐所表达的情绪、情感;音乐的风格特色;人物性格的把握以及谱面上作曲家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例如节奏,歌词等。这些前期工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单纯的演唱者的“声音技巧”所不可替代的。
(一)演唱时情感的诠释
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们,都十分看重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都是由情感所反映的,情感抒发着人的主观感受、体验,同时也表达了对客观世界的态度。作为声乐演唱者的我们,亦或是艺术创作者,情感都始终扮演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所以,在演唱中想要达到更好的审美效果,情感是诠释歌曲的第一要素,才会让听者达到尽可能大的共鸣,使歌曲具有更大的感染力。那么,如何把握歌曲的情感呢?在充分了解歌曲创作背景的前提下,既不能抛弃作品创作的真实性,即尊重作品(歌剧)的本身所要传达的精神,又要抓住人物的性格,此时情感就自然而然生发出来了。作品的真实性是我们进行二度创作时所不能摒弃的原则,一个作品创作出来都有它所想要传达的意义,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创作者所想要传达出的思绪,我们应该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去加入我们自己的想法,体验。其次,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沉浸表演有很大的帮助。
在歌剧《启明星》中,《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这首咏叹调是全剧的高潮,阿珠的情感波动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情感可以概括为阿珠对戈桑死去的困惑和绝望。在歌曲的首句,“是我把毒药放进了酒浆”标记了弱音记号,是中音区的低吟,紧接着第二句“是我杀害了心爱的戈桑”则标记了渐强和重音记号,宣泄了阿珠内心的自责和绝望。两句话力度的对比,语气的层层递进,将阿珠内心的绝望推向了高潮。第二部分的情感为阿珠对美好爱情的缅怀。两次“戈桑是我”,强调了戈桑在阿珠的心中的重要地位,“灵魂的归宿,生命的火光”都表达了阿珠与戈桑爱情的忠贞,同时也为后面阿珠追随戈桑自刎做了铺垫。“神圣的誓言,幸福的理想”,对称的修辞手法,体现出阿珠对美好爱情的追溯。而“像幻梦般消亡”,情绪瞬间转变,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成为幻影,这一句标有渐弱的记号,传达出内心的无助。在第二、三部分中,夹杂了一段念白。“这是梦么,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不,这不是梦…”是对于前面乐句的解释和呼应,也是联结下一部分的过门,为剩下乐句情绪的转变和烘托,进行了铺垫。第三部分为阿珠对归国的憧憬与向往。启明星引领着路的方向,即将要踏上回故乡的路,阿尔泰的青松,伊犁河的流水,凯旋的拱门,充满着对祖国的眷恋和怀念。阿珠是多么向往能够与心爱的戈桑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此时戈桑已经不在了,再美的景色也都黯然无色,没有了心爱的人的同行,她的绝望和痛苦都在一霎那间倾泻。故乡的风景与此刻的内心成为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心里的绝望为阿珠的自刎埋下了伏笔。第四部分为阿珠誓死追随戈桑的决心。“失去了灵魂的归宿、泯灭了生命的火光、枯萎了爱情的花朵、毁坏了幸福的希望”,这四个排比句式的运用,将阿珠从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回归祖国的热情中拉回了现实,将绝望的情感推向高潮,更加坚定了追随戈桑的决心。启明星象征了阿珠的美好爱情,和对祖国的爱,同时也代表了戈桑。启明星寓意着戈桑为祖国死去的伟大象征,它不仅仅是阿珠一个人的启明星,也是整个尔扈特人民心中的启明星。所以在唱段的最后阿珠唱道:“我无从辨清这奇惨的冤情、无力医治心灵的创伤”,只有追随着心中的启明星而去。最后一句的强音记号,“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是整个咏叹调的高潮,这句歌词将情绪全部抒发,将阿珠即将赴死的决心表达的淋漓尽致,对戈桑的爱、对无法回到祖国的遗憾以及内心的痛苦全部倾吐。
(二)歌剧人物性格的把握
在咏叹调《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中有两个主要人物“阿珠”和“戈桑”,在剖析人物心理的时候,除了要充分了解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还要探析作曲家创作时的意图。一首歌曲,一定是艺术创作者对生活或者客观事物的反映,是来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歌词的写作,乐思的构成,旋律的走向,甚至是每一个谱面记号都有着创作者赋予它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要充分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摆脱时代差异,自身的经历以及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与作曲家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当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或者是歌剧里的某一选段时,要捋清不同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为所要演唱的人物性格进行深入的剖析。
阿珠在得知戈桑死去后,愿意坚守诺言陪伴戈桑,誓死追随戈桑,体现了阿珠的勇敢与悲壮,而当她沉浸在与戈桑的美好爱情憧憬中时,又体现了她的感性与单纯。整个咏叹调中,呈现了阿珠性格的两面性,所以在演唱这首歌曲时,不仅要把握好情感的诠释,熟悉音乐的风格特色,还要求演唱者在不同乐句的演唱时把握好阿珠性格的转变。
三、歌剧的音乐要素分析
(一)音乐的调式调性
歌剧《启明星》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歌剧,所以作曲家在创作时采用了大量的民族调式,既运用了新技法创作,又与中国传统技法相结合。咏叹调《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的调式为民族五声调式中的羽调式,羽调式在音乐色彩上是与小调相似的,整体色彩更加暗淡,柔和。在歌曲的首句,大量运用了民族调式中的羽音,呈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渲染了悲凉的环境,使歌曲中的人物性格更具有悲剧性色彩,所以在演唱时要表达出诉说般的效果。从歌曲中的旋律音来看,运用了大量的五声音阶,并且与蒙古族的音调相结合,具有浓郁的蒙古族风格特色。所以,表演者在演唱这首具有民族风格的咏叹调时,要注意把歌曲的“蒙古味”表现出来。在歌曲的中段部分,旋律线条比较优美流畅,在演唱这段的时候,要注重歌曲的韵味和声音的自然,不能去一味的追求声音的音色和共鸣,忽视了歌曲的民族风格特色和人物性格,要注重乐句的流畅和声音的纯朴自然。
咏叹调《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深受大家的喜爱,离不开其中优美的旋律,在第三部分——阿珠对归国的憧憬与向往中,旋律已经从上一段旋律中昏暗的色彩转变为明亮,旋律线条也更加的连贯流畅,这段旋律的描写更侧重于“阿珠”和“戈桑”两人对于回归祖国的美好憧憬,声音的把控上要更倾向于明亮,所以在演唱时要注意前后乐段的旋律的对比,改变声音的色彩。
(二)音乐的力度和速度
不同的表演者对于作品的力度和速度的处理都有着各自的见解,是表演者基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上形成的。笔者认为,《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的力度处理有几处需要注意,在歌曲的首句1—4小节中,标记了p的弱音记号,是阿珠对于戈桑之死的困惑和自责,旋律停留在中音区,在演唱时不可以没有声音,尽量大口吸气用最小的气息控制声音的发出,所谓弱而不虚。而在歌曲的结尾处,“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标记了f强音记号,则体现了阿珠誓死追随的决心,声音要很坚定,最后歌词的音较高,在演唱时应注意避免尖锐的声音,充分打开声音的共鸣,使声音坚实饱满。速度上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在歌曲的第一部分,这段旋律侧重于诉说,像讲故事一般地表达了阿珠对爱情的坚贞,同时标记了p弱音记号,有很多的四分休止符,在进行音乐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乐句的完整,不要因为休止符而使乐句断开,做到“停而不断”。第二处是,整个歌曲出现了两次“霎时间啊,像梦幻般消亡”,都标有了渐弱的记号,这两句歌曲的速度和速度的处理上都应该很自由,每一次出现都应该有不同的对比,第二次的处理应该比第一次更加的感叹,强烈。第三是,在歌曲的第三部分,“启明星啊,你发出那闪闪的光亮”,三连音的节奏,表达着阿珠对祖国的美好回忆和憧憬,这里的速度标记了a tempo回归原速,整体速度的处理上应与前一段快速形成对比。力度和速度的变化处理是演唱者在多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切记力度和速度的变化应该尊重原作,层次要分明有理。
(三)音乐的歌词
在一首声乐作品中,文学性的歌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歌词暗示着人物的心理活动,剧情的发展,所以充分的研究歌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在咏叹调《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中,在第一、二部分中间有一段独白,是要用台词的方式说出来,但是又要用声乐演唱的高位置去“唱”出台词,而不单单是说那么简单,“这是梦么?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不!这不是梦!戈桑死了,是喝下我敬给他的奶酒死的……这…”,这段独白,是阿珠对内心的疑惑的抒发,同时也是对戈桑之死的自责,具有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在说这段独白的时候,要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剧情中,想象自己杀害了心爱的人的痛苦,声音的前后变化要突出,语句的处理要跟随钢琴伴奏的起伏自由发挥。出现了两次的“霎时间啊,像梦幻般消亡”这句话,不仅要在速度和力度上形成对比,在歌词的处理上也要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在歌曲的最后一段,“失去了灵魂的归宿……去追随我心爱的戈桑”,要将整个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全部倾吐,是对戈桑之死的深刻缅怀,也是对沙皇的压迫和叛徒的控诉,演唱者声音应该尽量扩大,将整个歌剧的悲剧色彩呈现。■
——寒窑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