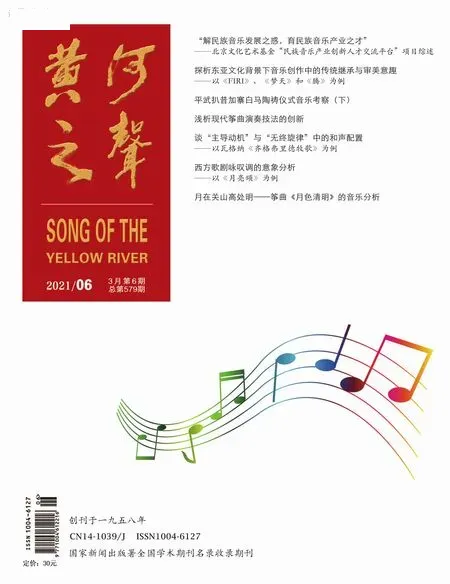试论歌词创作“出新难”的症结与突破
张咏民
当今社会,每年仅发表的、出版的或经谱曲演唱的歌词,就有成千上万首之多。然而,真正能够留得下、传得开、唱得响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细看这些作品,其实也都比较完整,但为什么有的不能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有的却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瞬间抓住我们的心。
究其原因,我觉得作品能否“出新”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正如乔羽先生所言:“歌词最容易写,歌词最不容易写好。”这其中也包含着“出新难”这个问题。那么,当今歌词创作“出新难”的症结表现在哪里?有哪些突破的对策?本文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谈几点感受。
一、症结表现
(一)跟风雷同,缺乏个性
一般来说,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当饱含作者鲜明的思想感情,应当具有较强烈的个性色彩。人们只有从中发现与众不同的闪光点,才会愿意去读去听去看。而如果一部作品,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没有任何的独创性,自然不会激起人们的兴趣。不得不说,在当前歌词创作领域中也存在着平庸化、雷同化、浅表化的问题,导致很多作品千篇一律,毫无特色,面临着一出现就被淘汰的窘况。
前些年,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一度大热,像《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套马杆》《我从草原来》等作品,让人们开始向往草原的美丽景色和无边无际的自由生活。当然,就有不少歌词作者把创作目光转向了草原,无论是否去过草原,都试着拿起笔书写对草原的向往和热爱。而创作中,并没有真正从成功的作品中悟到精髓,只是较生涩地把草原、毡房、牛羊、骏马等概念化的词汇植入歌词,认为就是草原风了。其实不然。因为,表现草原的特色不能只是表象的,我们需要以草原为依托、为切入点,写出它给予每个人的不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在草原的常住牧民和一个从未去过草原的外乡人,他们对草原的感情会一样吗?答案显而易见,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创作不能盲目地模仿跟风,看到别人写什么火了你就去写,却往往只是效仿写出共性的那部分,而忽视了个性的理解和表达。
再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时间,全国上下涌现出大量鼓舞斗志、助力抗疫、讴歌英雄、颂扬大爱的主题文艺作品,充分体现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也彰显了文艺的力量。在歌曲方面,我们听到了像《坚信爱会赢》《你有多美》《爱是桥梁》《解放军来了》等风格不同、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但同时,也看到了有些内容雷同、空泛、平庸的歌词,除了几句围绕“逆行”、“口罩”、“白衣天使”等字眼展开的语句外,没有发现特别有个性、有想法的句子。而作品《武汉伢》却吹来一股新风,它另辟蹊径,选取以武汉人的视角展开,串联起武汉的主要景点,描绘了武汉的风土人情,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特别是其中一句“如果有一天,她也需要我,搭把手,就过了”,让我们听到超凡脱俗、属于自己的声音,让人瞬间感动得泪目。
(二)惯性思维,概念先行
所谓惯性思维,是指人们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思考问题,好比物体运动的惯性。对于歌词创作而言,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用以往的经验和思维方式去指导创作。当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相似题材时,省去许多探索的步骤,节约不少思考的时间,但也常常会形成盲点,缺少一些创新或改变的可能性。
比如,我们在创作歌颂人民教师题材的歌词时,往往会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春蚕”、“蜡烛”等概念化的表达,陷入一种固有的模式,导致作品不是与已有作品雷同,就是肤浅俗套,缺乏特质,让人们过目即忘。但是,宋青松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则突破了以往的写法,通过小时候对老师的印象和长大后成为老师后的感受进行对比,将老师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别出心裁的构思。这首作品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是无不道理的。
同样,在创作军人题材的歌词时,不能只是习惯性地认为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就一定要写出阳刚之美。其实,军人也是人,他们远离家乡,也有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牵挂。所以,王晓岭的《当兵的人》一经问世,就得到部队官兵的认同和喜爱,在社会上也是广泛传唱。原因在于它没有局限在以前的框架中,而是写出了“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的原因,也说出了“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的道理。如此用心的设计,让这首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光彩。
歌词创作的思维惯性除了表现在创意上,还体现在词语的搭配、词性的用法及句式的结构上。通常,我们会按照传统的语法规范进行歌词创作。然而,方文山的歌词却有意打破日常生活中的约定俗成的词语搭配关系,通过语言的重组、变形、错位、倒装等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编织出新的质地”。试看他的《千里之外》,“一身琉璃白,透明着尘埃,你无暇的爱”。这里的“透明”将形容词用作动词,“你无暇的爱”与“透明着尘埃”构成了主谓倒装;再比如《东风破》一词,“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这一句中他将名词和量词做了错位搭配,用具体的数量短语来修饰抽象名词。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盏”来修饰灯,而这里却用来修饰“离愁”,让人顿觉新颖。方文山的词作中,类似的词类活用现象还有很多,分析这些非常规的用法,对于打破常规的思维惯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意象老旧、落入俗套
我们所说的意象是指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意象在歌词创作中的运用,能起到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作用,可赋予作品较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思想内涵。
然而,在实际创作中,我们极易陷入一堆常见的意象群中,难以跳出。如:在写到祖国时,常会选取黄河、长江、长城、昆仑等意象;在抒发思念之情时,常会选取月亮为意象;在送别朋友时,常用柳、长亭作为意象……然而,这些意象如果反复用,势必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也会使作品在新颖度上大打折扣。通常来说,物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即一个物象可以传达出多个寓意,而一个寓意也可以有多个物象来表现。因此,我们在歌词创作中要尝试开掘新的意象,传达新的寓意,做到俗中生新、熟里见巧。
在这一点上,张藜深谙其道,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成功的例子。品读他的歌词,我们不难发现,他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赋予其新意,达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效果。他在《命运不是辘轳》一词中写道:“女人不是水,男人不是缸,命运不是辘轳,把那井绳缠在自己身上。”词中的水、缸、辘轳、井绳都是农村常见之物,但张藜突破了寻常的意象,把任人摆布的女人比作是缸中之水,只能依附于男人;辘轳和井绳则寓意人的命运被传统陈旧的观念所束缚,形象贴切,蕴含哲理。再如,他在《苦乐年华》一词中一连用了八个意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感受,表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生的苦乐交加。他把生活比作是“一团麻”,说明生活的烦恼,又用“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喻指生活的美好。这些本是平时常见的意象,但却与寓义对象之间建立了新奇的联系,使歌词新颖脱俗、意味深长。
在反映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中,有一首作品叫《山杏花开的时候》(杨玉鹏词),通过对“山杏花”这一意象的塑造,象征进村的扶贫干部,为群众修路架桥,并通过发展山杏果产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第一段这样写道:“看见你走来的时候,山杏花正开满枝头。”此时的“山杏花”已由眼前的物象,形成“你”进村扶贫给当地群众带来脱贫希望的意象。而第二段写道:“看见你走来的时候,山杏果刚好又熟透。”此时的“山杏花”已结出“山杏果”,寓意实现了脱贫,村民的生活像“山杏花”一样美好,像“山杏果”一样甜蜜。这首歌词的意象选取新颖、贴切,生动地表现了主题,收到了点石成金、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角度不新,开掘不深
“角度”一词,来源于绘画、摄影。亚历山大·罗德钦科曾说过:“一个人必须采取几种不同的镜头视角,一个主题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情况下去观察和体验,而不是用同一个视角去观看。”毋庸置疑,角度的选取对于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歌词创作也是一样,角度不同,效果也会不同。尤其对于同类题材的创作,角度选得好不好,决定了作品能否出新,能否吸引大家的眼球。留意一些成功的、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会发现它们大多会有一个新颖独特、不同凡响的角度。
创作中,思念故乡的歌词作品很多。若按常规的写法,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朝思暮想的地方,那里是我的故乡。杨柳青青,槐花飘香,年年伴随我成长。炊烟袅袅,小河流淌,留下多少好时光。啊,故乡,无论我身在何方,都会把你守望。”很显然,这样四平八稳的写法,难以抓住大众的心。然而,我们来看晓光的《那就是我》,一定会被它的新颖角度所吸引。“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磨。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我思恋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噢,妈妈,如果有一支竹笛向你吹响,那就是我……”作者用了一连串的意象,构成了四幅最常见、最朴实的故乡风景画,通过“一朵浪花”、“一支竹笛”、“一叶风帆”、“飘来的山歌”把个人与故乡建立起联系,营造出新颖的思乡意境,给人一种独特的思乡体验,不得不说角度选得精巧。
再如,孟广征的那首《我热恋的故乡》让我们惊奇不已:“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试想,我们写故乡一般多选择正面描写,而这首歌词却着眼于“我的故乡并不美”,道出了记忆中的故乡是“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干涸的小河”、“贫瘠的土地”等如此贫困落后的面貌。到末段笔锋一转,写到“哦,故乡,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这样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切入角度,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故乡陈旧面貌的焦灼心情和憧憬故乡有个美好未来的真挚情怀。如此神来之笔,应归功于角度选得新。
选好角度的同时,也是对主题更深层次的开掘。如乔羽的《黄果树瀑布》一词,并没有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用黄果树大瀑布讲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从高处跌落,往往气短神伤。水从高处跌落,偏偏神采飞扬……人有所短,水有所长。水,也可以成为人的榜样。”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二、突破对策
针对以上列举的一些“出新难”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去试图解决。
(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生活原本就是丰富多彩、充满喜怒哀乐的,那么,反映到文艺作品中也应该是绚丽多姿的。因此,我们只有走出书斋,走进火热的生活,扎根人民的土壤,才能看到最鲜活的场景,才能听到最质朴的话语,才能捕捉到最丰富的信息,进而找到“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出新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如果没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那我们的歌词创作就难以摆脱惯性思维的桎梏,难以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审美效果。
(二)加强学习,苦练内功
朱光潜曾说过:“有些年轻人是不学而求创造。”意思是说,只热衷于写而不重视学,是不可取的。歌词虽然字数少,篇幅小,但却蕴含着大量的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写好一首歌词,绝非是表现出来的百余字那么简单,它需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和文化背景。因此,对于从事歌词创作的人来说,一定要多学习,不仅要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学习民间的文学精华,更要不断地从生活中、从大师的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提升文学品位和音乐素养,为歌词出新做好充实的知识储备。
(三)锤炼语言,多写多练
歌词是一种听觉艺术,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解决歌词创作“出新难”的问题,锤炼语言是关键。我们都知道,歌词的语言要求通俗易懂,精炼流畅,让人们在较短的时间里一听即懂。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语言的锤炼,通过词语、句子、句群的锤炼和各类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增强语言表达的功力,多写,多练,多积累,多总结。
(四)感受音乐,放开想象
想象是艺术创作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欣赏者总是期待着新奇的作品出现,所以艺术家的想象力要超出欣赏者并付诸实施。我们的歌词如果缺少想象,就会失去灵性。通过赏析像《我和我的祖国》《天之大》等这样填词的优秀典范,会发现依曲填词不失为一个打开想象翅膀的捷径。因此,我们不妨多听听音乐,在旋律的起伏流动中,在具象、印象、抽象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想法,展开充分的想象,为歌词主题内容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进而使作品出新出彩。
艺术创作是一项富于智慧和情感的创新性实践活动,每一次艺术创作都是一次创新的过程。歌词创作唯有推陈出新,才能使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作为歌词创作从业者或爱好者,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探索突破“出新难”的技巧和方案,用心用情用功地投入创作,力求每一首作品都能闪耀出新颖独特的光芒。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