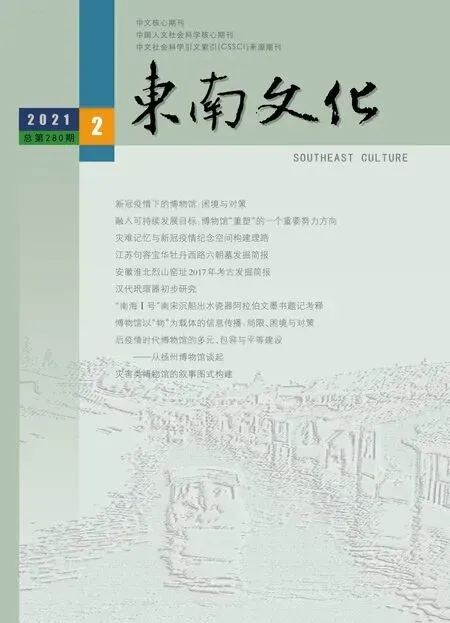博物馆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局限、困境与对策
周婧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博物馆传播的是依托实物重构的信息。当前,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以及立足物及其研究进行的多元阐释的耗时耗力,导致了一部分博物馆出现信息传播的错位和偏向。以“物”为载体的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局限在于难以阐释隐性信息以及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造成博物馆传播的信息无法与过去、现今等未知领域,与观众的需求和兴趣以及与观众整体的感知觉相适应。为弥补信息传播的局限,博物馆应重视物及其研究,满足不同物的差异化阐释需求,策展人保持价值中立等。为突破信息传播困境,博物馆应重视对物、人和传播手段有机组合的阐释,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的相宜性等。无论如何,博物馆应坚持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向。
参观博物馆是一种基于真实物件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的可贵之处在于信息的真实性和物质性。真实性一方面指物所载信息在原载体上,既不能复制也不能伪造;另一方面指物作为信息媒介的真实,即当物从现实情境中抽离出来,被纳入博物馆收藏序列时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属性——成为传播某一主题的媒介。借助这种媒介,信息受众能超越时空,透物见人见精神,甚至见到一个社会。物质性指物是具备三度空间的物质实体,观众可通过全方位的观察、互动和体验,获得感官刺激、情感联结,甚至心境的改变。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的仿真体验无法取代现场目睹毛公鼎、彩陶钵等真实物件的震撼与触动。博物馆说到底是传播信息的机构,但其传播的媒介和信息较为特殊,具备真实性和物质性的双重属性。当前,由于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以及立足于物及其研究进行多元阐释的耗时耗力,导致部分博物馆出现了信息传播的错位和偏向:不尊重物及其所载信息,而依赖外部观点的强加和演绎。为避免盲目跟风及其导致的身份迷失,有必要重新审视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问题。
一、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发展史
近现代公共博物馆三百余年的发展史,是一部信息传播的变迁史。根据传播理念“重单向发送、重被动接收和重主动构建”的阶段差异,笔者将其大致划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为专注于物件展示的信息单向发送阶段,基本出现在15—16世纪,主要是在16世纪,处于“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或“前科学”时代。收藏的唯一标准是收藏者的个人兴趣,对象为化石、标本、文物、油画、雕塑等各种奇珍异宝,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1599年,第一部收藏目录《英雄们的盔甲》出版,该书保留有关于盔甲的描述说明和精品版画,是涉及珍奇柜这一类型的最早材料之一[1]。当时的物件展示及其信息发送,主要是为满足收藏者的观看和把玩之需。
第二阶段是专注于知识传播的信息被动接收阶段,大约出现在17—20世纪。受“科学化”思想驱动,博物馆逐步成为传播公共知识的权威,开始关注到信息传播的对象,即知识输出的接受者。首先,17—18世纪,科学家与珍奇柜发生关联,通过合理摆放展品顺序,进行归类和分组,客观上推动了珍奇柜的发展。如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将实物标本引至展览中[2]。其次,艺术博物馆大致在17世纪末步入本阶段,出现了沙龙绘画展,通常由评审委员会来决定作品是否被采纳。1784年,克雷地安·德·梅歇尔(Chrétien de Mechel)对贝尔维埃特美术馆(Belvedere Museum)重新设计、分类,并出版了一本藏品目录,该目录以时间为序而非依据美学或类型学描述艺术史[3]。再次,历史博物馆从18世纪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派生出来,因其聚焦于分类收藏,也开始步入权威知识的传授阶段[4]。1727年,博物馆学真正的奠基之作《博物馆实务》(Museographia)问世,该书强调了一个关照知识、内向省思的世界。
第三阶段为专注于意义建构的信息主动编码阶段,肇始于20世纪中期。1949年,信息论学者克劳德·艾尔伍德·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和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创建出最早的信息论传播模式“申农—韦弗模式”[5]。在博物馆领域,1967年,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其同事哈利·帕克(Harley Parker)在纽约市立博物馆举办的研讨会中率先指出,当前博物馆的设计是线性的,但世界正在变得非线性,博物馆需打造一个信息交流系统。遗憾的是多数与会者并未听懂他们的观点。一年后,邓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发表《观点:作为交流体系的博物馆》(A Viewpoint:The Museum as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Museum Educa⁃tion)一文,指出博物馆的物不是一般的物,信息交流体系是构建在物之上的,存在一个发送者和接收者[6]。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学家伊万·马罗维奇(Ivan Marović)提出博物馆学更像是信息科学、传播科学,引发博物馆学界的广泛关注。他指导的博士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也成为这一观念的拥趸。因此,本阶段的特征是信息反馈得到重视,博物馆尝试根据接收者所需来组织信息发送,甚至邀请观众主动参与信息编码。
二、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之局限
尽管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真实形象、易于感知、便于互动、连接情感、短时获益等,但同时也存在与生俱来的局限,揭示并认知其局限是成功传播的前提。博物馆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局限具体如下。
局限之一是物载信息除了表层的显性信息外,还包含多层隐性信息,这些隐性信息通常难以不言自明和不证自明。物一旦离开原先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7],如果后续未经研究者和策展人的双重编码,且观众在解码时又缺乏“先有”储备,那么观众往往只能接收到表层的显性信息,其他层次的隐性信息则可能被自动过滤,这无疑是对遗产利用的一种极大浪费。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之所以广受称道,原因之一就是善于将物的隐性信息显性化,变劣势为最大优势。此外,当物件的显性信息较为普通时,若非有意加以强化,即使是显性信息也易于被观众忽视或误读。
物载的隐性信息解读起来困难重重。一方面,对物所载信息的事实判断较易,但价值判断却难。这些物之所以被收藏本是人类的一种选择行为,其幕后推手是当时代的社会背景及其形塑的价值观。但随着原生环境的消失,收藏者当时的选择依据也会消失。正如雷恩·梅兰达(Lynn Maranda)所言,事物(things)是一种广义的客观存在,而实物(objectives)则是一个完整含义体系中的客观物品,相较于事物,实物是人类定向性应用的结果[8]。因此,博物馆需要反过程来破译当时人的收藏动机,从而实现价值判断的信息再现,以重构自然与社会图景。另一方面,除了横向呈现的信息外,物在世代的颠沛流离中还被叠加了时过境迁的流转信息,这些新信息使物具备了新意义,对这类信息的解读也极其不易。苏珊·皮尔斯(Susan M.Pearce)以参加滑铁卢战争(Battle of Waterloo)的军官的夹克为例,指出仅仅客观描述“这是一件红色的夹克,有几枚肩章……”[9]远远不够,人们想看到的是某种情绪,而非一块布料,它象征着取得胜利的英国人和理想化的法国革命者。但随着时间推移,事件的亲历者辞世,滑铁卢相关电影和小说诞生,此时话语发生改变,人们依然记得这场战役,然而它却是由观众通过想象力重构的,并且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构建出一种新的符号。博物馆中的物在进入博物馆前后,经历时代更迭,生命被延续的同时也衍生出新的意义。苏东海指出,“观众不会止于对文物感性材料的了解,因为这只是了解文物意义的开始”[10]。博物馆只有将信息层层剥开并予以传达,才能不负一代代投身其中的创造者、收藏者、守护者和研究者,不负物本身的生命历程。
局限之二是遗留下来的物即使信息被逐层析出并加以编码,仍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只不过是真实信息的片段再现。物被保留至今受很多偶然因素支配,尤其是在早期,这些残缺不全的物及其信息七零八落,对研究者拼接完整历史造成困难。为此,除了要不断优化博物馆学、考古学、地质学等理论和方法,以提炼物证中留存的各层信息外,还要借助各类记忆载体进行整合和二次编码,最终转化成空间意义的视觉表达。同时,为了突破物的隐性信息无法自行言说以及完整证据链缺失的信息困境,辅助展品由此诞生。辅助展品虽然始终面临真实性与科学性的考问,其推广使用也是弥补阐释时信息不足的无奈之举,但却无意间给传播方式的创新和表达媒介的选择带来无限的可能和包容,从而使博物馆由冷媒介变成热媒介。
三、博物馆信息传播中的三大困境
由于物的多层信息深藏在物之中,博物馆的传播载体又具备三维深度感,而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它不能简单地将知识载体交给公众,需要在信息传播时负责向公众解释和说明藏品[11]。因此,博物馆媒介的信息传播至少面临三大困境。破解这些困境,是实现博物馆特定空间内物人有效对话的关键。
困境之一是如何实现博物馆传播的信息与过去、现今等未知领域的相宜性。相宜性指的是“与之相适应”[12]。博物馆展示的对象及内容有助于突破个体时空体验的局限性,因而吸引一批批观众慕名前来,但观众“个人背景”——“独特的经验与知识的储存库”[13]的差异给博物馆的信息补缺及有效沟通带来困难。事实上,观众的认知结构中关于对象的知识成为其观看时选择和判断信息的依据,一些哲学家称之为“前有”,没有这个“前有”,认知就难以发生[14]。观众对展览进行信息解码时会出现“内行气象万千,外行一头雾水”的状况。所以,对展览进行信息编码时,如何平衡极富深度的专业知识与多数观众认知起点的落差,是摆在信息传播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困境之二是如何实现传播的信息与观众需求和兴趣的相宜性。王小平等指出“隐喻”(相似性)与“转喻”(相关性)是人类认知世界、表达情感和组织意义的重要载体[15],是认知发生时最为底层的作用机制。同时,“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为“共情”产生提供了神经生物学证据[16]。综上,无论是认知发生的底层机制,还是共情的生物学基础,都表明博物馆努力实现与观众自身需求和兴趣相宜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的观众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期,我们对博物馆观众尚缺乏实证与思辨研究。所以,实现与观众需求、兴趣的相宜性,仍是横亘在信息传播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困境之三是如何实现空间传播与观众整体感知觉的相宜性。观众从决定参观到进出博物馆并留下相关记忆,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体验。19—20世纪,观众基本为被动体验[17],直到20世纪后半叶,博物馆才开始探索如何为观众打造积极的体验[18]。空间问题由此获得重视,博物馆空间不仅是展览的容器,还是展览阐释的参与者;认知科学的二次革命后,具身认知理论也告诉我们,身、心和环境三位一体,环境能促成观众认知的成功。博物馆特定的“环境语境”以及观众在空间形态下的“认知规律”,彰显出博物馆媒介传播的异质性,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研究对象[19]。首先,博物馆的空间是有结构的,展览也有结构,空间结构可参与到展览阐释中,该现象在叙事展览中尤为突出。玛格丽特·霍尔(Margaret Hall)将展览分为分类式和主题式,其中主题式有叙事式和情境式。叙事展览是按线性逻辑组织,而其他展览则属于非线性。在叙事展览中,内容的线性逻辑需要与空间的情境重构互相配合。因此,在叙事展览中,线性逻辑对空间结构存在严苛要求,如果不对空间的情境重构进行合理策划,而情境重构本又具有一定的自由性,那么展览稳定的线性逻辑就会被瓦解。如何将文本和空间有效结合,创建两者相得益彰的阐释性展览,是博物馆信息传播面临的又一挑战。其次,展览要素的空间表达具有特殊性。控制观众参观注意力及其分布的影响因素有体量、位置、照明、色彩、方向等,但这些因素并非我们传统学习中的影响因素,所以极易被忽略而陷入“世俗化迷思”,即缺乏意识又不去注意,从而造成更深的偏见和无知。由此,从整体策展到要素表达,实现空间传播与观众整体感知觉的相宜性可谓是步履维艰。
四、博物馆信息传播局限和困境的应对之策
针对博物馆信息传播中的上述局限和困境,笔者尝试提出可能的弥补和破解之策,以促使物载信息经由专业阐释,成为观众易于理解甚至启发思考的信息共享体。
(一)弥补信息传播局限的应对之策
1.满足不同物的差异化阐释需求
作为信息载体的物,包括人工物和自然物两类。一般来说,文化遗存、当代物件等实物展品以及装置、造型和媒体等辅助展品,都属于人工物,往往会被赋予某一功能;而自然遗存则属于自然力的产物,通常不会被赋予特定功能。其中,人工物又可被分为两类,装置、造型和媒体一般是专为特定展览展示而创造的;而文化遗存和当代物件却并非如此,根据创造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区分成三类:纯审美的物、纯实用的物、审美和实用兼具的物,三类物之间具备不同的阐释需求。纯审美的物如雕塑、绘画等,是一种图像语言,本为观看而创作。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过程将自身观念可视化,且艺术品所指向的物往往是我们熟悉的。因此,纯审美的物本身拥有传播能力,其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即内容。观众借助视觉观察,便可获得它最具价值的物载信息。但近年来,为帮助观众更好地读懂纯审美的物,弥补观众艺术史知识的缺失,艺术博物馆开始学习传统博物馆,使用具备阐释功用的辅助信息和传播手段。而关于纯实用的物以及审美和实用兼具的物,它们通常并非为观看而生,形式也不等同于内容。因此,“这类物件是沉默的,所承载的记忆和信息都深藏在物质之中”[20]。博物馆化的结果是,它们由私人空间步入公共领域,使用情境和性质均发生改变,如不进行阐释,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普通观众则可能看不懂。例如,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T形帛画基本属于审美和实用兼具的物,画上绘有两千年前古人对天界、人间和地下最富幻想的图案,其实际可能是用作引导灵魂的工具——招魂幡[21]。面对这类物,审美只是前提,因为其表层的图像语言并非最具价值,需要博物馆为观众重构理解物的特定语境,揭示其所蕴含的内在意义。
2.研究物的识别信息,更需深入研究其作为认识世界的媒介信息
物并非是语言或文字锁定的材料,但人类在认识世界时却存在符号表征的诉求。这就需要研究者开展物的研究,解读其内蕴信息,并以文字、语言等符号加以表达。研究者未进行研究之前,藏品只是没有被人类智慧照亮的物质堆积,也无法为博物馆提供科学依据[22]。研究者通过研究将信息与载体分离[23],通常会产生两类成果:一类是物的识别信息,如命名、断代和分类;一类是物的媒介信息。笔者认为前者是基础,后者才是目标。因为博物馆关注的重点并非器物发展史,而是人的历史[24]。如果不将物视为媒介,开展综合且系统的研究,就难以揭示其时代的特征、变迁及趋势,严重影响对其后续信息的重构。而藏品媒介信息的研究成果,不仅符合博物馆中物的研究性质,还能促成其教育优先的功能履行。以湖南省博物馆“根·魂——中华文明物语展”的曾侯乙鉴缶为例,展览不仅呈现器物的纹饰、造型等识别信息,更揭示出其用来冰酒、温酒等功能,凸显了战国时期不断改进、追求极致的匠人精神。
3.信息分层是获取物的媒介信息的有效手段
为了将物载信息转化为语言和思想领域的表达,且富有成效地服务于展览阐释,需要基于策展视角,对博物馆通过物研究获取的信息进行分层。先后有一批学者就该问题展开过讨论。彼得·门施将信息分为四层:自然物质信息(或物的结构性特征)、功能信息(或意义特征)、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信息(或联系性特征)、记录性信息[25]。蒂莫西·阿姆布罗斯(Timothy Ambrose)和克里斯平·佩恩(Crispin Paine)将其分成三层:内在信息,即通过检查和分析物品的物理特性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外在信息,即从其他资源了解到的物品相关信息;被赋予的特殊信息或含义,即物品对不同的人曾具有的含义和现有的特殊含义[26]。不难发现,上述两种观点基本停留在现象层面,但其论述的视角仍给笔者带来启发。对笔者产生更为深刻影响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事物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时提出的“四因说”:质料因,构成事物最初的“基质”;形式因,事物特定的形式或原型;动力因,事物变化或停止的来源;目的因,做一件事的“缘故”[27]。这一观点趋近本质且概括性强,稍显遗憾的是未明确指出纵向逻辑上的流转信息,不过足以启迪笔者对2016年提出的信息分层进行修正。2016年,笔者、严建强曾提出物包含三层信息:本体信息,外观、制作和功能等;衍生信息,意义和精神等;流转信息,使用者和收藏者变更或者退出使用、进入收藏领域后被赋予的新信息[28]。受“四因说”启发,笔者现将“物”所包含的三层信息发展为:本体信息,物的质料、形式和功能信息;衍生信息,制作物的动力和目的信息;流转信息,新的动力和目的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本体信息。
4.依靠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力量
当基于策展所需对物载信息进行分层时,涉及材料丰富、方法多样,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厚学养,还要拥有丰富经验;不仅需要社会科学背景,还要拥有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背景。因此,该项工作对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及其跨学科提出较高要求。如美国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不仅邀请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其实物、照片、档案、口述史等展开研究,还邀请了纸张保护专家对样品进行分析,以寻找房东或租客装饰房屋的证据,从而推断当时移民租客的生活水准[29]。因此,各馆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规模不一的研究部门,大馆甚至还可主办学术期刊,成为学术研究重镇。如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美国的史密森尼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法国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英国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等均主办了学术期刊。作为一个馆藏物的信息中心,博物馆为拓展和深化研究成果,不但需要馆内人员的合作,还需要馆外专家的加盟,甚至可考虑将公众纳入,以形成研究成果“众筹”之势。如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市民科学”(Citizen Science)项目,邀请市民通过收集样本、观察记录或转录手写记录等方式,积极参与馆内科学研究,目前参与者已达数千人[30]。
5.策展人保持价值中立
尽管博物馆希望通过物来再现远去的自然和社会,但它们只是历史的碎片而非历史本身。所以,复原事实本是一个美丽的谬论。尽管展览成品是一种客观呈现,但实际却是策展人主观意志的间接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某一主题或文化的认知甚至判断[31]。当物件去脉络化进入博物馆并转化成某种有意义的展品时,策展人需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将自我身份边缘化,从物载信息中提炼立场和观点,而不是主观强加。当遇到有争议或言说困难的主题时,不妨一改权威性面容与中心话语,既可真实再现信息探索上的不足,也可将博物馆展览打造成多元声音的发声平台,不致令各种声音失去表达自我的话语权。1964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举办了名为“我心中的哈林区”(Harlem on My Mind)展,这本是一场关于非裔社群生活的艺术展,但展品却全部由白人摄影师和策展人选定。社群“被代表”的结果是非裔艺人在博物馆门外抗议,馆长出面公开道歉,自此少数族裔的展览不再被白人学者和博物馆员工垄断[32]。
6.展览无需刻意求大求全
博物馆希望通过展览全面系统地呈现某一主题,这一夙愿似乎并不可取。因为一旦确立该想法,而物入藏时又面临着偶然性和不均质性,那么必然会过多依赖学术资料和辅助手段,结果展览中物的地位和价值将大打折扣,展览可能变成一部与通史无异的三维再现。物和文献在与人类各种背景的互动中,存在迥异的生命轨迹,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33]。相较于文献,博物馆中的物在反映自然活动和人类行为上虽不够系统,但却更为客观而生动。贾尔斯·维拉德(Giles Velarde)认为“任何脱离物的叙事性质的陈列,成功的希望都是十分渺茫的,一个陈列只有以物为基础,组成它所要展示的整个发展序列,这才算是成功的”[34]。展览只是一个展览而已,无需刻意求全求大,而应重视物载及其关联信息,由此创建的展览才会是排他的、充满个性和生命力的。
(二)突破信息传播困境的应对之策
如果说“弥补信息传播局限的应对之策”主要论及物及其研究,那么“突破信息传播困境的应对之策”则主要探究人和传播手段,以及由物、人和传播手段有机组合的阐释问题。展览若要实现阐释和传播的成功,仅依靠物的研究已远不足够,还应拓展至博物馆学研究。因为无论是针对人、传播手段的研究,还是将三要素相结合的阐释研究,都是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倡导博物馆学研究正当其时且迫在眉睫。
1.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未知领域的相宜性
为了提升这种相宜性,首先要明白观众的先备知识状况,这需要依靠观众研究中的前置性评估。前置性评估是指“在任何实际工作开展前的评估。在这类评估中研究者需要明确问什么问题、收集什么数据以及如何使用”[35]。包含准备、规划、实施和应用四阶段,其中规划阶段至关重要,涵盖目标确定、方案设计和内容形成三大版块。通过前置性评估,可获悉观众的背景知识、期待和疑问,并在策划时将研究发现纳入,构建博物馆与观众的相关性。正如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所言,“如果不以任何方式与观众个性和体验内容关联,那么阐释将是无效的”[36]。2020年上海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就上海博物馆东馆展览等问题,合作开展了一场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前置性评估。方案设计的依据是东馆初定的“中国古代文化”展览主题,包含雕塑、青铜等十个部分。通过数据分析,获得基本陈列和公共服务的45个二级编码和90余页的调查报告,如在展览主题上观众希望增设中国艺术发展史等,评估结果将有助于针对性地调整展览规划和改善观众服务。
其次,针对性提升观众的知识储备及知识水平。一是重新定位策展团队。策展团队应兼具信息研究者或信息传播者,甚至还是观众倡导者。信息研究只是前提,信息传播才是使命。凯瑟琳·麦克莱恩(Kathleen McLean)指出:“如果我们希望展览真正吸引人,不只是教育工作者和评估者,而是所有的展览专业人士,都必须成为传播者和观众倡导者。”[37]因此,策展团队应转变理念,明确其三重身份。在能力不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释展”[38]环节或“观众踏查”[39]等方式弥补,这些做法在西方大型博物馆的策展实践中已经实施。二是以介入的方式进行改善。目前多数观众为初学者或外行,但他们又想从短时参观中获益,为此要尝试改变观众,具体措施包括在开展前进行广泛宣传、强制观众欣赏导入式视频,还可提升展品本身的阐释性。以大英博物馆集合100件展品的全球巡展为例,该展在2012年正式面世前,馆方已于2010年与英国BBC合作推出了一套广播节目,创下1100万人收听的记录;其后,出版了荣登畅销书榜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这些预热手段培养了潜在观众,并提升了其认知起点。又如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Th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唐代沉船展”(The Tang Ship⁃wreck),策展人在步入展厅必经的墙面上设置了视频,再现12世纪前水手拓展贸易的情形,介绍船只的制作过程、工艺、承载商品和遇难原因,使观众快速补充有关“黑石号”沉船的信息。
2.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需求和兴趣的相宜性
首先,要了解观众具备哪些普遍的需求和兴趣。正如贝弗利·塞雷尔(Beverly Serrell)所言,“观众带着各种各样的兴趣来到博物馆,尽管他们多元,但有很多共同的期望和需求”[40]。因此,我们需要尽力去发现并服务于最常见的共同点。当前,观众在人口学和行为学上的相似性包括[41]:在各类博物馆中,青少年比重不足;最受欢迎的展项能吸引各类观众;当观众难以理解或无法建立关联时会直接放弃;观众普遍拒绝长标签而喜欢短标签;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会被具体、粗放的展项吸引;观众都偏爱舒适和放松的空间;观众都较为关心热点问题[42]。应通过系统、深入的观众研究,积累中国观众的普遍需求和兴趣,在秉承专业导向的同时兼顾观众导向,创建出专家叫好、观众叫座的精品展览。
其次,评估观众的需求和兴趣。在开展相似性研究的同时,各馆在吸引观众方面亦存在个性。为此,需要开展“参观动机”评估。参观动机是指“激励公众朝向特定目标行动的内在驱动力量,驱使满足个人的社会与心理需求,是个人选择参观博物馆的重要原因”[43]。它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心理活动,主要受内在需求和外在刺激的双重影响[44]。影响因素的构成也是多种多样[45],需求和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国际上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46],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玛丽莲·胡德(Marilyn G.Hood)[47]和阿利克斯·斯莱特(Alix Slater)[48],但我国直接相关的论文还比较少。所以,应基于国外业已成熟的动机研究,参考其获得共识的影响因素,通过因素分析,明确我国观众在参观某馆时的影响因素及其构成,以便针对性地提供观众所需的展教和公共服务。
再次,发展观众在参观中的需求和兴趣。博物馆学习是不受限的快节奏学习,观众在多元智能、学习风格、身份、体验偏好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应当进行分众研究。约翰·福尔克(John H.Falk)归纳出探索者、促进者、寻求体验者、专业/爱好者和充电者五种身份模型[49]。史密森尼博物院的安德鲁·佩卡里克(Andrew J.Pekarik)指出观众存在四种体验偏好,分别是偏好想法、人、物件或身体。因此,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开展基于年龄、职业、教育、收入等人口变量的浅层次分众研究,还应拓展至基于观众行为、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等更为深入且本质的分众研究,这些成果将有助于我们打破机构本位的单一视角,构建多元的“分众”视角,从而为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适当且精细的服务。
理想状态的博物馆学习应是一种建构式学习,为此博物馆要邀请观众主动参与,使其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为主动的信息建构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参与式文化,该文化后被移植至博物馆领域,妮娜·西蒙(Nina Simon)根据参与程度不同,提出贡献型、合作型、共同生产型、主人翁型四种参与模式[50]。博物馆可依据自身业务的参与程度选取不同模式的参与技巧,但这些技巧的使用必须与各馆的核心理念相结合[51]。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高质量的博物馆阐释虽然没有显性地邀请观众参与,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身心不自觉地完成了主动参与,这才是参与式博物馆应追求的最高目标。
3.增进空间传播与观众整体感知觉的相宜性
为了增进这种相宜性,首先,应了解观众参观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完整体验。完整性体验肇始于观众决定去博物馆的那一刻。对首次或偶然性观众来说,在博物馆的参观过程基本包含四步:适应(3~10分钟)、专注观赏(15~40分钟)、浏览(20~40分钟)和准备离开(3~10分钟)[52]。因此,博物馆不仅要重视观众的寻路和定位,还要将参观体验变得丰富,以延缓博物馆疲劳,并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和持续力。出行的方便与否同样可能决定观众的参观频次[53]。观众在博物馆除了漫步展厅外,还会使用洗手间、享用餐饮、购买文创产品以及接受员工服务,这些都是他们体验的一部分。所以,博物馆还应着力改善停车、洗漱、餐饮等公共服务,并将博物馆物载信息融入各类公共服务中,从而使展教活动和公共服务构成一个整体阐释系统。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The Asian Art Museum)的博物馆餐厅Café Asia推出与其传播使命相符的亚洲文化风情美食,包括“乾隆皇帝套餐”、椰奶鸡肉汤等。事实上,在步入展厅前,不少观众已决定了参观时长[54],这也反映出进馆前的参观动机对观众实际参观的影响,而动机的产生又深受个人背景影响。所以,想要吸引观众前来,虽间接但更重要的做法是将博物馆打造成易于亲近的交流平台,避免因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55]造成文化区隔,从而吸引大量文化资本低的潜在观众前来。
其次,通过展览的内容及其形式,为观众创建完整的观展体验。一是确定传播目的,以实现展览的集中性和连贯性[56]。传播目的应是明确清晰的一句话,包括“主语、动词和结果(怎么样)”。它是提供给策展团队的工具,而非给观众看的,是团队达成的一种共识。如美国纽约科学馆(The New York Science Museum)的“演化与健康”(Evo⁃lution&Health)展,传播目的是“每一次适应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二是依托物载信息,撰写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内容文本,形式的空间逻辑符合内容的文本逻辑。其中,根据内容结构的不同,可创造两类空间规划。一类是针对线性阐释的定向式空间规划,观众只能沿着线性动线行走,在限定的选择中去理解展览内容及安排;另一类是针对非线性阐释展览布局的,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非线性放射状空间规划,这类布局通常有一个中央核心区域,周边配置发散出去的支持性空间,该类型的空间设计易于为观众提供导向;第二种是非线性随机式空间规划,这类布局缺乏中心叙事,更多鼓励观众自由选择;第三种是非线性开放式空间规划,这类布局是空间内所有展览内容都一览无遗,可为观众提供开阔的视野,使他们能绝对自由地选择参观路径。无论如何,包括空间规划在内的形式设计必须忠实于展览的主题和内容,是对展示主题和内容准确、完整、生动的表达[57]。
综上,物的研究是信息阐释中最为基础的一项工作,地位不可动摇。不过要真正实现当代博物馆“物人沟通”的成功,还要依赖“基于观众研究的阐释与传播”等博物馆学研究。从国际上来看,博物馆的专业化大约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后不过100余年,围绕以“物”为载体的信息研究,相关文献仍然不够丰富,因此任重道远。我们既要围绕这类研究的性质、特点、目标和历史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还要围绕其理念和方法等开展应用理论探索。
五、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迅猛发展以及20世纪中后期波及我国的博物馆变革,不免让博物馆人手忙脚乱而顾此失彼,呈现出弱化研究、生造观点和花哨炫技等信息传播中的一些错位和偏向。笔者之所以选择本议题,原因有二。其一是“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在20世纪,博物馆更加注重收藏和研究,而非观众和教育[58],因为基于物的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59]。但至21世纪,博物馆开始将观众置于中心。这种“物人关系”的理念转向,伴随展览要素的丰富、技术的进步和功能的拓展,可能会传递方向上的错误信号,即“从物到人”的趋势代表着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全部。同时,也可能导致对“从物到人”中的“观众为先”理解的简单化,单层次地理解为非专业导向、无边界地迎合观众。目前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于观众在空间形态下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行为极不熟悉且这一问题突出,但万不能以此为由而矫枉过正或执此废彼。因为“物”始终是博物馆存在的根基,公共博物馆承担阐释物的使命。其二是立足于物及其研究的多元阐释耗时耗力。当前一批新锐展览正在兴起,它们强调理念先行,热闹一时,成为网红打卡地,却忽略物的研究及其价值。因为理念先行的展览不必进行长期的藏品研究,而只是需要外部观点的强加和演绎,通常耗时较短且易博得眼球。笔者担心这种博物馆热的假象可能会引发盲目乐观和简单跟风,长此以往,其中部分博物馆可能会变成丧失灵魂的躯壳,成为诉诸感官刺激而内容中空的媒介,最终可能的代价是陷入与其他机构无异的“身份迷失”。虽然博物馆需百花齐放,但在有些浮躁的当下,主流方向的保障似乎更显重要。为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回到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问题上,再议博物馆传播中的这一底层问题,探究此类传播的局限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反思。
未来学家赫曼·卡恩(Herman Kahn)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四次浪潮将迎来“以休闲为导向的社会”(leisure-orientated society)[60]。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理性的逻辑思维让位于感官的视觉呈现,视觉传播彰显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博物馆作为一种由物及其信息所构建的形象传播系统,在这个超节奏社会和终身学习的年代,因其视觉化、生动性和体验感等特点,似乎正适逢其时并备受推崇。即便博物馆迎来了发展契机,但展览的量化考核和各类媒介的竞争刺激仍会让我们迷途失路,此时,物才是博物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物的保存、研究和利用乃是博物馆诞生的缘起和发展的理由,正如卡里·纪伯伦(Kahil Gibran)所言,“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由于历史或行业阻隔,物虽有“千言万语”但却“缄默不言”,我们期待借助这些历史长河中遗落下的记忆碎片,由策展人从物载信息中生成展览的主题、结构和表达,并在传播目的的指引下,现场重构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客观世界,让观众感受到自然变迁的沧海桑田和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借由物证这把钥匙,开辟人类认识世界的崭新视角,以小见大、证经补史、透物见人,帮助解锁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未知领域,在输出知识的同时促进理解、思考,并给予他们情感关怀,以达成慰藉与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