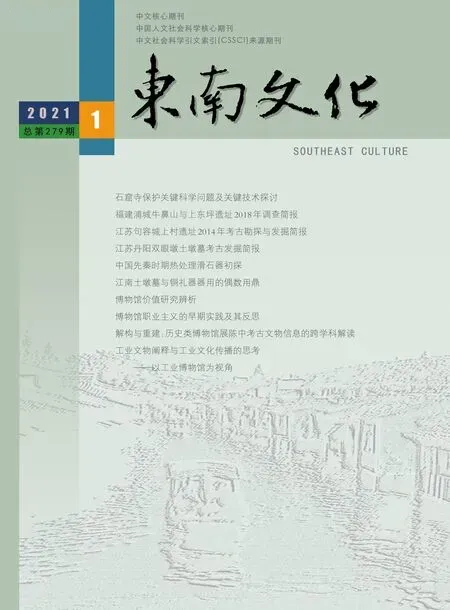博物馆职业主义的早期实践及其反思
张 昱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职业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西方社会的一种职业意识觉醒和职业制度建设。20世纪70年代新博物馆学诞生前,博物馆职业主义经历了早期实践阶段,具体表现在: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意识产生,专门职业获得认同,专业组织相继成立,专业培训课程建立,对伦理道德愈发关注等。这一阶段的发展及对其弊端的反思,为此后博物馆的改革明确了方向:注重专业人员培养,陈列展览和文化传播探索出新理念、新方法,拓展更多样化的社会职能。这些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建设提供了理性依据,即博物馆为社会服务是人员职业化的最终目的,有序推进职业标准的制定,继续强化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激发专业组织更大的行业引导作用等。
在我国博物馆事业快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既关乎博物馆发展理念的革新维度,也关乎其社会评价和公众感知,更关乎未来其所能达到的社会贡献的广度与深度。“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1]是西方社会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产生的一种职业意识觉醒和职业制度建设,也是早期博物馆行业提升整体专业能力的重要实践。纵观博物馆职业主义的发展进程,20世纪70年代起早期职业主义遭到批判,同时新博物馆学诞生,因此,可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看作博物馆职业主义的早期实践阶段。尽管该阶段的一些成果被后人诟病,核心争议在于带来的专业人员“专业性”与社会“整体性”的冲突,但不可否认,当时诸多博物馆专业组织的成立、博物馆职业获得的社会认同、高校博物馆培养课程的逐步建立与拓展、对博物馆伦理道德的关注等都为当代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化建设提供了反思其本质、规避其弊端的重要参考。
一、博物馆职业主义的产生背景
“职业”(profession)区别于“工作”(occupa⁃tion)和“行业”(vocation),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作为地位身份象征的职业概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作为制度象征的职业概念[2]。厄内斯特·格林沃德(Er⁃nest Greenwood)总结了“职业”的五大特征:系统化的理论、权威人士、社区约束力(社会认可)、职业准则、专业文化[3],对职业概念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争论聚焦点开始由职业概念向职业形成过程转变,即对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及最终形成的职业主义的分析。博物馆职业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源于以下背景。
(一)博物馆从业人员渴望社会身份认同
19世纪英美两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职业主义随之产生,且带有明显的自我规制特征。职业人士积极创造一个能免受市场和国家侵害的职业领域,强调了在划定专业范围、设定成员资质、限制非成员竞争、制定道德行为规则等方面的专业权威,并以此实现职业身份的社会认同。为此而奋斗的群体中就有博物馆从业人员,在职业主义的语境下他们对认同感的期待实际上是一种更丰富、更复杂的职业诉求。这一时期,博物馆工作的许多推进和改革都被认为是为职业主义“斗争”的副产品,例如将不断提高的成就和行为标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积极挖掘博物馆服务的更大潜能;又如在试图引起公众对博物馆工作价值的关注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博物馆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科学思想影响至博物馆领域
伯顿·J.布莱德斯坦(Burton J.Bledstein)在阐述科学对职业主义的意义时提到:“科学作为专业权威的源泉,超越了政治偏袒、人格堕落和党派排他性,成为一种专业纪律的态度。”[4]科学站在了一个外在、平等和公正的角度,推动不同职业沿着更合理的轨迹发展。19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在大学课堂中提及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当博物馆学与科学的客观性连同起来时,科学方法和标准化实践强化了要将博物馆工作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并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必要职业技能的想法。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刊登了《博物馆的关系与职责》(The Relationship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u⁃seums)、《博物馆的分类》(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useums)两文,强调 curator[5]应当遵循其他专业团体的经验,坚定自身作为博物馆特有职业的存在。此外,他还认为博物馆管理已成为一种职业,应当尽快编纂博物馆管理法规,为其建立崇高的职业标准。
(三)世界级展会促成了博物馆的一轮建设高潮
1851年,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以下将“世界博览会”简称为“世博会”)。英国利用这一契机,在伦敦构建了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大型博物馆网络。其中包括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189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旨在于世博会后继续为公众提供一个无差别对待的公共场所介绍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由此,该博物馆也被视为重要的“教育遗产”[6]。日本博物馆的诞生和发展也与世博会息息相关。1867年,町田久成(Hisanari Machida)等人参加了巴黎世博会,回国后多次向政府提交筹建博物馆的建议。不久,日本政府颁布了《古器旧物保存法》(《古器旧物保存方》),并制订了博物馆建设规划[7]。世博会促进了博物馆场馆建设,强化了其社会教育职能,由此进一步影响了从业人员的需求总量和机构岗位设置。
二、博物馆职业主义早期实践的表现
有学者提出,博物馆职业主义是指在基于问责制和道德的框架内执行专业职责[8]。这一概念显示出博物馆是具有共同目标和挑战的复杂机构,需要公认的行业管理制度和特定的工作标准。戴维·卡尔(David Carr)将职业主义的形成标准归纳为: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有特别的伦理维度,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职业人员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9]。因此,博物馆社会服务意识的产生、专门职业的认同、专业组织的成立、培训课程的构建、对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被视为博物馆职业主义早期实践的重要表现。
(一)博物馆公共服务意识的产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博物馆除收藏、保护等职能外,欧美各国政府也希望利用其文化属性影响个人行为,减少犯罪并增强被传统社会利益排斥在外的个人的自尊心,为创意、休闲等其他产业提供“增值”。作为公共治理的文化工具,博物馆愈发重视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并推动机构工作的改革。一方面,博物馆不再仅仅注重藏品数量的增长,也开始强调藏品征集和利用的效率。1916年,约翰·科顿·达娜(John Cotton Dana)曾呼吁博物馆从业人员应当更具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利用藏品,实现与不同受众共享知识信息。另一方面,博物馆开始从强化社会教育和社区服务入手,探索与公众关系的突破。就社会教育而言,1926年,美国成人教育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成立,博物馆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918年,日本内阁《关于通俗教育的答复》(《通俗教育に関する答申》)中也提到社会教育改革应促进博物馆建设。就社区服务而言,20世纪20年代,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聘用注重社区关系研究却鲜有博物馆学背景的建筑学家菲斯克·金博尔(Fiske Kimball)为馆长,这被视为博物馆转向公众的标志性事件。同一时期,博物馆观众研究兴起。1928年,爱德华·S.罗宾逊(Edward S.Robinson)提出“博物馆疲劳”现象,引发展览说明文字的改革,展览的观赏性随之增强。
综上,关于博物馆职业主义和公共服务的关系:首先,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博物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为公众服务和为藏品服务;其次,职业主义所带来的知识专业度、工作有效性和社会责任感也让博物馆赢得了社区与公众的信任。
(二)博物馆专门职业的认同
1776年,门德斯·达·科斯塔(Mendes da Costa)提出“博物馆学家”(museographists)一词[10],是从博物馆实务角度对专业人员群体的早期描述。至19世纪末,许多博物馆从业人员通过重构社会服务与专业贡献,确立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博物馆职业的产生首先反映在curator岗位上,帕特里克·博伊兰(Patrick Boylan)认为当时的博物馆专业人员主要由所谓的 scholar-curator[11]构成。收藏家们聘用他们来协助作藏品的保护和更广泛的科学工作。1921年,日本博物馆也出现了“学艺官”“学艺官辅”等专职人员[12]。20世纪30年代,维克多·J.达尼洛夫(Victor J.Danilov)概述了亚历山大·G.鲁思文(Alexander G.Ruthven)曾提出的问题:“博物馆员(museum man)是在博物馆工作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商人、教师、编辑、动物标本剥制者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掌握收集、保存、演示以及运用数据的方法。”[13]但这里所提到的“博物馆员”无一是博物馆的特属,因而不足以成为“职业博物馆员”。劳伦斯·维尔·科尔曼(Laurence Vail Coleman)于1939年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当时博物馆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此后,阿尔伯特·E.帕尔(Albert E.Parr)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学界对博物馆专门职业的共识逐渐形成。
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而言,1948年的首次全体大会使用了museographer一词来概括博物馆专业人员,包括收藏家和展览技术人员。1950 年,“修复人员”(restorers)被认可为专门的博物馆职业。1953年,第三次全体大会提出博物馆需要聘用具有公认教学资格的教育专家,并成立博物馆教育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 Education)。1965年,ICOM提出至少有11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是博物馆职业有效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curator、科学实验室人员、艺术品修复人员、保护技术人员等[14]。1978年,ICOM定义了加拿大博物馆界的24种不同的职业类型[15]。显然,博物馆职业类型在不断丰富,自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博物馆职业类型也增加了一倍以上,尤其是在藏品保护、博物馆教育、展览设计、博物馆管理、博物馆营销和财务等领域。
(三)博物馆专业组织的成立
专业组织能够公开承认职业身份,因此自19世纪后期起,人们越来越欣赏专业组织的这种职业价值。博物馆领域最重要的专业组织当属创立于1946年的ICOM,其以建立卓越标准、领导国际论坛、建立专业网络、引领全球智库和执行国际性活动为宗旨,提升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和促进各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但在此之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专业组织就已经出现,它们以共同的目标为前提,帮助博物馆从业人员开展日常工作,实现职业理想。
1889年英国博物馆协会(Museums Associa⁃tion,MA)率先成立,旨在促进博物馆从业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和机构的交流,为博物馆的建立和管理运行提供帮助,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地位。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现更名为“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AAM)成立。其核心目标包括:确定博物馆宗旨和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并根据经验和科学研究为博物馆的日常活动制定专业标准。在上述职责的基础上,英美博物馆协会逐步将职责拓展和细分:规定和监督进入博物馆领域所需的学术培训,提供继续教育计划,发表学术研究,制定和执行行为标准,代表和捍卫成员的政治利益等。专业组织为从业人员提供了从行政管理维度和哲学维度思考博物馆工作实质的平台。
如果说英美博物馆协会的出现是源于基层实践的实际需求,反映了博物馆从业人员与日俱增的职业渴望,那么日本博物馆的专业组织则是自始至终都受到政府的高度控制。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制订了重建公共设施的规划,其中包括推进博物馆建设。1928年,博物馆工作促进会(博物館事業促進会)成立,三年后更名为“日本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日本博协”)。协会主要负责制定博物馆法规,调查应建立的博物馆类型、规模和具体部署,以及促进已建博物馆更好地发展[16]。从职责上可以看出,同英美博协不同,早期日本博协更优先强调自身的政治属性,但并未对从业人员的境况显示出冷漠。1929年的馆长会议就提出教育部应对博物馆从业人员采取积极的培训措施。
(四)博物馆培训课程的构建
职业主义强调专门化的知识和培训,这意味着博物馆专业人员应当接受充分的智能和技能训练,由此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和同样的生产关系[17],形成专业领域的排他性和认同感。在建立正规的大学文凭课程之前,博物馆和行业组织就开始人员培训的探索,如19世纪70年代法国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的博物馆学术和专业实践培训等。1930年,MA在伦敦建立博物馆文凭培训课程,课程面向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内容包括六个月的博物馆实习工作,一系列短期课程和行业导师的专业指导等[18]。二战结束后,专业培训在提升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能力方面的中心作用被日益重视。1971年,第九次ICOM大会正式确立了博物馆培训课程的九个要素:博物馆学导论,包括历史和目的;博物馆的组织、运作与管理;博物馆建筑、空间布局和设备;藏品档案的建立和变更;科学活动与研究;藏品管理;陈列展览;公众;社会教育活动[19]。这一框架不仅引导了行业培训,也为大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设定了标准。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设置以大学为基础的专业培训课程是建立职业身份的一个共同阶段[20]。可以说,博物馆领域的行业培训和全日制大学课程几乎同步发展,只是后者的大发展时期略晚于前者。1917年,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wa)制订了美国第一个博物馆学士学位培养计划,提供了以博物馆学为中心的跨学科课程,该课程主要针对自然历史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的部分大学也开设了博物馆学位课程。1966年,在英国大学扩张的全盛时期,博物馆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被引入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课程为期一年,内容涉及五个领域:博物馆史和当代背景、材料和文化、藏品管理、博物馆经营以及博物馆服务。1971年,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艺术史系也设立了“美术馆与博物馆学”课程。
(五)对博物馆伦理道德的关注
史蒂文·布林特(Steven Brint)有言:“职业主义承诺,面对需要应用大量复杂知识的技术性工作,要有称职的表现。……从道德层面而言,要在充分理解其所服务的重要社会目的的基础上,展开响应行动。”[21]为了实现技术层面和规范层面的正当性,专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其成员以最佳方式解决其领域内的问题。最终目的之一便是当成员在面对有争议的私人物品和集体物品问题时,能作出恰当的选择[22]。因此,职业道德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原则体系,融合了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社会教化过程。
20世纪初,博物馆就开始了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关注,如英国博物馆界认为专业人员对博物馆特定的标准和一致的道德行为的了解至关重要。1925年,AAM发布了全球范围内首个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博物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 Workers,以下简称“《准则》”)。《准则》将博物馆的社会意义定位为为了人类和人类未来的福祉而托付财产的机构,博物馆的价值与其赋予公众情感和知识生活的服务成正比。因此,博物馆工作的本质是一种服务,从业人员的行为基于三重伦理:献身于事业,相信同业们的无私,基于高度正义的荣誉感是其思想和行为的源动力[23]。
但这一版《准则》中并没有明确出现“专业”或“职业”一词,而是从公共关系、机构关系、理事会关系、馆长—职员关系等维度阐述了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责和行为规范。1978年的修订版《准则》中才有了“职业”的相关描述。在这半个多世纪内,博物馆成功吸引了多元观众群体,艺术品市场飞速发展,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得到了更充分的重视,创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因此,1978年版《准则》更强调从社会服务特性看待博物馆工作。
20世纪70年代前,除美国之外,ICOM也针对博物馆职业道德开展了积极的研究。1968年,ICOM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制定《关于征集的道德准则》的必要性,后于1970年正式发布,旨在指导博物馆避免收藏被盗或非法出境的文物。自此,国际博物馆学界把博物馆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课题加以研究[24]。
三、对早期博物馆职业主义的反思
职业主义的产生让专业人士免受伴随19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结构化的、严苛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的伤害。职业主义关乎个人选择,也关乎保护或拓展个人选择的群体行为。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将1900—1979年间职业主义的发展描述为“职业人士的胜利”。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职业主义所导致的个人傲慢、集体屈服、不同职业之间的相互排斥越来越明显,其核心问题在于未能解决“专业性与社会整体性之间的冲突”[25]。
就个人而言,职业人士在陈述其与社会的关系时无法达成一致。即使仅在文化方面,更不用说在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方面,博物馆专业人员仍未能确定自己的角色,由此降低而非增显服务对象的丰富性。这导致新进人员无法企及专业工作,依赖向已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职业人士寻求专业知识,但他们又想与职业人士的传统工作范式和知识架构保持距离。同时,大量新进人员的到来也让职业人士对构成专业地位的因素产生了困惑。用珀金的话来说,职业人士原本试图通过用难以理解的语言使他们的专业知识神秘化并疏远大众,以此为自己创造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即“被大市场忽视的细分市场”)[26]。但这样的利基市场却让博物馆专业人员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两个群体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安的关系,归根结底是无法消除进入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核心的不平等现象,致使社会流动性快速下降。许多职业人士拥护“中立”,这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博物馆早已嵌入社会,不可避免地也陷入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之中。
就组织机构而言,职业社会中的机构渴望一种“传统的”身份,即在社会结构中保持简单、既定的角色,统一所有复杂的功能,并提供不可辩驳的专业权威。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显然无法延续,博物馆在当时就已经拓展出文化治理、社会教育、社区服务等职能,早期职业主义的坚持将导致机构功能的碎片化,使得博物馆的职业认同变得更为复杂。此外,职业主义如若推动博物馆协会成为地方权威的“俱乐部”,那么将严重削弱其作为专业组织的能力及代表博物馆的发言权。职业主义建立的文化警戒线,虽可保护现状,但却隔绝了创造力。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MA就从之前主要关注curator的职业资格转向了向所有在博物馆内或为博物馆工作的人员开放,包括志愿者。
尽管早期的职业主义有许多弊端,但其带来的职业精神却在此后的博物馆实践中得以留存和发扬,并改变了博物馆的性质。其一,对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培养获得了持久关注。如今,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馆长以及在博物馆从事教育、传播、藏品管理的从业人员都完成了大学的相关课程。这意味着专业人员在博物馆内承担了大量重要工作。其二,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文化传播不断探索出新理念和新方法,以实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如curator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强调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并在更加拥挤的休闲和旅游市场中强化博物馆的竞争力;如今在各博物馆,对建立科学系统的藏品和档案管理制度的倡议已经司空见惯。其三,专业组织扮演着推进、协调、监督等角色,逐步提高了机构“可达到的专业标准”。职业主义建立和维持了各种强大的国家级和地方性专业组织,可以直接解决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专业问题。其四,社会职能的多样性也为博物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博物馆越来越重视游客服务与馆藏服务之间的双向互动,这种平衡兼顾了历史和现代的专业目标。职业主义留存的对专业性的追求,帮助从业人员认识到博物馆的每项职能都对专业所能营造的福祉作出了贡献,让他们的工作有了必要的意义。
正因为有了原有制度的基础及对这一制度的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职业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除职业结构性研究之外,强化了职业自主性、职业与外部主体关系和公共领域内的集体行为等方面的研究[27],职业主义的侧重点由职业抑制性规制转变为职业开放性引导。加之新博物馆学对博物馆变革产生的深远影响,博物馆突破了原有的职能局限,强调专业人员要适应工作结构的变化,具备广博的职业知识、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更强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各国纷纷实施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培训计划,帮助博物馆专业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提升自我学习能力。
在早期的博物馆职业主义的探索中,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参与者,尽管中国高校的博物馆教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但真正起步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第一部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也于1981年颁布,次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博协”)才正式成立。但职业主义从产生、发展到被质疑、改革的轨迹,却为当下中国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化建设提供了理性依据。
其一,社会服务是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早期职业主义推崇的价值观是让特定的职业通过职业化过程实现更大的社会服务效能,对当代博物馆而言也是如此。反映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上,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作为休闲文化和社会教育设施,展现塑造价值认同的强大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博物馆的观众管理;致力于提供更丰富的个性化和参与性体验;寻求广泛的机构合作,提升展览交流、公共项目、内容评估的质量;储备和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挖掘所服务机构的更大潜能。
其二,制定职业标准以指导从业人员有序开展专业工作。目前我国《国家职业标准》中与博物馆相关的职业有“陈列展览设计员”“展览讲解员”等,《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的相关职业为九类,这与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的现状相比,都还显得十分有限。国家层面的职业标准将是博物馆行业进行职业能力培训和评价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职业标准可分为“准入型”标准和“水平型”标准。“准入型”标准旨在确保刚进入博物馆领域工作的人员已接受了必要的、基础的专业培训。“水平型”标准旨在引导专业人员获得更有效的职业发展路径。但从早期职业主义实践的困境中可发现,职业标准不应作为博物馆专业人员为自身框定的权威领域,而应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开放和包容的特点。具体体现在:标准应当是短期固定和长期变化的,对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博物馆发展趋势及社会担当有所反映;标准应当服务于广泛的博物馆从业人员及有意愿进入博物馆工作的群体,尤其是帮助新进人员尽快地适应博物馆工作;标准的评价方式应当是多元的,2019年12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文物博物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就强调对人员的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
其三,强调博物馆专业教育与培训,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多职业发展机会。职业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实质上围绕构建更先进的职业文明而展开,职业文明的作用是更关注日常工作中的人、场所和内容,以保护和提高生产力。这就要求博物馆对从业人员进行大量的培训,积累实践经验,建立职业自主权和对工作的自豪感。在专业培训方面,目前,从国家文物局至地方文物主管部门、文博行业组织、博物馆,都在开展各类专业培训,并且积极开拓在线课程资源,以惠及更多的博物馆从业人员。为了进一步提升培训效益,还应当做好加强职业培训需求的调研、增加授课人员的专业多样性、建立专门的职业培训组织等工作。在专业教育方面,我国文博相关学科已建立起从本科生至博士研究生完整的培养体系,同时,实践性质更强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实践教育的课程体系、授课方式、教材师资、职教衔接等方面仍有待完善。此外,在完成了专业教育与专业培训后,还应当对学生和受训者在博物馆职业领域的持续性社会服务能力进行跟踪辅导。
其四,博物馆专业组织应发挥更大的行业引导作用。在早期博物馆职业主义的实践中,各类博物馆协会就在谨慎地避免自身成为垄断性权威,并尝试启发博物馆从业人员成为博物馆创意发展的推动者,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而这依然是当下博物馆专业组织的核心职责。作为我国博物馆行业最权威的行业组织,中国博协是相关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社会团体法人,不具备行政管理权力,其主要职能是辅助与促进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在机构性质上,中国博协既不像英美博物馆协会那样,作为民间的行业组织对行业发展有较强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也与日本博协强烈的政治角色所不同,其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协调政府、行业和公众的关系上,中国博协应当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咨询、服务和协助作用,并在部分领域进行主导。例如成立人员培训专业委员会,专门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相关工作,包括协助国家文物局制定相关政策、统筹全国资源、建立机构和专家数据库、组织相关活动、引导地方文物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搭建沟通交流平台等。同时,在根据博物馆职业标准评价从业人员职业能力时,能够在明确博物馆职业类型划分、建立职业素养框架、辅助实施多元评价方式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