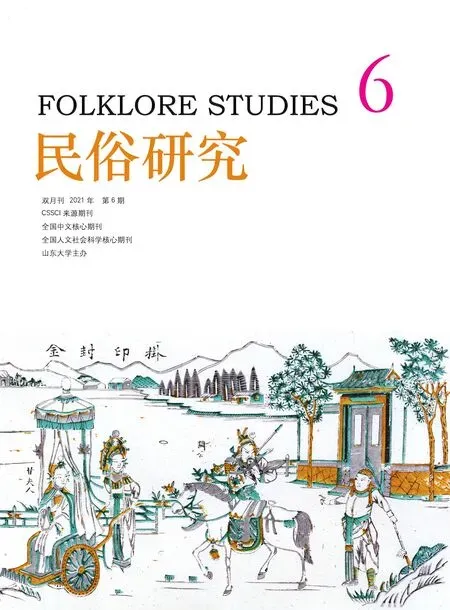运河社会变迁与扬州杖头木偶戏的艺术重构
路 璐 吕金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社会性”传统是连接“大历史”与“小历史”的桥梁,是理解中国社会这一超复杂系统的重要载体,集中表现为国家行政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事实上,两者并非完全对立,中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治“地方化”与地方社会“国家化”的有机融通。因此,过分强调国家力量的下移或者地方传统的固守,都容易造成对中国的“社会性”传统的认识偏差。张士闪以中国历史上的“礼”“俗”关系为切入点,提出“礼俗互动”的分析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借助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实现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贯通,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使文化认同成为调适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1)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这一理论意在揭示国家政治设计与地方社会运行之间的互动,是“社会性”传统研究的新维度。受其启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观察中国社会之视角的不足,力图实现两种视角的贯通,以便更好地理解在中国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介入地方”与“地方融入国家”两种趋向的交织状态。
扬州杖头木偶戏作为中国当代木偶戏的三大代表性艺术类型之一,与运河城市扬州的兴衰关系至密。在这一艺术传统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行政、地方社会两种力量的形塑作用尤为明显。比如,清代定都北京,被誉为“天庾正供”的漕粮需经运河由南方转运北方,此举促进了运河城市扬州的繁荣,为扬州杖头木偶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可以说,考察杖头木偶戏与运河城市扬州的关系,为透视中国的“社会性”传统提供了一个窗口。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扬州杖头木偶戏的研究聚焦于梳理历史脉络(2)参见陈年生、封保义、焦锋、郑平:《傀儡演真情——扬州木偶艺术》,广陵书社,2009年;常骥良:《扬州木偶戏的探索》,《艺术百家》1994年第2期;封保义:《扬州木偶艺术发展的三次飞跃》,《艺术百家》1994年第2期;唐悦:《扬州杖头木偶戏源流考述》,《齐鲁艺苑》2016年第1期。、总结木偶造型特点(3)参见王贵洲:《扬州木偶戏中木偶造型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方向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崔茜:《扬州木偶服饰的研究》,西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钱钰华:《扬州和闽南地区木偶造型艺术的异同分析》,《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分析舞台美术特征(4)奚社艳:《演绎古老神话,焕发新活力——评扬州木偶〈嫦娥奔月〉》,《大众文艺》2018年第17期。等方面,尚未能从运河城市扬州的兴衰与杖头木偶戏的传承这种“社会—艺术”关系视角进行深入剖析。
探讨杖头木偶戏与运河城市扬州的关系,需要关注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制度变迁、中观层面的运河城市扬州兴衰、微观层面的杖头木偶戏嬗变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少学者倾向于关注宏观层面与中观层面的互动,聚焦于国家漕运事务与运河区域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马俊亚分析了清代以来漕运的维持对淮北社会走向衰败的负面影响(5)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吴琦总结了漕运对运河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及其经济结构脆弱性特征的双向作用(6)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孙竞昊讨论了中央政府政治一体化整合的初衷与运河沿线不同区域发展的差异。(7)孙竞昊、毕鲁瑶:《差异性与一体化:帝国与区域视野中的中国大运河及其历史遗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上述研究对于我们思考运河城市扬州这一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极具启发。而将杖头木偶戏嬗变这一微观层面纳入考察范围后,运河的“社会性”成为连接三者的纽带。所谓运河的“社会性”,是指受到运河影响的区域的“社会性”,主要包括区域民众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与生活活动等。(8)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扬州杖头木偶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其在流转变迁的过程中与运河城市扬州休戚与共,运河的“社会性”特征尤为明显。基于此,本文将杖头木偶戏置于以扬州为中心的运河区域社会中进行审视,探讨杖头木偶戏与扬州所承载的运河文化空间的有机联系,揭示国家行政、地方社会与艺术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社会变迁中的扬州杖头木偶戏
木偶又称傀儡、窟儡、魁儡等。扬州是木偶戏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时扬州民间就开始流行木偶戏。(9)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中华书局,1988年,第3730页。明末至清代中期,扬州城内木偶戏风行,种类繁多,杖头木偶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等众彩纷呈,前者逐渐成长为主要种类。(10)曹永森主编:《扬州特色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395页。清末民国时期,杖头木偶戏的生存空间由扬州转移到泰兴、泰州、靖江、如皋、扬中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杖头木偶戏又回到扬州这一孕育它的文化空间之中继续发展。时至今日,扬州杖头木偶戏依然生机勃勃,与泉州提线木偶戏、漳州布袋木偶戏合称中国当代木偶戏的三大代表。纵观扬州杖头木偶戏的演变历程,其与运河城市扬州这一文化空间的变化息息相关。
(一)因河而兴:运河城市扬州的兴衰与杖头木偶戏
杖头木偶戏深受运河城市扬州这一极具历史景深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滋养。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修筑邗城,据《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11)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62页。,邗城遗址即位于今扬州一带。因邗沟水运交通频繁,扬州经济社会得以不断发展。运河的开凿不仅对扬州城市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也为扬州木偶戏创造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地位下降,扬州一跃而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富甲天下”(1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4715页。,时谚称“扬一益二”。经济繁荣为扬州地区的文化繁荣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唐代初期扬州人口增长迅速,从贞观十三年(639)的23199户、94347口增长到天宝元年(742)的77105户、467857口。(13)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第115、127页。大量的人口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提供了潜在的观众群体。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木偶戏在扬州民间社会逐渐流行起来。据中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曾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杜佑与友人言及致仕以后有“入市看盘铃傀儡”之愿,所谓“入市”即指进入市井之意,说明此时扬州的木偶戏即已流行于民间,而标之以“盘铃傀儡”则意味着木偶戏远不止“盘铃”一种。
唐末,扬州屡遭兵燹。据《旧唐书·秦彦传》记载,光启三年(887)寿州刺史杨行密围困扬州半年,“城中刍粮并尽,草根木实、市肆药物、皮囊革带,食之亦尽”,此后数年,淮南节度使孙儒与杨行密又多次战于扬州,以致“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北宋司马光《送杨秘丞通判扬州》有“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的诗句,字里行间已然失去了如唐代诗人一般的赞赏之语。南宋时,南北对峙,扬州从内地转变为边郡,元代漕运又改以海运为主,运河原有的沟通南北的功能大为削弱。在此背景下,扬州的经济地位已不及唐末以前的水平,城内文化消费活动低迷,此时的文献中未见有关木偶戏的记载。相反,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南方经济最富庶的城市,民众的文化消费活动频繁,观看木偶戏即为其中之一。吴自牧《梦粱录》称临安“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14)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嘉庆十年学津讨原本,第279页。,表演形式多样。可见,运河城市扬州的盛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扬州木偶戏在民间的发展状况。
明末至清代中期,随着中央王朝对漕运的依赖程度加深,运河城市扬州的经济臻于鼎盛,“天下殷富,莫踰于江浙,江省繁丽,莫盛于苏扬”(15)黄钧宰:《黄钧宰集》,王广超点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整个扬州城的文化环境日渐竞尚奢丽,史载扬州盐商喜好昆曲,“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燦”(16)黄钧宰:《黄钧宰集》,王广超点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在如此繁荣的文化消费环境中,木偶戏在扬州非常盛行,成为当地民间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曾被清末诗人黄鼎铭《望江南百调》称赞为“扬州好”的典型意象。按照表演方式划分,主要包括杖头木偶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等艺术类型。其一,杖头木偶戏。乾隆年间戏曲家李斗《扬州画舫录》有云:“(韩园)闲时开设酒肆,常演傀儡子,高二尺,有臀无足,底平,下安卯榫,用竹板承之,设方水池……隔以纱障,运机之人在障内游移转动。”其二,提线木偶戏。乾隆年间文学家郑板桥《咏傀儡》戏称:“笑尔胸中无一物,本来朽木制为身。衣冠也学诗文辈,面貌能惊市井人。得意哪知当局丑,旁观莫认戏场真。纵教四肢能灵动,不借提撕不屈伸。”其三,布袋木偶戏。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艺人)围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运三寸傀儡,金鼓喧嗔,词白则用叫嗓子,均一人为之,谓之肩担戏。”随后,杖头木偶戏日益成为民众观戏的主流形式之一。总的来看,清代中期以前,扬州木偶戏的成长历程与运河城市扬州的盛衰过程基本一致,运河兴则扬州兴,扬州兴则扬州木偶戏兴。
(二)沿河而迁:城与乡之间的文化适应
清代中期以来,扬州杖头木偶戏遭遇了三重发展危机。其一,文化市场竞争。扬州作为运河城市,除百戏云集外,评话、书法、绘画、古玩、歌舞、赏花、游园等艺术形式多样,文化消费竞争激烈。特别是乾隆年间徽班齐聚扬州,群歌齐舞、色艺兼优、屡次名动京师的徽剧迅速占领演出的中高端市场,杖头木偶戏表演在市区逐渐衰微,演出空间逐渐下沉至城郊、乡镇及农村。清道光年间文人韩日华《扬州画舫词》有“竹棚一带绿荫中,百货开场傀儡工”之句,民国文学家易君左《闲话扬州》则有:“扬州还有一种傀儡戏……在一块荒坪里围一个布棚”之语,都是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因为城市空间狭小,“绿荫”“荒坪”一般较少。其二,政府政策严控。嘉庆三年(1798),清廷发布禁演昆腔、弋腔以外戏曲的诏谕。如立于苏州梨园公所内的《翼宿神祠碑记》有云:“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17)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95-296页。受此影响,当时扬州杖头木偶戏的发展空间同样处于被压缩的状态。其三,社会环境变迁。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张秋(在今山东阳谷)至临清的运河水量骤减,难以通航,十数年后漕粮海运兴起,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渐遭废弃。(18)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9-340页。对运河城市扬州而言,漕运的停摆导致围绕着漕运而展开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项活动骤然消失,扬州由盛转衰。正如彭慕兰所言,国家治理资源的持续撤出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减少对运河城市的打击是致命的。(19)[美]彭慕兰:《腹地的建构: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民国时期,虽有一些有识之士或地方乡绅提出治运构想,力图修复大运河,但终因国弱民穷、内部倾轧不已等原因而告终,致使繁华千年的运河城市扬州在急剧的时代转折中一落千丈。
运河虽然衰微,但运河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依然沉淀于具体的民俗事象中,扬州杖头木偶戏即是个中翘楚。此后杖头木偶戏被迫离开城市,就开始向传统农耕内陆乡村寻找新的栖身之地,沿着通扬运河来到三泰地区。旧通扬运河始建于西汉文景年间,其前身为吴王刘濞开凿的一条西起扬州茱萸湾(在今湾头镇)、东通海陵仓(在今泰州)及如皋蟠溪的运河,目的是在其封域内“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2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825页。。泰州与扬州由运河沟通,血脉相连,它们共享着大致相似的区域文化。因此,杖头木偶戏离开扬州后,开始在高邮、兴化、宝应、泰州、泰兴等地崭露头角,显示出惊人的文化适应能力。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地域选择比较恰当。杖头木偶体型较大,表演时需要空旷的场域,三泰地区河港较少,陆上交通畅通,适合表演。(21)陈年生、封保义、焦锋、郑平:《傀儡演真情——扬州木偶艺术》,广陵书社,2009年,第3页。表演杖头木偶戏时往往因地制宜,或在村头的空地搭台,或在打麦场上搭台,或在乡村集市的绿树丛中搭台,遇到雨雪天甚至还可以在农庄的堂屋里搭台。其次,在文化内容上主动迎合乡民的审美需求。在扬州城内,杖头木偶戏极尽精美奢丽,转向乡村之后即主动适应新的受众群体需要,满足乡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从内容到形式都迅速地实现了“在地化”,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的依赖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它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此时杖头木偶戏多以唱神戏为主,表演歌舞、鬼神故事,这些神戏承载着乡民的生命意识、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识,缔结着杜赞奇所言“权力的文化网络”(22)[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中的文化象征符号。乡村传统的民俗节庆为木偶戏班提供了生存机会,庞大的乡村演出需求催生了大量杖头木偶戏班的诞生,如清末刘家木偶戏班、民国苏家木偶戏班,这些戏班亦农亦艺,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搭班演艺,穿梭于市镇之间。
(三)回归家园:“礼”与“俗”的互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运河建设专委会随之成立,江苏大运河全面复兴,河道得以疏浚、维护与拓宽,航运得以恢复与发展,苏北运河升级为二级航道,货运日渐繁荣,有效地促进了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江苏运河中的新通扬运河几乎平行于旧通扬运河,于20世纪50年代开工,西起江都区芒稻河,经江都、海陵、姜堰至南通市海安与通榆运河相接。运河网络的复兴有效刺激了杖头木偶戏的当代回归。与此同时,国家政策的出台也是杖头木偶戏获得新生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出台“五·五指示”,支持各地“采取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的方式,建立地方示范性的剧团、剧院……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据点”(2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扬州杖头木偶戏艺人敏锐地把握时机,散布于泰兴、泰县两地的民间木偶戏班开始从乡村向县城转移,组建新剧团,整个过程中木偶艺人对剧团整合投入了巨大的热情。(24)访谈对象:戴荣华,扬州木偶团团长;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扬州戏曲园。1959年,一批民营剧团改制合并为泰兴县木偶京剧团一团、二团和三团,公立的木偶剧团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1968年,泰兴县木偶京剧团一团与二团经过二次整合组建了泰兴县木偶京剧团。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大家都觉得机会到了,都特别团结,不管是马家班,王家班,李家班,大家都心在一处,劲往一处使。”(25)“那是对扬州木偶戏重新回到城市语境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机,是一段艰苦与团结的岁月。”访谈对象:颜育,省级非遗传承人;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扬州市京杭之心。1973年,剧团上调至扬州,经历地市合并后,于1982年更名为扬州市木偶剧团。
从民间“家班”到民营剧团再到拥有行政编制,围绕“国家制度”而建构的“文化文本”(26)张士闪认为在乡村社会语境中,“国家制度”经常被视作一种可供谈论、交流、改装或化用的“文化文本”。参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正是借助扬州杖头木偶戏这种民俗艺术形式不断地渗透到地方社会之中,这种“地方化”过程也在不断改变着扬州杖头木偶戏的生存空间。作为一种“俗”的存在,扬州杖头木偶戏取材于民、服务于民,是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惯习,也是民众情感、意志的投射;从“礼”的一面来看,扬州杖头木偶戏在努力阐释地方民众自身生活的同时,也在努力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木偶艺人在创作和表演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国家意识形态融入其中,早期是在木偶戏正式表演前加“帽子”,先唱一小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福利与政策,紧跟主流意识形态,为此改编或创作了反映革命文艺的《智取威虎山》《海防前哨》《杨根思》等剧目。当下,扬州杖头木偶戏贴近国家政治话语的方式则是努力抓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契机。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扬州与大运河水乳交融,扬州杖头木偶戏也努力凸显其“运河”特色,近期剧团排演的代表性剧目的情节、场景都与运河血肉相连。在展演空间方面,扬州杖头木偶剧团配合大运河的各种节庆活动进行表演,如2019年运河文化嘉年华在扬州举行,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每天上演不少于3场8部的木偶剧。同时,凭借扬州国际运河城市联盟成员的身份,扬州木偶剧团频繁出国演出,进行国际传播,逐渐成为扬州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总之,此时由国家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指令,可以视作国家向民众提供的认同符号与归属路径。(27)张士闪:《眼光向下: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的考察》,《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扬州杖头木偶戏在努力表达地方民众自身生活的同时,也在努力向国家寻求文化认同,在这种相互吸纳、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动框架。正是在这种互动框架中,扬州杖头木偶戏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新的文化符号,甚至在新的语境中衍生出新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形塑出一种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标识。与此同时,在大运河这一文化空间中发展起来的扬州杖头木偶戏,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为当前构建命运共同体、呈现国家形象提供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28)路璐、丁少康:《大运河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三、扬州杖头木偶戏的艺术重构
扬州杖头木偶戏自其形成起,其物质形态和内在意义便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历经千年变迁,扬州杖头木偶戏依然生机盎然,其发展离不开该地域内自然环境、社会结构、风俗民情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依存,更离不开扬州杖头木偶戏自身深厚的艺术重构力。
(一)叙事与空间展演形式的重构
扬州杖头木偶戏叙事与空间展演形式的重构受到两重因素的影响,一是运河的“社会性”。运河城市与扬州杖头木偶戏这一艺术个体息息相关,正如扬州木偶剧团团长戴荣华所言,“咱们这个木偶戏,可能有那么点不同,它是运河边上的艺术”(29)访谈对象:戴荣华,扬州木偶剧团团长;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8日;访谈地点:扬州戏曲园。。一旦运河这个文化空间母体发生变化,扬州杖头木偶戏也会随之出现改变。二是积极与当下对话,与当下主体对话,与其他艺术形式对话,与世界木偶戏新理念对话。扬州杖头木偶戏剧团年轻演员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强调说,剧团“不排斥新理念”,“去国外表演的同时也是不断去学,有新的东西放进来,剧团不排斥”。(30)访谈对象:赵静宇,扬州木偶剧青年演员;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京杭会议中心。扬州杖头木偶戏不断融入学习国际木偶表演中最新的叙事理念与空间展演形式,这是它比较突出的特质。
上述两重因素时常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叙事与空间的重构,它并不是刻意地讨好当下,而是“用过去的古旧元素与信息建构新兴释义与主权的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31)Anne Eriksen,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Invented Tradition and Devotional Succes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42, no.3(Sep.-Dec.2005), pp.295-321.。比如,《荡寇少年》以运河边上抗日儿童剧为类型,有将传统运河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甚至科普文化等一揽子承接的雄心。又如,《琼花仙子》以扬州民间传说为母本,加入科幻类型元素,将广泛流传于扬州大运河景观中最常见的热点元素琼花拟人化,并进一步塑造为银河中外星人与传说中仙女融合而成的主人公。剧中主要人物的活动空间在人间扬州和天上银河两地交叉开展,时而是星汉璀璨的太空境地,时而是实实在在的瘦西湖、五亭桥之境,有效地联接着当下文化语境中受众的时空感以及个体与世界的想象。再如,扬州杖头木偶戏的获奖常青树——《嫦娥奔月》精品剧目,其不同版本的叙事重构几乎与历史中主流话语变迁同步,1980年版的木偶剧《嫦娥奔月》整部剧处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突出的是嫦娥的抗争意识,可以说是民众对恢复常态化生活的渴望在故事语境中的想象性复现,符合当时拨乱反正的时代语境,在美学上又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有互通款曲的话语勾连。2016年,《嫦娥奔月》再次改编,其叙事创新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包容性理解,注重对民间话语的吸纳。对历史上《嫦娥奔月》这一剧目各种话语的沉淀与指涉,类似于杜赞奇描述关帝信仰变迁中的“复刻”(superscription),即“多种阐释元素相互作用、协商,重构阐释领域。而复刻的话语力量则来自这些历史的积淀”(32)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2页。。此外,新版《嫦娥奔月》吸收了民俗传说中关于嫦娥江南水乡普通女孩身份的设定,已不再是1980年版中直线性的人物塑造,而勾勒出了嫦娥从水乡女孩到女英雄再到神仙的人物成长曲线,充满着女性主义的视角。
对于展演空间,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民间艺术界,曾普遍流传着一句民间俗语“水路即戏路”,大运河江苏段水网连缀,多重区域文化、多重艺术形式在运河烟波空间里交锋、交融。在历史上,扬州杖头木偶戏既吸收了花香火、秧歌、杂耍、龙灯、麒麟、荡湖船等民间歌舞元素,也汲取了昆曲、徽调、京剧等精品戏曲养料,甚至还有一些民歌清曲、田间号子等乡村艺术元素。当下,扬州杖头木偶戏艺人基于对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体认,以偶性(33)偶性是指表演活动中以真实的木偶为本体,而非以人扮演的人偶为本体。有人指出:“人偶剧不是纯粹的木偶戏,或者可以说根本不是木偶戏,传统木偶戏的本体艺术是操纵,它这个杖头木偶必须有杖头木偶的东西才行。”访谈对象:焦锋,原扬州木偶剧团团长;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20年9月2日;访谈地点:焦锋家中。为基础,在强大的叙事完整性的支撑下积极并连贯地使用各种艺术形式。在它的舞台空间,既有传统的审美文化空间,温婉熟悉的江南水乡环境、人偶合一、神韵必备的戏曲水袖舞元素,也包括现代审美空间,皮影、木偶、真人演员的表演统合在多景区的空间调度,类似于电影中的景深叙事,即不同主体在立体时空里多层次动作同时存在并复合运行,这些剧中人物或神怪之间那种微妙、富有张力的潜关系通过深度空间的场面调度传达出来。当扬州木偶戏将纱幕投影、非遗木偶戏、新媒体承载的全息投影特效在并行使用时,就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在以偶性为主、又有多种艺术形式从容配合中可以进行充沛的人物塑造、制造剧烈的戏剧冲突,呈一气呵成、愈进愈深之势;另一方面,人偶同台、真人叙事、现代科技营造的意境氛围又带来一种陌生、间离感,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木偶舞台的束缚,对舞台空间处理的新思维、新观念丰富了木偶戏的表演张力。
(二)主体培养的当代重构
费斯克认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不仅是主体自身形成的,更是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的”(34)[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8-53页。。文化主体是最重要的,扬州仗头木偶戏的传承核心也在于人,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民俗传承人的培养对杖头木偶戏的生存与发展尤其重要。引人深思的是,在对扬州杖头木偶剧团的实地调研中,无论是资深传承人,还是青年演员都表示“让木偶戏活下去首先是木偶表演者自己的事情”。扬州杖头木偶戏的传承也经历了从血缘传承、地缘传承到职业化的业缘传承的转变历程。
早期的扬州杖头木偶戏采用“家班”传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扬泰地区的木偶戏兴盛,泰兴县的农村几乎每家都会表演木偶戏。据解放前的统计,“泰兴县43个乡,有29个乡117家的木偶戏班”(35)常骥良:《扬州木偶戏的探索》,《艺术百家》1994年第2期。,这一时期的木偶戏班“都是家庭班子,就是父亲、母亲、儿子、媳妇、外孙等家庭式的,父亲当班主……特点是半农半艺,农忙的时候是农民,农闲了就出去唱戏挣钱,它不是专业的”(36)访谈对象:焦锋,原扬州木偶剧团团长;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20年9月2日;访谈地点:焦锋家中。。这种依靠血缘关系建立的家族式戏班,人数多少不一,一个班子一般七八个人,其中二人充“文武场”,即一人敲锣,一人操琴,其余的人则参与木偶的操作表演和配音,演出的剧目大多是幕表制,没有固定的台词,但大段唱词是固定的,每个演员都需要熟记二三十出常见剧目的固定唱词,音乐、造型、妆台、幕布、头饰都由家庭成员自己制作。受限于当时演员的文化水平,这种家庭班子的传承方式多为边学边演、边演边学,口传心授,“过去是班主带徒弟,一个班,都是自己家人,老子教儿子,儿子教孙子或外孙,口传心授,过去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叫口传心授”(37)访谈对象:焦锋,原扬州木偶剧团团长;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20年9月2日;访谈地点:焦锋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形势及木偶艺术本身的不断发展,家族式戏班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批民间戏班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小型的民营木偶剧团开始出现。此时的剧团依然是以家族传承为主,也逐渐出现了家族外成员加盟的“师徒制”传承方式。随着政府部门对木偶艺术的日益重视以及社会经济大环境的需要,公立木偶剧团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组织形式的变化,整合后木偶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剧团开始对外招生(38)为发展杖头木偶戏,培养人才,泰兴县木偶京剧团一团、二团联合于1962年、1965年分两批次,招生21名学员;一团二团合并后的泰兴县木偶京剧团于1970年、1972年两次招生32名学员。这四批学员,大部分留在了剧团工作,其中一部分成为剧团艺术骨干和全国木偶界的佼佼者,对扬州杖头木偶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学员经过短期的艺术培训后,剧团安排老艺人为师,手把手教授新学员,师徒传承成为主要的传承方式,这一时期开始由血缘传承向地缘传承转变。
现在的培养方式则是对传承人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培养与传统的师徒相传心法两相结合。扬州艺校、扬州木偶研究所、江苏省木偶剧团三者联动,努力探索文化主体培养的联合机制。2016年,扬州艺校开设木偶班,培养经过三年系统教育的科班生,木偶班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其一是基础文化课,学习世界文化艺术品类与当下受众审美趋势,旨在提升文化主体的综合素养,其后是定位到点——对扬州木偶戏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风格、流派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在《荡寇少年》的演出现场,出乎笔者意料的是,年轻表演者对杖头木偶戏的特色如数家珍,他们说:“木偶戏是一种综合性表演艺术,它把戏曲、舞蹈、话剧都结合在一起。你让一个戏曲演员来演话剧他不一定演得好,你让一个话剧演员去唱戏也不一定能唱得好,但是我们木偶演员不一样,木偶戏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木偶戏演员是一个全能的演员。现在音乐剧、戏曲、舞蹈这些元素木偶戏都有,特别多,都与木偶戏融合在一起了。”(39)访谈对象:赵静宇,扬州木偶剧青年演员;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京杭会议中心。其二是专业课教学,扬州杖头木偶戏省级非遗传承人颜育认为,木偶艺术与人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偶合一”,“真人会的才会传达给木偶”,(40)访谈对象:颜育,省级非遗传承人;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扬州市京杭之心。因此木偶操作技能的培养尤为重要,从举功、练功操等基础延伸到形体课、声乐课、舞蹈课,学员每天的基本功都雷打不动的坚持。(41)“早起,吃个早饭到单位每天都要静举,一般这个静举正常人举不下来,但是我们一举最起码得半个小时,有时一个小时我们都举过。这些事是我们这些刚进团不久的同伴每天的日常生活,除了每天早起练习‘举功’,舞蹈排练、拉伸也必不可少。”访谈对象:赵静宇,扬州木偶剧青年演员;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7日;访谈地点:京杭会议中心。其三是剧团师徒培养,学员经过学校学习后,通过考核进入剧团,剧团指定优秀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亲身示范、现场教学即通过师带徒这一传统的方式来加强训练。戴荣华团长认为:“年轻毕业生进来之后不能直接上台表演,都需要专业的演员以师徒传承的方法慢慢指导他们。如演员在舞台上怎么站,站的位置,舞台调度,站在什么位置做什么动作,如何刻画人物,这个人物在舞台剧里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刚出学校的新演员都没经验,需要我们来教,慢慢地培养。”(42)访谈对象:戴荣华,扬州木偶剧团团长;访谈人:袁红艳;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8日;访谈地点:扬州戏曲园。
学界很早就对文化传承的主体予以关注,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化传承主体的才能、个性、世界观等往往被贴上了“集体性”标签而变得模糊。杨利慧认为,表演理论扭转了这一趋势,民众的日常实践被总体地纳入了民俗学的视野后,“民”不再是抽象化的、被动的传统接受者,而是有血有肉的丰富的生活实践中的人。个人的风格、个性、经验、际遇等都被考虑了进来,民俗学真正触摸到了有质感的个人层面。(43)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正如彭牧所说,民俗学以前关心的是事象,现在才是事象背后的人。(44)彭牧:《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因此,今后的扬州仗头木偶戏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其所有从业人员的个人生活史,聚焦当今专业学校、剧团联合的科班培养与传统以师带徒方式的传承模式,以此获得对于这一珍贵艺术传统的深刻认知。
四、结 语
扬州杖头木偶戏,与运河城市扬州的文化空间变迁息息相关,交织着重重叠叠的历史文化记忆,并由此不断发生着艺术重构与文化衍生。在研究这一民俗个案时,需联系与其息息相关的区域文化以及血肉相连的文化环境,意识到它是与周边环境、运河母体之间进行着交流的开放系统,是不同文化空间交融与交汇而成的连续性统一体。
从宏观上看,2018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国家策略,大运河文化带包括隋唐、京杭、浙东运河三部分,“丰厚的历史馈赠也转为巨型的空间布局,从当下空间体量看,大运河也是巨型文化网络空间,它流经8省35市,跨越地球四十多个维度,遗产涵盖分类与内容广袤繁多;同时在当下,大运河北连‘环渤海经济带’,南接‘长江经济发展带’,纵贯‘一带一路’,在国家战略空间起到文化带柔性穿引、融通的重要作用”(45)路璐、吴昊:《多重张力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在这个历史的宏观叙事中,民俗学应有所作为,也大有作为,应积极介入大运河文化带的规划与建构。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应仅仅注重物质景观遗址叠加文旅开发的简单框架,更应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发掘民俗个案背后承载的区域史,从对区域历史的精细雕琢,进而推动大历史的整体构建,凸显“历史中国”的整体图像。因此,大运河蕴藏的民族国家话语,就暗藏于每一个沿运民俗个体的生活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