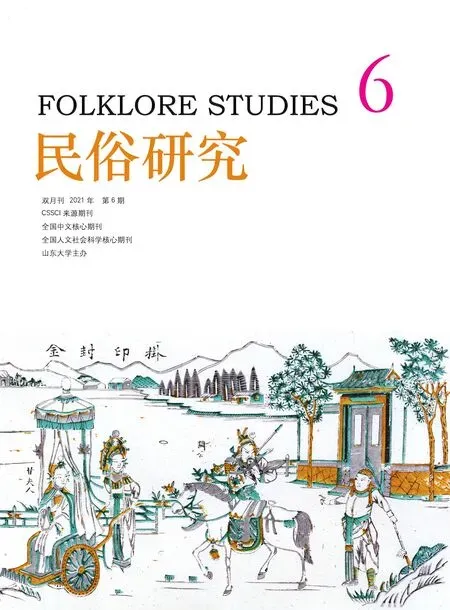汉代黄河河套区域农业发展与边疆农牧文明的互动与融合
王方晗
黄河提供了适宜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资源,使青藏高原以下的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中心之一,发展出灿烂而辉煌的华夏文明。位于黄河中上游两岸的河套地区(西至贺兰山,东到呼和浩特东,北到狼山、大青山,南至鄂尔多斯高原)依托黄河带来的自然条件,从汉武帝设立郡县直至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间,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尤其体现在农业方面。这与汉政府的大一统思想及在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政策息息相关,也是汉政府巩固北疆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汉代是中国成为农耕社会的重要转型期(1)Cho-yun Hsu, 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00).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4.,同时将农业文明扩展到各个边疆地区,与游牧、狩猎采集文化相交融。河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宜耕宜牧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沟通汉匈交融的经济与文化廊道。在河套地区大规模发展农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深入持久而全面地主导一个地区的经济进程,也是中央政府边境开发的典范之一。
汉代河套地区的农耕文明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学者们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试图复原汉代农业开发的状况,包括相关政策、主要农作物、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水平等(2)参见王子忠:《秦汉时期的内蒙古农业(上)》,《内蒙古农业科技》1992年第5期;王子忠:《秦汉时期的内蒙古农业(下)》,《内蒙古农业科技》1992年第6期。,其中也涉及到农业在河套地区开发策略中的位置,以及具体措施和开发主体问题。(3)参见刘磐修:《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另一方面,学者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农耕经济发展与当地水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上。侯仁之和俞伟超首先通过考古遗迹探索环境的变迁,指出黄河河道的迁移、气候变化导致该地土地沙漠化,而汉代大规模的农垦和后期的弃荒则加剧了这一进程,在河套以西地区形成了现今的乌兰布和沙漠。(4)参见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在汉代之前就已有迹象,以自然因素为主导。参见贾铁飞、石蕴琮、银山:《乌兰布和沙漠形成时代的初步判定及意义》,《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1997年第3期;贾铁飞、银山:《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全新世地貌演化》,《地理科学》2004年第2期。墓葬遗存也作为重要的材料印证了农业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砖室墓代替木椁墓的趋向,反映出农垦造成的林木砍伐使地方木料供应减少。(5)参见阿其图:《朔方地汉墓形制的多样性及其成因研究——北方地区墓葬研究之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然而,在强调汉代河套地区农业文明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考量该地处于农牧交互带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农耕与游牧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河套平原地处汉代北方边境,黄河贯穿其间,水草丰茂,形成了农牧皆宜的环境条件,也因此成为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图改革,胡服骑射,在兵强马壮之际北破林胡、楼烦,将势力扩张到阴山南麓地带,形成了农耕和游牧文明的碰撞。此后,匈奴在北方草原崛起,趁秦汉交替之际南下夺取河南地(河套以南部分区域)。而西汉王朝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主动出击,“遂取河南地,筑朔方”(6)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6页。。汉与匈奴围绕着河套地区展开了密切的互动,使该地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交互的重要廊道。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该地农业经济在交互中的作用,不仅包括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也包括这些边疆经略如何产生文化上的影响和辐射。故而,本文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纵深考察汉代黄河河套地区的农垦开发,复原当地农耕社会面貌,揭示农业在汉与匈奴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农作物在游牧社会中的价值以及对边境政治互动的影响。
一、汉代政府的边疆经略与河套区域农业发展
河套地区在汉代包括朔方郡、五原郡、西河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汉书》中形容其中的朔方郡“地肥饶,外阻河”(7)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3页。,充分说明黄河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条件。(8)除去水和土壤资源以外,河套地区还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包括《汉书·地理志下》中提到的金连盐泽和清盐泽,也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必备要素。关于盐业资源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可参见Bryan K. Miller, “The Southern Xiongnu in Northern China: Navigating and Negotiating the Middle Ground”, in J. Bemman and M. 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Archaeology, vol, 6. Bonn: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43-144. 薛瑞泽:《汉代河套地区开发与环境关系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第1期。首先,河套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地带,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虽然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受西北干冷季风影响较强,气候寒冷干燥,但黄河干流、支流及周边的古湖泊共同构成了河套地区灌溉农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水资源。黄河故道流经汉朔方郡临戎县县城以西(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补隆淖镇),并分为南北两道,自朔方以东又有多条支流。除黄河外,古代湖泊也是河套地区灌溉系统中的重要部分。黄河河道在汉代朔方郡地区逐渐东移,而河水在废弃的河道和周围地势低洼的地区积聚成湖泊。(9)参见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其中,黄河北道水积形成屠申泽,位于汉朔方郡窳浑县北部(今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保尔浩特古城),面积颇大,“泽东西百二十里”(10)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中华书局,2007年,第75页。,也是重要的灌溉水源地之一。其次,黄河带来的泥沙在河套地区沉积,形成了冲积平原,以亚砂土、亚粘土和中细沙互层为主的地层提供了富饶肥沃的土壤(11)参见薛瑞泽:《汉代河套地区开发与环境关系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第1期。,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主父偃在给汉武帝的奏疏中称赞朔方土地肥饶,而赵并则评价河套东部地区的土壤为“膏壤”(12)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125页。,即言其土肥美也。
汉代政府充分利用了黄河带来的丰沛灌溉用水和肥沃土壤,将农业作为对抗匈奴的边疆战略的一部分,大规模发展农业经济,这主要体现在农耕人口与农作物两个层面。其一,自西汉以来展开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北境进行屯垦,纳入屯田系统,进行农业生产,可以长期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其二,迁移至此的农民开展屯田殖谷,为军事征伐和当地驻军提供粮食,实现了从汉初“输粟于边”的低效率模式到本地屯田的转换。
(一)从“输粟于边”到“屯田于边”
汉代在河套地区发展农业是边疆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其目的在于推广屯田制度,在守卫边境的同时在当地进行垦殖,保障粮食供应。
河套地区濒临汉代边境,与匈奴的冲突不断,汉政府派遣大量兵力驻守,因而需要数额巨大的粮草以维持军队生存和保障军事行动。根据推断,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驻军通常保持在30万左右,一年大概需要800万石的谷物,消耗巨大。(13)参见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为了维持所需的军粮,汉文帝接纳了晁错的进言,“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14)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4页。,即从内郡以入粟拜爵的方式筹措粮食并运输到边郡。
然而“输粟于边”的供粮方式效率低下,为汉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而在汉武帝时期逐渐转化为“屯田于边”。主父偃作为这一策略性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以秦始皇时期粮食转运为依据提出输粮的弊端,将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于向北郡输粮带来的财政压力。他提出,秦占领的北河地区“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15)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0页。。主父偃提出“输粮于边”带来两个财政问题。一是巨大的经济负担。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粮食耗资巨大,“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16)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8页。,年费可能达到10.8亿钱。(17)参见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二是转运过程中损耗惊人,效率极低,“率三十钟而致一石”(18)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0页。,有大量的粮食浪费在运输途中。这一军粮供应方式策略性转向的基础在于河套地区本身发展农业的潜力。主父偃认为,秦代治理北境失败的根源在于北河地区土壤贫瘠,不适宜农耕,粮食必须从其他地区长途转运。相较而言,河套尤其是汉代朔方郡附近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网,可以就地种植农作物,“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19)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3页。。
在主父偃的建议下,河套地区开始实行屯田,主要集中在河套外围的北侧和西侧,利用黄河沿线充足的水资源发展灌溉农业。所生产的粮谷可以就地为边境驻军解决粮食问题,也为抵抗匈奴提供较为稳固的物质保障。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动、积极且长久的边疆开发典范。
(二)汉代政府开发河套农业的措施
尽管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河套地区就出现了农耕,但游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20)参见张波:《河套地区古代农业发展述略》,《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2年第1期。至秦代,开始经营、开发河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夺取河南地,将边疆拓展到河套平原和阴山一代。此后,秦政府主要实行了两个政策充实边疆。首先是设置郡县、建筑城池,沿黄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21)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6页。。其次是移民驻守北疆。临河筑城当年,“徙谪,实之初县”(2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53页。。据葛剑雄估测,充实44个县的人户,当在2-4万户、10-20万人。(23)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秦政府于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迁北河榆中三万家”(2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按秦汉最常见的五口之家计算,有15万人。葛剑雄认为秦朝迁往河套地区的人口有30万。(25)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这些移谪发实县的罪犯、实边的移民,绝大部分要从事农耕。另外,葛剑雄认为:“蒙恬率领的30万军人中也应有一部分转为屯垦。”(2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河套地区大规模的农耕开发,自此开始。
汉文帝时期,晁错提出移民实边,“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27)班固:《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7页。。汉武帝重夺河南地后大致因袭了秦的边疆政策,继续进行大规模开发。一方面是设立郡县,他在当年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后于元朔四年(前125)设置西河郡,并在郡下设县。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直至西汉末,河套地区包括朔方郡10县,五原郡16县,云中郡11县,定襄郡12县,西河郡16县等。另一方面是移民实边,充实新设立的边地郡县。在占领河南地的当年,政府随即“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8)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页。。六年之后的元狩二年(前121)秋,“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29)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9页。。其后,由于黄河下游洪水泛滥,“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30)班固:《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2页。。这三次大规模移民虽然起因不同,前两次以实边为主,第三次为赈灾,但陆续为河套地区带来了百万人口,为农业开发带来了充足的人力。
与此同时,汉政府开始在河套大力发展灌溉农业。前文述及,实边的移民大多被纳入屯田系统,充分利用黄河流域优良的自然条件进行农垦。汉武帝时期的屯田地点主要集中在河套、河西和西域,其中对河套地区投入巨大,成为汉代最为重要的屯田系统之一。首先,当地县官为初到边地的新移民提供土地、农具、耕牛等。在晁错的“募民实塞疏”中就提到要给予房屋、土地、医巫,解决衣食等。而汉代政府也的确满足了边地移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且“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31)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鼓励开展农业种植。其次,汉在北方边境兴修水利设施,“通渠置田官”(32)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0页。。《史记·河渠书》中提及武帝时期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33)班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84页。而实际上,政府对灌溉系统的建设耗资巨大,甚至与内陆地区的水利工程投入相当,“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34)司马迁:《史记》卷三○《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4-1425页。。第三则是任用人才负责农业生产。汉代在边郡设置农都尉一职,“主屯田殖谷”(35)范晔:《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1页。。在青海省乐都县出土的东汉晚期的“三老赵掾碑”中提到赵游都曾任职朔农都尉,应是负责朔方郡屯田垦殖之人。(36)参见王献唐:《那罗延室稽古文字》,齐鲁书社,1985年,第316-335页。出身于北境世族的赵氏,不仅有西汉名将赵充国,族内其他成员也多在边郡担任要职,说明政府对于河套地区农业的重视。另外,考古学家还在河套地区的霍洛柴登汉古城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发现了“西河农令”的官印,也印证了汉代边地具有相对完整、成熟的农垦管理官制。(37)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三)汉代河套地区区域农耕社会面貌
在汉代政府的号召下,移民及其后裔在河套地区形成了农业定居社会。考古工作者在河套地区发现了大量汉代遗迹和遗物,是复原该地区区域农业社会状况的珍贵材料。河套面积广大,各区域自然、水文条件不同,农业发展和当地居民情况也各有不同。以汉朔方郡西北,即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为例,主要呈现出依黄河水网分布,以中原地区移民为主,以农业经济为中心辅之以畜牧业、家畜养殖业的特点。
朔方郡西北的三座汉代县治均位于黄河干支流处,灌溉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于农业垦殖。其中,临戎县城地处汉黄河干流西侧,而窳浑、三封县城则沿屠申泽分布,有助于当地居民广泛种植北方旱作谷物。对该地墓葬出土人骨进行的稳定同位素测试反映出汉代河套地区的粮食种植种类以粟和黍为主,且品种丰富,而先民的日常饮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摄入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说明他们可能也延续此前游牧民族占领时期所遗留的畜牧狩猎的生产方式。(38)参见张全超等:《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纳林套海汉墓出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4期。另外,汉墓中出土的陶制猪圈、鸡舍模型说明当地家畜饲养也颇具规模,也有可能是肉食的来源。除了经济生产,黄河水网带来的水资源也保障了农耕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当地汉代村落遗址中有古井遗迹(39)参见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而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陶制水井模型,配有辘轳和小水斗,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先民日常取水的场景。(40)参见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
丰富的墓葬资料体现出农耕社会的丧葬礼俗特征,表明当地居民以中原屯垦移民为主。从年代上看,巴彦淖尔地区的四个汉墓群纳林套海、包尔陶勒盖、沙金套海和补隆淖集中于汉武帝以后,特别是昭帝、宣帝和元帝时期,与移民垦殖的文献记录吻合,说明有大量人口在此期间定居于河套地区。(41)参见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页。这些墓葬的形制与中原汉墓相似,而随葬器物也表现出浓厚的汉式风格,承袭中原的丧葬礼俗,大量使用陶制明器,包括井、仓、灶、樽、鼎、博山炉等。
然而,与中原一带相比,汉朔方郡的居民墓葬更加注重农耕的表达。陶仓明器是汉代丧葬习俗的典型器物,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希望陶仓可以大量储存粮食,为死后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在河南和陕西两省发现了大量西汉早期的圆形陶仓,多为五个一组,部分带有“万石仓”“粟万石”“小麦万石”等铭文。(42)例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白庄汉墓M121、M122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对于汉代中原地区陶仓的研究另可参见Armin Selbitschka, “Quotidian Afterlife: Grain, Granary Models and the Notion of Continuing Sustenance in Late Pre-imperial and Early Imperial Tombs”, in S. Müller and A. Selbitschka (eds.), Über den Alltag hinaus: Festschrift für Thomas O. Höllmann zum 65. Geburtsta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7, pp.89-106.随葬陶仓的传统传播到北方边地之后尤其受到重视。本地出土的陶仓数量众多,根据学者统计,出土有陶仓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47.7%,且每个墓中出土的陶仓数量集中在1-3件。(43)参见李雪欣、魏坚:《巴彦淖尔汉墓陶仓区域特征初步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而更为突出的则是陶仓形制的多样性,包括圆形、长方形和方形三大类,后二者较为独特,目前在其他地区发现较少,可能是当地先民为了强调粮食储存而创造出的新器型。(44)参见李雪欣、魏坚:《巴彦淖尔汉墓陶仓区域特征初步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为了保障死后粮食的供应,墓葬中的鸮俑和直筒罐也被改制为盛粮的容器。(45)参见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9页。根据对陶仓的使用推断,汉先民在迁徙到河套地区之后参与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同时说明粮食生产在北方边地的重要性。实际上,移民实边与屯田垦殖也影响到汉与匈奴的关系。
二、农业与汉、匈之间的贡纳体系
对汉代河套地区农业的研究必须重视其地理位置的复杂性。该地位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区,而移民实边和屯田垦殖的政策也必然会影响到汉与匈奴的关系。为边防驻军提供粮食以防御匈奴自然是农业的重要贡献之一,但除了军事层面,汉政府也利用农业和粮食作物维持贡纳体系,以经济和外交手段影响与匈奴的边境互动。余英时在汉代胡汉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汉朝出产的物品一直是贡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被当作经济武器来影响与匈奴之间的权力斗争。(46)参见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50页。但学界对贡纳物品的研究多集中在丝绸、漆器、铜镜等奢侈品上,很少注意到农业产品。笔者的意旨在于强调农作物在汉匈政治中的战略性地位,揭示汉政府如何通过调整输粮策略吸引匈奴部族归附,维护长期的贡纳关系,从而改变西汉晚期北方边疆的政治局势。
河套地区的农业在西汉中晚期蓬勃发展之时,恰逢匈奴内部分裂之际。宣帝神爵二年(前60),虚闾权渠单于过世,右贤王握衍朐鞮继位,但却因暴虐嗜杀引起族内人民的不满,也导致匈奴上层对单于继位问题的争议。匈奴贵族纷纷自立为单于,随后发展出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屠耆单于和呼韩邪单于混战的局面,史称“五单于争立”。
其中,呼韩邪单于在甘露元年(前53)归附汉朝,寻求庇护。当时,呼韩邪正处于被强敌郅支单于击败的危机中,不得不从单于庭出走。北有郅支,而汉朝在南,呼韩邪新败,势力衰微,因而左伊秩訾王规劝呼韩邪南下附汉,“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47)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7页。他认为归附可以解除汉的威胁,使部族免受两方夹攻之苦,且可以借助汉的力量抗衡郅支,逐渐恢复实力。呼韩邪采纳了内附的建议,率领部下南下靠近汉代北境,派遣质子入朝,并于甘露三年(前51)亲赴长安朝见汉帝。作为归附的条件,呼韩邪也得到了汉政府丰厚的馈赠。在朝见之时,呼韩邪不仅得到了“匈奴单于玺”,被认可为匈奴最高首领,也获赠大量礼物,比如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矢、棨戟、车马、黄金、钱币、锦绣、杂帛、絮等物。
汉政府在接纳呼韩邪部族的同时也与郅支建立了贡纳关系,对二者实行羁縻政策。郅支在得知呼韩邪内附的消息后,深恐遭受二者联合进攻,随即遣使入朝,并送质子,也得到了汉政府慷慨的回赠。因此,汉在此时与匈奴的关系并非一味支持呼韩邪,而是通过制衡来防止一方独大,从而维护边疆的安定。
在对呼韩邪与郅支的平衡中,汉代提供的粮食和驻军则改变了匈奴内部权力斗争的走向,帮助呼韩邪取得了胜利。因为二者最大的差异之一就在于汉政府只向呼韩邪输送了农作物和军队,以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方式打破了双边平衡,扶持呼韩邪的力量。除去每年度的贡纳之外,汉代文献中还专门提及了两次对呼韩邪部族的输粮活动,虽然性质不同但均有助于其恢复实力。首先,汉政府提供粮食保障汉在塞外守卫呼韩邪的驻军。在朝见汉宣帝临近北归之时,呼韩邪“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48)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0页。,他表示愿意留居光禄塞(今包头市西南),如有紧急情况可以保卫汉的边塞受降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巴彦布拉格城址)。为了约束并保护呼韩邪,汉派遣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等领兵一万六千,同边郡兵马一起护送呼韩邪,又命董忠、韩昌等驻军塞外,护卫呼韩邪,之后“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49)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0页。。这些粮食为护卫呼韩邪的驻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给养,有助于其恢复实力,对抗强敌郅支。
在元帝即位初年(前48),汉政府第二次向呼韩邪部族输粮,起因是呼韩邪上书“言民众困乏”。汉元帝为了维持匈奴的归附,诏令云中、五原二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50)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0页。。游牧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法自给自足。苏联考古学家哈扎诺夫(Anatoly Khazanov)通过对北方草原地区游牧的人类学观察指出,游牧不能离开辅助性的经济活动,通常需要以其他经济方式来补足。(51)参见 Anatoly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另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史料提及,到西汉中晚期呼韩邪统治之前,北方草原至少发生了三次饥荒,大多由于雪量过多覆盖草原,阻碍了正常的畜牧活动: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52)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5页。;后元元年(前88),“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53)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1页。;本始三年(前71),“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54)班固:《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7页。。这些记录证实了游牧生业模式的不稳定性,也从侧面说明他们需要与农业社会互动,以获得食物资源。呼韩邪通过归附汉朝而被纳入贡纳体系之内,从汉获得大批粮谷,解决了游牧经济固有的问题,为面临饥荒困顿的民众提供了赈灾食物,不仅可以笼络人心,也有助于他积蓄实力,对抗郅支。
郅支在得知汉拥护呼韩邪的举措之后,怨恨汉助呼韩邪而不助己,又听闻呼韩邪力量益强,只能率部向西远徙。自此之后,匈奴内部二十余年的变乱局面得以终结,呼韩邪得偿所愿,统一匈奴。作为供应粮谷的主要来源,河套地区以其边境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影响了汉与匈奴之间的互动形式,从单纯的军事对抗转向外交手段,利用农作物维持与匈奴的纳贡关系,实现了北方“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55)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6页。的安定局面。
农产品在汉和匈奴的贡纳体系中占有战略性位置。汉政府将其作为砝码置换匈奴部族的内附与边境和平,而匈奴则将其作为巩固实力、笼络部众的重要经济资源。作为农业社会,汉朝,尤其是河套地区强大的农业生产能力是吸引呼韩邪内附的因素之一。汉政府通过输粮维持呼韩邪的归附,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匈奴内部的权力斗争。虽然汉与呼韩邪和郅支都建立了贡纳关系,并各有封赏,但对前者的粮食输送实质上暗含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不仅供应了护卫的驻军,也培植了呼韩邪的势力,最终依靠经济手段重塑了北方边疆的政治局势,在短期内解除了匈奴对边境的威胁。不仅如此,农产品在此过程中也影响到了匈奴社会。
三、河套农耕文化廊道与匈奴文明的嬗变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之外,农产品对匈奴文化也有重要影响。虽然目前匈奴社会的材料有限且相关研究甚少,但笔者在此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农作物在匈奴,尤其是匈奴贵族饮食文化和丧葬礼俗中的作用,并将其置于文化互动中探讨农耕文化对游牧社会的影响。如对于游牧民族而言,粮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呼韩邪会专门上书要求汉朝输送粮食?这种文化上的互动与融合可能通过何种方式发生?黄河河套农耕文化带在其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
匈奴社会对于农业文明元素的吸收离不开黄河河套地区。它既是重要的农耕文化区,也是北方边境汉与匈奴频繁互动之地,双方以此为中心一直有人口迁徙和商贸往来,以人和物的双重媒介构筑了经济文化沟通的廊道。熟知边疆状况的侯应在反对罢边的奏疏中提到了常态的迁徙模式:“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56)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4页。总结来说:其一为内附的降民,由边境外进入汉代属地;其二有军事征伐中的逃兵,以及投奔他们的亲属;其三为生活困顿的边人,听闻“匈奴中乐”,意欲逃至匈奴;其四为亡走的盗贼;另外还有匈奴掠走的民众和叛逃的官吏等。而呼韩邪的内附则产生了一种非常态、更为密切的互动形式。他的部族长期驻扎在河套朔方郡以北,在朝见汉朝皇帝的过程中途经河套,又有大量汉军随其驻扎,并有农产品供应。因此,河套地区常有汉匈人员往来,为农业和游牧文化的沟通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汉匈双方在北方边境的互市也为文化互动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因为它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以物品为媒介传播农耕文化,也吸引了大量匈奴民众和贵族前来,接触汉代的饮食和文化。虽然目前河套地区关市的分布尚不明确,但自汉文帝开关市以来,匈奴一直相当重视这种贸易形式。据贾谊《新书》记载,汉朝的美食和美酒一直是市场上深受匈奴喜爱的货品:“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57)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151页。农耕文化可能通过饭食和人口流动向北方草原扩散,逐渐被融入游牧社会中。
经由河套的廊道作用,农作物进入了游牧社会,因其罕见性而成为外来的珍奇食物,深受匈奴上层的喜爱。西汉时期,匈奴单于受到汉朝的影响而喜爱汉的食物,甚至被亲信中行说劝诫,“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58)班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759页。。粮食作物以贵族阶层为主导的消费方式延续到了呼韩邪时期。根据推算,他向汉政府讨要的两万斛边谷实际上仅够供应一小部分部卒。在额济纳地区出土的汉简中记录了在当地驻守边关的下层官吏每年的粮食配给,约为36-48斛。如果将谷物按照匈奴每日饮食的10%来计算,两万斛仅够四五千人食用,仅占当时呼韩邪部族人口的10%。(59)参见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这一悬殊的比例说明虽然以赈济民众为名,但这批粮食很可能是作为外来食物供应给匈奴上层,满足贵族饮食中对粮食作物的需求。
这一特殊的消费形式意味着谷物成为游牧政权贵族网络(elite network)的一部分。贵族网络是匈奴社会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指游牧社会的贵族阶层通过控制对外贸易的渠道和外来物资而突显特殊的身份,也通过将外来的奇珍异宝向下层分配来巩固政治地位。(60)参见Ursula Brosseder, “A Study of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J. Bemmann and M. Schu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2015, pp.204-205. Susan Frankenstein and Michael Roland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Context of Early Iron Age Society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ulletin, vol. 15 (1978), p.76. Edward Schortman and Patricia Urban. Networks of Power: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Late Postclassic Naco Valley, Honduras.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11, pp.192-195.在这种社会机制中,匈奴的贵族网络横跨整个欧亚大陆,所获取的奇珍异宝十分丰富,从中国出产的铜镜、漆器、丝织品到希腊化世界的铜质马牌饰等等,都在其中。相较而言,农作物容易腐烂,很少能在墓葬中保存下来,因而一直没有被看作是贵族网络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深受匈奴贵族欢迎,并且要从外部获得的珍奇资源。在内部势力衰弱期间,从汉朝获取粮食的能力对于维持贵族网络以及贵族的统治格外重要。呼韩邪所获的粮食不仅彰显了他作为单于保持对外交换的渠道和能力,也迎合了部族上层的饮食喜好,换取贵族的忠诚,保障他的政治地位。
除了饮食以外,粮食作物还通过墓葬的形式树立匈奴贵族的社会身份,维护匈奴上层的统治。虽然粮食在河套地区附近的匈奴墓中较为罕见,但考古工作者在蒙古和俄罗斯南部的部分匈奴墓葬中发现了谷物遗存,多为未脱壳的粟米。这些墓葬纪年集中于公元前后,包括诺音乌拉(Noin Ula)20、22、23、31号墓,高勒毛都(Gol Mod)1号墓地1号墓和伊里莫瓦谷地(Il’movaya Pad)40号墓等。(61)参见 Elena Korolyuk al., “Panicoids in Xiongnu Burial Ground (Mongolia, First Century AD): Problems of Identification” ,Turczaninowia, vol. 21, no. 2 (2018), pp.145-159. Elena Korolyuk and Natalie Polosmak, “Plant Remains from Noin Ula Burial Mounds 20 and 31 (Northern Mongo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8, no. 2 (2010), pp.57-63.这些墓葬虽然数目较少,但规模庞大,大多为土台墓(terrace tomb),带有墓道,地表有高出地表的土台,为长方形或梯形,形状和尺寸与墓穴基本重合,高度一般为0.5米至1.5米,一般属于高等级墓葬,墓主为匈奴中身份地位较高的贵族阶层。这些墓葬中陪葬品丰富且规格较高,多随葬来自中原地区、中亚、西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器物,例如汉朝的漆器、丝织品、铜镜、玉器、马车,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金银器、毛纺织品、玻璃器等,符合匈奴贵族网络的特点,也是高等级墓葬的典型特征。(62)对于匈奴墓葬形制及等级的讨论参见Ursula Brosseder, “Xiongnu Terrace Tomb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as Elite Burials”, in J. Bemmann et al (eds.),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09, pp.247-280.潘玲、萨仁毕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而谷物的随葬模式也与这些舶来品类似,基本出自贵族墓葬,可能与其他来自遥远地区的奇珍异宝一样被匈奴上层阶级当作墓葬中彰显身份地位的物质符号。
农作物对游牧社会葬俗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礼仪层面。它们大多出现在墓室内部,一般是平铺在墓室内部木质地面或毛毡之上,比如诺音乌拉20、22和23号墓的谷物均铺撒在墓室的毛毡上,而22号墓中还有一部分谷物原被放置在小袋子中,沿墓室北墙摆放;诺音乌拉31号墓中的谷物置于棺内毛毡上;高勒毛都1号墓地1号墓也用于覆盖地面。这种特殊的埋葬形式与匈奴其他墓葬中作为食物的粮食作物不同,后者以车姆克谷地墓葬和诺音乌拉11号墓为代表将谷物置于陶制容器中,说明农作物在墓葬中的出现可能并非只是食物。学界推测这些谷物很可能具有礼仪性作用,此前也有学者将其与马王堆一号墓中以谷物铺于棺椁底部的形式相类比,认为这种丧葬礼俗可能是受到汉代影响,随着匈奴与中原日益密切的贸易和政治交往而传入草原游牧文明,并首先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欢迎。(63)参见Natalie Polosmak and Elena Korolyuk, “And the Soul will Revive as the Grains of Millet”, Science First Hand, vol. 35, no. 2 (2013), p.118.他们不仅在北方复制了形制与战国晚期高级别墓葬类似的土台墓,墓穴、墓道、土台、填土内砌石墙等形制可能受到中原的影响(64)参见潘玲、萨仁毕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也将马王堆一号墓中类似的谷物随葬形式纳入了当地丧葬文化中。针对这些粮食作物具体的礼仪作用,有学者认为它们代表生命的过程,由种子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循环往复,给死者以复生的希望。(65)Natalie Polosmak and Elena Korolyuk, “And the Soul will Revive as the Grains of Millet”, Science First Hand, vol. 35, no. 2 (2013), p.118.由于匈奴丧葬礼仪的文献极度缺乏,涉及具体礼仪层面的资料较为分散,相关问题只能留待日后再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但综合目前的发现来看,谷物在匈奴葬俗中应当具有礼仪性作用,因此深受贵族的重视。
在汉匈交往更为密切的东汉时期,农业和农作物被更深入地纳入游牧文明中。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南、北二部分道扬镳,北部继续留在漠北,而后西迁,南部则归附于汉,在单于比的带领下南迁,入居塞内。在归附之初,汉沿袭了此前的策略,通过向南匈奴输送粮食的方式将其纳入贡纳体系之内,“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66)范晔:《后汉书》卷七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4页。。但同时,东汉政府大力鼓励内迁的游牧人口发展农业,循吏将劝课农桑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农业的方式逐渐使他们农业化、定居化,最终纳入中华文明的怀抱中。汉朝境内的南匈奴也的确经历了较为平稳的经济汉化过程(67)参见[日]江上波夫:《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山川出版社,1950年,第33页。,到曹魏时期,内附的匈奴人已经通晓农业耕作,并被汉族豪强地主雇佣务农。(68)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39页。
作为南匈奴归附后的主要驻地,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在河套地区发展到了新阶段。自单于比内附之后,汉在建武二十六年(50)于五原境内为其设立单于庭帐,后迁移至云中郡,再迁至西河郡美稷县,基本位于河套区域。他所率领的八部牧民也分布在该地区,主要集中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各郡,从陇东到晋北、冀北一带,但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河套。他们在东汉政府的倡导下利用河套地区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和基础,逐渐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型。埋葬在神木大保当汉墓的南匈奴部族就反映了农牧经济并存的状态。(69)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该墓地位于陕北的神木县大保当镇,结合出土器物类型和人骨鉴定分析,是属于南匈奴人的一处家族墓。墓地中既有游牧骑射常用的衔、弓弭等,也出土了铁质农具,主要有锸、铲等,有力地反映了墓主所从事的农牧混合型生业方式,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另外,该墓地的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器物等也呈现出汉和匈奴文化因素交杂的情况。南匈奴参与农业经济活动说明其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发展到了更深的层次。随着游牧人口直接迁移并定居于河套农耕文化带,他们在经济生产方式和丧葬礼俗上也受到了农耕社会更为深远的影响。
农作物对于匈奴而言并非只作果腹之用,它已经渗透到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之中。在与农耕社会密切的互动中,谷物成为深受匈奴贵族喜爱的珍奇食物,也因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融入高等级墓葬的丧葬文化中。作为贵族网络的一部分,贵族通过掌握粮食资源和向下分配彰显自己的身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也是呼韩邪在危机时刻向汉求粮的本意,而汉朝政府也通过输送粮食这种战略性资源改变了北方的政治局势。随着南匈奴南迁,农业经济直接进入了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主要的生业方式之一,也在文化,尤其是丧葬方面直接受到农耕文化的辐射。在此过程中,河套地区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迁徙人口和贸易货品的方式推动了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的互动与融合。
四、结 语
黄河对河套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黄河所带来的水资源和土壤资源是农业经济的重要基础,为汉代在该地区的定居和农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依托于合宜的自然环境,汉代的边疆政策得以实现,在黄河水网附近建设郡县,从中原地区移民实边并纳入屯田体系,强调农业垦殖,为边防驻军提供物质基础,成为汉政府稳固边疆的关键因素。
汉代河套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影响了汉与匈奴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正是由于匈奴在边境的威胁,汉代开始在河套地区大规模开展屯田实边。该政策在为本地提供农耕劳动力和农业作物、保障汉代对匈奴的军事扩张和防御的同时,也以外交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匈奴内部分裂、势力衰弱之际,汉朝的经济实力和粮食供给成为吸引呼韩邪部族归附的重要原因。汉政府以从河套区域筹集粮食,输送给内附的呼韩邪的方式使其长期处于纳贡关系之内,并支持他最终统一匈奴,换取北方边境的和平。在汉与匈奴密切的交往中,农作物渗透到了游牧文明中,作为罕见珍贵的外来产品深受匈奴贵族的喜爱,不仅成为饮食的一部分,也在墓葬文化中占据了特殊的礼仪性位置。通过向贵族和部众分发农业作物,呼韩邪巩固了单于的地位,积蓄实力,最终在与劲敌的斗争中居于上风。在东汉时期,南匈奴迁入河套地区使得他们直接被纳入了农耕文明当中,受汉文化影响逐步走向农业化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汉与匈奴互动中的重要因素,深深影响到双方的边疆经略、政治交往及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