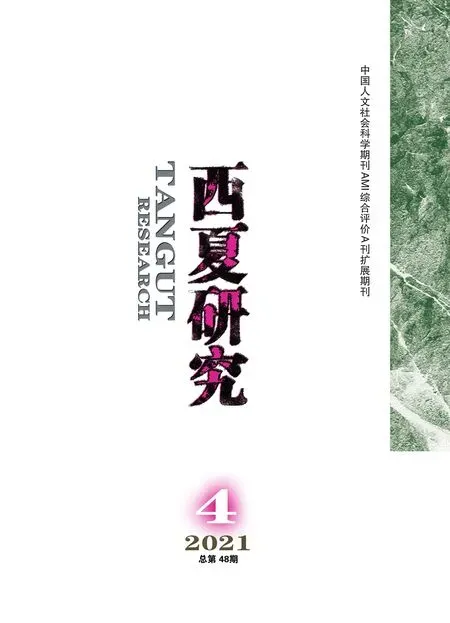论林竞的西北情结及其社会影响
□袁栋梁
林竞(1892—1962)字烈敷,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任京绥铁路材料处长、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调查编辑处处长、交通部参事。及至国民政府以后,林竞先后担任西宁道尹、青海民政厅长与甘肃民政厅长、国府参事等职。在1917年至1927年间,他三次考察西北,足迹遍及察、绥、宁、甘、青、新等各省。30年代以后,林竞积极组织且参与了新亚细亚学会、开发西北协会等活动,极力主张“开发西北”,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认可,遂有“西北拓荒者”与民国以来谈西北问题“第一人”之称。
过往学者对林竞虽有所论①,但依旧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研究内容上更多突出对林竞西北考察内容的介绍。第二,所论的史料基本以他的考察日记《西北丛编》为主。鉴于此,笔者除了结合林竞的相关著述之外,还竭力搜集民国其他文献,以其“西北情结”作为研究视角,探究他此情结形成的过程、缘由,以及社会影响。笔者通过对林竞这一著名的“西北拓荒者”个案分析,试图以小见大去展现民国考察者对西北的共同情结,从而凸显西北对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一、亲临西北:林竞“西北情结”的形成
林竞的“西北情结”形成于1917年至1927年间三次考察西北,及随后任职于西北的为官历程。然而出于这种诚挚的情节,终使林竞走向启迪国人探究西北的过程。
他在考察中写道:“然举之以示国人,知之(西北)者,有几人哉?知之而潜然以思,谋所以辟大荒,探宝箧,而图为不朽之业者有几人哉?”[1]所以,林竞本着“奚得穷源,若为崎岖,何来真相”[2]1的考察精神,意在为国人增添一个新领域,“述其梗概,俾资留心边地者之需助”[3]2,以便世人探究西北。他对西北考察,涉及民族、宗教、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历史沿革等内容,并将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状况复杂,不免相互争夺。同治兵燹,导致民国初年有些地区依然破旧不堪,如宁夏县“盖自同治兵燹后,至今尤未恢复旧观也”[2]83,安西县旧有人口“两千余户,同治回民起义后,只余数百户,历年劳徕绥辑,尚不及千户”[2]207。林竞提出,“此后应绝对本民族共存共荣之旨,施无偏无私之政,以达化除畛域之境”[1]。同时,他认为国人胸怀“真如海洋之量,无所不包也”[2]130,希望能够通过包容实现团结民族。
国计民生方面,西北人民处境较为凄惨。林竞看到甘肃“人民穷苦,十余岁男女至仅着一破裘,而下体则任其裸露,可谓极世上之最可悯者矣”[2]159。新疆居民“于街北挖池蓄之,称曰涝坝,以备全市一年饮料,池底余沥,臭不可闻,卫生二字诚难言矣”[2]252-253。贫穷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匪患丛生,内蒙古“达拉旗近年被匪掳掠一空,已成赤贫矣”[4]。宁夏“穷民之多与税局相辉映”,当局“既不能培养生息,又复变本加厉,人民安得不穷”[2]94。
西北边疆工商凋敝,百业不兴。林竞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工商业、资源、农垦等方面作了独特阐释。绥远一带萧条的工商环境直接影响了传统皮毛业的发展。林竞认为该地“地旷人稀,居民脑筋单简”,“工业迄未发达”,建议“倘能搜罗专门人才,集资购办机器。将细洁绒毛,以治绒呢。粗短之毛,以治毛毡。生皮以治熟皮”,如此“便以行销甘新青海内外蒙一带”[5]。西北地区蕴藏丰富,各种资源种类繁多。林竞在新疆考察时看到奇台县“煤窑地方见该煤矿发火,夜间如同白昼,延烧周围达百余里无人过问”,过天山“经阿克苏见盐山口全山悉系盐质结成,其佳者如水晶”,但整体难有所为,“苟交通一便,则其余可迎刃而解矣”[3]13-14。西北地区宜农宜牧,其中河套平原的灌溉农业古已有之,民国以后荒地较多,林竞看到“蒙人仅知以荒地作牧场,从事牧畜,而不知种植”,“汉人之欲开辟其地者,彼复多方拒绝,死守其地,任其荒废”[2]49。至于缘由,林竞指出,“垦务局往往积欠荒价,不能照付,甚失蒙人之心”[4]。
概而言之,鉴于上述复杂的社会问题,林竞产生了经营西北之决心:“他日西北开发,不特经济方面,予全国以莫大之助力,则历史上西北所留存各种政治难题,均可迎刃而解矣”[2]393。于是,繁荣西北的崇高信念开始扎根于林竞心中,亦是其“西北情结”形成之来源。
西北曾在国史上有着辉煌的地位,“即吾国的学术文化为世界上最早六发源地之一”[6]2,其特有的历史、景观流芳百世,有着独特之魅力。当林竞游览宁夏北塔时,记述该塔“高十层,鼓勇而上,万象罗列眼底”[2]83。对于自然景观,林竞记述道,“五泉山,即皋兰山”,“余等由中间石磴拾登,则见佛舍重叠,楼阁轩敞。更登高一望,目穷三面,黄河冻冰,白光一带。城市烟火,罗列眼前,诚奇观也”[2]125-126。可见这些景观足以让林竞惊叹不已,亦使其加深了“西北情结”。当林竞抵达绥远时,看到“商人殷勤招待,并无望报之意”,感叹边地“遂得保存醇厚之风,此诚内地人士所不能梦见者也”[2]53。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西北的敬畏之情。林竞认为:“吾人旅繁华之地,恒以人物嘈杂,扰乱心神,致生厌烦。苟行西北大荒,则觉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一顽石一蝼蚁,无不可寄以同情,所谓境随心迁,心随境变,信然。”[2]71其实很多西北考察者与林竞都有如此心境。李安宅在20世纪40年代考察西北藏区时指出,边疆“奇花异草,美不胜收,足以使人陶醉,如坐春风”,而“边民”也是“具有天真的健美”并“富于超世的热情”,因此他认为“不管经过多少困难,总不能不说边疆具有一种吸引力”[7]。这也确实加深了考察者的边疆情结。
然而,西北考察充满了艰辛。林竞凭借顽强的精神三次完成了西北考察的重任。诚如他在西行途中所见,“此去一片戈壁,草木不生,焦躁如常,无论冬夏,一经日晒,热可炙人,长途行旅,渴不得饮”[2]199,“一物未入口,至是以不知饿,亦无办法,然求一点开水而不可得”[4]。面对环境之困难,林竞写道,“连日跋涉,尘垢满身”,“天下事有其苦者,必有其乐,旅行者之生活,毋乃类似”[2]119。笔者以为,林竞一行人何以无畏牺牲之精神远赴西北,通过他与其妻书信可知。“此行苟为个人利禄计,则余宁舍利禄,而回京一视为快,无如所负使命甚大,不得不守公而忘私之戒。”[8]可谓一语透露其探究西北为国利民的志向,亦是林竞“西北情结”之初衷。
由于林竞考察时常与当地政界人士多有融洽,对促进西北与中央关系起到积极作用[9],因此后来任职于西北。1928年,出任西宁道尹的林竞看到当地尚无医院设施,卫生条件极为落后,便积极筹建了平民医院,这是青海现代卫生事业的开始[10]132。他在西宁工作期间,“整饬吏为己任”,又“致力于村民之训练,以谋旧村之改善”,“躬自操作,事无不举,人无不服”[11]。因其组织能力及才干,被刘郁芬所嘉奖,称其“苦心经营不遗余力”,拟每月“准给津贴洋二百元”[12]。后来林竞与当局政见不和,最终悲愤辞职,但这种服务建设之精神,更能彰显其建设西北之情结。
由此观之,林竞之所以能够矢志不渝地提倡开发西北,这与其早年亲临西北密切相关。他考察时所言:“过天山,度流沙,循葱岭之墟,溯罗布之源,睥睨欧亚,钩稽今古,为人类辟一新领域,为国人筹一新出路耶!”[2]195亲临西北的实践经历是林竞“西北情结”的重要形成过程。其一,西北考察让他看到了西北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并产生了建设西北的想法。其二,西北广阔的资源与土地使得林竞看到了经营西北的可能。其三,西北悠久独特的历史、自然景观吸引了林竞,亦加深了他的情结。其四,为官西北,虽然效果有限,反而鼓励世人探究西北之信心。当他的“西北情结”形成之后,终使林竞在后来走向了呼吁国人去探究西北的崇高使命。
二、林竞“西北情结”的缘由
“情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依恋,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思维偏向”,而“西北情结”是指“对西北广博历史背景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情感纠葛、执着眷顾”[13]。林竞对西北所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的缘由。
林竞以“班霍”自比,意在追求开发西北之伟业,实根源于西北考察。1917年,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有意经营西北作为皖系军阀势力范围,财政部官员多以西北艰苦而拒绝。林竞以“别人怕去,我偏要去”之原故,开始了第一次考察,并如他所说的“像这次的动机,可以说为好胜心所驱使”[14]。当林竞第一次完成考察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时,看到俄国的边疆建设比中国好,遂产生了经营边疆的想法。“要经营边疆便要自己先去”的“爱国心所驱使”[14],便是其第二次西北考察的动机。1918年冬,林竞奉交通部之命欣然远赴绥、宁、甘、新、外蒙勘测路线,完成了人生中第二次西北考察。两次西行使林竞在社会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1921年,林竞受中国华侨联合会款待并作了现场演讲,呼吁华侨“苟能移海外之资,国内之民集于西北,则地利既辟,康乐可图,人以何乐而为乱乎”,“数十年含蓄之元气一旦发洩,不特西北之荣,实华侨之光也”[15]。《京报》也称林竞“对于西北一带情形颇为熟悉”[16],亦足见其声望。林竞西北之行得到了各界认可,使其对西北产生强烈情感,他认为“革命是要在不革命的地方去革的,是要在黑暗的地方寻找光明的,南方虽然黑暗究竟是比西北好一点”[14],终促使林竞第三次西北考察。他将西北工作当成革命,是其“生平服膺主义,绝对以大多数民众为立场”,“并捻知东南革命风气较为普遍,故特注重西北工作”[17]29。可见林竞将发展西北作为复兴整个民族的事业。后来的西北考察者也都秉着这种精神,如薛桂轮考察结束后说道:“茫茫神州、沉沉大陆,倘有实行救国救民、利己利人之主义者乎!窃愿以最简单之方式、进最诚恳之忠告曰:‘还是到西北去。’”[18]62
此外,林竞也发现了边疆所呈现出极强的研究价值,并且“任何一个问题都够我们一辈子的努力”。其一,所谓中国军事史就是“西北的事情”,是可以研究的。其二,西北许多同胞长相各异、文化不同,有冲突,但是具有研究价值。其三,西北地区的社会制度、宗教与内地是不同的,如蒙古、甘肃的“封建制度”,青海西藏“政教不分”及回教喇嘛教等。其四,西北历史悠久,“被流沙埋没在地下的至少有几十国呢”[14],确实值得研究。由于西北有如此多的研究价值,也促进林竞长期以来重视探究西北的重要因素。
“治史必须贯通古今中外,整体之下研究具体。”[19]142治近代史“不仅在于贯穿内部的时空,还需上出嘉道,跨越国境,连贯古今中外”[19]125。故研究林竞的“西北情结”,需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思考何以会产生。
近代以来,救亡图强成为国人首要目标。边疆问题已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问题紧密相连②,而林竞在考察西北前的几十年正值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即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西北史地学主要侧重于社会环境与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及开发边疆的建议。如龚自珍“耕者毋出屯以恳,牧者毋越圈而刈,上亩虐下,下亩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20]312,指出新疆农耕人口与畜牧人口要彼此和谐共生的道理。西北史地学对后世的边疆研究影响深远。林竞等边疆考察者对边地国计民生、资源等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其方法可视为19世纪西北史地学的延续。民国年间,各种社会问题也让林竞等学人重新将目光指向了边疆。林竞表示,“内地各省,人满为患,地利将尽,复因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处处予我一阻力”,“故虽有善良制度与政策,施行极感困难”,反之“西北天府,乃全国未来之生产泉源”[2]2-3。对此,陈赓雅深感赞同,以“沿海有余之财力人力,开发西北,固属当务之急”[21]6。所以,王述曾感慨,西北“如此宝藏,不予开采,而使货弃于地,启外人窥伺之心,良为可惜”[22]。与此同时,边疆形势的恶化令人担忧。林竞指出:“强邻起窥伺之心,突厥趁危,西域动鼓鼙之兆。藩篱已撤,门户洞开,国防如是其急亟也。”[2]398民族学家李安宅更是说道:“处心积虑想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却不怕艰苦。日本人大批大批地前往内蒙古,英国人不断进入西藏去进行挑拨离间。我们自己的国土,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去工作呢?”[7]11另外,西北地区种类繁盛的资源也为经营提供了条件。林竞在考察时看到西北蕴藏丰富不禁感叹:“我乃拥有如此庞大之区,任其荒废。倘能及时开发,一面吸引世界之投资,一面即为供给世界物品之市场,前途希望如是其远大也。”[2]398吴学衡也说:“如果真能脚踏实地的在西北方面,痛下一番开发建设的功夫,则西北不仅在国防上得以稳固,而且全国民生问题的解决,与西北开发尤为有关了。”[23]林竞与后来学人的西北边疆情结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固然林竞的“西北情结”虽有其个人因素,但时代动因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近代以来传统的“王朝—国家”边疆体系逐渐崩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边疆亦愈发显得重要,就林竞所言,“昔日于边疆无所求,今则非边疆将无法以自存”[24]。正因为如此,“西北情结”已然成为了精神动力,使林竞等考察者千里迢迢奔赴西北,感受深厚历史底蕴的同时,也看到了巨大发展潜力。他们不约而同来到西北考察,其初衷与先辈们的西北史地学者如出一辙,也促进了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的高潮,为开发西北起到了思想指南。
三、开发西北:林竞“西北情结”的社会影响
林竞作为民国西北拓荒的先行者,他以各种方式提倡国人开发西北,对激发时人探究西北有着深远影响。
关于林竞鼓励国人探究西北,早在考察期间就已存在。1918年,林竞西北考察路过绥远时,看到“沿途平坦,岌岌红柳,相望于道”,感慨“大好河山,有待开发,海内之士,曷兴乎来”[2]53。1921年林竞受华侨联合会款待并现场演讲时,呼吁华侨开发西北,“西北为黄金世界,苟能从事开辟,不但可供全国之需要,实可容许全世界人类之要求”[15]。1924年林竞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能够派遣熟悉西北人员一名,随带土木工程师及农药专家书记各一人,前往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处分段调查气候、土水、风土民情、经济状况、商业状况等列为统计并制成图表以备开发西北的建议[25]。同时林竞还针对经营西北提出一些建议,诸如水利、修路、农田等建设思想,但北洋政府对其建议“虽经采纳,卒因经费无着,未曾举办,殊为可惜”[2]406。林竞认为,开发西北不仅能够振兴当地经济,更能复兴整个民族。笔者以为,这也是其“西北情结”的根本目的。如林竞在1925年第三次西北考察时对绥远都统所言,“国接扰攘,非和平不足以救国,经济困穷,非开发西北不足以裕民生,十年来环抱此志”,“余又将有三度西域之举,此行也,益将以此相号召”[8]。由此可知,正当人们在高谈论阔开发西北之时,林竞却十几年前就已经三度深入西北考察并主张西北开发,也无愧于民国考察的先行者。
20世纪30年代以后,边疆形势急剧恶化,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渐注意西北之开发,近来日人西进日亟,俄人赤化新省企图日渐显明,因此西北危险的程度,也不亚于往日之东北了”[26]。概言之,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使得林竞以更大的热情继续鼓励世人探究西北,进而投身于开发西北的事业中。1933年,林竞受梁漱溟邀请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并对“西北问题”做了演讲。林竞根据所见所闻指出,“从历史上政治上文化上去分析西北在中国位置之重要”,“在国难期间国人更当注意西北,因西北问题较东北问题尤为严重,倭奴虽抢占我东北土地,然而我东北人民多属汉族,对内地关系较深,只要人心不死,东北终有光复之一日”,西北种族不同“宗教之分歧”,“苟有外人稍一挑拨,则前途大可虑也”[27],希望通过开发西北挽救民族危机。其他考察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王述曾指出,若将东北与西北比较,西北“重要性实有过之”,且“西北内部的复杂,危机的潜伏,恐较九一八以前之东北为尤甚”,故“对于西北若不积极开发,以稳固边防,消灭危机,融洽民情,则西北势必导东北之覆辙”[22]。
与此同时,林竞也先是组织了开发西北协会,又与戴季陶、张继等民国元老发起了新亚细亚学会并兼任该会委员,而这两个学会在当时都是著名的研究边疆问题的组织,足以证明他对西北工作的热情。鉴于林竞是新亚细亚学会委员兼任理事,因而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关探究西北的文章。1930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当年,林竞发表了著名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边务》一文,重点阐述了他的三次西北考察动机与边疆研究的价值,可视其为林竞“西北情结”之根源,从中亦能看出他启迪世人去探究西北的目的。1931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林竞受邀做了简短演讲,“我国关于这类文化团体的组织,寥寥无几,以致中国问题反而由外国来研究,这是中国人多么惭愧的事呢”,所以新亚细亚学会的意义“就是采取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的方法,迎头赶上‘振兴’亚细亚文化,恢复亚细亚故有精神的意义”。其任务是“中国边疆问题之研究”、“东方民族问题之研究”,其中就边疆方面“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项来研究”,这样“分门别类,不厌求详,既可以得更深刻的研究,且可收分工合作之效果”,因而林竞最后也谦虚地表示,“本会同人,能力薄弱,深望各位先进,不时赐予指教与援助”,让本会蒸蒸日上,借以表达开发西北等边疆之情。[28]
此时的林竞是很多边疆学者的榜样。一位署名“真知”的学者在1930年专门前往林竞家中拜访,谈话中林竞渴望与“吾辈志趣相合,他日有缘可多邀研究西北问题之同志集谈,共谋西北之发展”[29]。20世纪30年代,林竞寓居上海,与寄情塞外、怀抱壮志的边疆研究团体往还至密。他与沪上各种边疆问题学会及边疆旅行团交往密切,并对即将考察的旅行团做恳切之演讲,“大意谓长途旅行,足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辟利源而裕国计,宣教化而辟新疆。故步行团为中国青年最好之出路”[11]。概言之,林竞对这些边疆研究团体不仅知之甚祥,还常亲赴指导鼓励其探究边疆。林竞亦主动鞭策后来的边疆研究者,勉励他们探索边疆“须要共同努力,则一切均可化解”[30]。此外林竞专门为周颂尧的《京绥游记》作序,称赞此书“于记载名胜古迹山川文物道里风尚外,又将农垦林牧水利矿产诸项祥查附录于后”,其用意“苟非宏开天府用裕国计,必无升平之望”,“故将以促海内仁人志士之兴起也”[31]2。他在激励后学的同时,也希望能促进更多人去探究西北。1933年,林竞特意为马霄石的《开发西北之先决问题》一书题词:“然真正能作实地考察者仍不多见,或虽实际考察,而能作真确之见解者尤不可多得:兹篇以西北人士作西北实地之考察,其所见自有独到之处。经营西北者不可不手执一篇以资考镜也。”[32]5由此可得,林竞对后学研究西北甚至中国边疆问题的鼓励与支持,追根究底与他开发西北的初衷不谋而合。
恰逢此时,林竞的西北考察日记《西北丛编》出版。《申报》等知名报刊也都多次报道了他的考察日记,有助于人们对西北的认识与开发。《西北丛编》是林竞三次考察西北的日记,其不仅是对西北地区的历史沿革、山川河流、国计民生、民情风俗、自然资源等概况的介绍,更包含了他深入西北对很多社会问题独到的剖析与阐释,形成了价值很高的开发思想。正如林竞所说:“开发西北,目下正高唱入云,而西北实地调查之作无多,此书免可为研究西北者参考之资料。”[2]2当时《申报》称赞《西北丛编》,“我们不得不感谢林竞先生著的这本《西北丛编》的出世”,“林竞先生是位旅行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能用科学的方法、政治的眼光注意到西北边地问题的一个”,“开发西北等问题说,在现今是高唱入云的时髦调,然而在十五年前林先生却早已注意到、而且曾行遍西北,这我们能不说他是开发西北的先觉者吗”[33]。另有期刊指出,“本书著者林竞先生,曾居住西北多年,无远不届,无微不悉,反留心西北者无不知有林先生其人”,兹编“其于政治经济方面,颇为记载。而于人情屈俗,物产,尤祥记无疑”,故此书“足为近日开发西北之参考,至履行西北者,得此为指南,则更为益不浅也”[34]。足见《西北丛编》是开发西北不可多得的资料,为鼓励国人研究西北提供了材料,也为随后的西北考察者提供了参考。陈赓雅《西北视察日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等30年代中后期的西北考察都是以国计民生、民俗风情等问题为主,虽角度稍异,但亦能殊途同归。
林竞在呼吁国人开发西北所展现出的昂扬激情,就像他为《青海风土记》作序时写道,“民国五年我去新疆,回到内地谈起西北两个字,听的人十个倒有九个要瞌睡”,然而“十几年来,在各处和几个同志们天天叫喊着‘开发西北,开发西北’,到了民国十三年以后,居然叫醒一部分人到西北了”[35]3-4。显然,鞭策人们去探究西北,亦是他“西北情结”突显的使命。“九一八”以后,开发西北成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继林竞之后出现了很多西北研究者,他们与林竞有着共同的“西北情结”。郭维屏指出:“我中华目前救亡国存之唯一出路,在乎开发西北也。”[36]1934年,远赴西北考察的陈赓雅也认为,“吾人际此河山破碎,边疆日蹙之秋”,应“前往新疆视察,期以所得,贡献国人,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并促开发计划之日早日实现”[21]8。另一位西北考察者马鹤天在《西北考察记》中指出,“以供研究西北者之参考”[37]。一言以蔽之,以林竞为主的西北问题研究者,甚至不远千里亲临西北考察,可以说他们的最终心愿在于让世人意识到西北的重要,从而完成探究并建设西北的历史伟业。
四、结 语
林竞早在民国初年就三次前往西北考察,亦曾短暂任职于西北。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逐渐形成了浓厚的“西北情结”。如他所言,西北是“理想世界,黄金政治,均可随时日而收工,非同内地之烦杂也。吾愿世之具班、张、赵、霍之才者,毋为鸡骛得失之争,大大悟,相率投荒,工作千秋万世之业,某虽为之执鞭是所愿也”,显然林竞将此情结内化成了动力,并激励世人探究西北的重任。时人称赞林竞“借以引起国民远大之志,是亦林君提倡开发西北蕴藏之先声也”[11]。
值得注意的是,林竞虽为著名的西北研究者,但并非只是个案,尤以当时严峻的社会形势下,依旧有众多学子参与探究西北。诚如马鹤天所说,“西北为中华民族发源之地,以将来言,西北为中华民族最后奋斗之场。唯有开发西北,是中国前途一线生机,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38],然而“开发西北,必先明了西北之实地情形”[39]。所以林鹏侠指出,西北考察的人皆以工业、矿产、农业、民情风俗等为主,“意在促起国人注意西北之重要”[40]3,可见其与林竞有着相同的情结与目的。正是这种情结催化成了“西北”动力,从而推动更多人去探究西北。
回顾国史数千年发展,周秦汉唐,无一不是立足西北而坐拥天下,故西北之重要尽人皆知,这亦是为何民国学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充满着“西北情结”,将西北作为繁荣整个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以林竞为首的学人呼吁国人探究西北的风潮,也促进了民国政府对西北的重视,但囿于各种因素,西北始终未得到有效地开发,这也成了林竞等西北探究者的遗憾。
注释:
①关于林竞的研究内容,学界也有相关论述,如郑立于《足下万里路 胸中八月潮——记中国西部拓荒先行者林竞》,《浙江方志》2000年第4·5期;李倩《民国时期的西北考察家述评——以林兢为中心》,《民族史研究》2011年;刘满《林竞和他的〈西北丛编〉》,载刘满所著《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张琦《林竞开发西北思想探析》,《丝路视野》2018年第18期;等等。
②此部分内容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