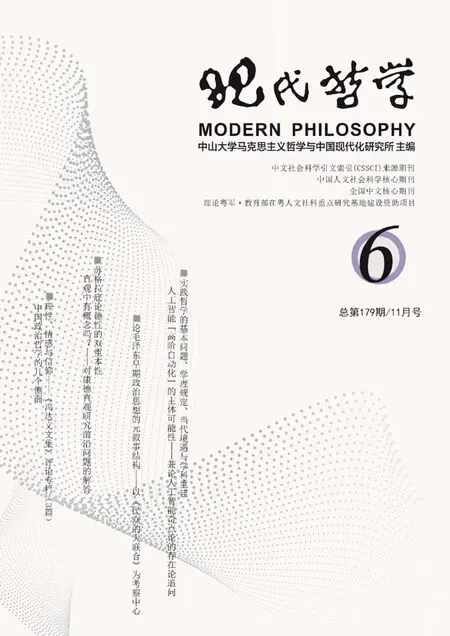论河洛王门学者孟化鲤的一体、安分之学
钟治国
孟化鲤(1545-1597)字叔龙,号云浦,河南府新安县人,师从尤时熙。尤氏学宗阳明而着意于践履,主张体之身心,在人伦日用之发见处用功,不为空虚隐怪之谈,颇为时人推重(1)关于尤时熙之学,参见钟治国:《北方王门后学尤时熙的良知学思想发微》,《孔子研究》2018年第3期。。孟化鲤承袭师说而颇有自得,是尤氏门下之彰彰较著者,但关于其为学的宗旨及评价却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杨东明对云浦以《易》为万古心学之源的易学观及其易学成就颇为推崇,认为云浦是明代河洛地区继曹端、尤时熙而起的大儒(2)[明]杨东明撰,邹建锋、李旭等编校:《祭云浦孟公文》,《北方王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88—1089页。。邹元标、冯从吾等人也认为云浦是克绍二程学脉的真儒(3)[明]邹元标:《奉政大夫吏部文选郎中云浦孟公墓碑》,《愿学集》卷5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6页;[明]冯从吾撰,刘学智、孙学功点校整理:《祭孟云浦先生文》,《冯从吾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5页。。云浦的弟子王以悟、吕维祺总结乃师之学以无欲为本,而其教导门人则重躬行而后论说,以孝弟忠信慎独为要,不为高深玄远之论,可谓平实、易简、纯粹(4)[明]王以悟:《理学云浦孟先生像赞》、[明]吕维祺:《理学孟云浦先生传》,《北方王门集》,第550、548页;[明]王以悟:《祭云浦先师》,《王惺所先生文集》卷7,明天启刻本。。黄宗羲认为其所言皆师说,并无创获(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9,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7—648页。。孙奇逢的评价则居于褒贬之间,既称其“从统宗处理会,其魄力自大”,又言其“主脑不清,文辞繁多,终是曲儒”(6)[清]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上引诸说到底何者更接近云浦之学的原貌?应当如何总结其为学宗旨?笔者拟就其常提的几个核心话头、理念加以详析,梳理其学说的内蕴及脉络。
一、万物一体之仁
就孟氏现存的著述来看,其所论述涉及到理学的方方面面,确实有孙奇逢所说的头项繁多的面貌。但以其核心理念而言,其为学的头脑、主旨还是很清楚的,万物一体之仁便是其中之首出者。云浦曰:“学问不外求仁,来书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已。圣人所以能如是者,无欲也,学不厌也……只此便是天地万物一体根基,所云学问要立根基,在此也。”(7)[明]孟化鲤:《答丘汝芹》,《北方王门集》,第397—398页。云浦此处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得自师说的对学问目的的看法:儒者的学问惟在于求仁(8)云浦认为其师之学“大要以孔门求仁为宗,而私淑于近世王文成致良知之训”。(同上,第479页。)。所谓仁,当然是此心之体、天命之性,性分所固有者,更是成己而成物、将天地万物视作一体的修养境界和切己体知。正如陈来指出的,心学的特点是把仁体内在化,将仁体说成心体,关注仁的体验意义和境界意义(9)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71页。。云浦此处的论述正是在境界和体验上谈说万物一体,并将之贯穿、归结到作为心之体的仁上。云浦指出,圣人之所以能够达至万物一体,就在于其无欲,这显然是从其所用工夫达成的结果上来说的。可见,王以悟、吕维祺总结云浦之学以无欲为本不可谓不准确。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无欲工夫有着更根本的指向——求仁,“孔门学问只是求仁”(10)[明]孟化鲤:《阅〈近溪集〉臆言》,《北方王门集》,第518页。。
仁是人之心性的固有者,而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生生之意即人心之仁,心性之仁有宇宙论上的依据、来源。云浦之论万物一体之仁包含了宇宙论和心性论两种进路,而且这两种进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心性之仁得自于天地生生之仁,故二者是二而一的。关于前者,云浦指出,易只是乾坤,而乾坤(乾坤、天地、阴阳在一般意义上可以通用)皆以生物不已为其根本品性。《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大德(根本品性、特征)就是能够不断地化生万物,生生不已。天地生生之德表达在人身上就是仁,其最常见、最真切的发露就是孩提知爱知敬、见孺子将入于井而怵惕恻隐(11)[明]孟化鲤:《答安良弼》,《北方王门集》,第510页。。因此,仁所包含的人际之间相互关爱的内涵与天地生生相关,或者说仁的万物一体之爱内涵要以仁的生生不息内涵为宇宙论依据。具体来说,万物一体之仁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人与天地万物原本一气相通。天地化生万物当然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气的因素,但气这一概念不仅从物质要素、力量上指陈万物一体的可能性基础,也兼包了伦理道德修养的工夫论含义,因此云浦才特意强调集义以养浩然之气的重要性。例如,云浦的弟子认为人之一身渺乎其微,因而对人之浩然之气能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云浦的释疑采取的就是以气说心的理路:人与天地万物异形而同气,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当然能够通达于天地万物(12)[明]孟化鲤:《答马子厚》,《北方王门集》,第410页。云浦又说“夜气即是良心,良心即是仁义”,也可作为其以气说心的一个佐证。(同上,第521页。)。云浦说:“今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则生生者人之心也。”(13)[明]孟化鲤:《函谷别言》,《北方王门集》,第490页。天地生生之心即人之心,人之心从气上来说就是通达于天地万物的浩然之气。所谓“浩然”是强调此气的感通直遂,云浦称之为“真心”的流露(14)关于“真心”,云浦说:“盖必其心如乾之大生,如坤之广生,盎然出之,顺遂不可遏,浑是恻隐之心,而后谓之真心。”意谓天地大生、广生之心表达在人之心上,能够顺遂地呈露而不可遏抑,就是“真心”。(同上,第490页。)。因此,要使此气充塞天地,须做集义的工夫。集义工夫,如同尤时熙所说,不是事上的积累,而是“即乎心之所安”(15)[明]尤时熙:《答化鲤·四》,《北方王门集》,第298页。,是心上用功。由此,我们可以过渡到从心性论角度对云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讨论。
我也,身也,诚也,恕也,仁也,皆心也。万物皆心也。故孟子首句说我不说身,次说身不说我。其说诚,说恕,说仁,又各不相凑搭,而皆不言心,则莫非心也。况口耳目乎?可以识一贯之学矣……身自备万物,万物皆是身。生来本如此,无初既之别。(16)[明]孟化鲤:《阅〈近溪集〉臆言》,《北方王门集》,第521页。
“万物皆心”并非取消万物的独立存在,而是就其与心的意义关联上指陈此心对万物的统摄作用,与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并无不同。同理,“万物皆是身”也不是对一个物理事实的指陈。万物皆心(身)的实质是指万物一体,不过这一“一体”是从自家身心一体的层面上来说的,进而在工夫论上指明做工夫的方向,即反求诸己、反身而诚、无我无物。感觉有我,当然不是一体之学;觉得无我,也不是真正的无我,因为真正达到万物一体之境,就不需要再起一个“无我”之念(17)[明]孟化鲤:《尊闻录》,《北方王门集》,第365页。。真正的无我是去我之私,去除以一身一家为我的小我之私。同理,无物也不是以万物为虚无,而是去物欲之遮蔽,去除对事物的过分执着。能无我、无物,才能见得真我、扩充此心,突破躯壳的局限,反身而诚——真的如此、确实如此——见得万物皆备于我,才能真正以万物为与我一体相关者或同体而在者,才能达到当下仁体全具的原本境界。进言之,正是在我与他者、万物原本一体共在的意义上,我才是我(真我),我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与他者及万物的原本一体。因此,我一定要通达于天地万物才能“其体备”——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体段完备的我。离开万物,离开己身与天地万物的原本共在,我也就不成其为我;反言之,天地万物也不能脱离这一共在,如果没有我,天地万物也就陷于灭熄了(18)[明]孟化鲤:《答陈实夫》,《北方王门集》,第502—503页。。因此,云浦断言:“此心、此性、此学与天地万物一体,何大如之!故曰从大体。”(19)[明]孟化鲤:《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523页。这个我与天地万物原本共在的一体才是真正的“体”“大体”。仁,只有在万物一体、与物同体的层面上才是真正的仁。云浦说:“人之一心,真诚恻怛为仁,此是本体,即是全体。凡发念应感处,不论大小轻重,即此全体发见,盖一端即统体也。”(20)[明]孟化鲤:《读〈参元三语〉臆言》,《北方王门集》,第517页。此心的发动应感(仁心的发动总是应事物之感而起的)、真诚恻怛,便是仁的全体呈露,因为人我一体、物我一体,故我之仁应感而动之一端便是统体之仁的当下呈现。
正是在此一体之仁的意义上,云浦认为孟子所说的“仁,人心也”说的是仁与心的同一性。“言仁即是心,心即是仁,非有二也。程子云‘义、礼、智、信皆仁也’,随出异名,总是一仁,仁则只是此心。”(21)[明]孟化鲤:《阅〈近溪集〉臆言》,《北方王门集》,第520页。按程子原话作:“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意在于指出仁对于义、礼、智、信的统摄、包纳以及识得与物同体之仁在工夫上的必要性、优先性。([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义、礼、智、信,名异而实同,都从属于仁或者说都是仁的内容;而仁就是心,心就是仁,二者本质同一。不惟如此,云浦进一步认为心、性、仁都是一个,不必在其中过于区分。缘此,云浦在与孟我疆的通信中指出,我疆认为人与仁“分之两端、合之一圆”之说表现出来的分别性并不妥当。
《大学》言心不言性,非遗性也,心即性也。若以其言心而遂目《大学》非尽性之书,可乎?《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遗心也,性即心也。若以其言性而遂目《中庸》非传心之书,可乎?推之《论》、《孟》、《五经》,或单言,或并言,词有攸当,理非二致。由是观之,心性之一彰彰矣,夫何疑?(22)[明]孟化鲤:《与孟我疆》,《北方王门集》,第379页。
云浦认为,心、性(也包括人、仁)本一,曰心、曰性只是言词上针对具体语境的调适,在实理上并无差别(23)这种将心、性、仁合论的方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其据以批评孟我疆之说则未必能惬我疆之意。我疆辩解说:“两端之说,自孔子始发之,颜子得之为文体之说,子思得之为费隐之说,孟子得之为形色天性之说,缘天地万物、古今圣传,只此两端而已矣。此外无道也,故曰一以贯之。观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指而谓曰‘合而言之道也’,分之则有仁与人之两端,合之则仁即人、人即仁也,又何异乎?”孟我疆此处强调仁与人合中有分,不能以本质的合一而取消其分别,这与云浦的统合性思路当然不同。实际上,孟我疆并非不知心、性的同一。因此针对学友对其识心不识性的批评,我疆回应说:“理一也,自其性之灵觉谓之心,自其心之生理谓之性,性无为心亦无为,心有觉性亦有觉,性非有觉,心何从而觉乎?此舜之所谓‘道心’,汤之所谓‘恒性’,孔子之所谓‘成性’,孟子之所谓‘良心’,皆是理也。谁曰心为心,而性为性乎?”心之生理是谓性,性之灵觉是谓心,心、性互发,体用一原。这段话所表达的理念与云浦并无不同,足见云浦对其的批评并不相应。([明]孟秋:《孟我疆先生集》卷5,清康熙五年刻本。)。可见,云浦的思想比较重视诸概念的统合性,因此才对万物一体之仁学如此推崇。心、性、仁人人本具,为仁由己,我欲仁则仁至,求仁、为仁的工夫是简易的,是愚夫愚妇也能知、能行的。但为仁工夫的易简并非指不用工夫,要达至万物一体之仁,也须重视去除私欲的工夫。云浦颇重视周濂溪的无欲工夫。他指出,心体(性)本虚,“夫心体本虚,人性上元不可加一物也”,心体原本就不遮蔽、滞塞于私欲(24)[明]孟化鲤:《答陈实夫》,《北方王门集》,第503页。。此虚不可被解释为空虚、一无所有,因为倘若如此,便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一意义上的虚何以区别于二氏之学?(25)云浦对佛教持总体上的批判、拒斥态度,如其云“慨洙泗濂洛既远,世之学士遂失其宗。趋步者近迂,训诂者多俗,而妙解者又闯入于佛乘”。再者,佛教用生死轮回来劝人向善,让人因怖畏而生信心,总不如孔孟之言来得平正切实。因而,云浦才在写给邹德涵(1538-1581)的书信中称道邹氏的《正学论》于世教大有裨益。邹氏《正学论》不仅批评道、阴阳、名、法、墨及佛教诸家,也批评训诂、辞章之学,在儒学内部也批评离动以求静、离用以观体、离人以洁己者为异端,主张即动即静、即用即体、即人即己,这种由用以见体的工夫理路也为云浦所持。([明]孟化鲤:《祭我疆先生文》,《北方王门集》,第479页;[明]孟化鲤:《答李》,《北方王门集》,第396页;[明]邹德涵:《邹聚所先生外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15页;[明]邹德涵:《邹聚所先生文集》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7册,第302页。)其二,虚何以能达至明、通呢?后一问题也可以转换成这样的形式:虚既然是空无所有,则明是何者明?明的是什么?通是何者通?又通个什么?缘此,虚应是指此心没有欲望填塞的状态,无欲则能虚——无蔽、无滞,无蔽即能明——光明、照察,能明即能通——通达、流行。“虚即明”说的是心体原本没有私欲的遮蔽;“明即通”说的是心体原本没有私欲的滞碍而自能通达于发用。此外,“虚即明”“明即通”也表明虚、明、通之间并非前后相继的递进关系。云浦关于“动直”的解释与此类似,人的生机原本直遂,没有任何邪曲,不直是因为私欲的“揉”(“揉木为轮”之“揉”,使之弯曲)使然。因此,无私欲则其动而能直。“直即公”,中心无私即是公——公正、正直;“公即溥”,行事公平、正直而无私即是溥——溥博、广大。“直即公”“公即溥”同样表示直、公、溥之间没有前后的承续关系,不是直而后公、公而后溥。要之,工夫的根本在于无欲,能无欲则自然能静虚明通、动直公溥。
二、安分尽心
安分尽心(云浦有时也称为随分尽心(26)[明]孟化鲤:《尊闻录》,《北方王门集》,第365、366页。)是其得自师说的核心理念之一。云浦称尤时熙晚年“有慨于世之学者,动辄谈及玄虚要眇之乡,以为入微,而考其躬行则不逮,故惓惓勉以职分见在处用工”(27)[明]孟化鲤:《祭西川尤先生文》,《北方王门集》,第479页。云浦大阐安分、尽心之学,同样是出于对其时学风、士风的忧虑,“今世士驰骛词章以博声利,风靡已甚,求真见性分不容已,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从而求师者,殆寥落如晨星乎!”([明]孟化鲤:《述言勉赵德高》,《北方王门集》,第487页。)。此说也是其万物一体之仁学的自然延伸——成就万物一体之仁,正是人的本分,“……此学元是正景事,非分外者,仁为己任,曾子吾师哉!”(28)[明]孟化鲤:《与徐仲云》,《北方王门集》,第424页。
“分”有三个内涵:分别、区分;本分、分位;分量、能力。事物以及人之间的分别、差异是其各自存在的前提,“一体”是以分别、差异为前提的“一体”,万物一体之仁绝不是以取消人际以及人与物的差别、区分为前提的。因为这一分别、区分的存在,个体才有在万物一体的物质世界、伦理世界中的分位以及所应尽到的本分。人总是在家庭、宗族、乡党、国家中存在的人,人生活于其中的伦理关系构成的世界是先于个体的人而存在的。由此,人天然地扮演了多重伦理角色、身份,承担着多重伦理责任、义务。这些身份和地位提醒人必须充分地依照其分量、能力去完成这些身份、地位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是为安分、尽心之学。
“安分”二字,首先提示的是在人人皆有的见在、当下的职分之尽上用功。云浦拈出“见在”二字加于“职分”之上,其意在于指出工夫的当下、见在性,反对好高骛远的工夫倾向。天地之所以高、厚不是不应当追问,但如果学者放弃目前、眼下应尽的本分而去追求所谓高明之境,则极容易产生两种恶果:其一,意见横生,知识障蔽,沦于玄虚而不自知;其二,如此则非但达不到圣贤的地位,反而连当下的所当为者也不能为,南辕北辙,愈行愈远。甚至由此造成一种希高慕外的学风,使学者以为可以一超直入,进而导致一种“圣者麟出”而世风日下的荒诞景象出现(29)[明]孟化鲤:《答杨晋庵》《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393—394、527页。。“今人好高,只不安分。”(30)[明]孟化鲤:《答顾泾阳》,《北方王门集》,第412页。安分,首先意味着人要安于当下的职分、本分,思不出其位,由其当下所居之位出发去为所当为,这是当下可见、可行的工夫,不要心生企慕怨尤而向外驰逐,因此才能无入而不自得。云浦认为,是即孟子所说的“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这绝不是不思进取、回护推脱,而是在工夫见之于实行的可能性上指出儒者所能用的工夫的次第和重心所在。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一体之仁的达成要从当下的职分之尽上着手(31)由此可见,云浦的安分之说对尤时熙的“于发动处用功”的工夫理路的继承。与尤氏一样,云浦有感于其时学者“徒骛玄虚,考诸躬行无当”“谈本体而玄虚枯寂”之弊病,主张即当下的本体之发见而用功,“自求见本体之说兴,而忠信笃敬之功缓,或且视之为琐屑,遂令正学名实混淆,而弄精魂者窃藉以为口实”。可见,云浦并非不求本体,而是认为在工夫论上于人伦日用中行其忠信笃敬先于、急于求见本体,如此才算是实学。云浦举了一个得自师说的比喻,颇能说明其于发处用功的理念。此处不妨一引:“夫道一而已矣,职分即道体也。譬汲水然,未闻汲水者舍面上而从事渊底也,面上水与渊底非两也。”道是一个道,本体上求、工夫上求都是求道,但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如同汲水,面上的水(发见处)与渊底的水(本体)原本不是两种水,但汲水者必定不会舍汲面上之水的易,而从事于汲渊底之水的难,工夫于发处用才能归于平实易简。([明]孟化鲤:《答顾泾阳》,《北方王门集》,第434、435、499、477页。)。人的分位不同、气力不同,则所要安、尽之分也不同,人随其分而尽其分,故时时是学、处处是学、事事是学。云浦指出,安分工夫不因所用事情的大小而或用或否,总要随宜而为(32)[明]孟化鲤:《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528页。。可见,安分尽心之学在具体的工夫节目上具有细密、入微、切己、踏实的特点,“安分尽心是脚踏实地工夫”(33)孟昭德主编,扈耕田、曹先武点校:《孟云浦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此外,安分之学也有竭尽所能地完成本分、分位所要求的责任的意味。云浦说:
夫圣贤之学,大学也。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准则,故成己必至于成物,物成而成己之分量始完足而无歉。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意之也。(34)[明]孟化鲤:《答陈连山》,《北方王门集》,第419页。
云浦大阐安分、尽分之学,除有批评当时普遍败坏的学风、士风、世风的意图之外,更有直指阳明学内部出现的由“顿悟超识、不由阶级之说”造成的忽略躬行实践弊病的意味。“圆融”“超悟”不是忽略职分当为的借口,因此云浦说只要是分之所在,那就应不避利害生死而充分地尽责尽职(35)[明]孟化鲤:《答杨晋庵》,《北方王门集》,第392页。。应尽之分是性分之固有,而贫富利害只是当下所遇之境况的顺逆,并不能对人人原本完具的本性有所加、损,因此安分工夫便应以尽其性分之固有为最终境地(36)[明]孟化鲤:《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527页。。云浦的这一观点与冯从吾的说法可谓不谋而合。冯氏说:“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分定故也。只一个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见人只是安分,便是尽性……陆子静谓:‘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才说得出‘分’字意。”(37)[明]冯从吾撰,刘学智、孙学功点校整理:《示四氏曲阜两学诸生》,《冯从吾集》,第128页。孟氏文集中有答冯从吾的书信一封,但冯氏文集中未见其来书,或许二人曾就安分之学进行过交流,故二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成圣成贤之学是“大学”,是讲求修己治人之大道的学问,在规模、气象、内容、方法上区别于讲求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的小学。云浦认为,大学首要的目标是由明己之德进至明明德于天下,所以成己而成物便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己身与他者原本共生、共在,因此成己必须达至成物(当然也包括立人、达人在内)而后才能最终完成。成物而最终成己,是自己分内之事,只有最终达于成物,才可谓尽了己分。这一观点发挥了安分之学的尽分义,从“分”的分量、范围、程度意义上扩展、深化了安分之学的内涵。
孟化鲤的安分之学还有第三个方面的义涵:知行合一。他说:
学不求诸心,开口便是病。上古无机变之习,无多欲之慕,亦无所谓知。饥食渴饮,惟率其所觉而为之,即今赤子之知可验也。孔曰“无知”,文曰“不识不知”,是己虚灵之体,不分知行。(38)[明]孟化鲤:《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523页。
云浦指出,他者与自我皆统括在万物一体之大我之中,我之性就是他者之性,人性不会因为个体的生死而或存或亡,也不因个体的寿命长短而有所加损。对此性分“见之定”——有确定的、真切的体知、见解,才能真正达于道、尽其分(39)[明]孟化鲤:《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522页。。云浦又说“非大开心目者,不足以语此学”(40)同上,第528页。,其意在于指出扩充分量(包括对自己之分的体知)对于尽分之学的重要性。此处的“知”不是闻见之知识,“学问元是易简的,人自有知识后,便染习坏了”(41)[明]孟化鲤:《书徐仲云便面》,《北方王门集》,第495页。,被工具化了的见闻之知有可能遮蔽良知;也不是生理本能意义上的觉知——如饥知食、渴知饮之类,而是孔子所说的“无知”、文王所说的“不识不知”之“知”,“无”“不”二字提点的正是其与上述的知的不同。如果真正知得、见得万物皆备于我、莫非我分内之物,自然就能无所不爱而尽其分量(42)[明]孟化鲤:《答安良弼》,《北方王门集》,第509页。。当然,“知分”之“知”并非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生理本能的觉知不能并存,对“分”的真切体知也表达在这些知当中,如云浦曾批评常人见到圣人无所不知,便以为圣人不可及而不求知,这种对圣人的想象是不准确的,圣人也好问好察(43)[明]孟化鲤:《己千录》,《北方王门集》,第525页。。再如,在提示初学者如何用功时,云浦说:“凡坐时须知在此坐,起身行动须知起知行,接应宾客须知接应。一切细微净秽事,务须知。”(44)[明]孟化鲤:《初学每日用功法》,《北方王门集》,第500页。一般的待人接物的知识甚至一切细碎的事务都要知道。此外,这一“知”也有醒觉、精察之义。动作云为、应事接物都应保持此心的醒觉,对其所知之物、事明辨精察,才能不被物欲蒙蔽。这一意义上的知,是见于躬行实践、人伦日用中的知,所以其本身与“行”是合一的。故可以说,云浦的安分之学内蕴了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理念。(45)可见,王以悟和吕维祺对云浦的工夫论的重躬行特点的总结不可谓不恰当,但躬行实践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工夫论特征,因此用之概括云浦的学术宗旨并不能将其学术的特点全部呈现出来。另外,需要补充的是,云浦常将安分与尽心合说。一般而言,安分自然包纳尽心,尽心是人在知分、安分、随分、尽分时能够竭尽其心力,故本文不再对其“尽心”说展开分析。
综上所论,孟氏友人杨东明、冯从吾、邹元标等人有忧于其时学风的败坏而特意标揭孟氏之学的拯偏救弊的作用及其在阳明学发展史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带有时代性色彩的褒誉。孟氏门人对其工夫论的核心主张的总结相当准确,但经由上文的讨论,可见“无欲”二字尚不足以综罗其学术的全部要旨。云浦之学,以求得万物一体之仁为归的,其无欲、无我、安分、尽分诸说,既重视去私去蔽以复其本体的工夫理路,又不忽视任运本体流行发用的工夫理路,故孙奇逢认为其主脑不清故而终是不通达的曲儒的看法并不恰当。就其在日用平常处用功的工夫论主张而言,云浦之学确实极为平实、真切、细密,但我们不能因这一工夫论主张承袭自其师尤时熙,便采信黄梨洲之说而认为孟氏之说仅守门户而无大发明。云浦既着力于纠正其时学风的偏弊而有工夫论上的重视躬行实践的平实面相,又对高明的本体(特别是万物原本一体这一本体)有较深切的体验,因此尽管他并未以良知为其形式上的论述核心,但就其能把握阳明学的真精神而言,视之为一个纯正、通达的阳明学者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