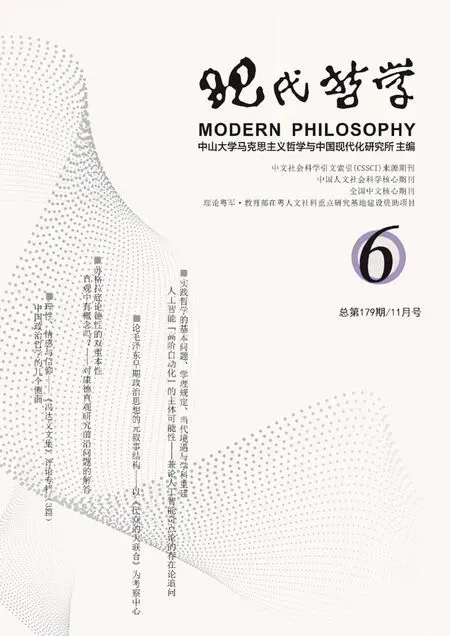责任,抑或是爱?
——列维纳斯与马里翁论人格个体化
余君芷
现象学从起初便与个体化问题结下不解之缘。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主体的个体化思考的不断深入是推动现象学发展的一个核心动机。以个体化问题为线索,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象学在一代代现象学家中的传承和变革。列维纳斯和马里翁的个体化理论作为其中的典型示例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现象学的卓越性——二者的个体化理论都具有两个面向:自我的个体化和他人的个体化。马里翁认为,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并不彻底。他基于对此的详细批评,提出自己的个体化理论。然而,一些学者如格施万特纳(C. M. Gschwandtner)和君特(L. Guenther)认为,马里翁对列维纳斯的批评并不公正,并且马里翁自己的个体化理论相对于列维纳斯而言反而是一种倒退。基于对列维纳斯和马里翁的个体化理论的详细考察,本文试图指出,格施万特纳和君特实际上错失了马里翁与列维纳斯的根本分歧所在——人格个体化问题。
一、列维纳斯:自我与他人在责任中个体化
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建基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总体化倾向的批判之上。“总体”作为一个“统治着西方哲学的概念”,使得“个体被还原为那些暗中统治着它们的力量的承担者”,以致“个体正是从这种总体中借取它们的(在这一总体之外不可见的)意义”(1)[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第33、48页。。尽管个体概念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支配西方哲学史的理性认知范式通过概念化把诸个体整合进一个总体,使它们的个体性消失在其中(2)[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第33、48页。。列维纳斯认为,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便是这种总体化的代表。胡塞尔所提出的“视域”概念正是那种总体,个体存在者在其中被衡量并且被赋予意义(3)[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个体存在者被视为意识构造的成果,但“个体化所具有的实际性在此被翻转为有关个体的概念,并因此而被翻转为有关个体之死的意识,在此意识之中,个体的独特性丧失于其普遍性之中”(4)[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1页。译文有改动。。在海德格尔处,存在本身相对于存在者具有优先性,这就意味着“与作为一个存在者的某人的关系(伦理的关系)从属于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系”(5)[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7页。。然而,“存在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特殊化,也从不进行特殊化”(6)[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列维纳斯的这个判断过于绝对,海德格尔强调存在问题并不能以一种单纯是形式的、抽象的、理论的方式来通达,而是要回到此在的实存的基本经验去探寻,此在在“向死而在”中个别化。([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63—365页。)。
列维纳斯认为,总体化的哲学并没有给真正的个体留下空间。在西方哲学转向主体性哲学以后,个体概念作为总体化工具尤其成问题。列维纳斯将个体所基于的总体批评为“无人称的”,更确切地说是“非人格的”(7)[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第二版序言第1页,正文第4页;[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7页、33、232页等。,个体由此丧失了其个体性和人格性。对列维纳斯而言,真正的个体应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作为个体的主体应当是人格性的。它的个体性不来自比较,也不来自被涵括在某个概念的外延中,也不来自它偶然的或本质的属性(8)[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前言第3页;[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1—33页。。这样的个体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伦理和正义要求这样的个体性作为它们的可能性条件(9)[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236页;[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46页。。那么,作为个体的主体,其独一无二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如何被建立的?列维纳斯的回答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能重新构成一个总体,而应允许自我与他人之间留有绝对的距离,不会彼此吸收或消解、而是彼此保存,同时二者又有直接的的关联(10)[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81—185页。。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与他人都是独特的,也是人格性的。这是列维纳斯一贯坚持的论题。虽是如此,列维纳斯对于这个论题的具体论述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面貌(11)关于列维纳斯前后期理论的一些主要变化及其原因和理论后果,参见余君芷:《论列维纳斯哲学中“爱欲”理论的转变》,《理论月刊》2019年第12期。。
列维纳斯早期着重于探索主体逃离其实存的牢笼的可能性。虽然主体通过具有身体而在匿名的存在(il y a)中具有一个位置,使主体能够占有它自身的实存(existence),但主体从此就被束缚在它的实存之上,“如同自我(moi)被牢牢地系缚于无人称的自身(soi)”(12)[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第102页,第108—109页,第117页。。主体厌倦其实存,却无法摆脱这个重负,因此主体渴望一种逃离。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具有超越性的关系,一种“无媒介、无协调人的关系”,“令人敬畏的面对面(face-à-face)”。在《从实存到实存者》(13)笔者以为《从存在到存在者》译为《从实存到实存者》更为恰当,因此在正文中选用《从实存到实存者》的译法,在注释中保留引文所出自的中译本的书名译法。和《时间与他者》中,爱欲(éros)是这种关系的代表(14)[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第118—119页;Emmanuel Lévinas, Le temps et l’autre, 9ème é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pp.79-81.。在爱欲关系中,他人的他异性(alterité)与形式上、逻辑上的差异之间有着根本区别,他人的他异性从女性(feminité)概念得到规定(15)Ibid., p.14.。在列维纳斯早期著作中,“个体化”这个术语并不常见,但主体对自身实存的占有——成为一个“实存者”——就是一种个体化。后来,“个体化”概念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并且列维纳斯早期的主要思想都被吸纳到他之后的论述之中。
到《总体与无限》时期,“个体化”成了列维纳斯一个正式术语。自我通过身体来占有它的实存,这个事件被细致地描述为一种“家政”“内在生活”“心灵现象”“享受的自我主义”,它以“自身聚集并拥有表象”(16)[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为特征。这种内在生活就是自我的个体化原理(17)[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这种个体化并不是作为概念的个体化,自我由此获得的独一无二性(unicité)是一种外在于任何种属的独特性(18)[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
自我在内在生活中的个体化,已经以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面对面关系为前提(19)[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面对面是一种伦理关联,其实质是话语,他人在其中作为“面容”自身显示为绝对的他者,与自我保持着绝对的距离即保持着超越,因此他人与自我并不构成一个总体(20)[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他人显示为坦率的对话者,并且面容本身已经是一种原初的表达、一种促使我对他负责的命令和呼唤(21)[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面对面作为自我个体化的前提,并不是在存在者层面或者存在论层面的奠基,而是为自我的内在生活提供伦理正当性。一方面,面容的坦率和赤裸是一种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凭其自身的显现;另一方面,这种赤裸也是一种赤贫,他人作为陌生者和一无所有者来临到我,向我投来恳求和要求的目光(22)[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他人的这种“临显”质疑自我享受的合法性,质疑我的自由并使我羞愧;但同时,他人的在场也为自我的内在生活的自由授权,即赋予其伦理正当性:自我的家政是为了欢迎他人,将自我所占有的东西呈交给他人,以此回应他人的面容的呼唤,对他人负责——这也是自我的言说的实质(23)[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在面对面的关系中,他人作为人格性的存在者呈现自身,自我也在他人对我的呼唤(appel)之中作为能负责者(responsable)而达到自身最终的实在,也就是人格性的实在(24)[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但在《总体与无限》中,爱欲关系已不再是面对面关系的典范,而是与其截然不同,爱欲中的他人是“非人格的和非表达的”(25)[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
自我和他人的个体化的根本来源在于作为话语关联的面对面关系。在面对面关系中,自我 “作为对话者,作为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者,作为面容”(26)[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32页,第33、129页,第95、97页,第133、150页,第10、11页,第41、185页,第50—51页,第51、60、64、158页,第122、163页,第244、255页,第241页(译文有改动)。而具有个体性。 “作为面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表达,它意味着当自我作为出发点时,他人作为面容向自我展现;反之,当他人被放到自我的位置上,自我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是他人的他人,自我作为面容向他人展现。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上述引文所表达的自我的个体性同样适用于他人。
与《总体与无限》相比,《别于存在》的论述更多集中到自我之上,“独一无二”成为形容自我的高频词。《总体与无限》将自我规定为在家政中自身聚集的同一者(le Même),而在《别于存在》中,自我这种同一性被明确否定了(27)[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92页,第146(译文有改动),第146页。。在此,自我的独一无二是一种“没有同一性的独一无二”,即“作为不具同一性者,此一者(l’un)[自我]超出了那在自身之内并且为了自身的意识,因为此一者已经是对他者的替代”。
自我“不具有同一性”,意思是不具有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后者意味着自身对自身的认同或者自身到自身的返回。对列维纳斯而言,自我是身体性的主体,在身体性的完全被动性即感受性中,自我暴露于他者对自我的传唤(assignation)(28)传唤(assignation)是一个法律用语,意为传讯某人到法庭接受审判。这与《总体与无限》中所说的“末世论审判”相呼应,主体正是在这种传唤中从总体超拔出来,在对责任的承担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个体性。([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234—236页。),这种传唤并不将我带回到自身之上,而是“从我身上剥除所有同一性的本质”(29)[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28页。László Tengelyi认为,这是列维纳斯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上相对于《总体与无限》作出的最大改动。实际上,列维纳斯一直坚持自我的非同一性,即自我在其自身性中的分裂,只是在不同时期对这种非同一性有不同论述。在《从实存到实存者》中,这种非同一性表现在自我对自身实存的厌倦;在《总体与无限》中,这种非同一性表现在生育之中;在《别于存在》中,这种非同一性表现在自我总是处于他人的呼唤的扰乱之中。(László Tengelyi, “Einzigkeit ohne Identität bei Levinas”,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VI, 2006, p.66;[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第107—109页;[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260页。)。自我向自身返回的通路被阻断,自我由此被“去中心化”,成为一个“为他”的主体,自我从而具有一种更根本意义上的同一性、自身性和主体性(3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93—252页,第141—142页,第265—284、251—252、214页,第209—210页。。自我在被动性中的暴露是无法逃避和拒绝的,这种被动性本身就是对他者的传唤的回应、对他者的责任的承担;因为这是完全的被动性,所以无论自我愿意与否,自我的主体性都在于献出自己而为他人受苦,以至于以自身替代他人的程度(31)[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93—252页,第141—142页,第265—284、251—252、214页,第209—210页。。正是在这种对他人的传唤的回应、对他人的替代中,自我被个体化,以至成为“独一无二者”,成为人格性的主体,(32)[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93—252页,第141—142页,第265—284、251—252、214页,第209—210页。。他人作为面容向我发出呼唤,他的个体性不是个体对象的个体性,而是一种“极端的独特性”(singularité extrême),它是他人对我的传唤本身,并且他“在我将他作为τóδε τι[此,某]而指出之前就已经传唤了我”,“他在被认出之前就命令了我”(33)[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93—252页,第141—142页,第265—284、251—252、214页,第209—210页。。
综上所述,主体的个体化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达成,这的确是列维纳斯一贯的坚持。虽然列维纳斯在不同时期对这种关系有不同描述,但与他人的关系始终具有一种神学深度。这不但体现在列维纳斯对诸如“临显”等神学术语的直接借用,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模型(无论是早期的爱欲关系,还是后来的面对面关系)对圣经的明显参照,更体现在上帝被列维纳斯视为他人相对于自我的绝对的他异性、超越性和在先性的前提,也是自我向他人负起责任并在责任中替代他人的根本动机:“上帝并不单纯是‘首要的他人’或‘最卓越的他人’或‘绝对的’他人,而是异于他人,而且是另一种方式的他人,这另一种方式的相异性先于他人之相异性、先于对邻人的伦理责任,这上帝和所有的邻人都不一样,他超越甚至于不在场,甚至于可能和il y a(有、存在)之冥然兀在(remue-ménage)融合起来。在此融合中,对邻人的替代得以‘破出存在’,也就是说赢得了尊严;在此融合中,无限之超越得到显耀。”(34)[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中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15—116页,第114页。因此,上帝也是自我与他人在彼此关联中得以个体化的根本原因,只是上帝并不是作为在场的存在者起作用,而是作为“无限”,作为一种“卓越意义上的善”(35)[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中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15—116页,第114页。。
虽然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涉及自我和他人,但实际上在《总体与无限》和《别于存在》中,列维纳斯对个体化的论述主要还是集中在自我身上,对他人的个体化着墨不多。这成为马里翁批评列维纳斯的出发点。
二、责任的个体化的不充分性
马里翁对列维纳斯的批评着眼于他人的个体化问题。在《圣爱绪论》的第六章《爱的意向性》中,马里翁将他人的显现方式规定为他人施加到自我之上的意向性,即“反意向性”(contre-intentionalité)(36)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他人对我的注视在我之中激起一种责任感,我感到自己对他人负有无限的责任,我对这种责任的意识超过了对我自己的意识,它压垮我,拆解纯粹自我的意向性,使我向他者敞开(37)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它阻止了超越论意识向自身的返还,使自我意识到自己对另一个意识有所意识(38)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在这种意识中,对于自我而言,他人具有优先性和在先性(39)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
这里表现出对列维纳斯的面容理论的明显继承。然而,马里翁认为,“反意向性”虽然在自我之中产生某种特殊感受,却不足以使他人个体化,因为命令涉及所有他者,它激起的是义务(devoir)。义务具有形式普遍性,不取决于具体涉及的是哪个个人。律法的命令感触我(m’affecte),在我之中产生一种敬重,这种感触使得普遍的命令在我之中具有一种类似我的感受的特殊性(particularité),但此敬重并不是对某个体他者的敬重,而是对普遍律法的敬重,某个他者的面容只不过是律法的普遍者借以感触我的一个中介。这里有一种对他者的中性化(neutralisation),他者的面容仍是可替代的。如果要使命令导向对他者的个体化,就需要从义务过渡到责任(responsabilité),即我并非通过他人来服从命令,而是通过命令直接对他人负责。然而,在责任中,他人被中性化的疑虑仍然没有消除,这里仍存在替代的可能性,因为责任的无条件性——只要是一个面容,我都对其负有责任——蕴含了一种普遍性(40)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117, p.119.。责任虽能触及如其所是的他人(autre comme tel),却不能触及对我而言是严格不可替代的某个他人(tel autre),不能达到一种“原子级的特殊性”(particularité atomique)、一种“这性”(l’haecceitas)(41)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117, p.119.。
在另一处文本《从他人到个体》中,马里翁通过梳理列维纳斯各个时期的个体化理论来详细说明这一观点。他认为,列维纳斯出发点在于用伦理学来克服海德格尔的实存的匿名性,(42)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他试图建立实存者(existant)相对于实存(existence)的优先性,即自我通过其身体性的受苦(souffrance)把实存占有为“我的”实存(43)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但自我在这个意义上的个体化是不完善的,所以列维纳斯将自我对他人的通达视为个体化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和他人都被个体化(44)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列维纳斯首先将这种情形规定为爱欲关系,在其中,他人作为“女性”与自我面对面。但马里翁认为,将他人规定为“女性”相当于将他人“中性化”,因为这里并不涉及某个不可替代的他人;并且,因为爱欲关系指向生育,他人只是通向孩子的一个环节,所以在爱欲之中重新建立起一种匿名性,我并不与一位独特的他者有关系(45)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
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分析的重点转向面容。面容所发出的命令“你不可杀”使得自我体验到他人的反意向性,它被视为他人的人格性的显现。但面容的困难在于它只表明这是他者,却不表明是哪位他者:“我,我自己,被面容的呼唤个体化,但面容,它自己,仍然是无人的面容(celui de personne)。就此,唯我论被重新建立,只是伦理学的唯我论代替了认识的唯我论。”(46)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马里翁认为,面容的个体化并不彻底,是因为面容缺乏明确的辨识,它只是作为一个命令被听见,但它不能被赋予一个专名,也不处于任何关系系统中(47)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他进而提出三点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面容仍然是无人格的、匿名的:首先,面容所宣告的“你不可杀”这条命令是一条普遍应用的命令,对任何一个他者都适用,他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个体性,都只是匿名的;其次,面容具有欺骗的可能性,它“压制、掩盖了个体性,即便——毋宁说,因为——它开显了无限者及其匿名的超越性”;再次,列维纳斯的“分离”的概念仅仅加深了自我的个体化,而不是他者的个体化,因为伦理学总是指涉道德律,道德律的普遍性要求对他者的特定性不予考虑(48)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所以,面容所隐含的这种普遍性最终不但掩盖他人的个体性,也会掩盖自我的个体性(49)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因为对自我的考量也会上升到普遍性的层面。
马里翁认为,列维纳斯在《别于存在》中建立了爱的统一含义,爱因此变成本源的,并且爱使得自我与他人个体化。马里翁还提到,在一场辩论中,他向列维纳斯提出将爱放在第一位、伦理学放第二位,列维纳斯表示同意,并说作为爱的“对象”的他人是独一无二的。从内容来看,《从他人到个体》似乎只是阐述了列维纳斯在他思想发展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克服之前阶段的困难,最后达到“自我和他人在爱中个体化”。我们很难说这是列维纳斯自己的观点。一是因为列维纳斯在《别于存在》中谈到爱不过是寥寥数句,并且涉及爱的文本中也无迹象表明列维纳斯将爱视为比伦理学更为本源,或是把爱规定为自我与他人的个体化原理。二是因为列维纳斯的赞同仅是口头的,并没有其他文本进一步阐明这种赞同。但我们能确定的是,《从他人到个体》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列维纳斯个体化问题的最为全面的批评。而“自我与他人在爱中个体化”,毋宁是马里翁自己的观点。
三、马里翁:爱的个体化
马里翁的这个观点先是在《爱的意向性》中得到表述。上文提到,马里翁将他人的显现规定为“反意向性”,即他人施加在自我之上的意向性。自我与他人的“目光的交叉”被规定为爱,自我与他人的“原子级的特殊性”(“这性”),只有在爱中才能被达及;他人要求这样的“这性”,因为只有这样,命令才能够使我体验到他人的目光施加于我(50)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pp.110、119、121,pp.122-125.。马里翁对 “这性”的追求相比于列维纳斯似乎是一种倒退,因为对列维纳斯而言,他人在传唤中的个体性比他作为“此,某”的个体性更加本源。然而,马里翁所说的“这性”与列维纳斯说的“此,某”的个体性不是同一回事,后者指传统存在论中的单个存在者或对象意义上的个体性,前者指一种严格的不可替代性。对马里翁而言,爱是责任的条件。在他人的目光之中,他人亲身呈交出他自己,并在这种呈交之中达到最后的个体性,自我亦是如此,自我和他人对彼此而言都不可替代——这也属于爱的规定(51)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pp.110、119、121,pp.122-125.。但这个观点并不能使马里翁的个体化理论与列维纳斯的拉开距离。把个体化的动机仅限于对反意向性的回应,马里翁似乎只是将列维纳斯所称之为“责任”的东西冠以“爱”的名称。然而,这一点在之后发生很大变化。马里翁通过他的“现象学三部曲”——《还原与给予》《既给予》(étantdonné)《论多出》(Desurcrot)——建立了被给予性现象学框架,并用它来分析爱的现象。 “自我与他人在爱中个体化”的观点在《情爱现象学》中发展成更复杂的理论。
在上述“三部曲”中,马里翁试图提出一种比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还原更根本的还原即“向被给予性的还原”。这种还原旨在使现象摆脱前两种还原所施加的先天限制,使现象真正按照其最本源的自身被给予性显现(52)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这种能够按其被给予性自身显现的现象就是“充溢现象”(le phénomène saturé),即直观充满并溢出意向的现象(53)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马里翁按照被给予性等级从低到高的顺序,列举出充溢现象的五种类型:事件、偶像、肉、圣像(面容)、启示。其中,启示集中了前面四种充溢现象的特征以及它们的最大化程度(54)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马里翁规定现象的被给予性等级是基于它们的个体化程度(55)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可见,在马里翁处,个体化是被包含在现象的自身展现的本质内涵之中的。
充溢现象的显现要求一种纯粹接受的主体,这种主体接受那自身给出者,也从自身给出者处接受它自己。马里翁将这种主体称为委身者(l’adonné)(56)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对马里翁而言,胡塞尔的超越论自我以及海德格尔的此在都具有个体化和唯我论的疑难,而委身者摆脱了这些疑难,它在获得个体性规定的同时也保留了被给予者的他异性,走出唯我论的困境(57)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
充溢现象的个体化不仅包含现象本身的个体化,而且包含委身者的个体化。当委身者接受那自身给出者并使其现象化时,委身者自身也因此被现象化。这种模式被马里翁称为“显影”(révélation),自身给出者和委身者既是“被显影者”(révélé),也是彼此的“显影剂”(révélateur)(58)J.-L. Marion, De surcrot: études sur les phénomènes saturés,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1, pp. 61-62.“显影”和“显影剂”都是摄影的术语。。自身给出者和委身者的显影强度是正相关的,当委身者更多地、更大强度地现象化自身给出者,委身者自身也会更大程度地被现象化(59)J.-L. Marion, De surcrot: études sur les phénomènes saturés, pp. 63-64.。由于个体化程度是衡量现象被给予性程度的指标,因此当显现的充溢现象被给予性程度越高,个体化越充分,委身者的个体化程度也越高。
马里翁正是将“向被给予性的还原”以及“充溢现象”的理论应用到对爱的分析之中。在《情爱现象学》中,本源的爱的现象是通过“爱洛斯还原”(la réduction érotique)来通达的(60)[法]马礼荣:《情爱现象学》,黄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07、364—371页。(黄作将马里翁译为马礼荣。)。爱洛斯还原就是向被给予性的还原在交互主体性——即一个委身者向另一个委身者给出自身——上的应用(61)同上,第40—41页;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p.442-443.。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62)对爱洛斯还原的过程的概述,参见余君芷:《爱洛斯还原不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吗?——与Claude Romano商榷》,《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在它的终点处,爱的现象完全自身展开,而处于爱洛斯还原中的自我与他人都会达到各自的和彼此的最后的个体性,也就是人格(la personne)(63)对于“La personne”(person)一词,黄作译为“个人人身”。笔者以为,这个译法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这个术语本身所带有的神学意味(毕竟在《情爱现象学》中,这个术语是与启示现象密切相关的),也不利于我们考察列维纳斯和马里翁的个体化理论之间的关联(下文将指出,这个术语实际上是二者的分歧的焦点所在)。所以,本文将此术语译为“人格”,指“人的位格”。的个体性。因此,爱洛斯还原也是自我和他人的最终个体化的进程。
爱洛斯还原也是通向启示、通向上帝的进程。爱洛斯还原虽然从两个委身者之间的关系出发,却最终展示出上帝作为最初的和最终的爱者,是爱的现象的根源,是爱洛斯还原整个动力机制的推动者(64)[法]马礼荣:《情爱现象学》,第407—408、418—419页。。对上帝的通达正是自我和他人最终个体化的条件。爱的现象的通达和启示现象的通达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因为爱洛斯还原的诸阶段之中,事件、偶像、肉和圣像的现象依次展开直至启示,正对应了启示现象的特征,即它集中了前四种充溢现象的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对应的充溢现象的个体化。
由于篇幅问题,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说明爱洛斯还原每一阶段如何依次对应于各个类型充溢现象的个体化(65)参见余君芷:《爱洛斯还原是根本的还原吗?——基于个体化问题的考量》,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哲学系,2019年。。我们只需要指出最关键的一点:虽然自我和他人的最终个体化即人格的个体化需要经过事件、偶像、肉和圣像等环节,但并不是其中某个环节达成的,而是通过用信心领受彼此的誓言、作出一种以忠诚委身为特征的“有预支的决断”(résolution anticipatrice)并将誓言委托给一位永久保证此誓言的第三者(最终是上帝)来达成的(66)[法]马礼荣:《情爱现象学》,第364—371、400页。。虽然马里翁描述爱洛斯还原的不同阶段时都使用了“源初的个体性”“最后的自我性”等字眼,但这仅仅意味着在爱洛斯还原开启以后,我们进入一个源初的和最后的现象领域,这个现象领域本身仍需要一个最后的过程才能完全自身展开,所以我们不能将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视为自我和他人的个体化进程的尽头。自我与他人的人格个体化以通达启示即上帝的神圣位格为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作为在先者却在爱洛斯还原的最终处得到开显(67)同上,第407页。,这表明爱洛斯还原的根本性。
四、模糊的焦点:人格问题
马里翁对列维纳斯的批评遭到格施万特纳和君特的反对。她们试图通过梳理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来表明,马里翁对列维纳斯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列维纳斯对他人的描述中那些被马里翁视为中性的、匿名的要素,实际上构成而不是抹消了他人的独特性。并且,她们反对马里翁“他人在爱中个体化”的观点,马里翁所说的爱反而会给他人带来列维纳斯所反对的那种总体化的暴力(68)Christina M. Gschwandtner, “Ethics, Eros, or Caritas? Levinas and Marion On Individuation of the Other”, Philosophy Today, Vol. 49, Núm.1, Abril 2005, pp.70-87; Lisa Guenther, “‘Nameless Singularity’: Levinas on Individuation and Ethical Singularity”, Epoché, Vol. 14, Issue 1, 2009, pp.167-187.。诚然,格施万特纳和君特确实指出了马里翁在论证细节方面的一些问题,然而,她们的批评错失了马里翁与列维纳斯的分歧的焦点,因此只是流于表面。这里不打算展开这些细节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被错失的焦点之上。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马里翁并不否认列维纳斯在个体化问题上的成就,他只是要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可以从马里翁对列维纳斯理论的评价、吸收和利用中看出来。《爱的意向性》和《从他人到个体》中,马里翁对爱的个体化的构想都不是在否定和拆毁列维纳斯的个体化理论,而是把爱作为自我和他人在责任之中个体化的根据。列维纳斯所说的自我被他人的面容所表达的诫命所“锁定”从而被个体化这种情况,被吸收到《情爱现象学》的交叉现象的个体化环节之中(69)[法]马礼荣:《情爱现象学》,第176—195页。。所以,马里翁批评的关键不在于列维纳斯的理论是否个体化,而是他所说的个体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怎样的个体化才是最终的、最根本的个体化?马里翁将最终的个体化规定为人格层面的个体化,只有爱能通达这种个体化。而在列维纳斯处,人格个体化是在面容中发生的。所以,马里翁和列维纳斯个体化理论的分歧正是在此,这也是格施万特纳与君特所错失的关键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她们指出了马里翁的批评的不妥之处,但仍不能使之失效。
然则,令人惊异且困惑的是,“人格”(la personne)概念这个如此关键的焦点,在列维纳斯和马里翁处却是“模糊的”,因为我们不能从二者的文本中找到对人格概念的任何正面规定。他们使用这个概念,仿佛这个概念是自明的一般。然而,从使用的语境看,我们确实能够看出二者对于人格的理解的相同与相异。相同之处在于:第一,二者所说的人格并不是指经验科学意义上的、个体的心理特征总体,而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的最深层、最本源的层面,这也是主体的最本己、最根本的个体性所在;第二,二者所说的人格都具有神学的深度,上帝被二者视为人格的展现的根本条件。相异之处在于:在列维纳斯处,人格更多地与伦理和责任相关;而在马里翁处,人格更多地与爱相关。由此可见,列维纳斯和马里翁的人格概念各自承接了犹太-基督宗教所赋予的一部分形而上学和神学内涵,他们的不同侧重却表现出犹太教精神与基督教精神之间的张力。
这样一种承接不禁使我们想起雅尼各(D. Janicaud)所提出的“法国现象学神学转向”的著名批评。然而,现象学并非在法国现象学处才“转向”神学,而是在其创立者处就已经与神学有着密切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在整个现象学发展历程中就没有断过。问题的关键毋宁是,现象学对于神学的提及究竟是不是以一种违背现象学原则的方式进行的?这里是不是涉及把神学的超越性非法走私到对源初现象的探寻之中,把所要验证的命题偷偷地当作前提,从而形成一种无效的虚假论证?对神学元素进行描述是一回事,用现象学的方法发现其来源以及证成其真理性则是另一回事,而后者势必游走在非法的超越性的危险边界之上。如果人格作为人的最本质的主体性层面的这个规定来源于上帝的启示,那么对于这个规定的证成必须基于对启示的证成。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证成并非指的是证明上帝的实有的存在,而是建立一种对具有绝对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位格的被给予性的现象学阐明,这种阐明可以提供在体验的内在性中所展开的现象与这种内在性所不能涵括的绝对超越性和神圣性之间的明见关联。这种证成和阐明意味着,人格和启示在主体的内在性之中都有对应的体验,并且这种体验自身表明为一种源初的、终极的体验,是其他一切体验的根据或根源。这是一切涉及神学意义的人格概念的理论所绕不开的难关,也是决定列维纳斯和马里翁在人格个体化问题上孰高孰低的关键。这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