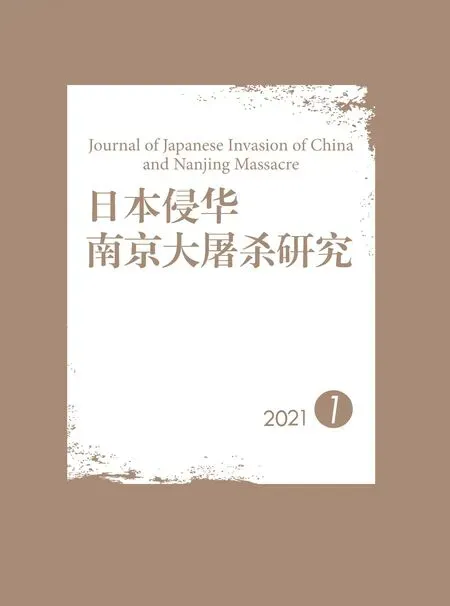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
——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尹晓宇
1936年8月24日,成都爆发了反对日本在蓉设立领事馆的抗议活动,其间两名日本人被打死,另两名日本人受伤,这就是“成都事件”。成都事件发生在1936年中日双方谈判调整外交关系的关键时期,因此受到中日双方的关注。两国外交部门也就成都事件进行了近半年的交涉,最终以中国方面惩凶、赔偿、道歉而了结。以往关于成都事件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幕后策划者和蒋介石及四川地方势力的对日态度上。研究者认为由于事件发生时南京政府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央和地方倾向反日,加之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刺激,最终导致成都事件的发生。(1)陆勇:《“蓉案”再研究——事件幕后策划者问题的探究与考证》,《宜宾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昌文彬:《“成都设领事件”中蒋介石、刘湘对日态度变化探微》,《前沿》2013年第4期。此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成都事件的起因进行系统考察。然而通过爬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成都事件发生在中日“调整国交”的关键时期,此时正是日本两任驻华大使交接职务,中日双方计划重开谈判之时。成都事件给双方重启谈判提供了契机。然而在交涉期间,双方讨论的焦点,往往偏离事件本身,转向全面调整中日关系。这启示我们,应将成都事件放在战前中日调整国交的大背景中考察。因此,本文拟运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新新新闻》《国民公报》等四川地方报刊,基于成都事件,考察由此引发的中日交涉的过程,并探讨战前中日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及有限性。
一、成都事件的发生
成都事件起因于日本计划在成都开设领事馆,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四川重庆开埠,日本派遣领事驻扎重庆,以管理重庆及西南各地的日本侨民。按照国际公法,各国领事馆只能在开埠地开设,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在四川省的领事馆只有重庆一处。
1917年,四川军阀刘存厚、罗佩金与戴戡之间发生混战,成都成为战场,当地日本居留民(2)日本侨民。也受到战祸的波及。为了便于与四川地方交涉赔偿日侨损失,并保护日本人利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草政吉于1918年6月14日,宣称奉日本国指令,在成都设立领事馆。(3)《四川一年来大事记》,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79年2月,第34—35页。由于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按照国际公法不能设立领事馆,因此草政吉公开的身份是日本驻重庆领事馆成都特派员。虽然中国方面未予正式承认,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事实上已成立并开始保护成都的日本侨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反日浪潮高涨,日本在成都的“领事馆”也受到冲击。1931年10月13日,日本“驻成都领事馆”被迫关闭,转移到汉口办公。(4)「在成都居留民関係(3 昭和6年10月26日から昭和9年4月2日)」、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204200、対支那国/帝国外交/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1-1-0-21_1_1_00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36年,日本计划在成都“重开”领事馆,此时恰逢中日两国关系好转,双方正交涉调整外交关系。然而,日本在成都重设领馆引发的“成都事件”,却影响了中日间的交涉。
1936年2月14日,日本驻重庆领事糟谷廉二到成都拜访四川省主席刘湘,希望能够“恢复”日本在成都的领事馆。(5)《驻渝日领谈来省任务 准备恢复驻蓉日领事馆》,《新新新闻》1936年2月15日,第10版。由于成都不是通商口岸,国民政府认为在此不宜设立外国领事馆,故未对日本的要求作出明确回应。6月,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驻华使馆官员岩井英一担任成都代理领事,赴成都处理“恢复”领事馆相关事务。
日本“恢复”驻成都领事馆,目的是扩大在华权益。岩井英一在申请设立成都领事馆经费的文书中提到,四川在中国被称作“天府之国”,成都作为四川省会,在政治、文化、交通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京”,是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前进根据地”。四川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在长达30年的军阀苛政下仍能维持不倒,证明其是日本商品理想的倾销地。如果日本能够在成都站稳脚跟,就可以进一步向中国西部的绥远、甘肃乃至青海等省派遣情报调查员,推进大陆政策。总之,日本要进一步在华推行大陆政策,扩大侵略权益,就必须在成都设立领事馆。(6)「成都総領事館再開ニ必要スル諸経費支出方ニ關スル件」(1936年7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外務省、2008年3月、436—437頁。
对于日本在成都“恢复”领事馆的计划,中国舆论表示反对。按照国际公法,领事馆只能在通商口岸开设,日本在成都开设的“领事馆”没有合法地位。然而,日本并不理会中国的反对,强硬回应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同时制订了岩井英一前往成都的计划。按计划,岩井8月1日从上海登船前往南京,一路沿长江西上,15日到达宜昌,18日到达重庆。岩井计划在重庆会见中国官员,以取得前往成都的许可。(7)「岩井書記生重慶到着後における成都総領事館再開への装置振り請訓」(1936年8月1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440頁。
针对日本的回应,中国民众掀起抗议运动,反对日本在蓉设领。8月2日,四川旅沪各大学同学会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称日本在成都设领不符合国际公法,且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不断侵略中国,故中国应力拒日本之要求。(8)《日本在蓉设领 川旅沪各大学同学会电外部制止》,《国民公报》1936年8月3日,第6版。8日,四川旅沪同乡会致电四川省政府,要求四川地方当局制止日本在成都设领。(9)《日在蓉设领 川同乡会电川请制止》,《国民公报》1936年8月9日,第6版。在四川省内,重庆学生和市民于8月5日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向省内外发布通电,寻求支持。(10)《渝市学生及民众 反对日本在蓉设领》,《新新新闻》1936年8月6日,第6版。
由于中国民众的反对,岩井8月12日到达宜昌后,暂时停留,以观察风向。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对声势,在岩井到达宜昌的当天,成都商界各团体致电南京,要求外交部与日本就设领馆问题展开交涉,四川旅沪同乡会也派人前往南京请愿。(11)《反对日非法在蓉设领 川旅沪同乡入京请愿》,《新新新闻》1936年8月13日,第9版。在民众强大压力下,外交部川康特派员吴泽湘13日接受记者访问,表示日本在成都设置领事属“片面行为”,政府不会接待岩井。(12)《日在蓉设领系片面行为 政府碍难接待》,《国民公报》1936年8月14日,第7版。次日,吴泽湘与日本驻重庆领事糟谷廉二面晤,表示在上海和成都发生了反对日本在蓉设领的民众运动,国民政府难以答应日本“再开”成都领事馆的要求。(13)「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をめぐる呉沢湘駐川康特派員との応酬振りにつき重慶領事報告」(1936年8月14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442頁。
然而,岩井并没有停止西进的脚步。在宜昌短暂停留后,岩井继续西进,于17日到达重庆。(14)《前日乘长阳丸过万 岩井英一昨乘轮抵渝》,《新新新闻》1936年8月18日,第5版。重庆各界民众8月19日举行大游行,向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请愿,阻止岩井继续前往成都。吴泽湘对游行民众表示不承认日本的相关要求。(15)《反日在蓉设领大会请愿结果圆满 吴泽湘允转外部向日交涉》,《国民公报》1936年8月20日,第7版。20日,成都留日同学会致电四川省主席刘湘,请求拒绝接见岩井。(16)《蓉留日学会电请刘主席拒见岩井》,《国民公报》1936年8月21日,第7版。四川省民众的反对活动进一步扩大,22日《国民公报》载,反对设领馆问题在四川省内已形成声势,“势难终止”。(17)《反日在蓉设领 全川各地民众再接再厉 不达目的势难终止》,《国民公报》1936年8月22日,第7版。
在民众和舆论沸腾的同时,中日两国外交部门持续进行交涉。对于重庆和成都等地出现的民众运动,8月20日,日本驻渝领事糟谷廉二在与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会面时,要求中方取缔类似运动,同时传达岩井拟于8月21日前往成都的消息。(18)「わが方成都総領事館再開への反対運動取締方重慶領事より呉沢湘へ申入れについて」(1936年8月20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445頁。同一天,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会见外交部次长徐谟,提出日本在成都设领的要求。会谈中徐谟表示,日本在成都设领馆缺乏法律依据,南京方面建议日本暂时推迟在成都的活动,待双方签订成都开埠的条约后再设立领事馆。须磨趁机又提出控制反对日本在蓉设领的中国舆论,徐谟表示会训令吴泽湘处理。会见后,须磨表示根据会见情况判断,日本“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不会遇到阻碍”。(19)「岩井の成都赴任を延期するようわが方政府へ取り次ぎ方徐謨外交部政務次長より申越しについて」(1936年8月20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第446頁。鉴于四川等地汹涌的民众运动形势,8月21日,吴泽湘通过外交部转告日方,希望岩井以个人旅行者而不是日本外交官的身份前往成都,如此可以减少对中国民众的刺激。(20)「岩井を個人旅行の建前で成都に赴かせ現地にて折衝するよう重慶領事宛訓令」(1936年8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第446頁。
为了顺利推进在成都设立领事馆,23日,岩井派遣与其一起西进并持有旅游护照的4名日本人——记者深川经二、渡边洸三郎,满铁会社会员田中武夫和商人濑户尚,乘坐汽车,于当日下午到达成都。同日,成都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21)《反对日非法在蓉设领 本市民众昨日大游行 集合万余人沿途高呼口号并发宣言 昨日午后四日人抵省》,《新新新闻》1936年8月24日,第9版。深川等人8月23日下午抵达成都后,前往大川饭店,饭店拒绝提供住宿,后在成都市公安局相关人员斡旋下,4名日本人出示自己的旅游护照,饭店得知此4人并无岩井英一,遂同意登记住宿。(22)《大川饭店致公安局呈》(1936年8月),成都市档案馆选辑:《1936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史料选》,《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24日一早,4名日本人离开大川饭店在成都观光。成都市公安局加以劝告,称目前民众反日情绪高涨,日方人员最好待在饭店内,以防意外。然而4名日本人“必须出城游览,屡劝不听”,故成都市公安局安排警员陪同游览。深川等人在游览购物途中已经引起成都民众的注意,但“未酿成事端”。下午,深川等回到饭店,几名学生模样的人到饭店询问4名日本人中是否有岩井英一,得到否定的回答后离开。紧接着又有民众到店质问为何秘密收留日本人,深川等人见状加以抗辩,两方情绪升级,饭店聚集的人也达到“数千人之众”。负责保护日本人安全的警察见状,向公安局报告,却发现电话线已断。饭店遭到民众打砸,秩序陷入混乱,公安局在混乱中救出受轻伤的田中武夫和濑户尚,深川经二和渡边洸三郎则不见踪迹。第二天凌晨3时,在天府中学和华阳县署附近发现两具尸体,后经辨认为深川和渡边。(23)《范崇实致四川省政府呈》(1936年8月),成都市档案馆选辑:《1936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史料选》,《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这就是发生于1936年8月的“成都事件”。
二、限定事件于地方层面的失败
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张群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为因应日本对华北的企图和广田弘毅提出的“三原则”,国民政府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外交方针。张群作为中国外交部长,自1935年11月上任起,先后与两任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和有吉明进行国交调整交涉。(24)关于张群参与调整中日关系谈判的情况,参见蒋永敬《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1936年5月,川越茂接替有吉明任日本驻华大使。成都事件发生在川越茂即将来华履新的8月底,恰好处在中日“调整国交”的间隙。
成都事件的处理直接影响调整国交的成败。因此事件发生后,中方迅速作出反应。25日,四川省政府密令成都市公安局,迅速缉拿闹事的“反动分子”,并查清日方人员受伤失踪的情况。(25)《四川省政府致省会公安局密令》(1936年8月),成都市档案馆选辑:《1936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史料选》,《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26日,蒋介石指示刘湘、贺国光及张群,若成都事件属实,“即就地设法了结”,并承认抚恤赔偿、缉凶、依法惩治,不使事件扩大或拖延,影响中日关系的调整,为了迅速了结此案,必要时可以“稍委曲”,接受日方提出的一些要求。(26)《蒋委员长致刘湘主席、贺国光参谋长及张群部长指示成都事件处理办法电》(1936年8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70页。这表明国民政府为了不使中日双方的国交调整受到意外因素的干扰,决定放低姿态处理成都事件。
为了协助四川省政府处理成都事件,查明事件真相,外交部派遣专员杨开甲、科长邵毓麟于8月28日飞赴成都。在杨开甲等起程的前一天,南京方面传来日方消息,希望成都事件能够妥善解决,不至于扩大。(27)《澈查蓉案并协助善后 外部派专员今日飞省 日盼妥善解决不愿扩大》,《新新新闻》1936年8月28日,第9版。29日,杨开甲与邵毓麟从重庆抵成都,开始进行调查,日本外务省也于28日派遣武官铃木和田中前往成都进行调查。(28)《邵毓麟即调查蓉案真相 杨开甲今晨由渝飞省 松村铃木等昨飞省》,《新新新闻》1936年8月29日,第9版。8月29日,国民政府重申之前颁布的《睦邻令》,劝告民众不要从事反日运动,以免给成都事件的解决增添障碍。
中方对于日方借口成都事件影响中日交涉进程有清醒明确的认识。8月31日,外交部报告蒋介石,日方有人认为成都事件是国民政府对日推行“双重外交”、私下鼓动排日所导致,建议国民政府“迅速解决”蓉案,以免事态扩大。(29)《外交部电蒋介石》(1936年8月3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010;《外交部电蒋介石》(1936年8月3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011。蒋介石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推测,日本很可能借成都事件要求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扩大日本在华北的权益,并签订上海与福冈间的中日通航条约。(30)《蒋介石日记》,1936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台北)“国史馆”,2014年12月,第137页。
为了防止日本借口成都事件获取更多的权益,国民政府努力将成都事件限定在地方层面。9月1日,张群在与日本领事须磨会谈时,首先承认中方对成都事件“负起一切正当而合理的责任”,但希望日方控制舆论,不要让成都事件的后续影响扩大,否则只会“在不幸之上,再加不幸”。(31)《张群与须磨谈话记录》(1936年9月1日),外交部档案·成都事件(一),(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1。在当天的另一场会谈中,张群答复了日方所提出的成都设领和排日问题。张群表示,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是一个历史问题,1918年北京政府的态度是“暂设”,意即可以随时撤销,但张群“原则上同意”日本在成都设领。对于日方指责国民政府煽动民众排日,导致成都事件发生的说法,张群希望成都事件能够在地方层面“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范围内”得到解决。(32)《张群与须磨谈话记录》(1936年9月1日),外交部档案·成都事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5。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与日本驻重庆领事糟谷廉二面晤时,也表示成都事件及与此相关的日本在成都开设领事馆的问题,应该由地方负责解决,以免给中央增加困难。(33)《刘湘东申电》(1936年9月1日),外交部档案· 成都事件(一),(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1。
然而,日本并不希望在地方层面上解决成都事件。9月2日,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外长张群之命,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面晤,了解日方对于解决成都事件的官方态度。会谈中,有田表示国民政府应消除排日的思想和行动,并以此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许世英观察,有田此言“虽云不欲扩大,要亦无作地方事件解决之意”,日方认为,在中央层面解决成都事件更为便利。许世英建议,成都事件必须“就地解决”,退一步说,即便是在中央层面解决成都事件,也要“就案论案”,以免日本借机扩大对华要求。(34)《许世英致外交部电》(1936年9月3日),外交部档案· 成都事件(一),(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1。事实上,在成都事件发生不久,日方即决定以交涉成都事件为契机,努力将交涉引导到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的方向上。(35)「成都排日不祥事件ヲ契機トスル支那排日不祥事件及解決交渉一件」、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09300、対支那国/帝国外交/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1-1-0-29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月5日,《东京日日新闻》从“可靠方面”获知日本针对成都事件对华提出的八项要求,包括取缔排日运动;修改排日教科书、根绝排日教育;禁止排日集会,解散排日团体;要求南京政府对国民党排日行动负责;排除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障碍;针对成都事件道歉、惩凶、赔偿受害者等。(36)《外交部致蒋介石电》(1936年9月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7-259。这些要求,前半部分涉及排日,后半部分则是成都事件的解决条件。日本决心将成都事件的解决从地方层面升级到中央层面,将成都事件视为中国排日运动的突出表现,在解决成都事件的同时,解决中日之间的其他外交问题,以调整国交。
尽管日本坚持将成都事件升级到国交调整层面,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给成都事件“降温”的努力。9月8日,张群在与须磨会谈时,主张先解决成都事件,再讨论中日调整邦交的问题,但遭到须磨的反对。须磨表示张群的看法“似与敝方意见出入甚远”,主张将成都事件作为进一步调整中日邦交的契机,进而讨论其他问题。(37)《张群与须磨谈话记录》(1936年9月8日),外交部档案·成都事件(一),(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1。9月10日,张群再次与须磨会谈,须磨表示日本希望将成都事件与中日全面调整国交一并解决,并称成都事件的发生,表明中国与日本调整关系的“诚意不够”,为了表示诚意,中方应该“自动满足”日本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华北机构问题、防共问题、成都开埠及开发四川经济问题,以及雇佣日本人顾问、取缔朝鲜人、中日航空联络及关税等问题。须磨希望中方至少应该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一两件,如此“中日邦交自能走上轨道”。对于须磨的主张,张群希望日本“勿将成都事件,牵连全面的调整”,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压迫中国的嫌疑,事实上不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好转。(38)《张群与须磨谈话记录》(1936年9月10日),外交部档案·成都事件(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3。
虽然中国尽全力将成都事件限定在地方层面解决,但日方坚持由中央交涉的方式解决。9月6日,驻华大使川越茂从南京前往上海,向日本使领馆官员传达外务省训令,讨论对华交涉步骤。(39)《川越召开会议 说明外务省训令方针 并讨论向我交涉步骤》,《国民公报》1936年9月8日,第2版。随后川越返回南京,希望与外交部长张群见面。成都事件及之后不久在北海发生的日本商人被害事件,使中日外交交涉变得必要。9月15日,张群与川越茂开始就成都事件进行商谈,表明中方将成都事件限定于地方层面的失败。
三、交涉重点的全面调整
9月15日的会谈,是川越茂担任驻华大使后与张群的首次正式会谈。某种意义上说,成都事件的发生,为张群与川越谈判调整中日关系提供了契机。张群回忆说成都事件“给日本造成了一个最好的借口”,(40)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即是指日本借成都事件重开调整国交交涉。
谈判之初,川越首先表明,为了日中邦交得到真正的调整,日本希望国民政府能“自动有所措置”,取缔反日排日活动。对于川越的要求,张群表示中国的反日空气是由日本不断侵略中国所致,日本的侵略是调整中日邦交的最大障碍。对于中国应“自动措置”的说法,张群并不反对,并表示中方将计划积极慎重地加以推动。川越对张群的表态并不满意,认为中方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取缔排日运动,撤销排日团体,以“改善空气”,促进邦交的调整。接着,双方谈到成都事件问题,张群表示将按“普通事件”处理,对此川越并不认同。与日本国内舆论一样,川越认为成都事件的发生,背后国民党在推波助澜,调整中日邦交,首先要解决国民党主导的排日教育问题。接着双方就教科书及报刊如何消除排日因素进行了讨论。(41)《张群与川越大使部分谈话记录》(1936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90—892页。在讨论没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双方还商议了北海事件、华北问题、经济合作等事宜。张群表示将成都开辟为通商口岸与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针相违背,不符合中国的立国精神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因此绝不能考虑。双方未达成一致,最终约定下次再谈。会谈后,川越接受记者采访,认为成都事件及北海事件并非偶然,要求中方做出更大让步。(42)《蓉北两案事非偶然?川樾昨答记者问》,《新新新闻》1936年9月16日,第3版。
对于日方的要求,蒋介石电令张群坚持原有底线,不因成都事件与北海事件一时未能解决而“自馁其气”,日方如果不愿意按照普通事件解决,那么国民政府将按照成都事件发生前的方针继续与日本交涉。(43)《蒋委员长致张群部长指示对日交涉方针电》(1936年9月1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3页。在继续谋求与日本交涉的同时,蒋介石也做了另一手准备,针对日本派遣军舰南下调查北海事件的行动,蒋介石电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预防对日交涉恶化可能带来的最坏事态,“准备一切”,若日军占领北海或海南岛,国民政府将视为日本对中国“引起大战”。(44)《蒋委员长致何应钦部长指示预防对日交涉恶化应即准备一切电》(1937年9月1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3页。
20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领事须磨等继续会谈,双方讨论了中日联航、关税、华北形势、雇佣日本顾问、中日共同防共等问题。(45)《张群致蒋介石电》(1936年9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057。两次中日谈判的记录显示,由于日方坚持要将成都事件与国民政府怂恿民众排日、缺少调整中日国交的诚意挂钩,故双方谈判的焦点从成都事件转向中日间尚未解决的其他悬案。
9月23日,川越茂再次与张群会谈。在会谈中,川越并不明确提出解决成都事件的条件,而是坚持中方应先承认9月15日会谈中日方提出的取缔排日、聘用日本顾问等七项要求。对此,张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提出对案,包括废止上海和塘沽两协定、取消伪组织、禁止走私、解散伪军等要求,并表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日关系得以调整的前提。这说明,针对日方借成都事件等突发事变,以达到全面调整中日关系,获取更多在华权益的企图,中方改变了原先的策略。国民政府也将交涉的重点转向中日间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悬案,以谋中日关系的整体调整。9月23日的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蒋介石得知会谈结果后,认为中日双方“等于决裂”。(46)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第151页。9月26日,蒋介石指示高宗武在与须磨的会谈中明确表达中方的不满,指责日方不应借口成都事件不允许中方提出条件,将“调整国交”简化为“人命官司”。(47)《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9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10200-00165-066。既然日本不愿单纯解决成都事件,而是要通过成都事件解决中国的“排日”等问题,那中方也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有利于己的关系调整方案。中日之间的交涉,一时陷于停滞。
在谈判陷于胶着之时,偶发事件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9月20日,汉口日本租界警察吉冈被杀。9月23日晚,日本海军“出云”号军舰的4名水兵,在上海公共租界遭到袭击,水兵田港朝光死亡。汉口事件和上海水兵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军方敏感的“神经”。日本海军派出陆战队前往汉口,并增加在上海附近的兵力,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为此,蒋介石加紧应付日本军事行动的准备,9月25日,他给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豫皖绥靖主任刘峙和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发电,请军队方面“准备一切,以免不测”。(48)高素兰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8,(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519—522页。26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局长举行会谈,决定促使蒋介石回京交涉,认为只有蒋介石出面,才能体现中方在交涉过程中的“诚意”,(49)《上海吴铁城电》(1936年9月30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第62页。中日之间才有继续交涉的可能,如蒋拖延不回,则在最后通牒过期后“采取行使实力之手段”。同日,日本海军省也出台了“对华处理方针备忘录”,计划在交涉破裂时对中国实施打击。(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中日双方有滑向战争的可能,形势一触即发。
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引起西方列强的注意。英美等国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认为日本对华的强硬态度是事态升级的信号,日本有可能乘西班牙内战的时机对华采取行动。9月29日,英国外交部通知驻华大使许阁森转告国民政府,英国驻日大使克莱武已经接到训令,“尽可能地使日本政府采取冷静行动”。(51)Foreign Office to Sir H. Knatchbull-Hugesson(No.88),29 September 1936,FO 371/20244.此外,日本政府也反对军部强硬化的处理方式,准备继续通过交涉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逐渐降温,双方回到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上。(52)《日三省会议结果 对华侧重外交》,《国民公报》1936年9月26日,第2版。10月初,蒋介石结束两个多月的华南之行回到南京。10月8日,蒋介石会见了川越茂,表示中日之间外交关系的调整,应该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和平友善的气氛中从容协商,对于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至于其他问题,需要由张群和川越继续谈判。(53)《蒋委员长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谈话纪要》(1936年10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5页。会见川越茂后,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表示,中日间调整关系的原则是“不威胁、不侵略”,解决中日之间问题的方式是“外交正当途径”。(54)《蒋委员长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1936年10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6页。会见结束后,日本外务省对中日之间的交涉感到乐观,推测中国会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日本军部虽然“仍极强硬”,并为今后可能出现的谈判破裂做准备,但也降低了调门,不再主张直接对华采取强硬手段。(55)《上海方唯智来电》(1936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65页。
蒋介石会见川越茂后,中日两国的紧张局势降温,双方重开谈判。在正式谈判开始前的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张群,要求在对日谈判中,坚持一揽子解决中日关系的方针,提出取消上海、塘沽两个停战协定的内容。(56)《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10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 002-080200-00270-056。10月19日、21日、26日和11月10日,张群与川越又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的重点不是成都事件,而是防共问题。(57)《外交部关于中日南京交涉的节略》(1936年9月15日—11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906—907页。张群与川越的交涉实际上成为重启的中日调整国交的谈判,会谈中双方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并未取得实质性一致。在11月10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中日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日方将防共要求限定于“北部”,并解释目的在于对付苏联;而中方也不再坚持废除上海、塘沽两个停战协定,但要求“冀察绥三省行政及军事上畸形制度一部分之改善”,即华北主权的保障。(58)《张群致蒋介石电》(1936年1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 002-090200-00018-188。双方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川越与蒋介石会见后,日本外务省与军方曾就对华方针进行讨论。相较于外务省的乐观态度,参谋本部对于中日交涉缺乏信心,尤其是交涉条件中有关华北的条款。为此,参谋本部虽然大体同意外务省继续与中国交涉,但同时表示,在交涉不顺的情况下,会在华北采取“积极的方策”。(59)《参谋本部公函》(1936年11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1—52页。在中日交涉进展不顺的背景下,日军在绥东地区支持伪军扩张,绥远形势紧张。11月中旬,绥远战事爆发,中日之间的交涉也受到影响。(60)关于绥远抗战,参见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11月17日,蒋介石指示张群告知日方,待绥远事变的情况弄清楚后,再与川越茂展开谈判。(61)《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11月17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20200-00026-082。2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表示绥东问题不解决,中日不能开始谈判,但也不明确表示中止或停止中日谈判,以免给日本人留下借口。(62)《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11月20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20200-00026-083。由于绥远抗战的爆发,中日之间的交涉陷于停顿状态。
四、交涉重点回归成都事件
历时两个多月的中日交涉陷于停顿,对双方而言都不是理想的结果,因此双方开始谋求重开交涉的方法。10月26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矶谷廉介在与中国驻日使馆武官萧叔宣会谈中,暗示在中日双方无法就全面调整国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如先“就事论事”,解决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再进行全面调整国交的交涉。(63)《程潜致蒋介石电》(1936年10月28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 002-090200-00018-172。矶谷的表态,说明日方在交涉不利的情况下,有退让寻求妥协的可能,加之在绥远战事中日伪军并未占到便宜,也促使日本军方回归到外务省所主张的外交交涉轨道上来。
12月初,青岛日资纱厂工人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酿成外交事件,这为中日重开交涉提供了契机。青岛事件发生前,川越茂即连续请求会见张群,以求重开中日交涉。12月3日,张群收到日本水兵登陆青岛的电报,当即决定一面向日方抗议,一面请川越到外交部商谈。在会谈中,川越突然开始朗读携带的备忘录,在张群拒绝接受后,川越等人将备忘录放在桌上扬长而去。(64)《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4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4-113。这份备忘录的内容,重点是成都事件的处理。日方要求国民政府彻底实施排日禁令,修改排日教科书,取缔排日言论,切实保护在中国旅行之日本人安全,并附上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解决成都事件对策草案中所提及的日方条件。(65)《川越致张群备忘录》(1936年12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915—921页。张群拒绝的理由是,备忘录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与谈判情形相符,且其中遗漏了许多中方意见,属于日方片面施加于中方的条件。(66)《张群与川越大使谈话记录》(1936年12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913页。
在川越送交备忘录后,12月4日,日本外务省希望中方“自动”满足日方要求,否则中止交涉,并准备采取一切“自卫”手段。(67)《俞飞鹏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5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168。面对日方的威胁,中方采取强硬态度应对。蒋介石电告张群,必须用正式公函退还川越备忘录,并且中方也应准备一份备忘录,将日方备忘录中所载有关防共的条款删除。(68)《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12月5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80200-00273-048;《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12月6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20200-00026-094。
相较于蒋介石对于川越备忘录的激烈反应,主管外交的张群则另有看法,他认为川越的备忘录并不能作为中日双方交涉的证据,并分析川越之所以提交备忘录,实际上是想将交涉的责任转移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身上,以便与中方迅速解决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川越实际上是搁置“防共问题”,以求得其他问题的先期解决。(69)《张群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5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182。12月7日,须磨在与高宗武会谈时明确表示,川越离京不代表交涉破裂,希望双方从速交涉以解决成都、北海两事件,否则“中日间真无外交可言”。(70)《高宗武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164。12月8日,张群建议蒋介石,现在日本方面要求先解决成都、北海两事件,与成都事件刚发生时中国方面“先行依照国际惯例了结”的主张相同,因此中方应积极表态,不要拒绝日方的请求,免给日方留下借口。(71)《张群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8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90200-00018-177。12月9日,高宗武开始与须磨就解决成都、北海两事件进行交涉。在9日的交涉中,须磨提出,在整体调整国交交涉难以取得进展的背景下,双方可先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逐次解决成都事件等一系列外交事件,如有可能,可以在解决成都事件的基础上,一并解决北海事件。(72)「日、支外交関係雑纂/昭和十一年南京ニ於ケル日支交渉関係 松本記録 昭和11年12月2日から昭和11年12月14日」、CAJ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41300、対支那国/帝国外交/政治、外交/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1-1-0-9_1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方提出的解决条件包括外交部长张群代表国民政府向日本道歉、四川省主席刘湘道歉、赔偿被害日人损失、申诫刘湘,并保证今后在川日本人免遭暗杀等。(73)《张群致许世英电》(1936年12月9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20-010102-0193。
对于日方所提出的上述条件,蒋介石表示,保障在华日人将来不被暗杀的要求,中方无法满足。(74)《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12月11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02-080200-00273-086。因此,12日下午,高宗武与须磨再次交涉,日方做出让步,不再坚持申诫刘湘,也不再要求中方保障日后在华日人不被暗杀,但要求将北海事件与成都事件一并解决,并表示赔偿的数额已是“最低限度”。张群对交涉结果表示满意。(75)《张群致蒋介石电》(1936年12月12日),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 “国史馆”藏,020-010102-0193。14日,张群就解决成都、北海两事件向行政院报告,称日方最终将成都事件的解决条件限定在道歉、处分、赔偿三个方面,北海事件则等成都事件完全解决后继续商谈。(76)《张群为解决成都、北海事件致行政院呈文》(1936年12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924页。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中日之间的交涉再次停顿。在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中日双方就成都事件达成最终解决方案。12月30日,外交部和日本驻华大使馆互换照会,同意张群代表国民政府就成都事件向日本道歉,免除四川省会警备司令和成都市公安局长的职务并处分其他人员,判处首犯刘成先、苏得胜死刑及其他凶犯徒刑,以及对日方死伤者支付抚恤金和损失费。日本驻华大使馆认可中国方面的处理方案,“认为本事件已经解决”。(77)《外交部为成都事件致日本驻华大使馆照会》(1936年12月30日)、《驻华日使馆为成都事件致外交部复照》(1936年12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924—926页。中日双方就此互换照会,历时近四个月的成都事件终于得以解决。
虽然成都事件最终以中国道歉、惩凶、赔偿告终,但日本在成都设置领事馆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37年7月前,日方多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要求,都被中方以四川省治安状况不佳,日本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可能会遭遇危险等理由拒绝。(78)「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に関し四川省の治安状況改善方努力中と王寵恵回答について」(1937年6月9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第461—462頁。张群曾口头答应日方,待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后,即允许日方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方表示四川地方形势仍无法满足要求,故继续拒绝日方在蓉设领。(79)《张群与川越谈话记录》(1937年2月9日)、《陈次长与日高代办谈话记录》(1937年6月8日),外交部档案·成都事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10102-0195。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为因应成都等地的排日运动,决定让重庆领事兼成都总领事,这一要求得到川康外交特派员吴泽湘的同意。(80)「重慶領事の成都総領事兼任案を同領事より呉沢湘へ説明したところ呉が賛同表明について」(1937年7月13日)、『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 第一部 第五巻上、成都総領事館再開問題、第465頁。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没能实现在成都再设领事的企图。
五、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
成都事件发生于1936年,正值张群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与日方展开交涉的关键时期。由于日本驻华大使的更迭,中日之间调整国交的谈判暂告一段落。然而,成都事件的发生,配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的到任,为中日重启调整国交交涉创造了契机。两国的国交调整随着成都事件的交涉渐次展开。持续近四个月的国交调整交涉,由于双方分歧过大,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而成都事件则在日本在蓉设领馆诉求未得到解决的前提下,以中方道歉、惩凶、赔偿,得到“暂时解决”。纵观中日国交调整的过程,可以看出此次成都事件交涉成果的有限性。
1935年,随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逐渐转暖,双方开始寻求调整两国关系的途径。1935年底张群任外交部长后,先后与三任日本驻华大使进行调整关系的交涉。中国希望通过与日本改善关系,迟滞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紧相关的备战工作,为最终解决与日本的各种纠纷与悬案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日本而言,建立在“三原则”基础上的调整国交交涉,目的是希望国民政府参与到防共防苏、经济开发之中,最终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1936年3月,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离任,中日调整国交交涉进入“空窗期”。在等待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重开交涉的过程中,外交部长张群曾在5月25日外交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呼吁中日两国开诚布公,交涉调整国交问题。(81)《外部纪念周 张部长演讲最近国际情势》,《中央日报》1936年5月26日,第4版。在此期间,日本也调整了对外方针政策。1936年8月7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的四相会议通过的《帝国外交方针》明确指出,日本要以“外交手段”达到消除苏联和共产党威胁和扩充军备的目的,(8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这表明日方有强烈的对华交涉意愿。在新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来华开始交涉前,意外发生的成都事件虽然给正在调整中的中日关系造成了冲击,但也为中日重启谈判创造了契机。对日本来说,利用成都事件及其之后的一系列突发事件,达到迫使国民政府与日本“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主要目标。因此,成都事件发生后,日方抓住所谓“排日”问题不放,攻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试图通过督促国民政府根绝“排日”,进而讨论关税、华北地位、共同防共等问题,以达到“广田三原则”和《国策基准》中所提及的“日华合作”目的。中方同样重视与日本调整国交,对于成都事件的发生,张群明确称其为“不幸事件”,承认成都事件对中日外交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同意与川越茂就成都事件进行谈判,这说明中方严肃对待与日调整关系的交涉。中日双方从各自立场出发,积极推动国交调整交涉,体现了国交调整交涉的力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交涉过程中重点的偏移,即由解决事件本身转为全面调整中日关系。
虽然国交调整交涉有一定力度,但由于中日之间的分歧,国交调整交涉的结果,存在很大限度。在谈判中,针对日方利用成都事件指责中国“排日”,希望通过督促中国取缔排日活动,进而在华谋取更大权益,中方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起初中方计划将交涉限定在地方层面,但相关努力失败后,在中央交涉层面,针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国民政府也提出有关取消上海、塘沽两协定的对等条件。国民政府的应对,一方面使交涉重点从解决成都事件本身转向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另一方面也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使得交涉窒碍难行。尤其是9月川越提出的有关经济合作、防共等七项对华要求,被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视作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升级版,意在将中国变成如同朝鲜那样的日本殖民地,(83)《日内瓦顾维钧等电》(1936年9月26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9页。中国难以轻易答应。(84)事实上,日方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据高宗武回忆,在川越茂刚来华时,日本高层建议川越早日将对华要求列一清单,逐条提出,以便交涉顺利进行。川越则以日本在1915年吃过“二十一条”的亏,此次交涉须“谨慎从事”回应。参见高宗武遗著,夏侯叙五整理注释《日本真相》,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绥远等地发生的军事冲突,更是给本来就难以进行的中日调整国交交涉蒙上一层阴影。在全面调整关系的交涉难以继续的情况下,中日双方重新将交涉重点放在成都事件上,最终在1936年末解决了成都事件。但是,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问题,却再次成为悬案,中日间从1935年开始的调整国交交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也没有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说,中日国交调整交涉的成果十分有限。
张群在回忆这一段中日交涉时指出,双方立场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85)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第64页。张群所提到的“南辕北辙”,即指1935年后日本当局不断扩大的对华侵略野心与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对日渐趋强硬的态度。有趣的是,此时中日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因此出现了自1935年底开始持续近两年的国交调整交涉。由于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调整国交注定只能是一场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