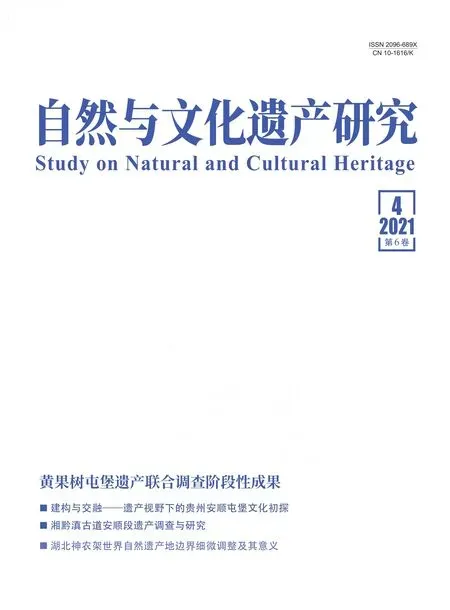走出“原真性”
——试论人文区位学视角下的泉州文化遗产
孙 静
(泉州师范学院 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文化遗产在过去30年间已深入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地方文化。文章想要回应以下问题,中国早期社会科学学派——燕京学派①燕京学派指的是20世纪初由吴文藻创立,以费孝通、林耀华、田汝康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该学派是继承了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治学传统,讲求社区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所主张的“人文区位学”对于当代遗产理论和研究具有何种借鉴价值和意义?以此视角剖析处于世界文化遗产进程中的泉州,是否将有助于反思遗产体系中存在的“原真性”议题?人类学或可以“人文区位学”为方法论介入中国的文化遗产运动进程。
1 伊势神宫命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遗产名录及公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推动建立人类文明共同文化财富的长效机制。始建之初的黄金标准《威尼斯宪章》是以传统建筑的物质形态,尤其以石质这类恒定性特征的建筑材料为依据来规范操作指南的。这一指南被诟病最多的是它根植于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将物质性(身)与精神性(心)相分离②WIJESURIYA G.Towards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heritage[J].Built Heritage,2017(2):1-15.,其具体表现为“纪念碑主义”③纪念碑主义指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始于对纪念碑及遗址的建筑、立面、形态的物质性保护。纪念碑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风土建筑和物质遗迹进行保护的一种理念,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和“原真性检验”④原真性检验指的是文物或文化遗产是原真的描述……是原初的、创造的、非重复的、独一的、真诚的、真实的、特别的、名副其实的,未经过伪装、模仿或是其附属品。。对前者的批评在于它根植于欧洲古典的历史建筑概念:城堡、宫殿、大教堂、修道院、寺庙、金字塔、陵墓和巨石。这种纪念碑主义迷恋于大小,并赋予那些规模大和造价高的文明的物质遗迹以特权[1];对后者的批评在于它贬低了东亚、非洲和大洋洲等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忽视了文化多样性。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制定并通过《奈良真实性文件》。这一文件制定的背景便是要对以往建筑保护及其原真性宗旨提出质疑,且在跨文化比较中推动文化遗产名录关注到文化相对性。这一文件生成的背景是法隆寺的木构建筑形成对欧洲古典石质建筑的挑战,前者表现为临时性的、替代性的建筑理念;后者则是恒定的、静态的建筑理念。
然而,伊势神宫比法隆寺更能启发人们思考遗产的实质:“它不是建立在永恒和实体之上,而是建立在事物的短暂和虚体之上”[1]。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是日本重要的神道教社,至今仍保留有日本古老的“式年迁宫”⑤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的重要空间。每隔20年拆毁一次,在相邻平地择址重建,循环往复。根据官方记载,这一传统已经存在了1 300多年。神宫最近一次,即第62次伊势式迁宫于2013年完成,下一次将于2033年开始。仪式。每隔20年的周期性仪式重建意味着旧有的建筑实体须被毁灭。法隆寺或许让以欧洲学界为主导的委员会意识到了其他文明与欧洲在建筑保护实践中的文化差异,伊势神宫则象征着一种以无常幻灭为特征的佛教循环时间哲学观对追求永恒性的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正是后者开启了对长期主导世界文化遗产的《威尼斯宪章》的全面反思。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遗产体制所引发的争论与质疑。遗产体制运行的悖论在于,其黄金准则“原真性”恰恰导致了各民族文化在追寻“原真性”过程中不得不舍弃、掩盖其民族和地方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使其迫于“登录”和被“展示”的需求。文化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是落后于本地实践的,是切割了当地文化完整性的。后者恰恰应当是前者的启发,而不应在前者的指挥棒下委身于任何一种被构建的“原真性”。
2 人文区位学
泉州继2013年当选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后,2020年又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之名,正式向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迈进。泉州的遗产化历程,无疑也将会是超越或委身“原真性检验”,两者择其一的命运。泉州完全可以像伊势神宫一样,超越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界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则制定者们提供新的启迪。在泉州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实现这种超越和突破的学科路径之一即是引入燕京学派所提倡的“人文区位学”。
考古学家孙华认为,泉州古城是因海外贸易而兴,城市肌理逐渐扩建形成不规则形态的商港城市,属于“随形就势”类型。该城市类型最重要的城市功能要素除了地方城市都具有的衙署外,城市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的遗址、远洋商船停靠的港口遗址、随海舶而来外商集中居住的蕃坊遗址、古代不同国家和文明文化交流的遗存、城市郊野生产外贸产品(主要是瓷器)的遗址,以及将这些外贸产品运输到城市港口的道路、桥梁等遗存都应该受到关注⑥孙华.中国古代城市的类型:兼谈泉州城的历史地位(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物质性、遗产与文明”国际学术系列讲座纪要,载于该研究院公众号),2020年10月。。“随形就势”反映的即是泉州城市形态、肌理与其生态、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伊势神宫不同,泉州的文化遗产价值扩展在对其城市肌理、山水生态、交通要道、城乡关系、内外贸易关系的全面把握之中。不得不说,这种复杂性恰恰是泉州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
要把握这一复杂性,除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研究之外,起源于社会科学大本营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在方法论上所坚持的“社会调查”也架起了空间研究与社会结构分析的桥梁,为处于文化变迁中的遗产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发。
2.1 人文区位学的特点
人文区位学的传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基本方法来自生态学。所谓区位,就是ecology。人文区位学指的就是对人类共同体适应于更大范围的社会环境这一过程展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2]。
芝加哥社会学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面对方兴未艾的社会调查,在破与立的交错中寻求社区何以成为共同体的答案[3]。芝加哥学派开创之初就形成了两个研究传统与方向:一是关于城市空间利用的人文区位学,研究城市空间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二是社区研究,关注的是人们适应城市空间环境的社会过程[4]。后者由帕克(Robert Park)带来中国,对“燕京学派”影响至深。
燕京学派所继承的人文区位学,具体表现为社区调查,也就是要求学者到田野地去做实地调研。通过对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和发掘,积累丰富的描述性田野资料,从局部来认识整体。燕京学派之所以对帕克带来的新视角充满兴趣,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社会文化变迁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身处文化遗产历程中的泉州,也处在文化变迁的历史潮流中,同样面临着破与立的问题。
2015年3月,泉州市政府规划的闽南文化生态园建设项目启动,该项目将泉州老城南部老街区纳入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内。这一项目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目标,力图使规划设计符合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基调。见人,即由居民所结合成的社区;见物,即社区具有文物价值、历史价值的文物及建筑;见生活,即在前两者基础上铺展开的当地人具体且丰富的生活世界。此三者指出了泉州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而人文区位学呼吁的正是研究者通过长期且深入的调查,梳理这三者所构成的人文生态。
在实践中,平衡三者关系却并不容易。在视角主义主导下,对“物”进行修缮管理,最易受关注、出成果。“人”和“生活”的意味和内涵却不易被“见”,因而也最易为政府所忽视。
2.2 超越传统的人文区位学
要面对泉州这样一个具有漫长历史传统的区域,传统的人文区位学还存在局限性。彼时的美国,帕克将城市看成人性的实验场,认为人文区位学和人类学有着有趣的关联,因为城市内部所蕴含的基本冲动与原始社会的并无二致[3]。帕克的继承者们未全然理解其所言的对城市中的人性洞察,而将城市视作是无历史的断面,忽视其纵向历史维度。也就是说,受生物学启发的“人文区位学”里包含着某种“生态论”,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形态论”,其研究并未充分给出历史的“地方感”[2]。在面对泉州这样具有历史文明积淀的地域时,亟须开展横纵交错的人文区位考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所领衔的人类学专业硕士、博士生的调研团队曾在泉州进行过几次此类实验,分别围绕安溪铁观音茶叶[5]、泉州城南3条古街[6]以及惠安小的宫庙和祠堂[7]展开。2013年,在对安溪铁观音的调研中,他们认为铁观音中包含着安溪人对“人——物”“人——人”“人——神”关系的独特感知。处于传统与现代、手工与机械犹疑中的安溪人无疑要回应对这一广义人文关系,以便度过铁观音危机。2015年,他们对泉州城南老街区的研究更为直接地践行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区位学。该研究反思了地方文史叙述的宋元繁荣中心论,考察了作为生活和社会过程的完整体系的文化及其水系与宫庙体系之间的关系,继而说明人、神、物3种力量如何在社区中交融并生。2016年,人文地理视角的引入,使得对惠安小人文生态及其社区历程之关系的考察更为深入。这个研究让他们意识到,社区或乡村并非现代文明进程的敌人,它们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互关联共生下形成的完整生态人文体系,整合了人、物、神诸生命因素,自身有着强大的创造力[8]。
在这些调查与研究中,他们试图呈现时代闽南区域文化中的广义人文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结构和动态面貌。他们认为,任何完整的社会共同体,都是人、物、神诸“存在体”共处的场所。要研究社区,就需要重视这3类“存在体”之间的关系[9]。
在实践中,处理三者关系并不容易。城市化带来的发展压力常常使得“物”的价值优先被考量,“人”和“生活”的价值处于次要地位,或主要服务于前者。三者关系的梳理也往往滞后于对“物”的保存、管理与修缮。同时,往往是具有年代价值的古物为人们所好。
2.3 泉州:复合的人文世界
传统的人文区位学构建了空间研究与社会结构分析之间的关系,而面对具有漫长历史文明传统的泉州,笔者呼吁一种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区位学。这种人文区位学既考察了它在人文地理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还将泉州置于诸文明交融复合的历史生成论当中。换句话说,作为遗产主体的泉州即是一个“复合的人文世界”。
泉州与世界体系的碰撞恰恰证明,世界性的海外贸易并不是在15世纪欧洲兴起后才出现的。借用施坚雅的中国历史结构分析,泉州的区域发展周期可被分为:①汉人在边陲地带的内部拓殖期;②唐中后期至元代,泉州海外交通核心地位和内部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期;③元末至清,区域性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引起的泉州核心地位的式微期[10]90。“在从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由一座中国东南沿海港城带动起一系列海外贸易活动,其所跨越的空间范围,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中间范围包括南洋、印度等地,在此范围内流动的物品与符号,包括了东西方各主要文明的成就,其广度并不亚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0]73。早就浸淫于世界体系中的泉州,或者说生长于世界主义的泉州,其文化底子便天然具有一种复合人文主义的意味。
具体而言,泉州“城”与“市”的此消彼长,展现了帝国是如何映照在泉州作为“城市”的历史之上的。这一复杂过程从历史深层结构上反映了泉州人文传统的复合性。“明以前的泉州,尽管也为城墙所包围,但其市的一面更为突出;而明以后,尽管围城未扩大,但得到了加固,市这一面的重要性则退让于城这一面”[10]111。传统国家可能并不像以往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其文化多元的程度反而可能达到一个空前状态。海洋成为13世纪之前泉州城市发展的重要通路,其社会文化形态应以“文化世界主义”来加以形容。这与拉铁摩尔[11]描述的因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文明的挤压所导致的文明南移有所不同,泉州所处的山海之地理特征迫使人们走向冒险与财富并存的海洋。然而,这样的尝试与探索在明朝建立后不久便逐渐终止。
许多历史学家对明清以来帝国在海洋贸易上(或对外贸易上)的保守主义有过阐释。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这种保守主义是由儒家的“性理之学”发展而来的“内圣之学”,即追求个人有限生命的道德圆满。儒家的“内圣之学”在政治经济上的表现即为对外海禁、对内绥靖、社区教化等政策。这样的意识形态导致的是自明帝国起,由传统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的蜕变与演进。与之相伴的是,由原来没有边界的帝国逐渐转为有明确法律意涵的、规定性的、疆界的国家。此时,泉州城市中“城”的一面逐渐凸显,也就是起防御保护作用的军事功能逐渐得到增强。与海防建设几乎同步展开的还有地方基层系统,都图乡、铺境系统到清朝时已十分完备,渗入城乡各个角落。与此同时,泉州地理、城市、房屋、寺庙和衙门等“物质性”遗存无不浸润着理学、易学的宇宙观。比如在明清方志中,泉州地理往往被划分为5个部分,即“星野”“山川”“封域”“城池”以及“铺驿”或“市里”。这5层的划分是“五服”古制的城市空间的缩影。除此之外,官方还要组织祭典。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方位宇宙观的移植,帝国的形象和意识形态在地方得以吸纳与展演[10]179-205。泉州成了中国微观宇宙的象征,此外这一象征体系还以年度周期仪式的方式不断被强化。
综上所述,泉州的地方史始终与帝国彼此映照。一方面,明帝国在民族国家的世界浪潮之中逐渐由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另一方面,明朝又渐渐形成了“内圣之学”上达庙堂以海禁绥靖的国家主义形式加以彰显,或下至乡间以民间教化的形式加以表达。显然,泉州的 “复合人文世界”便是在“治”与“乱”的辩证之中实现的,这与 “城”与“市”的历史辩证恰好吻合。泉州港的形成与繁荣,源自其“夷夏杂糅”的复合人口结果和文化特性,即定义为“乱”。明以前,“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乃是对“乱”的漠不关心。而明以后,尤其是元末泉州10年内乱,“乱”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要以彻底的“治”来改变现状,那么给予“生生”的空间就很小。这时候商盗泛滥,与之相伴的是“城”的空间加强。
除此之外,由宏观史学落回微观社会生活史视角,还要强调泉州人日常中所蕴含的年度周期仪式也为这一“复合的人文世界”提供了重要论据。泉州存在3套主要的年度周期仪式:第一套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被宣布为“法定节日”的仪式;第二套是由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创造的以地方文艺类型的展演为核心内容的周期性“艺术节”;第三套则是存在于民间的周期性仪式活动,包括以家为中心的祖先祭祀,以每月二度的土地公诞辰庆祝为周期的仪式以及铺境仪式[10]59-60。从本质上说,年度周期仪式就是历史、文化与权力的集合,或者说是不同的权力通过选择历史来选择文化的结果[10]61。
可以说,从公共仪式切入社会,是人类学家有可能展开具有历史意味的“人文区位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费孝通曾在禄村农田中对“消遣”进行了论述,被消耗在仪式性活动的时间没有增加劳动价值,从而为其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了文化基础[12]。燕京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田汝康通过研究摆夷社会,对这一公共仪式作出了更核心的阐释,他认为除了消耗之外,公共仪式还有助于宗教“超越性”的营造[13]。同时期,许光笔下的祖先祭祀也试图创造一种延绵连续的时间感和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14]。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志都从公共仪式中呈现出一种历史时间,通过社区年度周期的规定与生命周期的布置,勾勒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人文传统。王铭铭团队曾以居住在城南老街区的李妈[6]为例描述过泉州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这种“历史感”。李妈的仪式生活是由社区宫庙各神明的诞辰庆典及其家户中的祖先祭祀构成的,周期性的节庆占满了她的生活世界,她的生活节奏也由这些节庆调整着。也就是说,既可以认为这是泉州李妈消遣空闲时间,也可以将其视为泉州人对超越性和神圣性的追寻。这种追寻使泉州人与现代性的断裂时间保持距离,而与一种绵延的多重历史建立深切且动态的联系。
作为遗产主体的泉州,其历史与现状皆彰显了一种复合人文主义。这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且具有方法论的启发。在传统的人文区位学基础上,笔者认为地理和社会的环境或生态,都有深刻的历史性。关系论的考察,不拘泥于区位或社区的横切面研究,而更重视前后相继的历史关系,尤其是注意到作为灵验的遗产——公共仪式的重要性。
2.4 原真性的表现之一:好古主义
这种灵验的遗产,赋予了“物”之外的生活世界以意义与价值。同时,泉州人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仪式也对“物”的好古主义提出了异议,因为拥有仪式生活的泉州人往往对深切的历史及其蕴涵的道德真理抱有敬畏,而不是“物”本身。
“原真性”重要特征之一即是对年代价值(或称之为古老、怀旧)的追寻。2019年4月15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其顶部阁楼遭到大火侵蚀而毁坏。大火催生了文化界对西欧文明的反思,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最为关心的仍是修复问题。这一场修复在法国引起了争议,到底是修旧如旧还是引入创新设计元素?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依然是这场争论的核心。然而有意思的是,这场大火烧毁的本身就是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在1859年大修时加建的一部分。
修旧如旧的逻辑起点即是保护建筑实体的原真性,100多年前加盖的阁楼部分算不算“真”?多久的年代长度才算“真”?“真”的内涵和定义因而被时间性拉伸具有弹性。甚至遗产界本身对此也争论不休,其实践也不断挑战这一定义本身。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没有完工就成为世界遗产的教堂——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天主教大型教堂——圣家族大教堂(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又译作神圣家族大教堂,简称圣家堂(Sagrada Família)。该教堂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1852——1926年)于1883年接手设计和建造,而在他去世时,教堂才完工了不到1/4,直到现在也还没能建造完成。以“古老”来衡量,没有完工的遗产,又何以具有年代价值被冠以“世界文化遗产”呢?
因而,文化遗产国际学界本身便对此疑义纷纷,各国在实践中也未遵循同一套原真性原则。那么,对泉州文化遗产实践的启迪之一应当是:“原真性”框架或许无须被毫无保留地接受。“旧”“古老”或“传统”不一定要成为衡量“原真性”的唯一标准。以木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东亚地区,其文化遗产实践过程必然会遭遇以年代为考量的“原真性”检验,泉州也不例外。伊势神宫以神道哲学的仪式性重建已对其提出根本性挑战。笔者一再强调的是,这一框架与泉州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差距,它本身亦是可被挑战的,何况是在这一框架下指导形成的“年代价值”。
3 结束语
毫无疑问,人文区位学是20世纪社会科学学界提供的一种重要方法论,回应变迁中的空间及社会。泉州的复合人文世界,试图超越传统人文区位学,启发后者更具“地方感”和“历史感”。然而,作为遗产主体的泉州与这一复合人文世界之间是否存在沟壑取决于前者是否会陷入“原真性”博弈——这是自伊势神宫以来非西方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所提出的重大挑战。
“原真性”框架下对“物”的地位强调,对“古物”的重视本身便值得反思。“怀古”的追求是近代以来人类深陷于单线历史价值体系,并将“古老”置于“落后”一端的观念所致。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曾提出,现代人区分了事实与崇拜,并将二者重新整合。他以“事实拜物教”这一概念来说明现代拜物教形态。他指出,我们现代人表面上区分了主体与客体、事物与表征,但其实又悄悄把它们重新整合[15]。世界文化遗产体制的运行与这一现代拜物教具有某种深切联系。拉图尔对其的揭示可以启发我们走出“原真性”,恢复对“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区位学的关注。
在这一视角下的泉州所蕴含的哲学是更为总体性的,更为思辨且动态的——既蕴含在其“治”与“乱”的城市史中,也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其中,公共仪式生活从未远离他们。历史如同祖先一样,常常通过仪式的方式重返社会。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区位学,亦不是一种好古主义。它是一种对人文、生态与社区的“总体性”把握。这种“总体性”没有将过去和现在、历史与现实、古老和当代、主体与客体相割裂。因而这种“总体性”下的复合人文世界亦是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在其“生生”的情状中对渗透着拜物教的现代社会发出淡淡的嘲讽。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