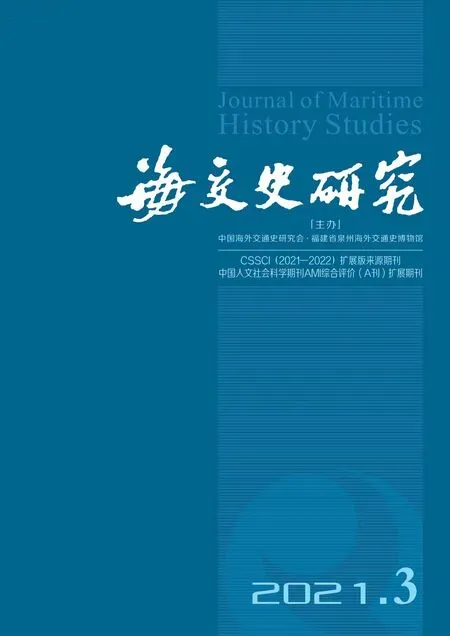登莱巡抚袁可立与朝鲜仁祖请封*
赵亚军
明天启三年(1623),属国朝鲜发生了史称“仁祖反正”的重大政治事件,朝鲜随即派遣使团为新主请封。时值明、金交战,属国政变的消息传到明朝,引起了明朝君臣激烈的讨论。明朝官员纷纷表态,其中节制海上、时任登莱巡抚袁可立的态度更是成为影响朝鲜请封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仁祖请封”一事已有较多的关注,(1)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刁书仁:《天启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以朝鲜国王李倧‘封典’为中心》,载《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6期,第151—158页;高明:《<朝鲜情形疏>与明臣对‘仁祖反正’之政策》,载《韩国研究论丛》,2004年,第306—315页;黄修志:《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46—56页;王桂东:《朝鲜仁祖国王请封述论——兼谈毛文龙之助力》,载《韩国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第69—88页;李迎春:《仁祖反正后所遣册封奏请使的记录和外交活动》,载《朝鲜时代史学报》59,2011年,第105—142页;[韩]Hongkyu Park,Giyeon Kim:《“仁祖反正”之朱子学的正当性研究》,载《韩国政治学会报》50(1),2016年,第51—74页;[日]夫马进:《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和“问罪”》,载《明史研究论丛》2012年第10辑,第289—310页。但大多研究并未关注到在这一事件中登莱巡抚袁可立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拟在借鉴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明实录》《朝天录》等史料,来考察袁可立在这一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
一、东北亚变局中的“仁祖反正”事件
明天启三年、朝鲜光海君十五年(1623)三月十三日,朝鲜绫阳君李倧趁国王光海君患病之机,在朝鲜“义理派”的支持下,联合宫中朝鲜宣祖王后昭敬王大妃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光海君李珲,并将其流放至江华岛,李倧继位为新王,史称“仁祖反正”或“癸亥靖社”(2)[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3,载《仁祖朝故事本末·癸亥靖社》,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66年,第723页。。这场政变是当时朝鲜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也与光海君对明和与后金奉行的两面政策有着很大关系。(3)光海君在位期间对外政策的相关研究参见李善洪:《从十七世纪初朝鲜内外局势看光海君的“两端外交”》,载《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第76—78页;文钟哲:《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光海君的双边外交政策》,载《满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63—71页;尹铉哲、刘吉国:《试论光海君的世子身份问题与即位初期的政策》,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36—140页;王燕杰:《朝鲜光海君时期对明、后金“两端外交”政策探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长宏:《朝鲜光海君在位期间内外举措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光海君李珲是朝鲜宣祖大王李昖庶子,在“壬辰战争”期间被宣祖立为世子,但是由于其非嫡非长的庶出身份,于礼制不合,并没有得到宗主国明朝的承认。宣祖在位期间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三十二年(1604)先后五次向明朝请封光海君,而每一次都被明朝所拒绝。甚至在朝鲜宣祖去世后,明朝也一度拒绝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直到继位的第二年(1609)光海君才取得明朝的册封。
光海君坎坷的请封历程对其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光海君在位期间又逢后金崛起,针对宗主国明朝和兵锋正盛的后金,光海君依违二者之间,并告诫臣下“为今日我国之计,君臣上下,所当务袪杂事,一意征缮。养兵选将,收用人材,宽纾民瘼,慰悦人心。大开屯田,操练器械,城池瞭候,无不整理。然后庶可有恃, 以保缓急矣。不然而或为怠忽,则大祸立至……益殚事大之诚,勿为小弛,羁縻方张之贼,善为弥缝,乃今日保国之长策……惟以先国家之急,为务可矣。”(4)《朝鲜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辛酉,第33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第224页。光海君针对宗主国明朝和后金,奉行“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 的两面政策。(5)《朝鲜光海君日记》卷143,“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第33册,第255页。朝鲜“义理派”认为明朝不仅是朝鲜的宗主国,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更有“再造”之恩,光海君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脱明”之嫌,与“天朝礼治体系”格格不入,更是背弃了朝鲜所信奉的正统观。(6)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9—209页;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7—70页。通过政变继位的仁祖面临着和光海君继位之初同样的情况,即必须取得宗主国明朝的册封,其政权才具合法性。朝鲜是明朝“礼治体系”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明朝最为看重的藩属国,朝鲜历代国王的继位都必须要得到宗主国明朝的认可,即新任国王统治的合法性源于明朝的册封。而此次仁祖的继位是通过政变的形式完成的,更是为礼法所不容,尤其迫切需要借助宗主国的册封来树立自己在国内的正统地位,这也注定了此次请封历程的曲折坎坷。
此次政变中,仁祖宣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策略就是指责光海君背离明朝与后金暗通款曲。他在政变之后即以仁穆王大妃名义下教书宣谕中外:
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 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帅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我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战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斁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7)《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甲辰”,第33册,第503页。
教书对光海君的通虏背明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强调朝鲜上下是秉持大义废黜光海君,意在表明此次政变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仁祖于三月十七日召见派往东江毛文龙处的问安使南以恭,令其在应对毛文龙时,“善为措辞,以同心协力之意,详谕于毛将可矣”(8)《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丁未”,第33册,第508页。,之后三月二十二日仁祖接见毛文龙差官以说明情况,“(壬子)上接见应守备于明政殿。守备名时泰,毛文龙差官也”(9)《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壬子”,第33册,第512页。。仁祖又令议政府左仪征朴弘者等移文明朝总兵毛文龙,乞为转奏,称:
本年三月内,奉王太妃教旨……嗣王珲忘恩背德,罔畏天威……陵(绫)阳君倧仁声夙著,天命攸归,乃于今月十三日讨平昏乱,已正位号……咨尔政府备将事意具奏天朝,一面咨会督抚衙门以凭转奏。(10)《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740页。
仁祖又于四月二十七日派使团前往明朝请求封典,“韩平君李庆全、同知中枢府事尹暄、书状官李民宬如京师奏请册封”(11)《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四月丙戌”,第33册,第528页。。其实在仁祖之前,朝鲜已经有着非正常得位而请封成功的先例。如朝鲜世宗李裪,本为朝鲜太宗第三子而非嫡长子,初受封为忠宁大君,后在太宗长子、次子均在世的情况下,被封为世子。当时在位的明朝皇帝为明成祖,成祖以“立嗣以嫡长,古今常道,然国家盛衰,实系子之贤否,今欲立贤为嗣,听王所择”(12)《明太宗实录》卷202,“永乐十六年七月丙子”,第2095页。为由同意了朝鲜的请求,后于永乐十七年(1419)正式册封李裪为朝鲜国王。(13)朝鲜世宗和世祖时期的请封,恰逢明朝成祖、代宗在位期间,成祖以“靖难”夺位,代宗则是代兄而立,朝鲜顺利得封,应当也和明朝两位皇帝得袭皇位之特殊经历有很大关系。朝鲜世祖李瑈,本是朝鲜世宗之子、文宗之弟,文宗去世后,年幼的世子继位,是为端宗。时为首阳大君的李瑈袭杀辅佐端宗的大臣金宗瑞等人,掌控朝鲜政权。后李瑈废侄自立,在请封时朝鲜隐瞒明朝,称是端宗主动让位与首阳大君李瑈,从而得到了明代宗的册封。(14)《明英宗实录》卷263,“景泰七年二月癸卯”,第5607—5608页。之后的朝鲜中宗李怿,是朝鲜第一位通过“反正”而得位的国王。明正德元年(1506),朝鲜国内发生政变,朝鲜大臣废黜旧王燕山君,拥立晋城大君李怿为主,随后以旧王无子病重、辞位让贤为名前往明朝请封。此次请封朝鲜亦是刻意向明朝隐瞒了政变的事实,而获得了册封。(15)《明武宗实录》卷33,“正德二年十二月戊寅”,第807页。
但仁祖请封与之前朝鲜历次请封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仁祖关于政变的事实并未刻意隐瞒地向明朝作了汇报,朝鲜政变发生时,正值明朝对后金战事节节败退之际,而朝鲜又是明朝用来牵制后金的重要藩属国。此时属国政权发生更迭,且有与日本相联络的传言,更是扯动了明朝敏感的神经,属国政变已经直接关系着明朝疆场的安危,引起了明廷疆臣的高度关切。因此不难想象,此时朝鲜国内发生政权更迭,将会给明朝君臣带来很大的震动。原本光海君主政期间针对明朝和后金所采取的“两端外交”政策,已经引起明朝的不满,两国关系非常微妙,而“仁祖反正”事件的发生无疑又给当时的中朝关系再添变数。
此时明朝的军事和外交布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针对兵锋正盛的后金,军事失利的明朝不得不调整其军事部署,依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建议,于天启元年(1621)在天津、登莱两处紧要地增置巡抚一职,同时由于陆路的阻断明朝改朝鲜贡道于海上,朝鲜使臣渡渤海在登州登陆,接待朝鲜使臣一事便由新设立的登莱巡抚负责。此时的登莱巡抚不仅承担着海上应对后金威胁的重任,同时还兼具节制东江、向朝鲜传达明朝旨意、监视朝鲜动向和联络朝鲜的职责。在明朝新的军事布局中,属国朝鲜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及其外交向背也直接关乎着明朝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属国政变一事上,明廷还需要着重考虑以登莱巡抚为代表的封疆重臣之意见。
天启二年(1622),首任登莱巡抚陶朗先被罢,明朝任命袁可立为新任登莱巡抚。袁可立抚登期间,明朝新的国防体系已初具规模。当朝鲜政变发生后,负责将政变消息汇报给朝廷的正是登莱巡抚袁可立,处在这一重要位置的袁可立也因此取得了对这一事件的优先发言权和重大影响力。“仁祖请封”事件则将袁可立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二、袁可立在朝鲜请封事件中的作用
(一)袁可立提供的政变情报直接影响了明朝廷的判断
朝鲜政变之后,仁祖很快派出使臣前往明朝通报情况并为自己请封。令朝鲜意想不到的是,明朝方面在朝鲜政变发生后不久便得到了仁祖反正的相关消息,其中有勾结日本、杀害旧王等对仁祖极为不利的说法,在朝鲜使团抵达京师前,明朝君臣已经围绕此次朝鲜政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明朝获知朝鲜政变的消息是来自登莱巡抚袁可立的奏报。政变之后的仁祖通过毛文龙揭报登抚袁可立,在明朝的高级官员中,登抚袁可立是第一时间获知这一政变消息的。而登抚事权之重,又有节制东江、联络朝鲜之责,因此在册封朝鲜一事上,袁可立的意见至关重要。
在接到毛文龙正式奏报之后,袁可立便向朝廷上言称:
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係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傥为封疆多事,兵戈宜戢,亦宜遣使宣谕,播告彼邦,明正其罪……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只奉国祀。如国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16)《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戊子”,第1741页。
针对朝鲜国内的这场政变,袁可立反应强烈。他从君臣大义出发,认为李倧未上报明朝而自行废立的行为,形同篡逆,是秉持儒家传统观念的明朝君臣所不能容忍的,应当声罪致讨。即使朝廷迫于形势最后不得不默认这一行为,也要仿效国初册封李成桂故事,令李倧避位,只奉国祀,而不能直接册封其为正式的国王。朝鲜太祖李成桂在夺得政权时,并未自立为王,而是以权知国事的身份遣使明朝请求册封,袁可立所提“如国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之建议,亦是对此先例的援引。之后袁可立又向明廷奏报了另一个重大消息,即朝鲜政变疑有日本参与其中,其在奏报中又称:
职犹有闻为珲境往来员役有语,朝鲜举国皆欲从权,而独李珲念昔年御倭之恩,望报中国,因罹今日之变。而李倧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备如此也,则徐可北联夷南通倭,舟楫帆樯倭所惯习,载奴以来,海上之事将大有可虑者!(17)[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8,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1—502页。
登抚袁可立身任封疆,十分重视朝鲜政变后对明朝海疆安全的影响。登抚无疑是在提醒明廷,发动政变的李倧有“媾倭”之嫌,事关明朝封疆安危,已不能像以往历次册封朝鲜那样等闲视之,必须加以审处。时人对“壬辰战争”尚且记忆犹新,而日本因素的出现,意味着此次政变将很可能会大大超出明廷君臣的预料,引起了明廷的强烈不安,因而登抚袁可立关于朝鲜仁祖“媾倭”的奏报,对明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继毛文龙题本之后,袁可立又从归国途经登州的孟养志处进一步了解了仁祖反正的情况,并得知朝鲜已派出使团为仁祖请封的情况。袁可立随即发出军令,指示麾下如遇朝鲜使团,当令其暂居庙岛然后速报院道。朝鲜李庆全一行于六月十二日在庙岛见到登州水营刘姓游击的票文,“本月初二日,蒙海防军门袁宪牌,照得朝鲜罪当声讨,而朝议未定。近据孟推官禀称,目下已差陪臣入请,如彼船到,当令暂止庙岛,速报院道,以凭差官查检明白,方许进关……毋得疏虞,致误军务。”(18)[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册,2013年,第278页。在李民宬等人看来“票文之语,不可正视”,使团由此意识到明朝对朝鲜政变反应非常激烈。当朝鲜使团到达登州之时,袁可立又派人对使团进行严查,之后方准进城,从这一系列行为不难看出登抚袁可立是以“篡逆”来对待这场政变。
六月十三日使团到达登州,次日得到登抚袁可立的召见,书状官李民宬记载了袁可立当面询问使团关于朝鲜国内的情形:
呈申文,抚院立语曰:“你国旧王在否?”答曰:“在矣。”曰:“有子否?”答曰:“有一子。”“在那里?”答曰:“同在一处。”曰:“闻旧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答曰:“无此理。”军门曰:“十三日动兵云是耶?抑旧君自退耶?”答曰:“其失德,详在申文中,老爷见之则可以详悉矣。一国大小臣民,不谋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权署国事,天命人归,从容正位,岂有动兵之事乎?”军门曰:“然则烧宫室云者,何故耶?”答曰:“宫妾所居之处,点灯失火,而正殿则依旧矣。”军门曰:“你国定乎?”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总镇毛驻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则岂有掩护小邦,欺瞒朝廷之理哉?”军门曰:“晓得。”仍命茶,谢拜而退。(19)[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279页。
会见中袁可立问及朝鲜旧王是否自退并进一步问及其子嗣情况,意在打探旧王光海君及其世子、宫眷是否如孟养志所说已遭仁祖屠戮。在得知光海君尚存之后接着问及当天朝鲜王宫内是否动兵以及宫室失火的原因,也是在进一步求证仁祖是否以救火为名发动的军事政变。虽然朝鲜使团回答的失德、点灯失火不具说服力,最后又不得不搬出毛文龙来应对袁可立的盘问,但通过此次会见及朝鲜使团递交的呈文袁可立进一步了解了朝鲜政变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确定了朝鲜光海君并未在政变中被杀。因此袁可立对待此次仁祖请封的态度也开始有所缓和:
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封疆重寄,行文防慎,此自事理当然,而今睹见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20)[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279页。
由此可见袁可立在进一步了解到朝鲜政变后国内的情况后,对待朝鲜使团的态度已不似之前那般强硬,之后又为朝鲜上本朝廷陈说,李民宬称“(袁可立)差伴送指挥许选,偕臣等护送进京,许选赍来军门上本,称道本国忠顺之状”。(21)[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33页。
朝鲜使团经过这次会见意识到诸如杀害旧王、火烧宫室等对请封极为不利的流言,已在明朝尤其是朝廷高级官员中传开。关于朝鲜政变的信息在传递到明廷的过程中陡生变故,为朝鲜所始料未及,此时请封使团又多了一项为仁祖辨诬的重任,惊骇之余匆忙回禀仁祖。针对明朝关于仁祖反正不实的说法,朝鲜使团称是因为袁可立听信毛文龙浪言及推官孟养志的诬陷,孟养志于天启二年(1622)七月从天津出发,“宣谕朝鲜,今于六月之杪倐然归来,赍有朝鲜回照,乃彼国篡立之详则”(22)[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333页。,经历了仁祖反正的整个过程,毕自严对朝鲜政变的消息以及武力政变、杀害旧王等说法就是来自孟养志的叙述。在给仁祖的汇报中,使团推测流言应出于推官孟养志“大概如孟推官者,曾往我国,不得充其所欲,大肆怨怨,构捏无极之言云”(23)《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七月己酉”,第33册,第543页。,并准备进京之后如若遇到明朝以流言诘问的情况,一概以孟养志的构诬为措辞来应答辩解。
继登抚袁可立表态之后,朝中群臣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明朝的绝大多数官员都与袁可立一样反应强烈:
内外诸臣抒忠发愤,有请声罪致讨者,御史田唯嘉也;谓必讨其罪而当再诘其详者,登莱抚臣袁可立、礼科都给事中成明枢也;谓不可不讨而不可遽讨,且弗受方贡,细核颠末者,督饷臣毕自严也;谓当令毛文龙诘问,责以大义,察其舆情之向背者,关臣潘云翼、南台臣王允成也;谓当诘此事只以通奴不通奴为主,珲诚通奴则倧之立非篡也,但擅立为罪耳,而责以讨奴自洗者御史游士任也,种种条陈咸有可采。(24)《明熹宗实录》卷37,“天启三年八月丁丑”,第1916页。
明朝诸臣对于仁祖反正的反应大大出乎朝鲜的意料。后来为仁祖请封的朝鲜使团到达京师后,李民宬见到明朝官员诸题本及叶向高辞本内容,不无心痛地道“并及我国废立事,议论甚峻”(25)[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30页。。
朝鲜使团一行于七月二十六日到达北京,之后便为请封一事奔走于各衙门,八月一日诣礼部,礼部主事官语于译官李膺等曰:“你国请罪旧君后请封可矣,事体重大,部里不可擅便,在圣旨如何耳。”于礼部请封未果,使臣又于八月三日奔内阁递交呈文,当内阁叶向高得知使臣为请封一事而来后便责问使臣:
阁老曰:“坏旧君自立,事不明白,何以来请邪……何故不报朝廷而径自废置邪?”答曰:“旧君在位,谁敢以失德报闻天朝”……叶阁老曰:“你国举事时,引用倭兵三千何邪?”力陈孟推官挟憾构诬之状。阁老曰:“若他外国之事则第循其请,你国与天朝一般,须加慎重,行查后方可准也。”(26)[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295页。
叶向高对朝鲜是否引倭兵举事的诘问,显然是采信了登抚袁可立奏本中关于仁祖为倭婿的说法,而仁祖未通知朝廷而擅自废立的行为又于礼法不容。为了明朝事体,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决定先行查朝鲜而后再议是否册封。仁祖为“倭婿”的说法,成为明朝行查的重要动因。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袁可立所提供的政变情报直接影响了明朝廷官员对于政变性质的认定,仁祖通倭的说法引发了朝臣对朝鲜怀有二心的强烈怀疑,直接阻碍着朝鲜请封的成功。
(二)袁可立获得行查朝鲜政变实情的委任和权限
使臣见明朝行查的决议已定,便试图说服明朝将行查一事委于毛文龙:
督府时驻小邦,本国事情,无不洞烛,自当从实查报,岂有容护小邦之理乎……伏乞老爷只移文于毛督府,使之明查题覆。若曰不可不送差官,则只差一介小官,到于督府,定以日限,使之查访而来,则往返似为快速,事体恐为便当。(27)[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32页。
对于使臣的建议内阁最初也表赞同,之后兵部也表态“小邦之事,轻动皇华之旌,屑屑焉曲访其迹,亵体谓何,惟专督之毛帅可矣”(28)[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297页。。而对于内阁、兵部的建议,科道官员表示行查之事不能轻率,应慎择查官,“礼科都给事中成明枢亦言……仍一面敕登抚以细讯属国之情,一面谕枢辅以详商讨逆之举”(29)《明熹宗实录》卷33,“天启三年四月戊子”,第1741页。,“礼科周朝瑞题:海外之使已轻,不宜再轻。乞勑当事,慎重选任,以全中国之体,无取轻四夷”(30)[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298页。,“兵科右给事中周之纲疏论时事言……朝鲜废立,诡谋叵测,堂堂中国何难声大义者,伏祈特谕登抚行查毛帅,彼中果否,即有申奏再行责谕,庶审局详虑,胜着可图,而疆圉有赖矣”(31)《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五月癸丑”,第1776页。,科道官员主张应由登抚全权负责行查一事。而对于使臣的提议礼部官员魏大中则直接回复使臣“毛帅不大紧,不要再说”(32)[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37页。,礼部也认为毛文龙不足以担此重任。之后礼部尚书在看到毛文龙为朝鲜请封的题本时,更是大发雷霆“尚书览未了,勃然而怒,奏本投地曰:海外一武夫,冒干此等大礼,则该部奚容议为?”(33)[朝]洪翼汉:《花浦先生航海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第476页。因此在行查一事上,礼部归重登莱巡抚,行查一事也全权委于登抚负责:
封国重典,非可率略从事……登莱巡抚建牙海上,体统严重,声息易通,合无一面移咨抚臣袁可立,一面箚付毛文龙,听其酌遣的当官员,到彼详加体访,取该国臣民公本回复,并抚臣具奏,恭俟圣裁。(34)[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298页。
在行查朝鲜一事上登莱巡抚制度上的权威凸显出来。礼部的建议得到了皇帝首肯,于是由登抚袁可立主导、东江毛文龙协助定以本年(1623)闰十月为期限共同行查于朝鲜。
仁祖反正之初,为能顺利取得明朝册封,一方面重点指责旧王光海君背离明朝的行径,另一方面欲通过支援毛文龙来示好于明朝,(35)[朝]吴庆元:《小华外史》卷5,载《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史部第12册,第617页。以期减少请封过程之阻力。因而朝鲜有助兵明朝八万之说,“毛文龙向苦无兵,而括辽人四万,以实军伍。而朝鲜又助兵八万,声势愈壮”(36)[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00页。。朝鲜仁祖的这一做法博得了登抚的好感,同时也影响了登抚对请封一事的态度,无疑是成功的。
登抚袁可立在接见过朝鲜李庆全一行后,便在给朝廷的军事奏报中阐述应趁机令朝鲜助兵,共同对付后金,“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37)《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七月甲寅”,第1882页。。登抚的意见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在令朝鲜出兵助效的问题上,明朝中央和登抚达成了一致。御史胡士奇题,“臣更有疑于朝鲜焉,不奉朝命而擅自废立,虽助兵效顺,安知其不二心于我。且八万之众,乌合蚁聚,缓急恐未可相恃。宜敕毛帅,侦其虚实,果真委身归命,戴罪讨贼,功过相准,然后羁縻勿绝。”(38)[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295—296页。督饷侍郎毕自严也认为“候其进兵剿奴,功绩昭著,而后封之。”(39)[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335页。曾与袁可立共事的兵部尚书赵彦则建议朝廷由登抚负责宣谕朝鲜助兵,“降敕谕一道发登莱抚臣,差官捧赍至朝鲜,先命李倧权管国事,如中国郡王管理亲藩事例,令发兵数万同毛文龙列营栅于附近海岛中,不时出疑兵、奇兵以扰奴……先命权署国事以收其心,后许册封以籍其力”(40)[朝]赵濈:《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第413—414页。。
(三)袁可立态度的转变促成了明朝廷的允封
当明朝遣官行查之时,朝鲜派出的第二支使团途经登州并于天启三年(1623)九月二十八日拜见登抚袁可立:
(登抚)仍问旧王在何处,答以在畿邑;且问旧世子在何处,权辞答以同在一处;又问你国军兵几何,答以小邦平日寓兵于农,别无组练之兵,顷日深河之役,丁壮尽死,今之现存甚为零星。今日边上一万分守仅足自卫,老爷若约束举事,固当竭力加调,务为同仇之义云。则军门曰唯唯。(41)[朝]赵濈:《朝天录》,第390页。
袁可立确认过朝鲜旧王情况后,便询问使臣朝鲜国内军队情况,使臣根据临行前备边司的指示,当面向袁可立表达了朝鲜上下愿与明朝同仇敌忾的决心。此举无疑大为改善了登抚袁可立对仁祖反正的看法。而明朝对朝鲜的一些处置措施又都交给登抚具体负责,登抚的意见也愈发重要,明朝对朝鲜请封的后续处置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登抚的影响。在处置朝鲜请封的问题上,身处前线的登抚更看重朝鲜在辽东战事上对明朝的军事支持。袁可立认为明朝可借朝鲜请封的机会,进一步争取朝鲜的军事援助,共同对抗后金。因此他建议朝廷,如果朝鲜“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42)[明]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载《拟山园选集》卷62,《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袁可立这一务实的建议得到了明朝的首肯,“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是以东事一视公”(43)[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载《媚幽阁文娱二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第433页。。于是接下来袁可立在接到朝鲜国内保结之时,虽暂未接到查官的正式回禀,仍将保结移咨礼部,为朝鲜助封。登抚的这一行为,可谓是默认了朝鲜的仁祖政权,袁可立态度的转变,推动了朝鲜仁祖请封的进程。
在明朝所遣查官到达朝鲜之前,朝鲜君臣就已经得到了使臣的呈报,“表(袁)军门御使(史), 因孟推官诬罔之言,不知本国事实,题本之辞,有不忍言者。科道官亦多参驳,阁老诸官相议,将出送查官事。”(44)《承政院日记》,“仁祖元年十月乙丑”,参见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承政院日记》,检索系统:http://sjw.history.go.kr/main.do.于是朝鲜上下便开始着手准备应对明朝的行查,并写就保结送往明朝。天启三年(1623)闰十月十九日,朝鲜使团听说本国保结已到,便再赴礼部请封。但礼部以未接到登抚袁可立的正式题本为由加以拒绝,“昨揭帖十二封,是你各道投毛总兵者,非公本也,公本到,自有登抚具题,本部因得覆请遣封”(45)[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05页。,礼部表示只有在接到登抚题本之后才能为朝鲜请封。之后使团企图以进方物的名义呈文礼部尚书,遭到礼部官员拒绝,“你国封典必待查官回到,然后方可施行。李庆全等每以此事呈文,有似督迫之为,尚书厌其烦,今又你们呈文请完,则必生怒矣”(46)[朝]赵濈:《朝天录》,第405页。。在未取得登抚题本的情况下,礼部屡次拒绝朝鲜使团请封的要求,朝鲜使臣这才意识到请封能否成功,登抚袁可立的态度至关重要。
于是在等到期限已过而查官仍无回报时,使臣便急忙派人前往登莱巡抚袁可立处,恳乞袁可立上请封题本,“以本国保结已到,查官钦限又过,将此辞缘具由题本,冀得请封阶梯”。同时以“本国保结已到,查官回报无期”为由再次到礼部请封,而礼部尚书认为“少待登抚回奏,方可施行”(47)[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36页。再次加以拒绝,礼部坚持必须等接到登抚题本之后才能上奏请封。使臣无奈只好继续奔波于内阁与礼部,礼部官员不胜其烦,便以“查奏无期,陪臣苦留,情理可怜,况本国保结已到,虽无抚院之本,似当有变通之举”等由诉于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林尧俞指示使臣“奈登抚题本未到,本部难于上请何……陪臣奏本,无前例,当以你本中事理,具举于本部题内,请裁可矣”(48)[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10页。。
在无登抚正式题本的情况下,由礼部尚书代为转奏请封:
臣部前议会同兵部移咨登抚,并札毛师遣官往勘……闰十月内登莱抚臣揭送彼国公结十二通……自宗室以至八道臣民合词一口,皆称珲为悖逆倧为恭顺,人情如此,固不待勘报至而已了然矣……当此为危急之秋……似未可以经常例论矣……伏乞先颁勑谕一道登莱抚臣,差官同陪臣至彼锡以?朝鲜国王名号,统领国事……俟恢复渐有次第,始遣勋戚重臣赍捧节册完此封典。得旨:李倧既系该国臣民公同保结,伦叙相应,又翼戴恭顺,输助兵饷,准封朝鲜国王。先与勑谕,著登莱巡抚官差官同陪臣赍赐,其册使候事宁,查照旧例行。(49)《明熹宗实录》卷42,“天启三年十二月癸巳”,第2186—2187页。
此时朝鲜请封终于获准。由礼部的奏本内容可以看出,最后朝鲜虽是在以礼部的名义上本之后取得明朝允封,但这也是在收到由登抚转呈的朝鲜国内保结为前提的。在为朝鲜请封的问题上,登抚的题本是请封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正常的情况下礼部绕开登抚请封是于事体不合的。礼部上本请封是在“此时急在边疆,似未可以经常例论矣”的情况下的变通之举。而登抚在未得到行查官员正式回报的情况下,将朝鲜公结十二通送至礼部,也间接地表明了对朝鲜请封持支持态度。之后被派往登抚处的朝鲜官员便取得了登抚袁可立的正式题本回京,“多般费力,始得袁抚院请封题本……以袁抚院题本奉圣旨,姓讳已有旨准封,该部知道”(50)[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第339页。。此时袁可立是在未接到查官正式回禀的情况下,写就题本为朝鲜请封,证明了登抚袁可立赞成册封朝鲜的态度。而明廷收到登抚题本后即发圣旨通知登抚,也表明朝廷对登抚的重视。
明朝虽然允封,但未派出官员前往朝鲜册封。天启四年(1624)四月,登抚袁可立在离任前接到查官正式回禀便奏报朝廷,并奏请朝廷派出专使到朝鲜进行册封:
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朝鲜更立情实,请敕专使以重册典……登抚袁据公本结状回文内事,理细核之维栋语言相符,随具奏,复云:“彼国臣民之众拥戴已经一岁之久,迄无异言,人心所在,天命攸归,封倧之典似不容己者。但册典宜重,以朝使则遵旧章隆大典。倧之受命而王也,感戴之忱将与带砺而同永矣。”(51)《明熹宗实录》卷41,“天启四年四月辛亥”,第2348—2351页。
奏本上时袁可立已经卸任登抚,明朝计划平定后金之后再正式册封朝鲜。于是朝鲜不得不再次派出使臣到明朝请求正式封典,仁祖派遣李德泂为谢恩兼奏请使,再到明朝请求赐给诰命和冕服。经过朝鲜的不懈努力,明朝派遣官员于天启五年(1625)六月正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至此得到明朝承认的仁祖终于成为了朝鲜“名正言顺”的国王。
仁祖请封的成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东北亚局势。取得政权合法性的仁祖一反光海君时的两面政策,在对后金的战事上给予明朝很多援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后金对明朝的军事压力,在“三方布置”战略中开始发挥实际效用。但也激怒了后金,进而导致了后来的“丁卯虏祸”“丙子虏祸”的发生,这也是当时朝鲜君臣所始料未及的。
三、“请封事件”中袁可立的“双重权威”
袁可立能够在朝鲜请封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由于明廷推重登抚,欲重其事权,另一方面也和袁可立本人在朝堂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
(一)作为登抚在涉朝事务中的权威
登莱巡抚这一职位是明朝在辽东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设立的。天启元年(1621)随着辽东局势的恶化,明廷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熊廷弼针对辽东战事提出“三方布置”策略,“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52)《明史》卷259,《熊廷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696页。。明廷采纳熊廷弼“三方布置”的策略,于天启元年(1621)六月设立登莱巡抚。
当年八月熊廷弼进一步提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53)《明史》卷259,《熊廷弼传》,第6697页。,朝鲜也被纳入到“三方布置”战略中来。与此同时由于辽东的失陷,明朝与朝鲜之间陆路不通,明廷便“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54)《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302页。,朝鲜贡道正处在登莱镇防区内,因此联络朝鲜方面便由登莱巡抚负责。天启元年(1621)八月,明将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为了更好的牵制后金,明朝于天启二年(1622)六月加封毛文龙为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开镇东江。为统一事权,明朝将东江镇划归登莱巡抚节制,此时登莱巡抚麾下节制了登莱镇和东江镇两个军事重镇。登莱巡抚的事权进一步增加,“牵制敌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55)《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304页。。
当天启三年(1623)朝鲜政变发生后,接报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转达到明朝中央。对于朝鲜政变一事除了朝中官员外,在天津督饷的毕自严认为“不可不讨而不可遽讨”。而以阁臣身份坐镇关门的孙承宗则与袁可立持相同的立场,“以高皇帝于李成桂亦姑容之,况鲜人以晖应奴、琮附我为名,而琮自称权摄国事,归附于我,则名亦自正”(56)[明]茅元仪:《督师纪略》卷6,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6册,第361—362页。。在明朝官员诸多意见中,坐镇三方的辽东孙承宗、天津毕自严、登莱袁可立这三位前线重臣的意见趋于统一,并在朝野影响最大,直接影响了从内阁到民间对朝鲜政变的看法,这从明朝文人对“仁祖反正”这一事件的记载中也可窥见一二。登抚袁可立在其《请讨簒逆疏》中称仁祖李倧“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57)[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8,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6册,第502页。,这一说法引起阁部官员高度重视,内阁当面询问使团有无倭兵一事。(58)袁可立指责仁祖“篡逆”“通倭”,不仅影响到了当时朝鲜请封的进程,同时也影响了明人对这一事件的历史书写,也成为入清后朝鲜屡次到清朝为仁祖辨诬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见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79—91页;黄修志:《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46—56页。浙江道御史彭鲲化更是直接上言朝廷:“朝鲜内变,国王李珲一旦为侄所废,彼先自乱安能助我,况无君之人岂肯倡义效顺,且为倭婿与奴连,若举朝鲜归顺奴酋,毛文龙必难久居,牵制无人,奴得安意西来,无复东顾之忧矣。”(59)《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五月乙未”,第1767页。
在袁可立之后,当时在天津的督饷侍郎毕自严又上《朝鲜情形疏》,内称李倧“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李珲投烈焰中,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60)[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333页。,“李倧以臣弑君,以侄弑叔”(61)[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第334页。等语,当时流传于明朝朝野间关于朝鲜政变的说法大多源于袁、毕二人的奏疏。如《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两朝从信录》《毛文龙演义》(又名《辽海丹忠录》)等书便是和袁可立、毕自严持一样的立场以“篡逆”的性质来记载朝鲜的这一政变:
高汝栻曰……朝鲜咸欲从奴,晖念昔年卵翼之恩,誓报中国,倧又系倭壻,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助也。(62)[明]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12,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7册,第810页。
按李珲,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称仁孝。李倧其亲侄也……常在李珲左右用事……因见李珲有疾,遂起谋逆……于三月初九日在于宫中举火为号,李倧率李贵等指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李珲,投烈焰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妃仗义执言,数李珲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倧遂即王位。(63)[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8,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6册,第499页。
明末文人陆人龙以时事小说形式写就的《毛文龙演义》一书,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代表了当时明朝民间对仁祖反正的看法:
臣弒君,子弒父,天下大逆,况杀其身,据其位,明明是篡,百口怎解……当日朝鲜国李晖……只因他有病,把国事托与侄儿李综,李综凭关自己有谋勇,有异相,有不良之心,每与边臣相结。有不一良之心,每与边臣相结。天启二年正月(64)注:应为天启三年(1623)。将他党与平山节度李贵召入王京防御,到三月初九,约人在宫举火,他把救火为名,与李贵入宫,恰遇李晖慌慌张张而来,指望他相救,不意李综竟将来一把拿住,撺入火中,并把他世子宫眷尽皆杀戮。(65)[明]陆人龙:《毛文龙演义》,陈志明校,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从明人对朝鲜仁祖反正这一事件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时人认为这次朝鲜的政变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政变是如出一辙的,他们用了中国传统政变中“君王托国政于臣下,反被臣下谋害夺权”的模式,来解释朝鲜的政变,是以自身经验出发,结合流言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想象式创作。
天启帝曾言“疆事当责成边臣”(66)《明熹宗实录》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癸未”,第1469页。,因而明廷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以登抚负责对朝鲜的行查,登抚的意见便成为明廷的主要考量。在其后的请封过程中,明朝廷也不断强调需要以登抚的意见为主要参考,在登抚没有表态之前,拒绝立即做出是否允封的决断。明朝推重登抚有着很深的政治考量,一方面是由于联络朝鲜本来就是登抚的职责之一,朝廷接收有关朝鲜消息的主要渠道亦由登抚提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明朝希望通过一再强调登抚的重要性来维护乃至加强这一新设职位的权威,以期登抚能在“三方布置”这一新的战略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朝鲜请封一事上,节制海上的登莱巡抚态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天启四年(1624)到明朝请求正式封典的朝鲜使臣洪翼汉一行,在登州拜见新任登抚武之望之后,在登州逗留近二十日,必欲取得登抚的助封题本。他们以上任登抚袁可立已上题本为例,请求武之望也一并上本,“伏乞老爷,另具一奏……且表(袁)老爷曾已题请……恳乞老爷照详政府申文及职等呈文,一依表(袁)老爷上本”(67)[朝]洪翼汉:《花浦先生航海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8册,第443页。。为求得登抚题本,使团甚至不惜贿赂登抚左右官员,反映出朝鲜方面已经认识到登抚在明朝处理宗藩事宜中的重要作用。但武之望显然不如旧抚袁可立那样重视朝鲜,其以新到任 “不可以他事轻先上本”为由,只写就一封私函与礼部尚书为朝鲜助封。(68)[朝]洪翼汉:《花浦先生航海朝天录》,第444页。
(二)袁可立本人的政治威望
袁可立,明朝睢阳卫人(今河南睢县),万历己丑(1589)进士,晚明重臣。袁可立在万历十七年(1589)得中进士后“除苏州府推官”(69)[清]王枚:《睢州志》卷6,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志辑》第3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在任期间,处理湖州“董范之变”,江南子弟王士骕、乔一琦通倭事件,平反知府石昆玉冤狱以及解救琉球渔民,(70)[明]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载[清]陆时化撰:《吴越所见书画录》卷5,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9—490页。颇有政绩,寻“擢监察御史”(71)[清]王枚:《睢州志》卷6,第372页。。在御史任上“上书忤当路,削籍二十六载”(72)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22,《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载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53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556页。,赋闲在家的袁可立并未消沉,而是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泰昌元年(1620),“起尚宝司司丞。踰年辛酉,升本司少卿……寻晋太仆寺少卿”(73)[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2010年出土,睢县袁氏家藏。。当时正值辽东事起,袁可立条上急务七事,针对辽东局势比较系统的提出七条对策,其中一条为“一出奇兵……宜急敕登莱抚臣督兵过海……等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救也。”(74)[明]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载《吴越所见书画录》卷5,第491—492页。袁可立对登莱镇在明对后金战事中的牵制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也为他之后出任登莱巡抚埋下了伏笔。天启二年(1622)三月,袁可立升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75)[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同年,袁可立被明朝任命为登莱巡抚。
复出后的袁可立曾于天启二年(1622)三月任通政使司左通政,掌言路,时人赵维寰上《拟上救时万言书》言事,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语:
书既具,上之银台,台长袁可立,读既谓予曰:“语太长,须节去数则。”余请曰:“不知欲节去何处?”袁缕指之,则皆触忌语,实最吃紧处也。余应曰:“若去此数则,何救于时?”执不许,时左台陈中湛先生,力为余从谀,而袁竟格不封。(76)[明]赵维寰:《拟上救时万言书》,载《雪庐焚余稿》卷3,《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8册,第457页。
因为赵维寰疏中有“触忌语”,袁可立指示其删去,因为作者的坚持不肯删减,最后袁可立“竟格不封”。通过袁可立对此事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出,当初因进言遭到罢官的袁可立,时隔二十多年后重回朝堂,已然变得愈加的老成持重,而其对辽事的关注,对登莱的战略认识,则直接促成了袁可立抚登之行。天启元年(1621)登莱镇初设,为登莱镇筹建出力甚多的陶朗先,便由登莱兵备按察使升任第一任登莱巡抚,(77)《明熹宗实录》卷11,“天启元年六月丙子”,第550页。相较于陶朗先由登莱地方官员升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则是由中央直接派出,开启明廷以重臣镇登莱的先例。
袁可立履任之际,明与后金在宁远、山海关一线陷入对峙的局面,此时处于辽南的金、复、海、盖四卫便成为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明朝辽阳失守后,“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78)[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117页。,就连沿海的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等岛屿也被后金控制。南四卫的失守对明朝后方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时人王在晋尖锐的指出“南卫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复、海、盖陷,而大海之险我与贼共之。贼常觇我之往,我不能禁贼之来……彼如乘风破浪,直捣津门,窥其所大利,攻其所大忌,是为引寇入门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莱,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蔽,山海无粮,何能久守?而京师亦危。”(79)[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140页。而此时新设立的登莱巡抚正肩负着规取四卫战略任务,“设抚镇开府于登,以安戢东江,而图四卫,为恢复辽东大计”(80)[明]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17,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5册,第309页。。袁可立上任之后,即开始着手整顿登莱防务,训练军队,并对后金发起海上攻势。袁可立经过数月的筹划,指挥麾下登莱、东江两大军镇主动出击后金,此次出兵“规取四卫,与毛文龙相应,共济大谋”(81)[朝]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296页。,并与坐镇关门的孙承宗遥相呼应。(82)[明]茅元仪:《督师纪略》卷6,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6册,第334—335页。在出兵筹划收复四卫期间,袁可立策反了当时后金管理南四卫的汉将刘兴祚。(83)[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关于刘兴祚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参考姜守鹏:《刘兴祚事迹补考》,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77—82页;郭成康、成崇德:《刘兴祚论》,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0—36页;高志超:《刘兴祚事迹考:明清鼎革之际辽东汉人的政治取向》,武汉:长江出版社,2010年。登莱对后金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84)《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七月甲寅”,第1 882页。,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85)[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在抚登期间袁可立多次取得对后金的军事胜利,并在渐次收复的一些沿海岛屿上驻兵巡逻,“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86)[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在朝鲜使臣的记载中沿海诸岛对后金防备甚严,“移棹近岸,唐人列立结阵,若待变者……参将曰:‘与贵国事同一家,安有疑阻。与贼相对,关防事体,不得不尔’……战船六只,炮杀手若干人皆浙兵……与奴相对,巡逻警备之方不可不严”(87)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载《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275页。。同时为海上大局计,袁可立全力支持东江毛文龙,为更多的争取朝鲜对东江的支援,袁可立与孙承宗商议将册封朝鲜之功送与毛文龙,“此当令毛将军做人情,便可停妥”(88)[明]孙承宗:《孙承宗集》卷20,李红权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667页。。在袁可立主持下登莱对后金的海上防线日趋完善,其取得的战绩进一步增强了袁可立个人在朝堂的影响力。
袁可立在新设立的登莱巡抚任上很快打开了局面,登莱、东江两个军事重镇的军力得到提升,一度瓦解了后金在南四卫的势力,压制了后金对辽东半岛的攻势,明朝新的军事布局初见成效。袁可立抚登期间“察属国之情形,务令受我戎索;壮孤岛之声实,恒使奋其长缨。外攘全赖于内修,指顾而莲妖荡扫;中权有资于后劲,擘画而榆镇立通”(89)《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夫妇诰》,天启三年,睢县袁氏家藏。,由于其功勋卓著很快于登抚任上又升兵部右侍郎。(90)《明熹宗实录》卷39,“天启三年十月甲子”,第1999页。在主持行查朝鲜时,取得既为登抚又是朝廷重臣双重身份的袁可立,在处置仁祖反正这件事上在朝廷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结语
登抚自设立后,便承担了应对后金的海防重任,朝鲜也成为登抚防区的重要一方。光海君主政朝鲜时,明朝就接到了不少光海君和后金勾结的传闻,而当时明朝应对后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非常希望朝鲜能坚定的站在明朝一边。因此当袁可立接到有关仁祖勾结日本发动政变的消息时,作为登抚考虑更多的是明朝登莱海防的安全。在袁可立看来一旦朝鲜与日本联合,“则徐可北联夷、南通倭,舟楫帆樯倭所惯习,载奴以来,海上之事将大有可虑者”(91)[朝]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8,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6册,第502页。。鉴于此,袁可立审慎的将之奏报朝廷。之后袁可立通过当面对朝鲜使臣的质问,确定此传闻系谣言,朝鲜依然对明朝恪守臣节,因此他建议朝廷可借朝鲜请封的机会,进一步争取朝鲜的援助,共同对抗后金。袁可立将此次政变与明朝海疆安危联系起来。天启帝曾指示“疆事当责成边臣”(92)《明熹宗实录》卷29,“天启二年十二月癸未”,第1469页。,因而袁可立的建议得到了明朝的首肯,而行查朝鲜一事明朝也交由登抚袁可立负责,礼部请封也必以登抚正式题本为前提,最后朝鲜请封的成功也是得益于登抚袁可立态度的转变。
纵观朝鲜仁祖请封的整个过程,登抚成为关键的一环。第二次朝鲜请封使团为取得登抚题本,不惜在登州盘桓十数日,表明朝鲜方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折射出登抚在请封过程中的制度性权威。而在天启初政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袁可立,在任登抚后不久又加兵部右侍郎衔,其从朝廷重臣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册封朝鲜切实可行建议,并为明廷所采纳,袁可立个人权威也得到体现。袁可立具有了登抚、朝廷重臣的双重身份,在取得双重话语权的情况下,最终促成明廷对朝鲜的允封,册封朝鲜之后登抚更是以海疆重臣的身份成为明朝制定对朝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并对明朝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