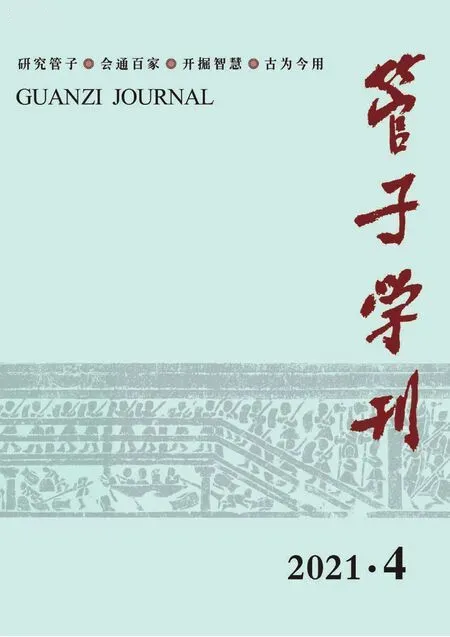黄老学中的身体与政治
——以《管子》四篇为中心的考察
何绍锦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国学院,北京100871)
自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一直是先秦思想研究的热门课题,而《管子》四篇又是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其主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思想类型研究。《管子》四篇属于道家、法家还是儒家作品,一直颇有异义,郭沫若、裘锡圭、杨儒宾、朱伯崑、李存山等学者都曾撰文讨论过该问题。对四篇思想归属的判定是研究其思想的基础,因为它涉及我们从何种角度切入其思想研究。本文采取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管子》四篇属于黄老道家作品。其二,心性论研究。《管子》四篇篇题均与“心”相关,内容亦多涉及修身,再结合齐地“气”的传统,应该说心性论是很自然的思路,杨儒宾《儒家身体观》相关内容及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均可看作该类研究。其三,政治学(哲学)研究。如果结合《管子》全篇及当时时代背景来看,政治学(哲学)同样是把握《管子》四篇的重要线索。代表性研究有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和郑开《道家政治哲学发微》等,他们将《管子》四篇纳入先秦政治学(哲学)脉络,并且提出四篇中“心术”即是“主术”。从四篇内容来看,《心术上》《白心》与《心术下》《内业》呈现出一定差异,心性的内容主要在后两篇,前两篇则主要关于治道和宇宙论。因此单纯的心性论研究,很可能面临割裂四篇的风险。同样,政治学研究也要处理四篇主题差异的问题,尽管“心术即主术”的命题已经暗示了一种可能性,但问题在于,这是如何可能的?换言之,一种对身体的治理如何获得了一种国家治理的普遍意义?这是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提供一种融贯地解读《管子》四篇的思路,同时也可以丰富我们对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了解。
一、身体的政治意涵与问题的界定
杨儒宾在《儒家身体观》中界定了儒家身体主体(body subject)(1)身体主体(body subject)是杨儒宾借用梅洛庞蒂的概念,其意在表明身体具有不同于事物的存在特征。所具有的四个面向,即意识的主体、形气的主体、自然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任一面向都可视为完型的视野中的figure(焦点),其余三者则可视为field(视域),意味着对任一面向的把握,都离不开其余三者提供的背景视角(2)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页。。儒家身体观是否只具有这四种面向姑且不论,如果将视野放宽至整个先秦时的身体观念,会发现,这其中缺乏了另一个重要的面向,即身体的政治意涵。如果我们接受杨儒宾提供的figure-field模型来考察先秦时的身体观念,那么,至少要在field中加入“政治”这一面向。
“身体”似乎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但如果检索一下中国古典哲学的文献,会发现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相当有渊源。尤其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与“身体”相关的论述,如下文所示:
单子曰:“君何患焉!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郄其当之乎!”……“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观存亡。故国将无咎,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曰绝其义;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丧有咎,既丧则国从之。”(3)徐元浩:《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84页。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4)王世舜:《尚书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6页。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7页。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3-514页。
引文中的“身体”描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身体特征,二是身体行动。但它们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即人的“外在”特征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假若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早期西周以“德”为代表的德性概念还未形成内在化特征,亦即德性还未从德行当中分离出来的话(8)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3-185页。,人们认为外在特征与内在德性具有一致性,这并不费解。在早期的政治话语中,德性/行又往往与国祚相关,因此,这种外在特征,亦即“身体”,便具有了一种政治的意涵。
从上述引文来看,不管是孔子的言行、观人的方式,还是单子对晋君和三郄的品评,诉诸的都是一些外在的标准。这些标准具有这样的特点:它预设了一种好的“身体”形态,这些标准是明确的,可达到的,有限的。这种外在的标准典型体现于西周的礼乐制度中:通过将人的“身体”(包括言行服饰等)纳入到既定框架下进行统治。这是一种看上去非常经验性、似乎也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但是,这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政治意义上的身体问题。因为它并没有回答如下问题,即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他为何又如何可以通过个体身体的修炼(修身)通达对于天下或邦国的治理。两个问题的不同在于,礼乐制度治理的起点是一套具有经验确定性的规范,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大家都遵守一套规范,从而实现一种秩序。治理的出发点是规范(礼),而不是个体。这并非说礼乐制度只具有外在的形式,我们仍可以追问其内在的精神或依据:用形而上学的术语说,它内含了西周以来的德、命观念;用更经验性的术语说,则诉诸于一种习俗与教化的影响力(9)就宽泛意义上的“修身”而言,上面提到的礼乐制度规范下人的行为,甚至我们今天遵守各种法规,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修身。只要是对自然身体的某种限制以达到某种“好”的目的,都可以看作是“修身”。这也是本文作此说明与限定的原因:西周丰富的“身体”词汇很多与礼乐制度相重叠,尽管在宽泛意义上都可看作是一种“身体”观念,但本文仍想寻找更具独特性的“身体—政治”观念。。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统治者的个人,为何可以通过治理自己的身体(修身)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两者似乎是一组异质性的范畴?我们知道“身体—国家”的隐喻并不是古代中国独有的思想。柏拉图著名的城邦—灵魂类比(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亦可看作一种“身国同构”(10)城邦—灵魂类比主要是为了讨论正义的问题,通过分析城邦这一较大对象的正义来推导灵魂这一较小对象的正义:城邦的正义在于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灵魂的正义在于其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具体参看《理想国》368d-369a, 434d-436a, 543c-544a, 544d-e。可参照伯纳德·威廉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和灵魂类比》(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收入论文集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d. Myles Burnyea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吴天岳:《重思〈理想国〉中的城邦—灵魂类比》,《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4-90页。,但中国古代身体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只是在类比意义上理解身体与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实质上,即认为治理身体等同于治理国家。
本文关注的“身体问题”主要具有两个限制性条件:一是它关注行动者主观的能动性特征。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心”的概念的使用上。不管是“德的内面化”“道德主体性”,还是“心的发现”(11)“德的内面化”见于小仓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传〉研究劄记》,东京:青木书店,1970年版。“心的发现”见于李巍:《“性”指什么?——孟子人性论的起点》,《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第109-114页。,某种意义上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即人逐渐意识到“身体内”与“身体外”的不同,对身体内部的修养越来越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二是强调修身主体的无限性(12)这里所说的“无限性”与心性论意义上的“内在超越”相关,但也有所不同。它同样具有“超越性”的内涵,即个体可以通过修身实践超越己身的限制;不同在于,这种超越性更多表现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而不只是道德或境界层面,详见下文。。修身的指向,不管是道家的“道”还是儒家的“仁”“诚”等,象征的都是某种超越个体的、宏大的精神境界或者道德、政治理想。而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气”的概念的使用上。“气”在先秦文本中,一般具有最为基本的构成性功能,这是先秦诸子共享的理论前提。《淮南子·原道训》谓:“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13)刘安著,许慎注:《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杨儒宾称“形—气—心”构成了先秦时一种很普遍的身体观念(14)杨儒宾:《儒家身体观》,第4、18页。。三者中最为核心的是气与心的互动。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治气和治心往往具有相近的内涵。如荀子便将二者合起来说:“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15)王先慎:《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页。孟子讲的“浩然之气”,表现出来亦有“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的特征。
二、《管子》四篇中的心、气、道结构
上文提到,“心”与“气”是我们探讨先秦身体观念的重要概念。儒家相关文献,如《孟子》《荀子》中虽然也能找到不少关于心与气的相关论述,但是,集中阐释心、气关系,同时又清晰地绾结了其政治意涵的典型文本,仍属于黄老文献,尤其是《管子》四篇,即《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篇题已经表明它们与心的概念的关联,而篇中丰富的心性内容又涉及“气”的作用。心、气关系构成《管子》四篇心性论的理论基础。但这种心性论又不只限于个体修身层面,它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四篇中“心术”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主术”(16)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页。郑开:《道家政治哲学发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页。另外,对于四篇的思想归属学界一直有所争议。郭沫若认为《管子》四篇属于稷下宋钘、尹文子的作品。详见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187页。裘锡圭认为《心术上》与《白心》乃田骈、慎到派所作,属于“道法家”作品。详见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收入《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330-352页。杨儒宾认为《心术下》与《内业》乃孟子后学所作,属于儒家心性论传统。详见杨儒宾:《论〈管子〉四篇的学派归属问题——一个孟子学的观点》,《鹅湖学志》第十三期,1994年,第63-105页。另有朱伯崑、李存山等学者专文讨论,不一一列出。从文献学的视角,固然可以对四篇年代之先后、类别进行判别,但从思想的角度,我们不妨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心术下》与《内业》讨论“心术”问题较多,而《心术上》《白心》更多涉及具体的君道和宇宙论问题。这是一些研究者的重要判断依据之一。但从思想的整体性出发,前者恰恰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就是本文所欲证明的,黄老学中的身体—政治关系。。而问题在于二者是在何种意义上等同的?通过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亦可揭示出黄老学中不同于儒道的、独特的身体与政治关系。
(一)气、精气与道
《管子》中涉及气的概念很多,如“灵气”“意气”“云气”等(17)“灵气”见《内业》:“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意气”见《心术下》:“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云气”见《内业》:“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8-129、167、126页。需要注意的是:《管子》中《水地》《形势解》篇也有“云气”说法,但主要指“云之气”,与《内业》所言“云气”有所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是“精气”,如下引文: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
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18)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89-90、100、173页。
陈鼓应认为第一段引文中“气”指的即是“凡物之精”的“精”,亦即“精气”(19)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90-91页。。这种理解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即模糊了“精”与“气”在《管子》四篇中的区别。仅从该段引文来看,两处“是故民(此)气”(20)陈鼓应援引戴望等人观点,认为“是故民气”中“民”即“此”字之误。参见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90页。中的“是故”一词表明,后文与前文构成一种因果关系,“凡物之精”具有的“上生五谷……流于天地之间”的创造性是此气能够“登天入渊”的原因,亦是在工夫上“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的原因。作者的思路是很清晰的。而从四篇中的其他段落来看,第二段引文“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已经表明“精”与“气”的不同。在第三段引文中,就像“智”不同于“事”一样,“精”与“气”同样不能等而视之。从概念史的发展来看,“气”概念的出现显然要早于“精气”的概念,“精气”和“云气”“灵气”等,是对“气”的进一步限定。而从上述引文来看,“精”所具有的创造性特征,更接近于“气”的本质属性,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精气”是一种“气”的类型,但是“精”不同于“气”(21)“精气”这一说法,可以粗略理解为“气之精”或“气之精华”,其字面含义便有本质的意味。《内业》:“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心术下》亦有类似表述,不赘述。冯友兰曾提到,“凡物之精”指的是“气中更细微的部分”。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但是“凡物之精”并不是旨在描述“精”的特征,而是为了说明“气”所具有的创造性根源,这与粗细无关,而是如后文所言,“道”的内涵被纳入“气”之中。。
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关涉到另一组重要的概念,即“精”与“道”。郭沫若认为《内业》与《心术》中的“虚”“气”“精”“神”等都是“道”的别名(2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2-564页。。从文本来看,《内业》谓:“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23)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96-97页。这与“凡物之精,此则为生”含义如出一辙。这也是为何上文要区分“精”与“气”的原因。气基本的构成性功能与道的创生义实际上都属于早先的传统。虽然同样具有创造性的内涵,但“道”与“气”仍属于两组不同的概念,“道”似乎被用以描述更为抽象的生成关系,如同人问一辆车为何会跑,回答是:因为有轮子的转动。很自然的追问是:轮子为何会转动?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继续追问,根本上还是为了解决车为何会跑的问题。而“精”的概念正是用以回应后一问题,如第三段引文提到的“一气能变曰精”,“精”被用以解释“气”的变化,正是在此意义上,“精”具有了与“道”相当的内涵。
我们说中国古代哲学家偏爱一种整体式的思维方式,而“精”恰恰起到了沟通“气的系统”与“道的系统”的作用。“气的系统”主要属于宇宙论的传统,两周之时,气已被视作盈于天地间的构成性材料(24)杨儒宾:《儒家身体观》,第12页。,昭示着人与外物隐含着交互贯通的维度。“道的系统”除了具有宇宙论的意义外,还包含了强烈的伦理维度,如孔子的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气后来发展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如《黄帝内经》中大量关于“气”与人身关系的刻画,气与人的身体能力紧密相连。而道则始终保持着它的抽象品格。并非说二者没有关联,但它们的不一致也正如上文所言。“精”能够在“气的系统”中添入道的内涵,从而更加融贯地解释整个生化过程,并且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精气”这一结合了气与道特征的概念,如何具有了更丰富的政治和伦理的解释潜力。
(二)“心中之心”及心、气关系
《管子》四篇均是以与“心”相关的术语来命名,“心”毫无疑问是《管子》四篇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论语》中虽有“心”字出现,但多停留于日常词汇层面,不足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道德经》中“心”字不少,但含义并不固定,如表示一般欲望和情感的“虚其心”,表示一种意志能力的“心使气曰强”,表示偏好的“以百姓心为心”(26)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276、253页。等。战国以来,“心”的哲学内涵逐渐凸显,孟子讲“尽心知性”,庄子亦有“心斋”这样的独特概念。而《管子》四篇中“心”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心中之心”的概念。如下引文: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言。
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27)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10、181-182、198页。
第三段文字“中”亦即“心”之义,“有中有中”如刘绩所言,即“心之中又有心”之义(28)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则三段文字都可看作是“心中之心”的描述,其中《内业》表述更为清晰。《管子》显然区分了“心”的两个层次,即一般所说的“心”与“心中之心”。如何理解这两个层次的“心”?杨儒宾认为两个心分别指的是经验意义的心与超越意义的心(29)杨儒宾:《儒家身体观》,第244页。。陈鼓应的观点类似,认为指的分别是形气(形下)的心和道德意义的心(30)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11页。。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后一个心指的是控制中枢(31)陈政扬:《〈管子四篇〉的黄老思想研究》,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毕竟文中提到的意、言、形、思、知很像是在描述一种认知过程。
从《内业》文本来看,作者首先提出的是心与官的关系,表明心在身体中具有统御地位,这与《心术上》提到的“心之在体,君之位也”意义相通。接着作者提到“心中之心”,亦即“彼心之心”,而它通过“意”这一心理活动体现出来。作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言说的内容是在“心”之中构想好了的,这是第一个“心”的功能,但我们构想的内容不是任意的,而是出于某种“意”(intention),这种“意”则是出自第二个“心”。
陈鼓应也提到《管子》四篇作者并不反对知识(32)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03页。。从上述分析来看,“心中之心”确实包含了知识和心理的辨析。但需要注意的是,意、形、言等概念,是作者用以佐证“心中之心”的存在。我们不应忘记引文一开始提到的“心治”“心安”的说法,作者真正关切的仍是某种修身或者“修心”问题,它与遍布四篇中的“心术”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心中之心”便与《管子》四篇中关于“精舍”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郑开已经指出,黄老道家的体道境界,在于如何使“神明”进入“道舍”(33)郑开:《道家政治哲学发微》,第315页。。这其实便是《管子》“心术”思想的核心关切。
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
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
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
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34)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00、108、137、157页。
结合四段引文来看,《管子》所谓之“舍”或“精舍”,即是第四段引文中提到的“心”;引文中的“精”“神”“智”用词虽异,但含义相当。“定心在中”“敬除其舍”“虚其欲”“扫除不洁”描述的是具体的“心术”实践,其目的在于“神(精/智)乃留处”。作为同样是以“治心”为目的的修身实践(“心术”),不妨将其看作是上文“心治”“心安”的具体展开,从而,作为“精舍”的“心”便可合理地推断为是“心中之心”而不是指自然意义上的人心概念。
根据上文的分析,既然“精”与“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同的内涵,那么,“神乃留处”实际上便是“道乃留处”。如下文所引:
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大道可安而不可说。
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处)。心静气理,道乃可止。……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
夫道……卒乎乃在于心。(35)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31、97、110、95页。
第二段引文中提到的“善心安爱(处)”“心静气理”与上文“虚其欲”等同属于“心术”实践的范畴,“道乃可止”即是“神乃留处”之义。第四段引文中的“卒乎乃在于心”也可与上文“心也者,智之舍”互相发明。而“道”不能言、不能视的特征正表明了为何对“道”的把握,或者说“留神”只能诉诸一种内在的修身形式,而非认知活动。
至此,我们可以对《管子》四篇中的心、气、道关系作一个小结。心、气、道关系根本上属于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人关系”问题。跟中国哲学的主流一样,《管子》主张的也是“天人相交”模式,其中起到连接作用的在于两个重要概念:“精气”与“心中之心”。“精气”概念结合了道抽象的创造性与气的实在性特征。“体道”的过程就是将外在的精气内在化的过程。人与道的统一,在《管子》的语境中,即是人与精气的统一。“心中之心”则进一步将这种修身活动限定在心灵层面。它不是指自然意义上的人心概念,而是经过“心术”实践后的心灵状态。“人与精气的统一”可进一步界定为心与精气的统一。
三、“体道者”形象与心术的政治品格
《管子》四篇中有大量具体的“心术”内容,不详细论。概而言之,即通过“内静外敬”的一系列工夫以达到一种“精气入舍”的状态。杨儒宾提到,《管子》中的“精气—全心”理论表明人的宇宙性特征,即人不是定型的、有限的存在(36)杨儒宾:《儒家身体观》,第248页。。换言之,管子预设了这样一种人的概念:人的自然状态是不完整的,人的完整性有待于进一步的修身实践来实现。但是,这种修身实践是否只是心性论的?上文已经提到心术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主术,《心术下》中明确提到“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37)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73页。。身、国具有某种同构性,一方面,对身体的治理可以类比于对国家的治理,但是,另一方面,两者间的关系又不只是类比的关系,而是在实质上,统治者的修身活动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心术”的政治内涵,集中反映在《管子》四篇对“体道者”形象的刻画中。如下引文:
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知)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38)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17-120、114-116页。
这段引文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具体呈现了“精气入舍”后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一形象表现出明显的政治隐喻的特征。“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显然不是单纯心性论意义上的词句。能使天下服、天下听的人,要么是君主,要么是具有君主潜能的人。这与《心术下》说的,“执一之君子,能君万物”是一致的。本文统一称之为“体道者”形象。这一形象,与传统的儒家怀柔万邦或者道家不主宰、不控制的圣王形象,有很大的出入。下文将从具体内容展开分析。
(一)充分的自足性
这是文中体道者形象最为显著的特征。无卜筮而知吉凶,不求人而得之于己,以自身的精气作用代替鬼神之力。卜筮、赏罚、共同体关系,这些几乎是传统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几种政治行为和关系。但是体道者必须超越这些外在的关系。这是《管子》四篇思想与儒家和法家的不同所在。儒家与法家或多或少都承认人的有限性,并且这种有限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跨越的。因此孔子入太庙仍要每事问(39)《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5页。,韩非更是全面质疑儒家推崇的圣王,谓:“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40)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页。但是《管子》称:“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气”“心”这种个体层面上的修身语词反倒具有胜过“赏”“刑”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任何外在的关系都昭示着主体的有限性,但是体道者必然要超越这种有限性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无限性。这是其心术思想与孟子心性论最为深刻的差异。如果说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是一种境界或者德性上的内在超越的话,“全心”状态所呈现的超越品格显然于此不同,呈现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超人形象”(41)陈鼓应称这些词句让他联想到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昂扬形象,两者在精神气质上的确具有相近之处。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47-48页。。
(二)蓬勃的生命力
《管子》受道家“道”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是与老子柔弱胜刚强相反,体道者表现出极为刚毅的特征(42)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19页。。《老子》中也有使用“气”的概念,如“专气致柔”等,但是,总体而言,老子所提倡的体道方式,主要是以虚、静、无等否定性词汇彰显的修身形式,这与老子批判儒家过度强调“有”的旨趣有关(43)需要强调的是,老子对于“有”的批判主要在价值层面与政治层面,如老子所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无事取天下”“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等。在宇宙论层面,道也包含了“有”的面向,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详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212、250、284、284、53页。,但《管子》在修身层面上并不全然排斥儒家的价值,如其谓:“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44)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第181页。虽然《管子》多次强调“虚”的工夫实践,但它所以提倡“虚”,是为了排除心中的欲望和情感,达到“神(精气)将入舍”的目的。这是它与老子修身论最为重大的不同之处:其“虚”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实”。这也是其修身实践的政治意义的体现,而非全然是心性论或者境界论的。时间稍早于《管子》四篇的《黄帝四经》开创了道的“政治性转换”,使源于老子的抽象的形上之道开始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特征,为道的社会功用提供了前提(45)陈鼓应:《黄帝四经今译今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页。。《管子》可以说同属于黄老学派的“道治”传统,而四篇通过“精气”与“心”(心中之心)的概念,进一步从这种“道治”传统发展出“身治”思想。“精气”所具有的类似于Charisma的能量,使体道者的生命力从内而外达到极为昂扬的状态,表现在体道者的知识(“便知天下”)、德性/行(“日新其德”),以及身体形态(“筋信骨强”)均达到了顶峰,塑造出一个德性饱满、身体刚毅、甚至具有神通的统治者形象。正如郑开提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老学著作中的‘君’就是‘走下神坛’的‘神明’,或者说‘窃居神位’的‘人’。”(46)郑开:《试论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28页。
四、从身体出发的统治
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对个体身体的修炼如何与对于邦国或天下的治理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孟、荀都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不管是“养浩然之气”还是“存夜气”,并不牵涉到政治问题。当然,从德治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养气”有助于提高君主的德性,从而间接得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荀子》中也有“心术”一词,如《非相》:“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4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73页。这里的“心术”与习语“心术不正”之“心术”意义相同,指内心的想法。《解蔽》谓:“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48)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82页。其中“心术”指用心的方法或思想方法(49)郑开:《道家政治哲学发微》,第310页。。归根到底,仍属于儒家贤良政治框架下的修养问题,关切点在于统治者的德性。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层级。《大学》中明确提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则“修身”似乎便具有了一种基础的政治意义。但是这种政治意义仍然不是直接的,在形式上,它依托于儒家一贯的家国同构,其背后是西周以来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的逻辑;在实质上,则仍然是诉诸德性的感召力,与孟、荀不同的是,它突显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统治层次。
先秦儒家中很可能并不具有一种直接的“身体—政治”意涵。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保守主义”,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治”与“德治”传统。从早期的政治实践来看,这是一套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统治模式,因此,即使孟子从齐地“气论”获得启发(51)白奚:《〈管子〉心气论对孟子思想的影响》,《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1994年版,第138页。,但“气”只被置诸修身论的框架中,作为其心性论的一种补充。荀子同样如此,只是他所回归的是“礼”的传统,尽管他可能意识到“礼”的不足,而援入了更多“法”的内容(52)如《修身》“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不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富国》“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等类似说法。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50、176页。。
《管子》四篇中的修身(或“修心”/“心术”)的意义不同。它与政治统治的关系是直接的,它用“身国同构”来代替儒家的“家国同构”。“家”作为儒家政治中最小的统治单位,暗示了一种“角色伦理”的内涵(53)“角色伦理”引自安乐哲说法,见安乐哲著,孟巍隆译:《儒家角色伦理: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它意味着人是通过与他人建立或远或近的关系来构建统治的网络。正如上文提到的,儒家清醒地意识到人的有限性。而《管子》反对这种层层递进的统治模式,《牧民》中提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54)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17页。统治的主动权,应该操持在君主手中,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私与无亲。这种对于公、私的理解是极反常识的,我们一般认为权力越分散越能体现公意,但是如果明白《管子》反对儒家“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便不难看出其背后的逻辑:当君主直接与民众发生联系时,便可能杜绝中间环节的徇私舞弊的情况。那么问题便余下君主自身的有限性:君主自己是否能“如天如地,何私何亲”呢?这样,君主的修身,亦即“心术”便成了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
回顾我们对体道者形象的分析,体道者展现出来蓬勃的生命力与充分的自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德性的范围,这或许与齐地悠久的养生传统有关(55)白奚:《〈管子〉心气论对孟子思想的影响》,第138页。。但正如上所言,《管子》四篇中的“心术”不只是修身或者心性概念,而包含了作者更深的政治思考于其中:即为了实现一种更加全面、高效、无私的统治。“心术即主术”的内涵在于:君主全面、高效与无私的个人品质便能带来全面、高效与无私的政治统治。其背后的形上依据在于上文分析的心、气、道结构,尤其是综合了气与道特征的崭新概念“精气”:既包含了身体能力层面的“气”的维度,又囊括了普遍的德性与创造的“道”的维度。
《管子》四篇中的“身体统治”可一言以蔽之,即:人与道的同一。这里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如上文提到的,“道”属于自孔子、老子以来的旧传统。《论语》中有不少与“道”相关的描述,其中“道”主要表示抽象的德性原则或者具体的规范,属于儒家“德治”传统,人按照“道”的要求行动,道对人而言是一种高绝的存在,人、道之间不存在“同一”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道家和儒家具有一致性,甚至因为道家之“道”具有更明显的形上学特征,道与人的对立更加明显。人属于“物”的范畴,对道采取一种“守”的态度,如其所谓“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56)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209页。。《管子》四篇道的观念虽然承自道家,但是,在对道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是“神乃留处”“精将入舍”还是“(道)乃在于心”,道完全内化于君主身体(心)之中,他并不是按照道的要求行动,而是他的行动即是道的行动,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身体统治”,而不是“德治”或者“道治”。第二,这种同一关系在理论结构上也不同于道德上的“自律”。我们将目光从先秦移至心性论成熟时期的宋明。不管是阳明“致良知”,还是朱子“性即理”,在理论上,都预设了人心内含道德判断的标准,只是对于如何呈现出这套标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工夫路向。这也是他们批评道家为“虚”而儒家为“实”的原因,“虚”“实”是就人心而言的。而正如我们上文所述,“精气入舍”的条件正在于内心的“虚”,从而为“精”(“道”)的入驻提供条件。儒家“仁义内在”说的一个直接目的即在于证明“人皆可为尧舜”。但是,《管子》四篇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毋宁说它很可能反对这样一个普遍性命题,如《内业》谓:“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民并不能知晓道,而它描述的“神将来舍”的场景,也类似于一种祭祀活动。也就是说,实现人、道同一是有一定的限定条件的。这也是本文反对仅从心性论上解读“心术”的原因,因为它并没有道德论所要求的普遍性。
余论
或许有人会问:这种先验的修身(“心术”)活动真能解决经验性的政治问题吗?
这里需要澄清两点:第一,我们分析其心术活动时,看到“扫除不洁,神乃留处”“敬除其舍,神将自来”这样的表述,似乎其中有某种神秘体验的意味。但是,《管子》的政治主张不可看作是非理性的,相反,它所描述的大量具体的主术内容,如君臣异道、督言正名、知时断事等,都基于审慎的理性考量。只不过作者认为对这些具体方式的运用有赖于对道的掌握,而道不可通过认知的手段把握。第二,当我们说政治是一种经验性活动时,意味着我们怀疑是否有一种知识或者德性能够囊括其所涉及的诸种不同门类的知识或技术。但对于未形成近代以来的知识分类的古人而言,道的综合性与有效性是被普遍接受的,求“道”既是一种德性追求,又是一种政治追求。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战国以来的思想家普遍思考秩序重建的问题,儒家如孟子、荀子自不必说,老子、庄子中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可看作是某种新秩序的蓝图。君主的权威得到更多的强调,这或许是由于游说之风的兴起,但根本上是固有秩序崩坏所至。改革者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如韩非子。韩非子质疑以血缘和德性为基础的伦理、政治关系,认为君臣关系根本上是利益关系,而“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57)王先谦:《韩非子集解》,第449页。,至于下层的民众,亦不能成为统治的基础,即其所言:“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58)王先谦:《韩非子集解》,第575页。,韩非所设想的理想之君主,亦是一个孤独而又“全能”的形象。不过作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韩非倚仗的是经验性的法与术而不是形而上的道或者精气。
——修身与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