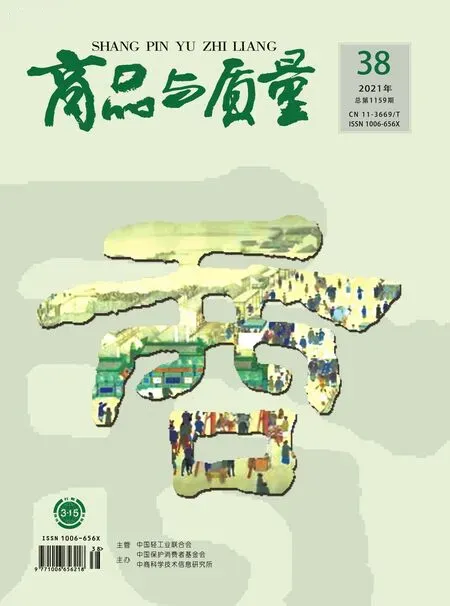野生动物疫病暴发成因及其防控对策
王安静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山东济宁 272600
1 野生动物疫病暴发的原因
近年来,造成野生动物疫病暴发、流行和不断加剧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
1.1 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导致全球性和区域性野生动物疫病频发
一般来说,大范围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往往与大尺度气候异常或极端气候有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ENSO)是影响我国乃至全球气候异常的一个重要的大尺度气候因子。ENSO可改变正常大气循环,影响全球降水和温度分布格局,造成重大气象灾害,并诱发生物灾害。过去50年,随着气候变暖不断加剧,ENSO事件更加频繁,这也许是造成近年来全球性重大传染病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张知彬等提出了“生物灾害ENSO成因说”,认为ENSO通过改变全球大气环流和温度、降水格局,为有害生物种群发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导致生物灾害频繁出现;Zhang还提出ENSO事件可作为大尺度、超长期生物灾害预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结果都证实了ENSO与生物灾害存在密切关系。例如,我国学者相继发现ENSO事件与欧洲的鼠类、中国的鼠类和鼠疫及出血热种群或疫病暴发密切关联。在美国,ENSO导致降水变化,增加了白足鼠的种群数量,从而导致美国汉塔病流行。在澳大利亚,ENSO驱动的降水增加,导致鼠类暴发及小型食肉兽数量激增,危及土著珍稀物种的生存[1]。在智利,厄尔尼诺事件伴随降水增加,导致当地鼠类种群暴发。
1.2 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导致全球性或区域性野生动物疫病频发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影响巨大。2016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达到72.6亿,全球40%的土地已经被开垦为农业、工业等用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四通八达,人员和货物流动频繁,养殖业不断壮大,经济全球化水平日益提升。2019年,据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杂志报道,一组科学家投票选出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类世对现代疫病暴发、流行和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2]。
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紊乱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发生的概率。通常,病原和宿主的多样性是正相关的。因此,宿主生物多样性越高的地区(如热带、亚热带)或类群(如鼠类),其病原的种类也就越丰富,相关疾病发生的风险也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发疾病多始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但在人类活动加剧下,由于土地利用、滥捕滥猎等,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动物疫病发生风险也会增加。2014年,Dirzo等提出“群落丢失理论”(defaunationhypothesis),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大型动物群落丢失,并使鼠类种群密度增加,进而加大了鼠传疫病发生的机会。也有人提出“稀释假说”(dilutehypothesis),认为宿主多样性增加,可以减少疫病发生的风险,而生物多样性下降则增加疫病发生的风险;根据文献回溯和大数据分析,有研究支持该假说,但是也有研究不支持[3]。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疾病发生与生物多样性存在尺度依赖的非单调性关系:小空间尺度存在稀释作用(dilute effect),大空间尺度存在放大效应(amplification effect)。Sun 等发现我国鼠疫发生频次与鼠类多样性有正相关关系,支持放大效应假说。
2 我国野生动物疫病监测与防控情况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传染病的关系。例如,清代诗人师道南在《鼠死行》一首诗中,首次记载了鼠疫与死鼠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采取查清鼠疫疫源地、监测鼠密度和开展“灭鼠拔源”等措施,我国成功地控制了曾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百年的鼠疫灾害;此外,通过大力推广爱国卫生运动和应用疾病控制新技术,许多动物源性的疫病(如疟疾、各类寄生虫病等)都得到了较好控制。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不断涌现,对公共卫生安全、畜牧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和威胁。由于许多疫病的跨种传播或起源都与野生动物有关,因而急需构建我国野生动物防疫体系,以有效地协同我国卫生和农业防疫体系开展疫病防控工作[4]。
3 加强野生动物疫病监测与防控的对策和建议
3.1 对策
①突破传统“公共卫生”理念,将疫病监测与防控扩展到“生态健康”层面。过去,我国卫生防疫系统比较侧重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而农业防疫系统则比较侧重养殖动物的健康和疫病问题。当前,疫病发生和防控问题涉及人、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以及受气候和环境多因素、多路径、复杂交互影响。②加强疫源生物监测,加强环境与气候变化对疫病暴发影响研究,提升疫病发生的预测能力。全球性和区域性疫病大流行,往往受大尺度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掌握气候和环境变化对疾病发生和流行影响的规律,对于提前疫病预警,采取预防措施,降低疫病暴发和流行的危害至关重要。③减少人、畜禽、宠物与野生动物接触,切断跨物种传播链条。绝大多数新发、再发传染病来自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且病原体可在人、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之间相互传播和演化。因此,切断人、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之间病原和媒介传播链条,对于大幅减少或降低疫病发生风险至关重要。④加强对疫源动物、媒介和疫源地的治理,减少疫病发生风险。对疫病防控,只是监测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疫源风险进行干预和控制。例如,美国向野外投放口服狂犬病疫苗,降低野生动物狂犬病感染率,从而减少其对家养动物传播的机会[5]。
3.2 建议
①完善监测站点布局和队伍建设,提升基层监测和防控水平与能力。根据疫源动物、媒介动物和病原生物及自然疫源地的分布特点,调整、补充和完善国家、省、县三级监测网络和站点。配备先进的用于野外监测、样品收集、样品贮存、病原诊断、疫情干预、信息整理等物资、设备和条件。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与指导。②制定重要疫源生物清单,查清自然疫源地并开展规模化治理。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动物分布区发生了快速变化,需要尽快开展新一轮全国摸底调查;并结合国际资料,制定我国重要疫源动物、媒介动物和病原生物物种清单及自然疫源地区划,查清疫源地,开展规模化治理。③提升疫源动物、媒介和疫病的监测技术、信息化和预警预报能力。制定和完善标准化的监测方法、数据采集和处理模式,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卫星定位等高精尖技术手段,构建覆盖全国各站点的自动智能化监测网络,实现疫源动物、媒介、疫病大数据实时监测和预警,以期在疫情分析、病原溯源、防控干预、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④提升野生动物疫病快速诊断、海量筛查和风险发现的能力。鉴于野生动物病原生物种类多、样品多、变异大的特点,现有监测方法、试剂、设备难以满足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的需求,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合野生动物疫病的病原监测、诊断方法和体系。⑤提升野生动物疫病研究水平和能力。建立或支持一批国家、区域研究中心和参考实验室,以支撑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和防控所需的技术和分析。
4 结语
人类活动加剧增大了疫病在人、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交叉感染的概率和疫病传播速度,加大了疫病暴发、流行的风险。为应对日益严重的野生动物疫病重大挑战,亟待加强和完善我国野生动物疫病监测和防控体系建设,提升对野生动物疫病的研究、监测、预警、干预和防控能力,服务国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