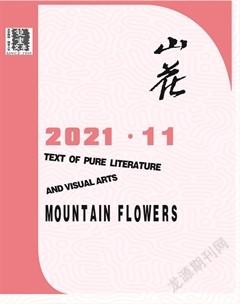永远的黄豆
李洪振
大豆,学名又叫豆菽。它作为一种极为平常的油料作物,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用于生豆芽,或磨成浆,或制作成豆腐,从而再衍生出各种豆制品,真是不一而足。
在乡间长大,对于一棵棵豆苗的记忆格外深刻。把豆种点播到地里之后,隔上三五天,一棵棵幼小的豆苗便顶着土层破土而出。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啊?它稚嫩、柔软,却有着一股子拼劲,像乡村里的野孩子。
而对于黄豆的记忆,可以追溯得很远。在故乡,那些个豆荚成熟的秋天,我曾经走在豆地旁的小路上,去十里之外的一个中学上学。秋天的太陽依旧毒辣,晒得我的头发,一根根几欲炸开。而地上的豆荚,正在成熟的末期,在烈日之下,我似乎听到了“啪啦、啪啦”的炸裂声……
到了秋后,田野里一片金黄。黄豆,作为田地里最贵重的农作物,自然要得到重点的照顾。割豆人,都应该是老手,或者说成年人。不然的话,丢一粒豆子在地里,似乎都是一种作践。而当劳作之余,点燃一处篝火,烧几束黄豆,埋在滚热的灰烬里,一股大地的芳香便从烟火中缭绕而出。
在割豆子之余,我们还会捉到一种名叫“豆虫”的虫子。它生活在豆地的土层下,采纳大豆的天地精华,从而形成浑身的蛋白质,全身通透,用油烹饪,或者剁碎成渣,皆是一味佳肴。但我对这类虫子,天生的畏惧,不敢享用。
在我的家乡黄淮海平原,每家都要种上半亩大豆,用来榨油,或是磨豆腐。在贫困的年代,豆腐作为一种稀罕品,也只是到了过年之时,家家户户才磨得盆满钵满,才喝得嘴角留着豆沫,才把剩余的豆浆用盐卤点了,做成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在乡下,只有过年才做上一筛子的豆腐,吃上满满的一个正月。冬日的阳光正好,把豆腐切成小块,晾晒。黄豆的油,被太阳逼出来,金黄金黄的,形成一层薄薄的膜。
已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亲自做一次豆腐了。现在,老态龙钟的母亲,已不适宜再做豆腐,我每次都是到超市里买一些,母亲总是嫌没有豆腐的味道。可什么是“豆腐的味道”呢?那大约是一种记忆,一种对往昔生活的怀念吧。这让我不禁想起童年的时光,那份酸涩而又甜蜜的回忆。
那一年,年关将近,太阳的余晖也显得短了起来。风是静的,连日的大风消停了,于是光线也显得直了,照进房子的走廊里,暖和得让人每一根汗毛,几乎都膨胀起来,在棉袄里暗自作祟。
我坐在门口,看着母亲忙里忙外,却很少能帮上她的忙。
过年磨豆腐,是一件大事。此刻,母亲将昨晚浸泡好的三斤黄豆,用清水淘净。在水中的一夜,让这些黄豆都暴胀了几乎好几倍,原来的皱褶也不见了,嫩嫩的像一个个小娃娃的脸,胖乎乎的那么圆滑。接下来的筛检工作变得容易多了,把被虫子咬过的,发霉变色的都一一挑出去。已经筛检了好几次了,母亲还是不放心,又一粒粒地将它们筛选了一遍,再一勺一勺地添进石磨里。母亲一边推着石磨,一边添豆子,乳白的豆浆便顺着石磨间的缝隙,一股股地流了下来,淌到石槽里,再流到盆里。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磨的那三斤豆子,是借来的,是串了好些家门,才借到的三斤黄豆,用于过年,用于打我们的牙祭,或者是撑门面,让这个家庭有些过年的样子。
那年,父亲刚刚从一场大病中初愈,几乎是从鬼门关里硬拽回来的,从县上的医院转回家里。那时家中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更何况是生病住院。如果换了别人,可能就让父亲在家里自生自灭了。可是母亲却力排众议,坚持借钱也要把父亲的病治好。于是,母亲只好觍着脸皮到邻里百舍,一家家去拼凑治疗费,十块、八块、五块……,甚至五毛、三毛……待到我后来上了小学,母亲把这本登记的借款账本给我看,让我记住乡邻的恩情。
密密麻麻的小字,歪歪扭扭,一共五张,合计是五百六十三元八角四分。这几乎是大半个村子的花名册,看得我泪眼婆娑。那一刻,我也分不清是对乡邻恩情的感激,还是内心里对贫穷的无奈感伤。
年三十那天,有几个人似乎是要登门要账,但等前脚跨进门槛,看到躺在床上父亲,和一壶煮沸的沙壶中药,以及闻到满屋子里飘荡的中药气味,又将伸出去的脚,生硬地收了回去。
欠人家的钱,是不能割肉过年的。母亲用这种最节俭的姿态,回应了乡邻的眼光,也让自己的脊梁直了起来。但这个年总归还要过的,还要给家里置办一些佳肴,给家里带来一些新气象。
那年,我五岁,给母亲当下手,在灶旁,把柴禾一次次送进炉膛里,红彤彤的炉膛。夜晚,火星飞溅,四处飞舞,像极了烟花。一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的豆浆汩汩地翻滚,香味四散开来。
那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没有肉的年夜饭。但母亲却做出了几种花样,有豆浆,有豆腐脑,有干煸豆腐,还有豆腐韭菜馅的饺子。热腾腾的,满满一桌子。
简陋的桌子上,三口人,有父母,有孩子,就是圆满的,就是有希望的。父亲那天,也破例下了床,和我们坐在一起,吃得有滋有味。
守岁之时,母亲把一捆豆秸点燃,用来驱赶寒冷。在熊熊燃烧的火焰里,豆秸噼里啪啦地发出声响,我仿佛看到在村东的平原上,在自家的豆地里,沉甸甸的豆荚,在烈日的暴晒下,向外弹射出一粒粒饱满的黄豆;仿佛看到金黄色的豆粒,正一粒粒地向我们滚来……
时光荏苒,恍惚已是中年。父亲已逝,母亲也变得佝偻。而多年的豆地,被反复地耕耘,被置换到不同的方位。从大块的责任田,到村口的丘陵,大豆对土壤似乎并不挑剔,仍一如既往地结出饱满的豆粒。
黄豆与人,大约也需要一种和谐的状态吧。想当年,父亲常常午后带着一把锄头疲惫地回来。如今,那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情景,已成回忆。烈日之下,一把锄头穿梭在豆苗之间的缝隙里,清除着杂草。掉落的汗滴,让豆苗吸收后,结出的豆荚,便多了一份人性的温存。
母亲越老,一块黄豆地便离她越近。从遥远的东湖,到如今老宅旁边的空地,越近也越小。直到有一天,她掌管的豆地,只剩下簸箕那么大小,小得只能容下寥寥几棵豆苗,她也要细心地照顾,像对待孩子那样养着。
说到底,其实一粒黄豆就是一段乡间的记忆,在它里面包容了几家欢乐、几家忧愁。只要老家还在,乡村还在,农业还在,文明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