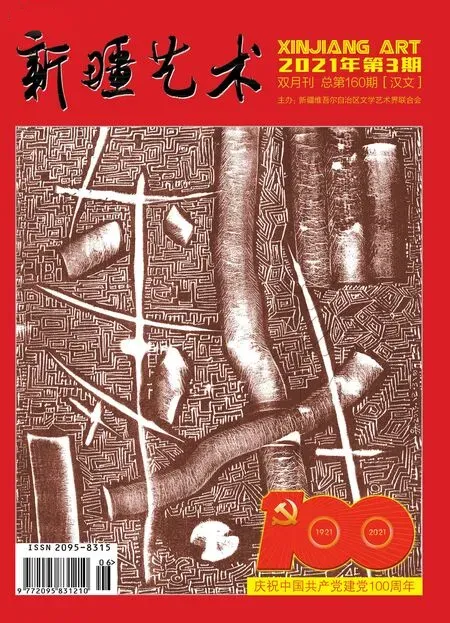科幻电影中的灾变叙事
——以《星际穿越》和《流浪地球》为例
□ 李先游

电影《星际穿越》中的五维空间
艺术作品对灾难,尤其是灭顶之灾的刻画最激荡人心,最能展现创作者的巧思和功力。我们发现,传统文学对于大洪水、地震、灾荒等自然灾变的描摹,意在“邀请”观众进入作品,其核心在于复制感受,在于营造逼真的感官体验以激起读者的共鸣和震撼。而科幻作品由高精尖的现代科学知识为支撑,有意给接受者的理解设置障碍,魅力在于探索新知的理性愉悦,其效果务求超越个人的日常感受和主观经验。故而,我们可以把科幻作品看作是依托前沿科技的一种低透明度、低参与度的文化文本。它一方面,凭借对科学资源的深度耕犁,用新奇艰深的知识压制接受者参与故事的可能性,刺激其追问真相的欲望;另一方面,通过对灾变异态的模糊表达,以奇情异想完成对特殊科学世界观的图示化阐发。这样,科幻作品便在精细准确与宏大渲染的张力中获得光彩。创作者那“灵光乍现的‘点子’跃升为了思想命题”“科幻由此得以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扬起了风帆。”
正如刘慈欣所讲:“对我来说,最大的瓶颈就是获得创意的过程,之后的故事和人物是凭借努力完成的,但是创意部分凭努力完成不了,可没有这个核心的创意不行。”可见,灾变形式的创意设计是科幻艺术成败的关键。以对死亡的想象为切口,科幻电影的灾变叙事包含着恐惧的感受性倒置和救赎的认识论倒置两个层面。经由这种双重的结构性转换,作为大众消费品的科幻电影将人类的认识边界置换为人性尊严、价值理性和伦理完满。在具象化的全景模拟中,科幻电影构筑起一个易于被大众理解并消费的温情的人性世界。
一、想象死亡:科幻灾变的结构性要素
死亡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驱动。科幻作品对死亡的想象性展开,总是与人们思考宇宙异态的各种可能相伴相生。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死亡看作科幻作品的效果或情节,而应该说,对死亡的艺术化想象为科幻提供了精神起点,它催生了科幻。
其实,用想象死亡来解构灾变的做法由来已久,文学作品中的死亡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事实陈述。古代西方,人们把对自我的认知和不可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佩琉斯的儿子、神性的阿喀琉斯的英雄崇拜时刻连接着他必定战死沙场的联想。而特洛伊战争的悲惨终结则通过众人对英雄的死亡想象得以刻画。“他的妻子朝家走去,频频回头顾盼,流下一滴滴泪珠。她很快回到那杀人的赫克托尔的居住舒适的宫室,遇见许多女仆聚在那里,引起大家不停地哭泣。她们就这样在厅堂里哀悼还活着的赫克托尔。”类似的,中国古代神话在描绘上古时期十个太阳的恶行时,也通过女巫女丑的死亡想象来渲染民不聊生的凄惨。“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也就是说,每当人们想到女丑至死都没有改变以手遮面的动作时,十日共垂于天的末日惊恐便历历在目。可见,想象死亡是以艺术之名对生命临界状况的窥视,它在死亡事实之前起笔,以惊异的形式摹写存在的边界。
科幻来自工业社会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反映出人类对技术的狂热。而伴随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世界性难题,言说死亡与探索异质生存问题结合在一起。“随着19 世纪人们相信现有秩序最终会被混乱所消解,宇宙将死于一片热寂”,我们看到,末日题材的科幻把对死亡的恐怖感转化成对异态生活的震惊感。
首先,作为创意的核心,对死亡的克服显示出多元科技理念的启示意义。《星际穿越》和《流浪地球》都是对地球灾变与末日绝境的描绘,而全新的科学观念是其亮点。《星际穿越》描绘了地球上沙尘肆虐、植物灭绝,人类会因氧气缺乏窒息而死。而由于主人公偶然发现了三维世界与五维世界的共时并存,问题从而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可见,五维空间的存在,消解了三维现实的终极问题,而死亡恐惧被正确认知宇宙置换了。由此死亡就不是终极,而成为人类探寻宇宙存在形态的一个环节。《流浪地球》中这种意蕴更加明显。作品的核心事件是动用科技力量使地球在持续流浪状态中延续生机。我们看到,其中的死亡威胁既来自眼前的地木相撞,也来自为期2500 年的地球流浪计划本身。作品用比死亡更孤独的“流浪”这一意象来隐喻宇宙灾变。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选择、生命延续都必须服从于人本主义情结之外更广阔的宇宙真理。
其次,科幻作品中“死亡/坚守”这组二元对立是灾变结构的基本模式。必死的黯淡前景与无望的煎熬挣扎彼此呼应,既创造出异态生存境遇的恐怖幻影,也展现了人类自身的主动反思。
具体来看,一方面,“死亡/坚守”象征着生死阻隔却殊途同归。《流浪地球》中人类不懈抗争,耗时几千年,一百代人持续接力,千方百计推进地球的流浪之旅。但很明显,对于囚居在地下城的居民而言,弃绝家园的“流浪”实际上等同于每时每刻接近死亡。《星际穿越》中英雄库珀为了解救地球人,自愿离开亲人孤身涉险。但在伟大事业和父女亲情的撕扯下,他在浩渺宇宙中游荡的每一分钟,人类开疆拓土的意愿都只是误解和绝望的另一种表达。
另一方面,科幻作品中通常还会出现宇宙空间站,它是“死亡/坚守”这一话题的深度展开。作为人类最高级的智慧成果,宇宙空间站具有双重属性:它神圣高级,是地球的完满复制品,代表着希望、抗争和坚持,也承载着浪漫的人性气息。然而,宇宙空间站又很不稳定,会在高科技的名义下放大技术文化的弊端,形成整个情节变化的转折点。正如《星际穿越》中库珀的最大痛苦就在于时间的失效、空间的变形。奇点拉长了时间,一小时等于七年的可怕事实使得宇宙空间站成为“孤岛”,从根本上葬送了行动的意义。也像《流浪地球》中国际团队共同进驻的领航员空间站和超高智能机器人莫斯,它们都既是助手又是领导者,既是安全屋又是隔离带,既永恒正确,又无情固执。可见,科幻作品中的空间站以人类的名义反人类;以人类的理性克服人类的特殊性;用人类的逻辑拆解主体存在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认为,科幻作品中的“死亡/坚守”在故事层面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一致形式:库珀穿越归来依然家庭残缺,刘启点燃木星仍然无家可归。科幻灾变的“死亡/坚守”模式启示人们:当以人类为基点审视死亡和理想时,它们都会因其自身浓重的主体意愿而无法独立言说真相。从这个角度讲,科幻作品的要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必死的恐惧和负隅抵抗的双向否定:以技术“驯化”宇宙根本就是虚妄,人本主义的“回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二、掌控安全:灾变叙事的技术乌托邦
科幻是讲究创意的艺术,科幻中的灾变是二次想象的结果,其目的是“在文学和科学幻想上取得某种平衡”。就像科幻作品无法完全依赖科学来自我赋型一样,被技术包裹的安全也只是艺术性的设想。也即一切对安全的追逐都有价值,但一切对安全价值的肯定都是幻觉。所以可以说,科幻电影中危机的解决,无论多么巧妙精彩扣人心弦,在本质上都是人类技术的乌托邦。
首先,从情节层面看,科幻作品中的安全感来自于否定现实、摒弃常态化的生活,表现为一种全然陌生化的悖反形式。例如《星际穿越》中挑选宜居转移星球的拉撒路行动;《流浪地球》中以行星推动器提供地球运行动力,以地下城安置人类幸存者,“这种陌生化更多是概念上的,而较少是语言上的。正是这种新的想法,而不是诗意文本的新语言,震撼我们,将我们带入感知活动。”由此所形成的个人行动法则就处处矛盾,库珀心心念念解救自己的家人而接受太空穿越任务,但他付出的代价是离开家人,背弃墨菲的信任。显然,那个深爱着墨菲的父亲,内心中操持着墨菲法,却走向了对唯一终极的追逐,这本身就是反讽。《流浪地球》中刘启憎恨父亲,竟然决计逃出技术操控的安逸地下城,来到危险无处不在的现实世界。诚然做出选择是其个体成长的象征,但也恰恰是这种不合常理的任性和冲动,构成了对地球安全伪象的有力控诉。换言之,在如何面对灾变这一问题中,科幻作品中的科技力量总是中立的,甚至,正是因为主人公自主选择了不安全,科技的价值内涵才得以被严肃审慎地思考。
其次,从科幻灾变的内在意蕴来看,科学幻想的动因就是对安全的固执、对安全权利和自由意志的偏执。这使得科幻作品偏爱塑造偏执人格的主人公,偏好设计不合常理却行之有效的激进行为。在流浪的地球上,地下城模拟着大家心知肚明却早已不复存在的“正常”生活,其后果是封闭了人们对“正常”的理解。而当得知地球不再适宜人类生活之后,找寻转移星球的伟大计划和卑鄙自私的个人偏狭合为一体。以拉撒路计划之名,设计者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最有可能成功求活的男人,却让那人的女儿在终年封闭的秘密研究基地为自己陪伴送终。

《星际穿越》中以手表为代表的时间意象频繁出现于对亲情的刻画中
由此看来,正如库珀发现五维空间之后的顿悟,科幻作品以庞大震撼的艺术效果编织了一个关于安全的人间神话:面死而生的人类根本无法绝对安全,那么就让他们在计算中、在等价关系中、在想象中争夺安全的权利吧。《流浪地球》的温暖就来自于此。托技术的福,残存的地球人千方百计地丰富地下城的生活,使它更切近地面上曾经的生机。吃饺子、撸串儿、包括说话的口音、吵架的腔调都带着浓重而绝望的怀旧。但这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反生活”。作为没有原本的复制品,所有在地球和木星相撞之前的现实感都是技术文明的纪念碑。《星际穿越》中通过演算分析,组织一批先驱者去“12 个可能的宜居星球”探险。的确,现代社会中“死亡与安全是两个等值的术语。”科幻灾变把握住这种深刻的内在危机,以不平衡、不稳定、不自由、也不完善的组织关系来重建仿真的人类社会的价值结构。所以,地下城的生活和拉撒路行动就是对死亡的模拟,是用“安全”不露声色而完美地表演死亡。由此,一种极具戏剧化的状况出现了:悲壮慷慨的英雄主义等价于美好的臆断和浪漫主义的功能性紊乱。
作为后果,安全成为技术文化的幻觉,它以技术的孤绝中立取消了人类的历史感、因果转承和伦理关系,故而个人能力被约减为生命的无用功能,不约而同地将生命体验具象化为对光速的膜拜。“科幻故事总是被超光速的速度所吸引。……一个因果关系的宇宙的全部可信性将随着这一速度的可察觉的变化而消失殆尽。”灾变中的主体只有放弃了对时间的感受和怀念,才能真正执着于自我选择,才能真正拥抱自由。
故而,从根本上说,科幻灾变并没有展示出一条通向安全的路径,而是模拟走向极致衰败和全面解体的人类个体的极端感受。而科幻的功能也不像传统的精神分析那样,期盼着将我们从幻象中解救。相反,科幻要做的是让我们进入幻象,在幻象的深度体验中带着距离切割真实、催生快感。这也就是本·波瓦所说的:“科幻中具有一种力量,那就是提供机会使人去思考,一种通过幻想世界反映出我们世界的多种侧面的能力。”
三、双重倒置:有意味的大众传播策略
科幻文体是戏剧性的,它对现实进行惊悚化处理,夸大了可能的危机。而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科幻电影又必须处理市场营销和观众期待等问题,对科幻文本的精神内蕴进行定向裁剪和改装。我们认为,整体来看,科幻灾变的叙事策略包含着恐惧的感受性倒置和救赎的认识论倒置两方面。经过这种双重的结构性转换,科幻电影将抽象冷峻的科学观念转化为温情积极的人本主义。
(一)恐惧的感受性倒置
科幻电影围绕着观众的恐惧心理大做文章。抛开科幻作品酷炫的外太空高科技的壳子,灾变影片中关键问题的解决总是脱不了世俗的烟火气。由于依托前沿科技,科幻中的恐惧在形式上并不一味追求具象清晰,在品味上也不显得激进幽暗。它颠覆或更新观众的知识储备,激发普遍的认知危机。直观看来,科幻电影通过图像直呈,将一切形式的灾变都归结为人类对自身根本性存在问题的追问。《星际穿越》和《流浪地球》好像讲述着不同缘由的地球灾变,但它们的底本都是逃离,都关乎人类的共同忧虑:作为浩渺宇宙中的微粒,我们如何判定自我选择和发展路径?且不说《星际穿越》中科学主义的计划A 从一开始就是无情计划B 的幌子,英雄豪情也不过是人间悲情的前奏。在《流浪地球》中,亲子之间的尖锐矛盾实则是三代人分别从偶然性、实用性和情绪天性角度对生死作出选择。在这一基础上,对地球究竟如何持续的问题就被自然转换为至爱亲情的疏离如何被克服。
可见,科幻电影的大众文化属性,促使它有意识地将无法控制、无从想象的巨大灾变转化为人情社会中的错误判断、信任危机和个性缺陷。这样,灾变的诸多不确定性和观众相关知识的欠缺就不再成为问题,观影过程便以射线的方式被设计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科幻电影人为地制造出一种从无限到有限的感受性倒置。原本在科幻艺术中被强烈质疑和颠覆的理性边界、因果原则和价值结构都再次复活。观众越是惊诧于影片的高科技效果所带来的视觉兴奋,就越是会将宇宙本相的反思定位在影片所设定的人物性格和类型特征上。这样,科幻影片中的英雄永远都是某种人的典型、某类人的象征,而不是科幻经典意义上所关切的孤独无助、精神游荡的微小宇宙生物。也由此,影片无论将灾变的解决设计成人类主动寻找宜居星球还是被动拖着地球流浪,这在感受和体验层面都处于同样的论说逻辑,都具有共通的情感可传达性。
如果说科幻电影是对现实问题的曲折回答,那么我们看到,为了刺激观众的观影兴趣,灾变叙事擅长提供一种应激过度的“恐怖主义”回应。它以此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
(二)救赎的认识论倒置
如前所述,因为安全是一种技术乌托邦的幻觉,所以科幻灾变叙事在逻辑上不认可救赎的可能性。但在科幻电影中,借由新科技观念的强大解构和重组功能,科幻中的救赎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还代表着某种谋划的极致,其结果是人类得以在技术保障下无限地平安延续。
在这里我们看得出,科幻灾变的救赎和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和解与强化。如果依照科幻的预言性,人类抵抗灾变从根本上说是毫无胜算的。然而科幻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它需要传递一种轻松、肯定和娱乐性的审美格调。而正如刘启和父亲的矛盾总是会在关键时刻被大局意识消解,和解作为解决灾变的可行途径,它取消了时间,取消了回忆,通过重复使得可能成为永恒。而库珀对五维空间真相的传递,也在父亲认错、亲情重建的话题下被简约带过。故而我们认为,通过和解的插入,科幻灾变中的救赎不再线索清晰、步骤明确。救赎本意所包含的确定、理性和真实感被大众并不熟识的高科技模糊感所替代。因而不是高清晰度,而恰恰是象征、留白、激情、顿悟,才能成为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救赎路径。

《流浪地球》电影海报
此外,在科幻电影的灾变叙事中,强化作为普遍使用的技巧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电影技术的迅猛发展,灾变叙事越来越依赖技术,而其形态也越发千奇百怪难以捉摸。在经历了灾变场景高频率高清晰度的恐怖画面轰炸之后,观众的自我认知系统走向崩溃。此时,我们会很惊讶,我们已经无法分析可能的现实了。惊讶、恐惧和震撼都编织进我们对现实可能性的认知中。必须承认,我们其实一直在认识自己“认为”真实的世界,我们自身和世界有无限隔膜。“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表象与实在界的辩证简化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虚拟化,我们日甚一日地置身于人工建构起来的世界,于是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冲动,要‘回到实在界’,踏踏实实地根植于某种‘真正的现实’。我们要回归的‘实在界’已经成为(另)一种表象:恰恰因为它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它具有创伤/过度之特征,我们无法使其融入现实,或者说,我们无法使其融入被我们体验为现实的东西,因此,我们被迫将其体验为噩梦般的鬼怪。”
换言之,在科幻电影对灾变解构途径的艺术设想背后,真实的效果不是带领观众思考宇宙奥义或者人生价值,而是走向对现实的疏离、对认识边界的消解。因为灾变总会在技高一筹的谋划和行动中被解决,那么我们就无须按照知识的或逻辑的观念再来审视现实问题。“在笑、痛苦或所有其他类似体验中发现的常识或知识要附属于——这来自于它们遵循的规则——‘可能’的极限。每一个知识在自身的范围内都是有价值的,尽管必须意识到只有极限存在的时候它才有价值——意识到根本的体验必须与它加在一起。”因此,科幻文学的启示意义和反思价值不在了,被取消了认识边界的救赎,以进步和完善为名,只留下巨大的视觉刺激。
所以,可以看出,科幻电影中的灾变结构策略显示出大众文化的内在要求。双重的倒置是以内心体验取消了人类行动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确定性。这样,电影成功地回避了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希望的缺席、兴奋的缺席,而表面的可能性封闭了同类的无限可能性。所以在科幻中人类永远不会毁了自己,因为投注的快感本身就是明智地对待恐惧的方式。
四、无用功能的狂欢
科幻永远都是现实的寓言,而科幻电影却是对现实的变形解释。正如波德里亚所言:“起因产生效果。即是说,起因总有意义和终结,它们从不导致灾难(最多导致危机而已)。而灾难则是对起因的废除。”科幻艺术是一种孩子气的文体,它铺陈灾难却不怎么看重它,因为科幻作为开启极限思维的智性文本,它诉诸于读者的思辨能力和反思意识。科幻艺术带着冷峻的嘲笑与现实保持距离,探讨可能性的问题。而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科幻电影,必须要在新奇艰深的科学知识的武装下显示出足够的气势磅礴和严肃庄重。痛苦和理智一样是认识的工具。科幻电影的灾变结构以痛感的拆解与重组来搭建一个可被大众接受的世界。而对极限和边界的思考只能滞留在科幻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