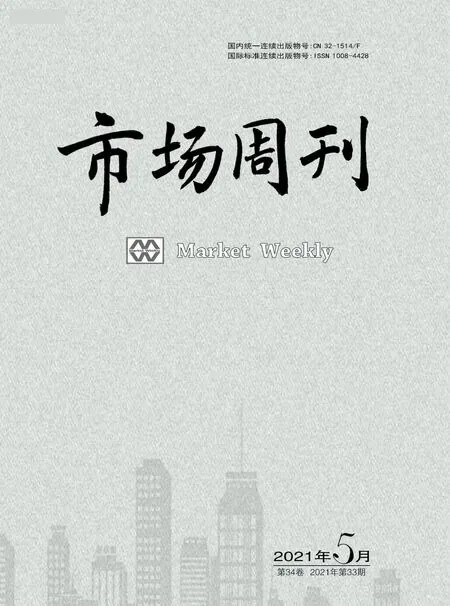论证券市场先行赔付制度的完善
黄梨珊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广州510006)
一、问题的提出
投资者保护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完善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欺诈发行等案例频频多发,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而长期以来,我国对于证券市场主体损害投资者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主要是通过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行规制,民事责任相对缺位,加之证券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高、耗时长、获赔率低等诸多原因,使得投资者陷入了维权难、赔偿难的困境。如何使受损投资者获得及时、充分的损害赔偿,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成为立法及实践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在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方面有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将先行赔付纳入证券立法的范畴,使得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先行赔付制度并非由证券领域立法首创,此前的保险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等均有相应的规定。而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基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处于弱势地位,先行赔付制度借由证券立法对投资者进行倾斜性保护合乎公平和正义的法理。在新证券法将先行赔付纳入立法之前,已有相关的法律文件提出要在证券市场建立先行赔付制度。而在司法实践中,2012年的万福生科案、2013年的海联讯案、2016年的欣泰电气案以赔付范围广、赔付率高等特点,在证券市场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为今后的先行赔付制度的规则细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
在新《证券法》已对先行赔付作出了基本规定的前提下,回应证券市场的实践需求,需要考虑如何将该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证券市场先行赔付的法律属性显得十分必要,具体规则的设计和安排需要符合先行赔付的法律性质,不得违背自愿原则。具体的制度完善则可以从赔付主体、赔付程序及先行赔付后的追偿权等方面进行考量。
二、证券市场先行赔付的法律性质
(一)诉讼外的和解行为
根据新《证券法》第93条的规定,先行赔付的实质是赔付主体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达成的诉讼外和解,和解以和解协议的形式实现。先行赔付协议具有合同属性,基于赔付主体和受损投资者双方的合意所达成,协议双方须履行约定的权利义务,该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而其他未参与先行赔付的连带责任主体承担的仍是侵权责任,但是实践中,赔付协议通常约定了若投资者接受了先行赔付则自愿放弃对其他连带责任主体的侵权赔偿请求权,而先行赔付主体完成赔付之后则可以向其他连带责任主体追偿。
(二)证券市场的自律性措施
先行赔付应当是证券市场的自律性措施,以当事方的自愿为基本原则。新《证券法》第93条规定中的“可以委托”一词说明先行赔制度只具有指导性和倡导性作用。在证券市场中,先行赔付主体通常基于维护商誉、减少对其后续业务的负面影响以及换取证监会的从轻处罚等方面的考虑而具有较强的先行赔付意愿,而先行赔付的成功实施一般也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对于不愿进行先行赔付的相关责任主体亦不可附加强制性法律义务,否则有违先行赔付的法律属性。同时,不仅对于责任主体不具有强制性,对于受损的投资者更不具有强制性。先行赔付作为一种能够让投资者获得更加及时、充分的损害赔偿的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以适格投资者的自愿选择为适用的前提条件,如果受损投资者基于自身的诸多考虑而不愿接受先行赔付,其有充分的选择权,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损害赔偿。先行赔付是证券市场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代表性制度安排,对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平衡机制
首先,先行赔付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其根本功能在于解决证券市场上的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证券市场主体虚假陈述、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往往造成大规模的投资者权益受损,中小投资者这一特殊群体具有社会性,其法益具有公益性,必须妥善处理纠纷,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否则有可能演变成群体性社会事件。其次,这类违法行为可能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秩序,打击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不利于证券市场的整体发展,因此,基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公共政策的考量,制定和施行先行赔付制度。再次,通过实施先行赔付制度,将原本应由弱势方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完成的赔偿请求,转由实力相对较强的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通过追偿实现,能够有效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权益,从根本上实现对投资者的倾斜性保护。
三、先行赔付制度的完善进路
(一)先行赔付的主体
立法明确的先行赔付主体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关的证券公司。为了鼓励证券市场主体积极适用先行赔付制度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应当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除对先行赔付主体从轻处罚之外,还可与《证券法》第171条规定的证券行政和解制度对接,当市场主体向证监会承诺对受损投资者先行赔付时,证监会可以中止调查,在其履行承诺后可以终止调查,而在其未及时履行赔付协议时则应当恢复调查。通过确定的行政执法措施达到鼓励先行赔付适用的积极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对先行赔付主体的规定采取的是有限列举的方式。因为虚假陈述、欺诈上市等违法行为与信息披露违规的亲缘性,故将先行赔付的规定与《证券法》第85条的规定进行对比。依据《证券法》第85条的规定,违规信息披露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过错推定责任。而先行赔付的主体范围并不包括发行人的董监高等,这里可能考虑的是董监高的赔付能力不足。但是在今后先行赔付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不应严格限制先行赔付的主体,如果发行人的董监高自愿参与先行赔付,也应当予以认可。因为真正实施虚假陈述、欺诈上市等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也有可能是董监高,基于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提前进行相应的损害赔偿具有合法性,同时,董监高的偿付能力不能一概而论,不排除财产实力雄厚的董监高能够进行先行赔付的可能性。
此外,立法并未禁止可能的责任主体共同参与先行赔付,因此,应当许可各个可能的连带责任主体协商共同出资设立赔偿基金用以对受损投资者的统一赔付,在共同先行赔付的情形下,可以避免个别市场主体虽有先行赔付的意愿但无独立进行赔付能力的情况,提高先行赔付适用的可能性和赔付率,最终体现为良好的投资者获赔效果。
(二)先行赔付的程序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在此前的三个先行赔付案例中,赔付方案均由先行赔付主体单方制定,投资者作为赔付协议的另一方主体几乎没有参与协议制定的机会,某种程序上来说,先行赔付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先行赔付主体手中,而受损投资者只能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这一境况偏离了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对受损投资者权益的维护。因此,在细化先行赔付的规则时需要充分尊重受损投资者参与协商的权利。但是同时也要顾及受损投资者范围广的特点,赔付主体显然无法与每位投资者进行一一协商,否则将使得先行赔付制度丧失其时间和效率优势。因此,需要合理权衡其中利害进行具体的规则安排。
具体而言,在赔付方案制定过程中,先行赔付主体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并就赔付方案的制定与受损投资者进行协商。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可以先结合责任主体的违法程度、投资者实际损失、先行赔付主体的财产状况等因素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拟定赔付方案草稿,并将该草稿向全体受损投资者进行公布,在公布期间内接受投资者的质询以及意见。其后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邀请受损投资者代表参加,充分听取投资者代表的建议,并就赔付方案草稿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对草稿进行修改形成正式的赔付方案并予以公告。受损投资者享有选择权,其可以选择接受赔付方案,如果不愿意接受赔付方案或仍对赔付方案不满意则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权。通过完善先行赔付的程序规定,提高受损投资者在赔付方案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使协议双方能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三)先行赔付后的追偿权
先行赔付主体完成赔付之后,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保障先行赔付主体追偿权的实现,可以提高市场主体主动适用先行赔付制度的动力。需要注意的是,先行赔付不等同于法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最终各责任主体应当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由司法判决确定,此时可能会出现先行赔付的总额与实际应当承担的违法损害赔偿总额不相等的情况。先行赔付应当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为基础,但是如果先行赔付主体为了修复受损的商誉、换取监管机构的从轻处罚等考虑而选择超额赔付,此时带来的问题是超额赔付是否合法以及超额赔付后能否就超额部分追偿等。虽然不排除超额赔付带来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先行赔付的实质是一种和解行为,和解协议具有合同属性,应当尊重协议双方的合意。如果先行赔付主体自愿进行超额赔付,法律也应当认可协议的效力。但是对于超额赔付后的追偿问题,有学者认为超额赔付可视为赔付主体自行承担超出的赔付,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时,其他连带责任人可依法提出相应抗辩。但是另有学者认为其他责任主体亦需就超额赔付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先行赔付主体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论文赞同前一观点,一方面,在先行赔付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其他责任主体并未参与协商,赔偿协议并未体现其他责任主体的合意;另一方面,先行赔付所带来的商誉恢复、从轻处罚等积极效果仅归于先行赔付主体,其他责任主体并未从中获益。因此,如果存在超额赔付的情况,其他责任主体可就超额部分对先行赔付主体的追偿权提出抗辩。
追偿权行使可能面临的另一障碍是其他责任主体破产的情形。如果发行人或者是其他责任主体宣告破产,先行赔付人享有的追偿权也就转化为破产债权。此时出现的问题是先行赔付者的清偿顺序如何认定。有学者认为,先行赔付可以视为赔付人代替责任人履行赔付责任,从而获得投资者对责任人的债权的过程。因此,破产程序中先行赔付人的债权清偿次序应当等同于未赔偿之前投资者享有债权的清偿次序。但是也有观点提出,若清偿顺序等同普通破产债权,先行赔付者将承担赔付款项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先行赔付主体一般也是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其本身就应当承担一定的违法风险。同时,先行赔付者基于赔付行为已获得恢复业界信誉度、从轻处罚等益处,无须再对作为违法者的先行赔付者提供进一步的破产债权保障。因此,破产程序中先行赔付者的债权清偿顺序等同于赔付之前投资者的债权清偿顺序具有合理性。
四、结语
先行赔付制度在投资者维权、救济等事后保护中起到“先行”的关键作用,某种程度上来说,先行赔付制度的适用于赔付主体和受损投资者而言是双赢的结果。先行赔付以自愿为基本原则,并非相关责任主体的强制性法律义务。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应当与行政和解、集团诉讼等制度有效衔接,多层次化解证券市场的纠纷和矛盾。适用先行赔付制度时,不宜严格限定先行赔付主体的范围,应当允许责任主体共同出资进行赔付。在赔付方案的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权衡投资者保护与投资者风险自负原则之间的关系,在稳定证券市场的同时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细化先行赔付的规则时,还需要注意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先行赔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其作为基金管理人与受损投资者就赔付事宜进行协商,有利于保障赔付结果的公平公正。在先行赔付完成之后,则需要重视对先行赔付主体追偿权的适当保护,但是,由于先行赔付主体一般也是违法责任主体,其应当承担一定的违法风险和违法后果,故对其因先行赔付形成的破产债权的保护不应优于赔付前投资者享有的债权。只有不断细化先行赔付规则,才能保障先行赔付制度更好地发挥保护受损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