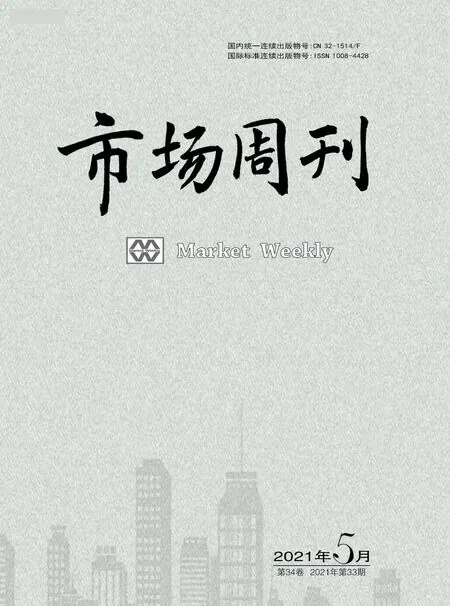网络舆论反转研究综述
——基于2015~2020年的CSSCI数据
张燕妮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510850)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负面信息而引发的舆情。如由某一偶然事件在网络舆论的放大下演化为网络暴力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由此形成的网络舆情往往是由非利益相关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推动的,不仅加剧事态的升级,也使得地方舆情防控的压力超越以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较2018年底提升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如今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并非局限于传统媒介,而是在微信、微博与各大新闻客户端等“互联网+”平台的实时推送下快速获悉相关信息。正因为如此,一些小概率的事件在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不断被社会放大,热度不断上升,但有些事件并非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在后续的新闻报道中因出现新情况或新证据而出现“反转”。
网络舆情反转的本质是虚假新闻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是网络舆情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一种体现,反转实际上是事实的反转。舆情反转事件引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媒体公信力受到质疑、公众受到欺骗,从而累积社会负面情绪,放大了社会的阴暗面,在短时间内渲染和加深了不良情绪,严重影响公众对社会的基本信任,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引发社会情绪不稳定和社会矛盾。为破解此难题,应加强对网络虚假新闻的管理和整治,坚守媒体的责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现如今,新闻反转剧屡见不鲜,典型闹剧频频出现,新闻界却不以为然,以致案情的披露出现多次反转。以2015年5月中下旬《杭州日报》误报大连男子李先生贩毒,实为警方因其与真实的毒贩同名同姓而导致的工作失误,连同媒体一起对李先生造成困扰,李先生发声却引来《杭州日报》并不诚恳的道歉,引起公众不满。公众认可由于案情复杂而导致的播报不够准确,但不赞同新闻媒体因为抢新闻或者蹭热度等不够严谨地传播信息,并认为在错误播报后,新闻媒体应做出合理的道歉,才能维持社会公信力。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众是关注事件本身的真相还是期待“反转”后的解释?为此,论文试图通过梳理近几年国内学者关于网络舆情反转的研究,以“舆论反转”“反转新闻”与“舆情反转”为关键词在CSSCI数据库检索,在剔除一些会议综述、笔谈的基础上统计得出相关文献50篇,从国家治理层面、新闻媒介层面与群众个体层面找寻现有研究的脉络与理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思,以期丰富网络舆情反转及其治理研究。
一、国家治理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反转治理
新媒体环境下,因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及把关人缺失等原因,导致负面新闻、虚假新闻与反转新闻频发。加之反转新闻兼具负面新闻与虚假新闻的双重特性,甚至在真与假中摇摆和穿梭,不断激起受众对真相的渴望的同时,也引发对他人、政府机构与媒介组织的怀疑与失望,进而侵蚀公众对社会、媒体与政府的信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在转型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双重语境下,社会信任机制出现问题又将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塔西佗陷阱”,激化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和谐,污染社会风气。
针对舆情转变的特殊现象,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热点事件舆论治理响应能力,争取舆论引导的时效性,利用政府主导力与话语权,实现公众情绪疏导和加强社会认同,针对媒体不实报道加强素质管理,增强其社会公信力,严格把关不实信息,拒绝过度传播和大肆渲染,避免高敏感度的社会事件信息披露造成不良的公众刺激效应。也有学者通过模型来研究舆论反转,有的通过考虑信息和组织氛围影响的群体观点演化模型,以经典Hegselmann-Krause模型为基础,运用MATLAB编程实现仿真实验,得出结论认为信息是影响网络舆论反转的最关键因素,在舆论爆发时,信息敏感度和组织归属感能够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偏向,因此,控制信息披露能够有效控制网络舆论。
综上,正确引领网络舆情,保障网上舆论阵地安全,事关当下我国意识形态主流阵地建设和国家政治安全。虽然网络舆论反转现象存在很多无法彻底根除的客观影响因素,但可以通过教育和约束网络参与者,使其培育以法治精神和法治价值为导向,并且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律方法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法治思维,以此来有效地降低网络舆论反转发生的概率,以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
二、新闻媒介推动下的网络舆情反转过程
网络舆情的出现不完全是源于网络空间,线上线下的互动促使媒体报道与受众关注,终形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的形成、反转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们认知事件的过程。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人们认知事件“参照点”的不同,会造成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不同。不同参照点在不同时点的出现并重复反馈形成舆情反转。其实质是人们因认知不同而形成的舆论上的多次建构,网络舆情反转现象中存在“参照点”效应。但即便新闻反转闹剧频频出现,也难以改变社会舆论的方向。
舆论反转既有负面性,也有一定的建设性,舆论在社会管理决策过程中具有提出社会目标的功能。破解舆论反转的关键是要着眼于舆情治理的前瞻性,把握社会矛盾的焦点和问题。有学者利用框架分析的内容量化分析方法,对微信公众号的内容编排、发布时间、标题内容等视觉结构符号进行分析,探究微信公众号用户的阅读行为和使用动机与“反转新闻”的深层关系,发现微信公众号具有超文本结构,其信息传播机制对公众号用户的使用行为和效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网络媒体的无意识议程设置、有意识议程设置及网民议程设置等是引发网民舆论反转的关键因素。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话语权的提高,导致的并不是喧嚣嘈杂、非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而是更为严厉整肃的制度管理反弹。在这种严肃的制度管理中,过度的管控会导致舆论生态失衡和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活跃度下降,而更广泛的群体将会在舆论场上更加活跃。这种生态失衡也会导致话语精英阶层参与式协商对话在社会决策中的缺位。
综上,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下社会公共事件热点舆情呈现出复杂的传播态势和特点,也存在诸多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共事件热点舆情处置,须尽快转变社会公共事件热点舆情管理理念为舆情治理理念,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做好政策解读,重视线上—线下、事件—舆情、眼前—长远双管齐下实现标本兼治。只有在厘清网络舆论演变机制的前提下,才能追根溯源,整肃网络空间,推动公众等社会参与主体正向参与社会管理,从而推动社会公平公正的发展。媒体追求新闻效应的同时,更应该秉持着新闻人正义与公平的信念,避免故意模糊化处理引导受众感性情绪的大幅波动,主动成为一座有社会责任感的时代瞭望塔。
三、群众个体参与下的网络舆情反转
网民群体的高度身份焦虑催生的社会信任缺失及怨恨情绪。其中对于职业角色的污名化源于依靠道德约束的信任模式的崩溃,权利角色的被污名化原因则表现为社会对利益、权利、权力三方面的结构性失衡的怨恨情绪,而在信任危机与怨恨情绪双重作用下,便出现了开放性角色的污名化。网民作为舆论反转中参与、扩散和传播的主体,其认知与情感会影响网民参与的行为意愿,其行为意愿又显著影响着舆论导向。
在舆论反转过程中,网民更多倾向于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进而产生从众心理或新的观点态度,引发群体极化效应。这种群体极化从以下几个角度影响网络舆情的产生与传播:群体极化中的“携带倾向”是网络舆情的潜在属性。在这种“协同过滤”的过程中容易滋生不理性情绪,产生群体极化倾向,从而影响网络舆情。在群体极化“过程聚集”中,又会形成网络舆情反转的隐性动力。但认知偏见既可以增强个体对原有观点的选择,也可以削弱其对观点准确性的判断力,即个体认知受认知偏见的影响。碎片化、开放性、选择性的叙事机制,情结、想象、情绪化群体思维构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多元话语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机制共同构成了网络舆论反转的三大机制。因此对其治理要遵循舆论反转的发展规律,从形成机制上入手,强化过程控制与管理,构建相互衔接、科学系统的治理机制体系。
综上,在突发事件舆论治理方面要注重公众情绪,把握舆论传播中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反转发生时应保证信息公开,杜绝谣言,并处理好舆论后续,降低负面情绪累积,促进良好舆论治理循环。有学者还通过构建微分方程模型研究反转机理,从而监测网民在表达和传播意见、态度和情绪的过程中出现向反方向转化的现象和趋势,并据此开展网络舆情反转预测和动态评估研究,提出要根据实时监测数据和动态预测数据计算反转度确定评估级别,进而确定不同评估级别的预案。也有学者通过引入前景理论,构建反转网络舆情监管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提出加强政府对网络舆论环境的监管力度,规范网民和媒体行为;加强媒体公信力建设,做好信息“把关人”的角色;提升网民媒介素养,理性表达观点等加强反转网络舆情监管的对策建议。正确引导网民的情感认知,避免因片面信息泛滥造成的舆论错位冲击社会信任体系,进一步降低反转新闻的负面影响。
四、研究展望
舆情反转小到影响网民的感性情绪和道德认知,大到影响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对国家治理提出一定的挑战。学者们对反转新闻的研究多以案例分析为主,或是利用构建模型展开分析,围绕其概念成因、新闻效应反思、新闻素养,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纵观既有研究,鲜少研究大学生群体对反转新闻的作用,尤其是由于大学生的关注,参与评论等进而推动舆情的反转。
总体而言,反转新闻不能简单定义为新闻的失真,而是新闻真相的别样呈现,这体现在反转新闻是新闻真相的过程化呈现、报道者的情感和观点也是新闻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反转新闻是深层社会现实的反映,故不可片面否定反转新闻的价值。但由于反转新闻与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存在一定的偏差,反转新闻对传统新闻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表现为大众媒体及其记者不再是大众信赖的唯一权威信息源、反转新闻的多样化表达冲击了新闻报道的有效性、反转新闻的出现使得新闻真假难辨。而舆论反转的矛盾焦点多指向社会日常伦理观念和道德争议。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潜在利益相关者的情感纠缠和观念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