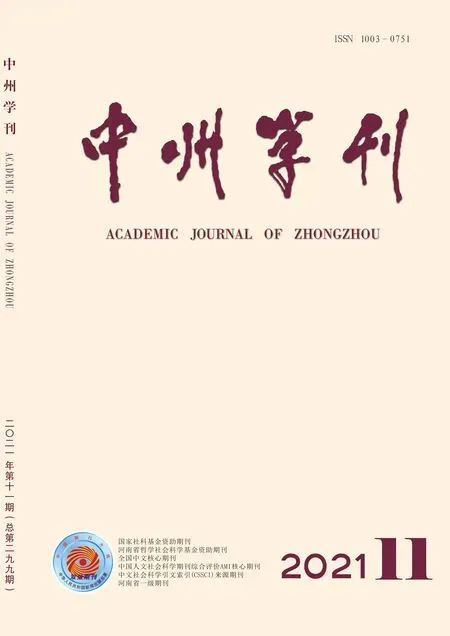现代性的双面书写
——论当代网络文学中的宏大叙事
高 翔
宏大叙事之于当代中国文学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宏大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统被追溯,从“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话语,到其后的革命叙事,宏大叙事建构了现代文学的骨架;另一方面,宏大叙事的式微构成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症候,引发广泛的探讨。在某些文论家看来,当代社会的样态导致宏大叙事被一种“小叙事”取代。
与纯文学视野中宏大叙事的整体倾颓趋势相比,大众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宏大叙事特性。自新世纪以来,主旋律文化所建构的革命叙事依然是宏大叙事的主体,不过从《历史的天空》《亮剑》《建国大业》《建党大业》等作品来看,革命宏大叙事表达开始具有更多通俗的、大众文化的特性,宏大叙事在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场域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表述。事实上,在网络文学鲜明的异托邦指向当中,本身就蕴含着宏大叙事的形式;在其价值结构中,无论是玄幻小说还是历史穿越小说,都蕴含着大量诸如民族主义等指向宏大叙事的价值体系。伴随着网络文学脱离简单的爽文倾向,其宏大叙事所表征的虚拟现实有了愈发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对网络文学宏大叙事进行研究的前提。
一、场域变换:宏大叙事的文化顺延
“宏大叙事”这一概念首先是在现代性的哲学场域中被定义的。启蒙主义所生成的科学精神、理性话语,导致人们对于认知世界、建构世界的绝对信心。鲍曼将现代性语境中人们以理性话语建构完美秩序的行为称为“造园冲动”,宏大叙事就是对这一行为的话语呈现,“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①。故而,宏大叙事所表述的,就是运用科学视角对世界进行总体认知和陈述的话语体系。从话语结构上看,宏大叙事不仅完成了对于历史和当下的逻辑化处理,而且生成了指向未来的政治效能。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既是一种话语结构中具有普遍性的“思辨的叙事”,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场域中的“解放的叙事”,它作为一种“元叙事”建构了现代性知识的合法化图景:“‘元叙事’就是指启蒙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故事。”②在他的表述中,宏大叙事成为现代性的鲜明话语方式。
文学场域中的宏大叙事,是以故事的完整性、逻辑性来完成对于现实的总体理解,并将其纳入现代性的“造园冲动”这一总体政治图景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启蒙”和“革命”之争构成近代文学的“元叙事”。其中,“启蒙”更具“思辨的叙事”之特点;“革命”更多地作为一种“解放叙事”而呈现。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革命叙事与现代性(现代化)叙事的流变中,持续不断地构建了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化想象所遭受的挫折,以及适逢其会的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广泛引入,先于社会情态的嬗变构筑了中国的后学思想语境。市场化进程的汹涌发展,大众文化的快速崛起,亦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想象“后现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样貌。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文学进入持续地对于宏大叙事——现实主义这一美学标准的反叛之中。先锋文学以形式反叛内容,解构了历史和现实的确定性逻辑,构成了对于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和女性的“私小说”,将视野“落入”日常生活和封闭空间,以个体化的场域空间取消了对于整体历史的考察。持续兴起的新生代作家的欲望叙事,则以“非道德化的个人立场”③,更为彻底地体现了市场化语境中宏大叙事的消弭。
与之相比,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史诗”倾向似乎建构了新的宏大叙事写作④。这些作品以长历史的视野对群像进行刻画,并将意义延伸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之中,这是鲜明的“史诗”气质的呈现。“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个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必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⑤在这里,史诗显然表征了一种通往宏大叙事的文体风格,不少文论家也将这两个范畴联系在一起进行表述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虽然具有反映社会历史变迁、构建民族国家的史诗气质,却并无宏大叙事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指向。它们不仅远离了启蒙叙事所建构的科学与理性这一基本价值视野,也在相当程度上质疑了现代性解放政治的可能性。尽管这样的书写构成了中国语境中“未完成现代性”的特定表现方式,但它们在内容上却以别样的历史呈现成为对于宏大叙事的特定解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本反映了宏大叙事在纯文学书写中的衰落。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利奥塔以“宏大叙事”来表征启蒙和现代性话语模式的消解那样,后现代语境中的“宏大叙事”恰恰具有一种否定性立场,表明了启蒙话语尤其是“解放政治”的深刻困境,宏大叙事遂成为一种乌托邦特质的叙事想象。“宏大叙事是一种逻各斯中心的总体性叙事,昭示着这个世界有一个‘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开头,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是线性演进的,有终极目的的,有乌托邦指向的——这正是长篇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模式。”⑦
纯文学宏大叙事的历史嬗变可以延伸到普遍的文化场域中去。根据东浩纪的观察,宏大叙事的凋零表征了从现代性跨入后现代的时间节点,它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呈现。在后现代语境中,文体层面的宏大叙事依然广泛存在,却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基于后现代的特性,宏大叙事已经不再是对于当代社会的总体理解,而仅仅是基于某些机要主义理念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从叙事效果来看,宏大叙事不再具有普遍的叙事效力。“因为后现代理论所提出之大叙事衰退,并非是论述探讨故事之本身的消灭,而是探讨对社会整体其特定的故事之共有化的低落。”⑧同时,就后现代的消费理念而言,也发生了从故事消费到资料库消费的变化:“从现代往后现代发展的潮流中,我们的世界观原本是被故事化的且电影化的世界视线所支撑,转为被资料库式的、界面式的搜索引擎所读取,出现了极大的改变。”⑨东浩纪以御宅族文化为例指出,对这一文化的消费并非在于对传统的故事、人物、世界观的消费,而在于对聚集了基于人物和设定的庞大数据资料的消费,它会不断地从其资料库中组合出各种各样的小叙事(拟像)。最终,这些宏大叙事亦只是后现代多元叙事的一种,并被纳入资料库当中的故事类型,“这些想象也只能视为属性资料库消费基础上的小叙事加以掌握理解即可”⑩。
就中国语境而言,这一宏大叙事逐渐沉降到通俗文学中,并且从文化结构上形成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补偿:“宏大叙事凋零之后,‘纯文学’方向发展出‘现代派文学’,直面价值的虚空;通俗文学则向幻想文学的方向发展,以‘捏造的宏大叙事’(或称‘拟宏大叙事’)进行替代性补偿。”在邵燕君看来,东浩纪所谓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断裂,对应着中国语境中启蒙主义的式微,“拟宏大叙事”由此成为一种在“后启蒙”语境中价值弥补的方式。“拟宏大叙事”以虚拟想象来进行宏大主题的建构,这一点在网络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呈现。同时,邵燕君也从当代网络小说的迭代出发,认为中国网络文学逐渐进入到一个以二次元文化所表征的资料库模式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样态之中,从而进入东浩纪式的“小叙事”模式当中。
以东浩纪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宏大叙事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日本相对鲜明的文化转型相比,中国的文化场域更为复杂和多元。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就已经在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从国家主体政治建构层面来说,依然处于现代性叙事之中。伴随着时代政治语境的变化,宏大叙事具有更多的表述可能,并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学的场域中予以呈现。同时,东浩纪式的资料库模式在中国方兴未艾,二次元文化亦只是网络文学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书写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的实践已经表明,宏大叙事依然可以通过小叙事来得到表达。例如,二次元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显著的文化事实。故而,当代网络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不仅是“后启蒙”时代对于大众的意义填充,更具有特定的现实意蕴,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
二、历史重塑:宏大叙事的呈现维度
相比于传统纯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中国现代性叙事的脱嵌,网络文学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想象有着更为鲜明的叙述。作为一个自发形成的文学场域,网络文学以全新的生产机制脱离了传统文学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网络文学显现了网络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性,这与它的幻想气质并不矛盾。新媒介文化作为一种话语场域,重新生成了诸如“网络民族主义”“工业党”等具有宏大叙事特质的能指,网络文学写作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特征。从总体上看,民族主义叙事、工业党叙事和文明叙事,呼应了当代中国从上到下不断重构的现代性想象,从时间上构成网络文学宏大叙事想象的基本视角。
在近代中国的文学表述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基本的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依然被视为一个整合现代性话语的核心能指。“新时期文学开始后,阶级革命叙事开始退却,而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却在‘现代化’旗帜下,进行新的整合努力,并试图树立‘文化复兴现代中国’的新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这种主流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温和,内涵繁杂,更为侧重建构一种和平崛起的总体叙事。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从知识界发轫并一路蔓延到大众文化的民族主义冲动。从《中国可以说不》等的热销,到新世纪以来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崛起,《战狼2》等新主旋律电影的兴盛,当代民族主义在新的时局下得到新一轮的暴发,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更为强硬的话语形态。
网络文学顺应了这一民族主义话语潮流,在(男频)历史穿越小说的时间视野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2002年的《中华再起》最具首创性,它讲述了主人公穿越回清末、扶助太平天国战胜清政府、对抗列强进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过程。这种以穿越重构近代史的方式,引发了盛行一时的“晚清救亡流”的书写。《中华再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与当时一些爱国主义话语平台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清晰地表明了民族主义从新媒介话语空间向网络小说文本的沉降。晚清是中国百年耻辱的开端,又是现代性的起点。小说文本试图以重商主义、工业化等来建构强大的中国,显然是对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复制。这种以现代性叙事来消弭民族屈辱的历史想象,从“虚拟现实”的视角上重构了宏大叙事。在此之后,“晚清救亡流”的作品虽然理念殊异,但都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历史想象。
如果说关于晚清的想象在异时空重现“救亡”叙事,带有迫切的民族主义情感表达;那么,对于更早的历史的回溯,则带有更为全面的“历史考古”的印记。被称为历史穿越文奠基之作的《新宋》出自专业的历史系学子之手,其书写特色在于从社会、思想、吏治等各个视角全面考察了宋朝的社会形态,并从主人公的视角对国家进行全面的设计。在此之后,关于宋、明的穿越文迅速成为一种潮流。总体来看,尽管《明》《回到明朝当王爷》《宰执天下》《临高启明》等代表性作品各有特色和侧重,但都具有“开启现代性”的情愫与色彩。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力图建构一个属于东亚的现代性历史。他从中西比较视野出发,将宋以后的历史看作东亚现代性的滥觞,并且具备了相应的思想启蒙,但“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西洋在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很快就迈入了近代史的阶段”。这种对于东亚历史的遗憾在宋、明穿越小说中得到了呈现,这些文本将宋、明视为华夏落后的起点,并以严肃的历史思考来发掘乃至重构这一时期的现代性因素。在《宰执天下》中,韩冈以朴素的民族情感来推行国家的建设,《回到明朝当王爷》中的杨凌看到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及改造国家的紧迫,《临高启明》更是以彻底的实验性写作,对于开启现代性进行科学式的呈现。在这些文本当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指向现代性的民族主义叙事;叙事的后果,则是重构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族。
在民族主义这一能指之外,工业党叙事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工业党叙事作为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而出现,网络文学中工业党叙事的兴起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民族国家是现代性“造园冲动”的主体,而工业化是其技术内涵。无论是吉登斯、贝克还是鲍曼,都从不同的视角,将工业化理解为现代性的最核心特质之一。第二,从新媒介语境来说,工业党叙事源自网络上的工业党,尽管工业党的生成颇为繁杂,但是以工业化视角重构“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并建立国家的合法性论述,显然是其最重要的话语诉求之一。第三,在主流媒介对当代中国的表述中,工业能力是重要一环。引发热议的《超级工程》和《大国重器》等纪录片中,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基建狂魔”的称号成为想象当代中国的重要话语资源。正是这种主流话语和民间叙事的合力,使得工业党在网络文学中得到呈现。
网络文学中的工业党表述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穿越小说中对于科技的描写,这堪称工业党叙事的滥觞。此类文本中,科技和相关工业力量的发展所迸发的伟力,成为穿越者改变世界的“金手指”。比起各个文本在政体和制度设计方面的摇摆,工业化和相关的生产力想象成为表征现代性的核心要素,这一书写在《临高启明》中得到了集大成式的体现。在对科技——工业的发展进行全景式呈现的意义上,《临高启明》以虚拟现实建构了特定宏大叙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党”文本。比起偶发性的、个体性的穿越,临高五百众的“规划式”穿越已经表明了其“工业化”的内涵:这是一个集体性的、具有高度体系性的工业化图景,是一个在虚拟时空里表达历史必然性的总体性叙事。“‘临高集团’的行动意愿,不再是伪装成‘自然正确’的被动偶然,而是长期准备、广泛动员、精心培训、计划有素的‘必然性’实践。”临高八百众所强制推动的工业化进程所表征的高度计划性和集中性,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耦合了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历史,彰显了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图景。
二是当代语境中的工业党叙事。对比以《临高启明》为代表的古代时空的文本,当代语境中的工业党叙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涵。齐澄的一系列作品《工业霸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是工业党文学的代表,其中《大国重工》最具有典范性。文本以作者穿越回1980年作为开始,以工业党视角重新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在故事中,主人公冯啸辰原本是国家重大装备办的处长,穿越后也一路高升,始终以上位者的姿态对国家的发展进行总体思考。小说对于工业化的想象主要聚集在矿山、冶金、电力装备等作为发展基础的重工业领域,体现了鲜明的国家视角。“穿越”的身份恰恰让史实和当下形成一种对比关系,使全文不断进行着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利弊得失的分析和总结。总体来看,全文塑造了众多的工业党形象,并以工业化图景呈现了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其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它自《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小说以来,重续了以官方视角围绕工业化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的努力。这一兼具网络小说的书写形态与主旋律叙事模式的文本样貌,鲜明地呈现了在纯文学愈发趋近于小叙事的文化语境中,网络文学反而承担起宏大叙事之表述的吊诡现实。
如果说民族主义叙事展现了一种消弭历史耻辱的冲动,工业党叙事在于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进行合法化辩说,那么,文明叙事显然是基于当代社会历史图景所进行的宏大想象,这种想象在时间场域中更加具有未来视角。1993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影响广泛,预言了所谓“历史终结”之后新的世界趋向。吊诡的是,一方面,在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图景中,伴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浩瀚图景,“历史终结”的唯西方视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西方价值观的相对衰退,文明得以随着民族国家的视野不断浮现出来。“全球的普世价值没有了,人类世界再度丛林化,各民族国家诉诸文明认同,展开生存竞争。”
与民族主义叙事、工业党叙事始终聚焦于国族内部不同,文明叙事乃是现代性叙事从国族内部走向外部的反映。网络文本中的文明叙事集中在网络科幻小说之中,此类创作从“文明存亡”“文明关系”“文明形态”等视角对于文明进行总体呈现,并与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当代科幻文学发生了紧密的互文关系。早期智齿的《文明》、彩虹之门的《地球纪元》聚焦于文明的兴衰演替;《太阿降临》《修真四万年》等文本展现人类在茫茫宇宙的开拓;《废土》《宿主》等文本则表现了人类在文明毁灭之后的痛苦挣扎与复苏。
与刘慈欣作品相比,这些作品不以科学性见长,但其对于文明的不同表达映射着对于当代文明的总体理解。《废土》《宿主》以残酷的末日生存法则和族群对立,呼应着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而《修真四万年》《间客》等显然具有更为乐观的视野,希望在文明冲突当中寻找到不同文明的共存之道。这些具有未来视野的科幻想象,以另一种方式深入刻画了文明冲突这一当代主题。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是在现代性范畴中出现的,那么,文明叙事理应被视为对于当代世界语境的一种重新想象,是现代性之后的总体性叙事。
总体来看,民族主义、工业党以及文明叙事在时间场域中构筑了一个对当代进行总体想象的连续线索,象征性地表述了中国当代被不断压抑的现代性话语。按照汪晖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和世界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当代话语体系中,新自由主义不断以市场的自由自发状态建构社会历史的“自然进程”,进而对政治话语进行消解。“因此,‘政治化’的核心就在于打破这个‘自然状态’,亦即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以‘去自然化’对抗‘去政治化’。”网络小说对于宏大叙事的重构,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恰恰显示了一种对于历史、现实和未来可能性不断予以发现和创作的建构逻辑,并在总体意义上呼应了当代的政治语境,这是其得以呈现宏大叙事之面貌的根本原因。不过,网络小说交织着新媒介语境的幻想色彩,更深受市场机制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对于其宏大叙事的特性需要进一步深入辨析。
三、个体升华:宏大叙事的精神面向
在从现代性通向后现代的进程中,发生了消费者社会对生产者社会的取代,工作模式的演变塑造了日趋原子化的个体:“在后工业化国家中,后福特主义的经济转型,推动了个人主义化或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模式的发展。”与之对应,这一新的社会样态在网文中得到了呈现。网络小说所建构的异托邦世界变成一个充斥着风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环境,这是对于新自由主义以来的市场化语境的体认。同时,个体的成长也成为一种彻底技术性的升级行为,而摒弃了精神抑或价值指向。在这个意义上看,尽管网络小说文本所建构的“成长叙事”有着宏大的世界观,但其精神内核上却成为一个聚焦和指涉个体欲望的“小叙事”。网文结构由此呈现出一种双面性:一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体化色彩;另一方面则不断生成着关于当代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
这种大叙事与小叙事的结合,构成网络文学的鲜明特点,也深刻揭示了当代消费主义语境和宏大现代性进程并行不悖的现实。具体理解这一问题的话,依然可以从前论中的几个视角着手。在经典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杰姆逊将第三世界文学归结为“民族寓言”。这一“民族寓言”的含义首先在于,对于第三世界而言,始终存在着一个外在的“他者”,即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在这一他者的影响之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展现出一种强烈的应激反应,呈现出相对于这一他者的集体化样貌。而对于进入跨国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而言,此时的文化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导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分裂。“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和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杰姆逊看来,这是西方从马克思式的宏大社会话语,转到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之中。
杰姆逊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时稍显前卫,但却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契合了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一方面,当代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第三世界认知”作为一种集体回忆深刻影响着大众心理,“民族寓言”由此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书写形式。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消费主义的发展同样使得个体与共同体不断分离,并导致网络文学充分消费化、个体化的书写样态,彰显了指向欲望的力比多书写特质。故而,当代部分网络文学既具有宏大的“民族寓言”特性,亦具有鲜明的弗洛伊德色彩。《回到明朝当王爷》较为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故事中,主人公杨凌一方面官运亨通,众美在怀,是达到权力顶峰的人物;另一方面,则是他下江南、平倭寇、定草原,用铁与血洗刷了中原王朝的历史屈辱。作为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回到明朝当王爷》被认为很好地融合了历史和商业,达到了“‘大国崛起’与‘个体圆满’的双重yy”。在这里,文本重构历史的欲望是在个体欲望的驱动之下进行的,文本中所表述的民族主义由此成为个体力比多叙事视野中的空壳。
通过这一例证可以看出,杰姆逊视野中的“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悬浮的能指出现在网络文学中的。它很难摆脱个体欲望叙事的窠臼,但依然可以生成网络文学向宏大叙事迁延的可能性。在《宰执天下》《一品江山》等文本中,尽管依旧以个体欲望进行叙事,但严肃的历史趣味建构了更为真实的宏大叙事视野。当然,“民族寓言”作为一种“第三世界意识”,在历史穿越文本之外的作品中也有着鲜明体现。例如,在猫腻的《将夜》中,从守卫边疆到保卫国家,民族主义话语成为“情怀”的重要方面;在《完美世界》《人道至尊》等玄幻修仙小说中,“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侵略”的故事设计影射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总之,作为“民族寓言”的叙事模式在网络小说世界观中的广泛出现,显现的正是杰姆逊意义上“现代”与“后现代”相互混杂的叙事景观,表达了网络文学“小叙事”与“大叙事”之间的交错联系。
在网络文学中,个体的欲望化叙事是其起点,“技术化”是其表达方式。所谓技术化,是指用纯粹的技术视角来应对问题。在现代性的历史上,技术是对于科学和机器大工业的总体指认。尼尔·波斯曼将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围绕市场意识、工厂制度、科学发明而生成的对于技术的膜拜意识称为技术统治论,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从技术统治论到技术垄断的变化,其标志在于以管理科学为代表的技术原则对于思想和文化的统治:“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进行思考,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在这里,波斯曼关于技术的阶段性划分隐约对应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思想裂变:现代性的技术原则是总体性的,是基于改进生产力的社会建构;后现代则呈现出技术对于具体的个人的宰制,即技术成为个体的行为方式和准则。
当代网络文学对于技术的表达,深刻地展现了后现代语境中的技术观。一方面,大量的网络小说,如玄幻修仙小说、官场小说,都成为一种目的论视野中的技术操持行为。在《凡人修仙传》中,无论是韩立趋利避害的“韩跑跑”性格,还是其几乎完全借助法宝和灵药的“唯物主义修真”方式,都鲜明地表达了个体生存的技术化倾向。在《侯卫东官场笔记》中,文本彻底放弃了传统官场小说的价值指向,详细地展示了侯卫东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的官场生存之道,从而使文本变成一个“官场升级指南”。当然,这种技术化倾向亦表现在网络文本的具体内容中。在黎杨全看来,玄幻小说流行的所谓“老爷爷”以及相应的“随身流”,对应着当代个体依托于网络和大数据的技术化生活。“而网络小说中这些不断兴起的‘随身流’,实际上正是网络、系统、机器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缩影。”
按照鲍曼的观点,在失去现代性所创建的集体化图景的当代语境中,依托于市场的专家机制,是个体解决现实矛盾的核心途径,这构成了个体生活彻底“技术化”的生动写照:“现在,用以形成真正的个体生活环境的是专家知识和管理的技术。”以此推之,网络文学中大量攻略类、指南式技术文本的流行,正是这一现实的文本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党文学的作用恰恰在于重新呼唤现代性以来总体性的技术叙事。比起个体“技术”叙事视野的狭隘和价值的匮乏,工业党叙事重新赋予技术以历史视野,将沦为工具理性的技术重新呈现为基于唯物主义视角的科学话语。故而,如果说利奥塔式的后现代理论对于科学话语的解构使之成为个体化的技术碎片,那么,工业党叙事则力图从个体性上升到集体性,从技术回归到科学。正是这种从后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追溯,体现了当代中国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现代性的独特思想路径。
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绞缠,在时间视野中也有着清晰的呈现。对于现代性而言,鲍曼式的“造园冲动”昭示了现代性必然存在一个乌托邦视野,这一“乌托邦”想象广泛地存在于现代性社会实践和话语想象中。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否定,除却德里达、利奥塔式的理论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奥斯维辛等政治苦难来论述“解放叙事”的失败而获得的。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的“乌托邦”书写转而成为一种走向反面的“恶托邦”书写,《1984》和《美丽新世界》正是其鲜明反映。在这里,无论是乌托邦叙事还是恶托邦叙事,显然都具有以未来作为时间尺度的宏大叙事视野。按照邵燕君的说法,网络文学中广泛存在的“异托邦”叙事,来自后启蒙语境中精神空虚的个体所展开的自我幻想。它不仅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一种小叙事,而且不再具有通向未来的时间性。事实上,“异托邦”小说的文体结构往往是空间性的,通过空间的层次划分映射当代的科层体制和自我上升的路径。故而,“异托邦”文本体现的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特质:通过对于当下的沉迷消弭时间和历史感受。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叙事恰恰是通过对于时间感和未来意识的重现来重拾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一方面,“文明”这一范畴超越了现代性的主体民族国家,文明的存亡问题亦是基于“文明冲突”这一当代问题视域而建构。另一方面,文明叙事并不拘泥于乌托邦模式或恶托邦模式,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的意识形态之外寻找历史新的可能性。例如,在《三体》中,刘慈欣展现了一个人类文明乃至全宇宙走向毁灭的可怕想象,这一想象被重新追溯为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反思,这些反思从另一个层面重新激活了现代性的相关话语。
网络小说的文明叙事延续了《三体》的思考,《修真四万年》对此有着较为出色的呈现。一方面,这一文本在转换地图的空间模式中添加了时间要素,使得修真行为被演绎为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的历史迁延,从而超越了一般“异托邦”小说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文本中对于多方势力的呈现,表面上体现为“共和模式”“帝国模式”,乃至《1984》式的恐怖洗脑模式,实际上则有着更加丰富和繁杂的内核。文本对于“文明之争”的呈现,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上,更上升到道义和理念之争。在文本的最后,主人公和“洪潮”的冲突不仅仅是政治形态之争,更是时间意识之争:洪潮想要人类重回过去,而主人公即使面对可怕的危机,也要为人类文明寻找面向未来的新的可能性。在这里,《修真四万年》与《三体》尽管有着理念的差异,却都鲜明地表达了一种不同于乌托邦、恶托邦,同时也超越了自身异托邦形态的通向未来的宏大历史视野。这种从空间向历史的延展,是网络文学从小叙事走向大叙事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作为现代性的话语冲动,当代宏大叙事呈现出现实情境与西方现代性——后现代相关理论的不协调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理论引入中国,并对思想界和文学界造成持续的冲击。90年代之后,伴随着市场化的崛起,社会层面上也出现了深刻的后现代特征。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呈现出愈发奇异的“两级”模式:一方面,在愈发依托市场机制的今天,中国广泛出现贝克、鲍曼等人所描述的后现代特征,如“消费社会”“风险社会”“个体化社会”等,并在新媒介语境中出现了被称为“微时代”的症候。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中国重构了“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等现代性叙事;作为对文明冲突论的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彰显了现代性之后宏大叙事的可能。
这一现实与理论的不协调进一步反映到文学创造中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主流文学、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三种模式。自21世纪以来,诸如革命文学、反腐文学等主流文学模式有着鲜明的宏大叙事样态,却遭遇了文化感召力不足的问题。就纯文学模式而言,其书写显然与以城市为核心的现代性进程保持了谨慎的距离,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小叙事”样态。反而是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无论是网络民族主义还是新主旋律电影,都赋予宏大叙事以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如二次元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这一“三次元”话语通过二次元语境来表述一样,当代宏大叙事的症结在于,它无法直接连通现实语境构建宏大叙事,而需要在“小叙事”的个体欲望话语、情感叙事中进行转译和勾连。
作为新媒介语境所塑造的大众文化,网络文学承接了宏大叙事的可能。不过深受消费主义、新媒介文化影响的网络文学亦有着力比多书写、二次元趋向等鲜明的小叙事特性。网络文学中宏大叙事的建构,一方面显现了当代宏大叙事的衰弱:在关联网络小说书写形式的前提下,它不断被欲望化、虚拟化和奇观化,并衰弱为东浩纪意义上的脱离普遍主义和真理性的纯粹叙事方式。但另一方面,网络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又不断构成对于当代中国的象征性表述,填充着当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意义空间。网络小说宏大叙事的二重特性,对应着当代中国在现代与后现代、消费主义与宏大政治、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深刻杂糅和分裂,彰显了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层机制。而网络文学的宏大叙事书写,不仅构成了纯文学书写范式上的有效弥补,显现了当代中国语境与文学书写的错位;同时也展现了网络文学对于现实的表征能力,表明了其建构现实主义的深刻潜能。
注释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②戴传江:《论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的利奥塔后现代主义思想》,《江淮论坛》2003年第5期。③管宁:《后现代突围:非道德化的个人叙事》,《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④被纳入这一视野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具有显著寻根文学特质、彰显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品,如《白鹿原》《古船》等;第二阶段是新世纪以来重新追求“史诗性”的一系列作品,代表作有《秦腔》《笨花》《圣天门口》《受活》等。⑤[德]黑格尔:《美学》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7页。⑥参见彭少健、张志忠:《概论中国当下文学的宏大叙事》,《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马德生:《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宏大叙事的误读与反思》,《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⑦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⑧[日]东浩纪:《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黄锦容译,唐山出版社,2007年,第8页。⑨⑩[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81页。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大会还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这个施政纲领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显现了中国主体政治层面的现代性气质。参见庄庸、安迪斯晨风:《浅析网络文学中的二次元要素》,《网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房伟:《论现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内部线索与呈现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参见陈国战:《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文化研究》2012年第10期。彼时较为有影响力、可被归入“晚清救亡流”的网络小说还有《赤色黎明》《篡清》《铁血帝国》《我是军阀》等文本,这些文本的政治理念相差甚远,唯一的共同点是拥有以晚清为背景的“救亡”主题。[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张学锋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26页。吉登斯追问现代性的核心是资本还是工业化,这一说法从反面验证了工业化的重要地位;贝克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工业社会,后现代则是一个具有自反性特征的风险社会;鲍曼认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经历了“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型。参见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东方学刊》2018年第8期。赵文:《“工业党”如何在改造“古代”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临高启明〉的启蒙叙事实验》,《东方学刊》2019年第12期。刘复生:《文明冲突几乎成为当代文艺主线》,《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日。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7页。[英]保罗·霍普:《个体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邵燕君认为此类文本属于对宏大叙事进行补偿的“拟宏大叙事”,本文认为,“拟宏大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小叙事。[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4—235页。当代中国一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另一方面依然处在西方所主导的秩序准则之中。在这一语境中,“第三世界意识”并非一种显在情感,而是一种蛰伏的历史记忆。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8页。在杰姆逊的观点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乃是西方社会不同阶段所塑造的文化生态,不过在中国语境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和分离,这一点在文学层面体现最为显著。[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57页。在网络官场小说兴起之前,主旋律的官场小说侧重于对腐败的批判,例如《抉择》《大雪无痕》《人间正道》;而知识分子官场小说侧重于描述权力对于人的异化,例如《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黎杨全:《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23页。参见陶东风:《理解微时代的微文化》,《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3期。参见林品:《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