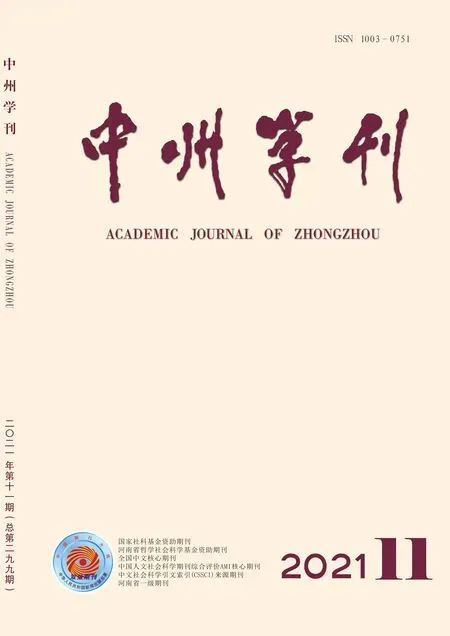叶燮“陈熟生新”思想的现代阐释*
杨 晖 罗 兴 萍
叶燮是一位具有历史感与现实感的诗论家,他坚持以“变”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体现了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就“陈熟”与“生新”问题,他以历时性的视角,从“相续相禅”与“踵事增华”两个层面,分别阐释了“前”与“后”、“旧”与“新”之间的流变与关系,成为传统诗学中对这一问题思考最全面的诗论家之一。对叶燮“成熟生新”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对于我们认识传统诗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要处理好“陈熟”与“生新”之间的关系,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问题无法回避。连续性是指新与旧之间的相关性,侧重连续,关注它们的共同性。非连续性是指新与旧之间的异质性,侧重断裂,关注它们的差异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何者为先,犹如鸡与蛋何者为先一样难以回答。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思考世界来源时,似乎倾向于连续性;但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又多主张“两一”,即对待合一,似乎先有“两”后有“一”,倾向非连续性。事物的演变在于对立双方的不断交替,就历时性角度看,非连续性在先,如果没有这种非连续性的差别,即没有所谓的“新”与“旧”的相异,便无更替可言。所以,就“陈熟”与“生新”而言,要先肯定其“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非连续性本身又包含着连续性的一面。非连续性的双方有差别,但又有相通性,否则就无法成为对立的双方。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回答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时显出差别,但它们都是在回答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体现出相通性来。同理,“陈熟”与“生新”虽然各执一偏,但它们都在回答如何面对“旧”与“新”的关系。诗的演变不是简单的复制,它总是在新的环境下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出现,犹如父母的生命基因传承到子女身上并得到延续一样。历史上的“陈熟”虽已过去,成为历史的记忆,但其生命基因可以通过“生新”得以延续。所以,“新”与“旧”的交替,同时又是“新”对“旧”的突破,这种非连续性同时又显示出连续性来。
我们既要看到“对待”这一前提,一”的结果。“生新”中必有“陈熟”的因素,因为只有这种相通,才可能超越“陈熟”,跨越古今。可见,只有“旧”与“新”的隔阂,才有“古”与“今”之别;只有“旧”与“新”的相通,才可能有“旧”与“新”的合一。理解“陈熟”是为了认识“生新”,通过对“旧”的超越,实现“陈熟”与“生新”的统一,即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
有学者认为,叶燮的“陈熟生新”“其实就是文学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①,或者说“陈熟与生新问题的实质是诗歌的继承与发展问题”②。虽然这些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陈熟”与“生新”的共时性视角,但就历时性角度看,的确道出了问题之根本。叶燮的“陈熟生新”是关于文学演变的问题,与其“因”与“创”、“沿”与“革”的问题相类似。如果将“陈熟”与“生新”置于诗歌延绵不断的演变长河当中来看,似乎既没有静止的“陈熟”,也没有静止的“生新”,所谓的“陈熟”或“生新”都是相对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非连续性中看到连续性,也要在连续性中看到非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叶燮那里,与“陈熟”“生新”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很多。如王运熙等指出的,“源、流、正、变是指诗歌的历史发展,而沿、革、因、创是指诗歌发展中的继承和创造的关系”③。蒋寅指出,“这里的沿、因即继承、沿袭,革、创即变化、创新,是文学史观念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④。可见,在源与流、本与末、沿与革、因与创等过程中,每一次衰落都孕育着新生,每一次新生总会衰落,正是在这种“陈熟”与“生新”的交替中构成了诗歌的演变轨迹。“陈熟生新”是叶燮关于诗歌演变的宏观表达,它包含“相续相禅”与“踵事增华”两个层面。那么,“陈熟”与“生新”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二、“相续相禅”中的“陈熟”
叶燮重视天地古今之变化,《原诗》开篇云:“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⑤正因为如此,朱东润说:“横山之论,重在流变。”⑥张少康也说:“叶燮《原诗》的中心是阐述诗歌的源流发展和演变状况。”⑦综观《原诗》及其诸多诗序可以发现,在他的“相续相禅”中,延续者是“陈熟”,禅让者也是“陈熟”,表现了对“陈熟”的高度重视。
1.“相续相禅”的重心在“陈熟”
如何理解“相续相禅”呢?就“续”的字义,《说文解字》有:“续者,联也。”《尔雅》有:“续者,继也。”就“禅”者,此处多为“禅让”之意。那么,“相续相禅”就是后者对前者的相续,前者对后者的禅让。因为有了“陈熟”,才有“相续”的对象;也因为有了“陈熟”,才有“禅让”的主体。可见,“相续相禅”的重心在“陈熟”。
叶燮是一位主变论者,他虽然强调“生新”,但不忽视“陈熟”。他在《原诗·内篇下》中用了五个“不读……不知……”显示对前者的重视:
不读《明》《良》击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朝诗之工也;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也;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⑧
因先有“不读”的对象,方有“不知”的后果,其结论是唯有“前者启之”,方有“后者承之”;唯有前者“创之”,方有后者“因”之而“广大”之。没有“前者”,就无“后者”,即无“陈熟”就无“生新”。他还特别用“夫惟”两字来强调对“陈熟”的重视。他在《原诗·内篇下》中所说的“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⑨,表达了“前人”与“后人”的辩证关系。正如朱东润所说,“此言谓不学古人,乃正所以深学古人,其意在此”⑩。
叶燮在《原诗·内篇下》中又以“地之生木”为喻,阐释了“陈熟”的重要性。他将诗之演变的顺序以“根”“蘖”“拱把”“枝叶”“垂荫”“开花”为喻,呈现了苏李诗、建安诗、六朝诗、唐诗、宋诗的变化逻辑,再次肯定这层层累进的过程是“从根柢而生”,于是有了“无根,则由蘖何由生?无由蘗,则拱把何由长?不由拱把,则何自而有枝叶垂荫、而花开花谢乎”的一连串反问。
值得注意的是,叶燮曾提到过“陈言”,这是借韩愈“惟陈言之务去”之说,批评时人因无“去陈言”的本事而缺乏创新。叶燮的学生沈德潜对此理解更为清晰,他在《说诗晬语》(卷下)第三十六条中说:“盖诗当求新于理,不当求新于径。譬之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未尝有两日月。”这是借唐人李德裕《论文章》中的“璧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的说法,提出“理”要新,而不当求新于径。用叶燮的“陈熟生新”来解释,就是日月“光景常新”,但本质未变,故能“生”中见“熟”,今对日月,虽有异样,然似曾相识。一生尽对日月,但无生厌之感,乃因语境不同,心情不同,虽有新元素参与,但仍是以前的日月。
徐中玉先生曾在《论陈言》一文中对韩愈“陈言之务去中”作解释时论及叶燮。他说:“在文学语言的创造上,在消极方面要除去‘陈俗’,在积极方面就要追求‘清新’……完全的成熟固不足取,完全的生新一样也无作用,必要从成熟中说话出来的生新才是真正的清新。所以叶燮《原诗》卷三中说:‘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在徐先生看来,“清新”不能离开“成熟”而“故趋新奇”,“完全的成熟固不足取,完全的生新一样也无作用”,“清新”来源于“成熟”。徐先生又从接受者的角度,分析了“清新”之所以被称赞,在于“用人人用惯看惯的一套材料,去安排编制出崭新的东西来”。这里肯定了“成熟”的作用。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叶燮“陈熟”与“生新”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叶燮对明代复古主义只得“陈言”而不得“古人之兴会神理”的创作的批评,与韩愈《答刘正夫书》中“师其意,不师其辞”的说法相通。可见,叶燮提出的“于陈中见新,生中见熟”的思想,正是对“惟陈言之务去”的进一步阐释。
叶燮提出“察其源流,识其升降”,同样显出了“陈熟”的价值。他说:
吾愿学诗者,必从先型以察其源流,识其升降。读三百篇而知其尽美矣,尽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为;……继之而读汉魏之诗,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为之,而无不可为之;……又继之而读六朝之诗,亦可谓美矣,亦可谓善矣,我可以择而间为之,亦可以恝而置之。又继之而读唐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又继之而读宋之诗、元之诗,美之变而仍美,善之变而仍善矣;吾纵其所如,而无不可为之,可以进退出入而为之。此古今之诗相承之极致,而学诗者循序反复之极致也。
叶燮提出古今之诗时变而有诗变,但其间必有“相承”的延续。虽然不必如《三百篇》,汉魏之诗、六朝之诗、唐人之诗、宋之诗、元之诗,但其间的“善”与“美”则是相承的。他批评公安派、竟陵派不能“入人之深”,正在于他们“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而栩栩然自是也。……入于琐层、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焉”。他批评“近代诗家”“一切屏弃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乃是“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涩,真足大败人意”。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陈熟”与“生新”的关系,无视“陈熟”。
2.漂浮中的“陈熟”
叶燮坚持以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看待诗学问题,因此他对“陈熟”的认识不是独立的、静止的,而是整体的、流动的,是将其还原到历史的原初状态,不仅看到局部的变化,更能从整体上认识演变的过程。叶燮认为,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流变过程,“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诗歌的延续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短时段中“盛与衰”的转化,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衰而复盛;二是长时段中盛衰交替,很难说清何者为盛,何者为衰。诗歌的演变正是短时段的局部运动和长时段的整体运动的统一,“是一个局部运动和整体运动交互作用的历时性过程”。
“陈熟”与“生新”的关系与叶燮所讲的“盛”与“衰”的关系一样,就一时而论,有“生新”与“陈熟”之别,但就千古而论,“生新”必来自“陈熟”,又必自“陈熟”而复“生新”。当然,前一“生新”已不等同于后一生新,前一“陈熟”也不同于后一陈熟。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言,“在源流滚滚的诗歌发展长河中,从一个阶段来说,有正有变,由盛而渐衰,而总的趋势则表现为每一次衰落孕育的兴盛”。
叶燮所谓的“陈熟”与“生新”的相互转化也如“盛”与“衰”的转换一样,从短时段看,或由“陈熟”转“生新”,或由“生新”转向“陈熟”;但从长时段看,并没有固定的“陈熟”与“生新”。诗歌演变是“启”与“承”的统一,“承”离不开“启”,诗歌传统需要不断地创新赋予生命力;“启”离不开“承”,诗歌发展离不开对诗歌传统的继承。但“承”与“启”的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诗歌的演变总是“旧”与“新”的冲突与转化,或“旧”融入“新”,或“新”取代“旧”,是关系、比例和价值的“调整”,是“新”与“旧”的“适应”,其“旧”是调整中的“旧”,“新”是“调整”中的“新”,它们通过不断的“适应”在各种条件作用下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是“承”与“启”,还是“盛”与“衰”,都离不开“对待”这一关系。叶燮不仅看到对待的对立统一,而且能把握住对立双方运动的特征,即对待双方属性在正负两极间滑动着,消解了恒定,体现出不确定性来。
其实,诗歌演变中的长时段是短时段的累进,任何短时段都无法摆脱长时段而独立存在。每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处在‘相续相禅’、有‘沿’有‘革’的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孤立的,彼此、前后毫无关涉的存在”。长时段中的短时段才真实,才有意义。短时段只是理论分析的需要,让诗变“突然”停下来,静止不动,这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而真实的情况是每一短时段都处于长时段的过程当中——这才是诗变的原始面貌。
叶燮论诗总是在长时段中认识对象,重视其“节节相生”“息息不停”,将短时段还原于长时段的真实面貌当中,消解了理论上的假设,在“节节相生”中去认识每“一节”,在四时之序中去认识每“一季”。因为,每一节,或每一季中的“生新”必将沦为“陈熟”,而“陈熟”又会孕育着“生新”种子,诗歌在“陈熟→生新→陈熟→生新”的不断交替中演变,呈现了对立双方交替的诗史演进模式。所以,就有了“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这一观点性的表述。
建安风骨慷慨悲凉,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是继“汉乐府”的“生新”之作,开一代诗风,但它又不可能长盛不衰,终将因时代变化,以及诗体自律之需求而流于“陈熟”。诗至六朝,“卑靡浮艳之习”沿袭至唐初,诗坛萎靡不振。唐之开元、天宝又达到鼎盛,有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与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相得益彰,沿着“盛→衰→盛→衰”的模式交替。在这延绵不断的流变当中,建安诗、六朝诗、初唐诗、开宝诗等,谁是“陈熟”,谁是“生新”呢?显然,它们既是“陈熟”也是“生新”,这将随着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既是下一段的陈熟,又是上一段的生新。虽然叶燮是一位诗之主变者,但他以宏观的视野,在“旧”与“新”的关系中不忽略“旧”的重要性,即不忽略“陈熟”的重要性。
三、“踵事增华”中的“生新”
时代在变化,诗体也在变化。叶燮论诗主张“生”“新”“深”,虽然他在“相续相禅”中侧重“陈熟”,看到“陈熟”的功绩,但他诗学思想的主体精神则是在“踵事增华”中的“生新”。
1.“踵事增华”辨析
在讲到创作起因时,叶燮提出“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即有现实感触,方能作诗。他说:“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这里的“熟”与“新”就涉及“陈熟生新”问题。“剿袭浮辞”与“搜寻险怪”都被“风雅所摈”,他列举了上古的饮食器具、音乐变化、古者穴居等,提出“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从宏观上描述了诗演变中“踵事增华”的特征。
“踵事增华”是两组动宾结构“踵事”与“增华”的并列。踵,作名词时表示足跟,《释名》有“踵:足后曰跟,又谓之踵”;作动词时表示步行、继步之义。“踵事”即继步前事,其目的在于“增华”。“华”即繁华,越来越茂盛。“踵事增华”字面的基本内涵是继承前事而越来越繁华。
在诗学上,“踵事增华”大约首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序》。他说:“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增加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冰块增大乃因积水而至,积水越多,冰块越大,“踵事增华”就是“变其本而加厉”。这里的“厉”为形容词,表示“越来越……”的意思,并无贬义,是对以往的超越。
“踵事增华”的这种意思还被其他多处地方运用。如宋人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一书中谈论“敦”的演变过程后说:“因时而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提出这种制器“与时为损益”,“时异则迹异”,认为“若乃敦者,以制作求之,则制作不同:上古则用瓦,中古则用金,或以玉饰,或以木为;以形器求之,则形器不同:设盖者以为会,无耳足者以为废,或与珠盘类,或与簠簋同”。总之,器物随时代演变而越来越精致完美,时代变了,就不能“求合于古人”。“踵事增华”是一种进化论思想的典型表述,重点在“生新”。
“相续相禅”的重心在“陈熟”,“踵事增华”的核心却在“生新”。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卷四曾鼓励诗人要有创新的勇气,他说:“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古人制作,各有奇处,观者当甄别。”叶燮则以“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的立场,执着地追求“踵事增华”中的“生新”。
叶燮认为“踵事增华”的动力,一在于乾坤不息,二在于人之智慧心思之无尽。诗的演变亦然,“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他将诗的演变比喻为人的行路:唐虞(尧舜)诗如第一步,三代(夏商周)诗如第二步,汉魏以后诗如第三步、第四步。在叶燮看来,踵事增华是万物演变的模式,前人“始用”,后人所以能“渐出”“精求之”“益用”。这也如他所说的,自《诗经》以来,“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无可或间也”。这是他主张“生新”的理论表述。
叶燮在《原诗》中还连续用了太虚、工拙、造屋三个形象的比喻,来进一步表述其“增华”的思想。他以“太虚”之喻讲诗的演变,认为汉魏诗初见形象,其外在格式初步成形,但远近浓淡俱未分明;六朝汉魏诗虽已烘染设色,初有浓淡之分,但远近层次无显明分野;唐诗诸多手法分明,能事都已具备;宋诗则更加精益求精,各种手法“无所不极”。叶燮以绘画技巧为喻,讲述诗之手法精益求精的过程:汉魏天然,六朝略备,唐诗大备,宋诗精致。他又以“工拙”为喻来讲诗歌的艺术追求,认为汉魏诗工中见拙,拙中见工;六朝诗工者为多,拙者为少,能从工中见出长处,拙中见出短处;而唐诗可以工言之;宋诗则有意求工求拙,但反对以此作为论诗之优劣。诗之优劣,从艺术追求上讲,渐渐走向精致化之路。他以“造屋”来比喻诗歌结构的发展,列汉魏、六朝、唐诗、宋诗为节点,结合前两个比喻中由不分而至分明、由拙而工,认为诗之演变如造屋之过程,由宏大而至精细,这是“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太虚、工拙、造屋三个比喻表现了叶燮对诗之演变的基本看法,即他所说的“变本加厉”,“以渐而进,以至于极”的“踵事增华”模式。正如蒋寅所言,叶燮所说的“踵事增华”是文变的合目的性,这为进化论文学发展观提供了一个矢量。
叶燮认为“生新”是诗歌演变的必然。他说:“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他从创作因触而发和欣赏之接受过程两个方面分析了“生新”的合法性。就创作而言,诗变系乎时事,触的情、景、事不同,创作也不同;就欣赏而言,“初见”尚好,“再见”不击节,“数见”不鲜,“陈陈踵见”则遭人“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从接受方面提出“生新”的必然性。
他进而以日常生活的实例论述诗变的思想:
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铏,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为惊喜;逮后世臛臇炰鱼脍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铏之庖进,可乎?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宫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鏽而木绨锦;古者俪皮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
这里从古之饮食器具、音乐、穴居等三个方面,再次论证了诗变的合理性,自然得出“生新”的合理性,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诗体、语体和风格方面的演变轨迹“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新”相通。
总而言之,叶燮并不忽略“陈熟”。但相比而言,他更重视“生新”。这种重视是贯穿他整个诗学思想之始终。
2.重视“生新”的诗歌批评
叶燮重视“生新”,不仅有较强的理论表达,而且将其作为诗歌批评标准。纵观他的批评活动,大凡有“生新”者都给予肯定,这形成其诗评的特色。他这样描述诗歌的发展演变:
汉苏李始创为五言……,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一一皆特立兴起。……宋初,诗袭唐人之旧……苏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
叶燮以“变”为核心来描述历代诗歌创作的轨迹,将“生新”元素多者,视为“大变”,少者视为“小变”。其中所列的代表人物,都是有所创新的,鲜明地体现出他诗歌批评的标准。这是他诗学观念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中国诗歌史上,叶燮最推崇杜甫、韩愈、苏轼三人,正是因为他们诗歌创作中的“生新”。他认为“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是因“惟神,乃能变化”,也就是能“生新”。叶燮对杜甫评价最高,说杜诗“包源流,综正变”,不仅具备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等“陈熟”的基因,而且“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更有“生新”元素,是“陈熟”与“生新”的统一,其影响之大“无一不为之开先”。叶燮认为杜甫之所以能别开生面,是因为他有“胸襟”。因其“胸襟”而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所以题材上能“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因其所遇而得题材,因其题材而抒发其情感,因情感而形成诗句,独开生面,“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叶燮对杜甫推崇之至,有“可慕可乐而可敬”的赞扬。
叶燮认为韩愈诗为唐诗一大变,“用旧事而间以己意易以新字者”,“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直接影响到宋代的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形成“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的生面目。虽然在当时韩愈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但“二百余年后,欧阳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韩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开启了“思雄”的生面目,连俗儒都能看到“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
叶燮也非常推崇苏轼,因苏诗为“韩愈后之一大变”。他认为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常一句中用两事三事者,非骋博也,力大故无所不举”,“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形成其“无处不可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入不得,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骂,四时之气皆备”的生面目。
叶燮之所以赞扬这三家诗,正是因为他们都开生面,有“生新”的创举。如蒋寅所说:“叶燮更具体地阐述了三家‘大变’和诗史背景,变革方式以及历史意义,显出独到的批评眼光。杜甫承先启后,不仅集前代之大成,更开启后世无数法门;韩愈惩于大历以来的成熟,一变以生新奇奡,遂发宋诗之端;苏东坡则尽破前人藩篱,开辟古今未有的境界,而天地万物之理事情从此发挥无余。”
叶燮用“河流之喻”来论说诗之演变。他说:“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出,虽万泒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他认为,诗之演变,就其源头而论,不同的是源,相同的是“皆朝宗于海”;就流而言,不同的是“经行天下”“忽播为九河”,相同的是“俱朝宗于海”,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陈熟”与“生新”的角度看,河流是由无数的波浪聚成的,后浪推前浪,也如“陈熟”和“生新”是互为前提、相互生成的。诗之变如一波水浪,诗的演变历史由很多这样的水浪组成,当一个水浪走向衰亡时,它便会被另一个水浪所替代。诗演变的转折点既是“陈熟”的结束,也是“生新”的开始。它不是新的替代旧的,而是“新”的包含了“旧”的,是“旧”与“新”的统一。
叶燮诗论中的诗歌发展进程具有历史延续性。他在探究诗歌的源流、本末、沿革、因创、正变过程中,将孤立的二元相互链接,融入整个诗歌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前者“禅让”并“相续”于后者,后者承接前者,踵事增华,形成正负二元交替的诗史演进模式,诗的演变就呈现出一个动态的、浑然的、互动的整体。
杨鸿烈在谈到中国诗的演进时,对持进化论观点的叶燮评价颇高:
诗的退化说——中国是崇古思想最发达的国家,这种说法在诗里自然很多,但这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要推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著者从诗的本质,和心理学方面观察都是部分的承认,但章先生要用人力来复古便是发可笑之论——并且从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能不承认诗是进步的。诗的进步说——这说在中国最是凤毛麟角——著者所引的只有元稹、都穆、方苞、吴雷发、袁枚、叶燮六人,叶燮的说法最详切明尽——叶燮正确的历史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应该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杨鸿烈肯定叶燮在《原诗》中表达的“增华”思想,并给予大量的引用,说“这样正确的历史观念不只有中国诗学思想发达史上提上一笔,就是在文化思或思想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呢”,表达了对叶燮的推崇。
中国传统诗学提出“陈熟生新”问题的时间虽然较迟,但它却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诗学诞生之初,人们似乎都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叶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前人更广阔、更深入,丰富了传统诗学的内涵。他一方面以历时性的角度,从“相续相禅”与“踵事增华”两个维度详尽地分析了“相续相禅”侧重“陈熟”,“踵事增华”中侧重“生新”的意义,肯定了只有在“陈熟”与“生新”的“相济”中才能赋予诗歌创作以生命和意义;另一方面他还以共时性的角度,从“对待”之不确定入手,消解以往“陈”与“生”、“熟”与“新”的优劣之争,将其还原到诗歌真实的、现实的创作演变链条中,肯定“陈”“生”“熟”“新”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它们之间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相济”状态。
总之,叶燮的“陈熟生新”思想已超出了简单的进化论或退化论的层面,突破了狭窄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完整的、延绵不断的生命体的成长过程。他对诗歌创作演变过程的描述和对其演变逻辑的探索,使诗歌艺术在时间轴上得到敞开,为后人阐释“陈熟生新”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②叶燮、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孙之梅、周芳批注,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3页。③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261页。④蒋寅:《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78页。⑤⑧⑨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霍松林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4、33—34、34、34、243、35、44、44、3、8、5、45、6、6、33、5、5—6、4—5、19、8、17、17、17、50、8、50、28、8、51、9、50、6—7页。⑥⑩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76页。⑦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徐中玉:《论陈言》,《国文月刊》第7册,1948年。蒋寅:《清代文学论稿》,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26页。沈德潜《叶先生传》有“先生论诗,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陈旧浮浅语须扫而空之。”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29页。王黼:《宣和博古图》,诸莉君校,上海书店,2017年,第296—297页。谢榛:《四溟诗话》,宛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07页。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520页。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11、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