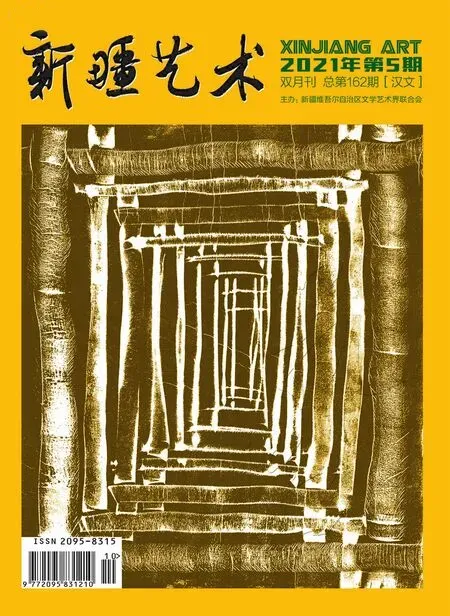摄影何以艺术?
——中国早期摄影实践中的“艺术”之辩
□ 邓立峰

刘半农作品《半农谈影》封面
自现代摄影技术诞生开始,摄影与艺术的关系就受到了西方摄影家和评论家的关注,虽然长久的讨论没有带来定论式的结果,但却依然引导着摄影实践者一次又一次带有艺术自觉的尝试。而在中国,关于摄影的“艺术”之辩,直到20 世纪初期才开始引人注目。
作为早期摄影艺术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以“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闻名的刘半农在他1927 年出版的《半农谈影》中谈起摄影中的“艺”和“术”的关系,把摄影照片分为“有极大用处”的“写真照片”和有“写意”功效的“美术照片”:“写真照片只须有得一个‘术’(technique)字,而这个字却必须做到一百分;写意照相于‘术’字之外更须有一个‘艺’(artistique)字——不过,‘术’字不必到一百分,能有八九十分就够了,‘艺’字却是不能打分数的:能有几分就是几分。”①
不难发现,刘半农将摄影“写真”的机械记录特性和“写意”的主观创造取向分离开来,为摄影的艺术性认知确立了一条典型的认识途径。而这种关于“写真”和“写意”的分野,也在中国早期摄影实践中影响深远,主导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摄影艺术取向;但与此同时,一种基于“写真”追求的艺术探索也随着社会审美形态的演变而慢慢发展起来——在中国早期摄影实践中,“写意”和“写真”的分野既带来了对于摄影艺术创作的不同体认,也使两者相互融合,对建立于摄影本体语言的艺术创作进行了探索。
当然,要了解这种探索的发展路径,我们首先要回到“美术照片”。
一、从绘画到摄影:视觉艺术的认知传承
为摄影冠以“美术”之名,是摄影实践者最早的艺术性尝试。众所周知,早在19 世纪中后期,西方画意派摄影家就利用柔焦镜头、布面相纸、低反差、图绘及刮痕等工具和技巧,甚至套用印象派、象征派等流派的绘画风格,制作具有绘画意境的画意照片,以此为摄影争取艺术地位。②而在中国,早期被认为是“艺术照片”的摄影作品也多是以仿画的形式来创作的,并被冠以“美术摄影”之名。
在汉语中,“美术”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语,据学者、书法家陈振濂考证,“美术”一词在20 世纪初由欧洲经日本传入中国。最初传入中国时,“美术”被用于指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之意,涵盖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但从1912 年开始,“美术”一词确立了其代指绘画、雕刻等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的“现代立场”。③在1927 年出版的《美术概论》中,“美术”被用来指代绘画、雕刻和建筑等“诉诸于视觉的空间艺术”。④因此,在具有艺术自觉的摄影行为开始逐渐盛行的19世纪20 年代,特指仿画风格的“美术摄影”照片的大量出现,体现了绘画对于摄影艺术认知的强烈影响。
可以想见,长久以来作为视觉艺术的主导范式,绘画自然是人们谈起视觉艺术时最先考虑到的艺术形态,这种主导地位,首先影响了人们将摄影纳入“艺术”框架进行讨论的过程。
从19 世纪40 年代开始,摄影术就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也逐渐开设了大大小小的商业照相馆。但是,直到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才开始大范围讨论摄影和艺术的关系,这与早期摄影跟中国传统绘画“极不相似”有关。有学者认为,最先出现在中国的商业摄影照片以写实的现实景象拍摄为主,这跟中国的写意绘画传统相去甚远,而古典西洋画中,摹写自然是其重要主题,因此,不同于西方,在中国,人们很难将机械写实的摄影技术与“艺术”观念连结起来。⑤当然,反过来看,在人们廓清视觉艺术范畴的过程中,有了绘画艺术的参照系,摄影作为视觉再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自然可以同绘画一样进入到“艺术”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和定义,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容易引发摄影家的艺术自觉行为。
而以仿画为追求的画意摄影,就是摄影尝试进入“艺术”框架的关键一步。
之所以最先选择以模仿绘画风格的方式来制作“艺术照片”,除了因为绘画长期占据着视觉艺术的“霸主”地位,恐怕还与人们对“艺术”概念的理解有关。
中国传统“艺”的观念,既表现为内含“智巧”意义的“实践技艺”,也表现为“契合性情”的“经验才艺”,前者“富有绝妙尚智的工匠精神”,后者“涵泳创造生命的人文精神”。⑥随着社会生产的精细化,两种“艺”的观念也开始分化,并逐渐形成了“技”与“艺”的对立,而“艺”的观念则更加强调主观审美性和精神内涵。
由此,处于宰制地位的绘画也更倾向于强调“艺”的人文精神内涵,其极致表现,便是向“精致”方向发展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⑦正如南朝宋画家宗炳所言,山水画成为了山水、画家和观画人三者产生精神共鸣的场域,而这种场域的形成,自然需要画家和观画人共同追求某种强调主观“意会”的审美情感基础。
长久以来对于“涵泳创造生命的人文精神”的艺术观念的吸收及传统文人画成熟的表现方式,使尝试将摄影纳入艺术框架的实践者首先选择了仿画的表现方式,因此,“美术摄影”成为中国早期摄影艺术实践的主流。
二、从“美术摄影”到“集锦摄影”:以成果为导向的“意境”生产
今天再来回看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术摄影”,我们会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主题或元素。以“水中孤舟”这一表现元素为例,在此时的“美术摄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渔舟唱晚》(周瑟夫摄)、《晚归》(徐苹萍摄)、《水乡》(胡伯洲摄)、《丝丝柳线系不住归心》(高奎章摄)等一众主题相似的摄影作品。
当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相同主题的文人绘画,如宋马远《寒江独钓图》、宋夏圭《西湖柳艇图》、元代吴镇《芦滩钓艇图》、清查士标《清溪放艇图》等等。以“水中孤舟”为描绘元素的绘画,或者表现人与山水一体的浑然交融,或者体现深邃的人生况味,它是传统绘画的重要主题。而随着“美术摄影”生发出的写意追求,它也成为此时摄影艺术所表现的一大主题。除了“水中孤舟”,类似“梅兰竹菊”、“高山苍松”、“湖光山色”等传统文人画主题均成为此时“美术摄影”拍摄的“热点”(如陆祯芝拍摄的《幽香》、敖恩洪拍摄的《白云苍松》、金承斌拍摄的《石投》等)。
除了表现元素和主题的承袭,“美术摄影”对传统绘画技法的模仿也是摄影者追求画意的一大体现。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郎静山的“集锦照相”。
所谓“集锦照相”,是指通过后期技巧,将不同底片上的元素合成在一张照片上的摄影技术。我们可以发现,“集锦照相”是以制作技巧来命名,但从郎静山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集锦照相”所具有的画意美学指向。在《论集锦照相》中,郎静山写道:“吾国历来画家之作画,虽写一地之实景,而未尝作刻板之描摹,类皆取其所好,而弃其所恶者,以为其理想之境界,不违大自然之正常现象耳。摄影则受机械之限制,于摄底片时,不能于全景中而去其局部,而往往以地位不得其宜,则不能得适当角度,如近景太近则远景被其掩蔽,远景太远则不足衬托近景,常因局部之不佳,而致全面破坏,殊为遗憾。今摄影集锦适足以补救之,亦即吾国画家之描摹自然景物,随意取舍移置,而使成一完美之画幅也。”⑧郎静山从中国传统绘画中得来于一幅画中“取其所好,弃其所恶”的技巧,将不同的景物放入一张照片之中,完成“完美之画幅”。

胡伯洲作品《水乡》刊登于1931 年出版的《好友佳作集》中

《松荫高士》 郎静山
在这“随意取舍移置”的过程中,郎静山对传统文人画技法进行了移植。比如,他运用了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技法,为整个画面创造多个平等的观看视角,在画幅的局部,每个视角都可以在方寸之间形成各自的透视关系。也正是对散点透视技法的运用,传统中国山水画才能体现高远的辽阔境界。郎静山将不同底片上的景物“移置”在一张照片上,从而突破了摄影因技术特性而带来的焦点透视的“天生缺陷”,使自己的山水照片有了恢弘的气势。同时,郎静山还大量运用“留白”的技法,塑造了其“集锦照片”独特的文人意趣。
“集锦”的艺术观念,完全抛弃了塑造艺术作品时的摄影本体语言,抛弃了这一现代工具的主体价值,而确立了以“成一完美之画幅”为目标的结果导向式追求。这种追求将照片视为最终的呈现载体,忽视了摄影这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行为特征和载体特性,简单来说,相比于最终产出成果的艺术形式,制作者更在乎成果的精神指向和审美形态。
而对于20 世纪早期的视觉艺术家来说,这种精神指向和审美形态更侧重于传统艺术所讲究的“意境”。为了达成这样的“意境”,刘半农探讨了影像“清”与“糊”的制作标准:“至于写意照片,却要看作者的意境是怎样:他以为清了才能写出他的某种意境,那就是他的本事;他以为糊了才能写得出,那也是他的本事。”⑨而摄影家王劳生则利用“操纵的手术”来达成自己的效果:“我们用十二分的审慎,观察而裁剪着每张底片,择其最佳的画面,然后再经放大而制成照片。在放大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用操纵的手术,补救底片受光的过多或不足。”
由此可见,此时的美术摄影家偏重于生产“意境”,摄影成为单纯追求“写意”的工具。
三、从意境到构图:在摄影行为中探索摄影本体语言
对于“意境”之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学者叶朗指出,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往往都不会注重对具体对象的逼真刻画,他们追求的是把握作为宇宙万物本体和生命的“道”,要把握“道”,就要突破具体的“象”,“因为‘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而‘道’是无限的”。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⑩
从叶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理解“意境”追求对美术摄影家在制作照片时运用绘画技巧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此时有越来越多的摄影实践者开始注重体现具体的“象”,将镜头对准日常的拍摄对象。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20 世纪早期的摄影家在追求摄影艺术“意境”表现的同时,也开始基于摄影技术和摄影行为本身的特征,从日常生活逻辑中发现照片的艺术感。
而其突破口,仍然是拍摄对象的选择。探究当时在通俗画报中被冠以“艺术摄影”的照片,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美术照片”中大量出现了以往中国传统绘画所不曾出现的对象和主题:表现女子娴静美好的肖像摄影(如霁明拍摄的《女画家关紫兰》、陈嘉震拍摄的《黎灼灼》),表现“力与美”的人体摄影(如陈传霖拍摄的《曲线》《晨操》《试腕》、丁升保拍摄的《含羞》)、表现线条与光影之美的建筑摄影(如卢毓拍摄的《都市之寂》、金哲悟拍摄的《午》)……当然,这些新出现的拍摄对象、主题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传入中国的西方摄影的启发(比如大量刊登在通俗画报上的西方人体摄影),但不能忽视的是,此时的摄影家也将自己的镜头对向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对象(比如农家畜养的家畜、农人劳作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摄影实践者也开始利用摄影技术的本体语言创造艺术感。早在1927 年出版的《半农谈影》中,刘半农就写到了视觉艺术中“光”的作用:“光是画的生命……在光的研究上,总要顾到‘参差’与‘调匀’两件事。所谓参差,是说画面上应当有黑处,有白处,不能一套板的平均;所谓调匀,是说画面上虽然有黑处,有白处,而这黑与白间的精神是融合的……”⑪利用光线的变幻来塑造空间感和“参差美”,是绘画和摄影都会用到的手法,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光线运用较为单一,侧重以着墨的浓淡来描绘简单的明暗对比。

穆戈龙拍摄的《日出而作》,1934 年出版
相对来说,摄影的光线处理方式则丰富很多,这也是摄影技术所带来的独特优势。很多摄影家也利用了这一优势,到了20 世纪30 年代,出现了许多以光线变幻体现艺术感的照片。如关紫翔所拍摄的《静物》(刊登于1930 年第483 期《北洋画报》),瓷杯和陶罐在木桌上投下了大小不一的阴影,形成了一种建基于自然差异的秩序感;穆戈龙拍摄的《日出而作》(刊登于1934 年出版的《黑白影集 第一册》),利用逆光剪影的效果突出了工人劳动时的场景。
除了利用摄影技术特性所带来光线处理技巧,此时的摄影制作,也不再一味地追求柔焦的效果和后期的“修图”,而更加注重利用构图来拍摄更具形式美感的照片。当时一些论者注意到,相比于绘画在构图、光线、色彩、笔触等方面的技巧,“摄影的技巧只有构图与光线两件”。⑫这样的论断虽然并不成熟,但也让很多拍摄者更注重取景时的构图。“因了光线和构图的适宜,常常有成为一张很美好的作品的可能。”⑬而一些以形式感和秩序感为美学追求的照片开始多了起来,比如郎静山拍摄的《状元红》、宋一痕拍摄的《结构》、胡君磊拍摄的《群舟》等等。
如果说侧重于模仿和修饰的“美术摄影”是以成果为导向的“意境”生产,更加侧重摄影技术特性本身所造成的艺术效果的摄影则更凸显摄影本体的行为,这是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艺术”生产,它更关注摄影行为的本体意义和创作价值,也更加注重对摄影本体语言的探索和思考。正是因为更加注重摄影技术和摄影行为所能带来的艺术呈现,摄影艺术的主体地位才开始确立起来,也使摄影慢慢脱离由绘画所设定的视觉艺术框架。
四、从“写意”到“写真”:纪实影像中“真”的灵魂
中国早期摄影实践者对摄影本体语言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在20 世纪30 年代中期,这样的探索更进一步,而这“更进一步”的标志,是“写真摄影”的艺术化。如前所述,刘半农笔下的“写真照片”虽然“有极大用处”,但并没有“写意照片”那样的意境。然而,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出现的以战地摄影、人类学摄影为代表的“写真照片”,在“有极大用处”的同时,摄影家也为其赋予了“意”,更加凸显其艺术品质。
当然,从摄影诞生之初,它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写真”,人们透过镜头满足的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欲望,而对于“真”的不断追求也是促进摄影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用于自我留影和社交目的的商业“写真”摄影,同时,很多外国摄影家和旅行家也将在中国拍摄的纪实照片制成相册或明信片、画片,但在19 世纪,把“写真”同审美联系在一起是难以想象的,人们更愿意将纪实照片与“实用”、“技术”等联系在一起。

张印泉《力挽狂澜》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虽然画意摄影是“艺术摄影”的主流,但仍然有一些摄影实践者把镜头对准现实生活,拍摄一些过往看来毫无美感可言的对象。到了20 世纪30 年代,更多的摄影家由从事“写意摄影”转向了拍摄“写真照片”。其中,张印泉是典型代表。张印泉出生于1900 年,幼时受到系统的中国画训练,19 岁时开始迷上摄影,受当时画意摄影风气的影响,拍摄了很多“美术摄影”照片。但从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开始,张印泉开始转换自己的风格,拍摄了以《力挽狂澜》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应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照片。
张印泉以摄影家之眼做出的风格转变,为他的纪实摄影拍摄赋予了浓厚的艺术气息。而抱着人类学考察目的拍摄照片的庄学本,则在边疆的考察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人类学照片。
庄学本在行走边疆的过程中,拍摄了很多以西部人民肖像和生活场景为对象的照片。评论家李媚这样形容自己看到庄学本肖像照片时的感受:“搜寻记忆,似乎还没有哪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的这些作品一样对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动。”李媚认为,庄学本的肖像摄影有一种“自我的消失”的境界。⑭的确,在早期西方的人类学照片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既是照片中表情呆滞、类似于标本的被摄者,也是可感受到的冷漠的、出于研究目的而留影的拍摄者。但在庄学本的照片中,我们感觉不到来自“他者”目光的凝视,无论是个人的肖像照片,还是群体的生活、行为照片,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拍摄者对被拍摄对象的感情和尊重。也正是由于这种充斥于影像的人文关怀,使其照片充满了感染力。

庄学本西行时拍摄的人像
之所以可以从庄学本的照片中体会到这样的人文气息和人道关怀,大概与他长期行走于边疆的经历及其与边疆人民的深入交往是分不开的。其实,在早期,庄学本也经历过摄影训练,并拍摄了一些具有“美术摄影”印记的照片(比如《陶工》和《桃关朝岚》),但在他踏上人类学考察行程之后,则为纪实摄影照片带入了艺术美感。
这种美感的体现,已不再靠“画意”,也不只靠“构图”等技巧,而更靠“写真影像”中所体现的“真”的灵魂,它使影像意义从画面上的拍摄对象延伸开来,也使影像本身充满了审美张力。凝视庄学本的摄影肖像,仿佛可以从被摄者的眼眸和神态中体会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建基于“真”的艺术感,也表现在沙飞、方大曾、王小亭等人的战地摄影之中。
说起纪实摄影艺术范式在20 世纪30 年代的转变,当代论者往往会着重提到当时社会环境的转变。例如,说起张印泉由画意摄影向纪实摄影的转变,孙慨认为:“风格的转向并非一蹴而就。个人生活轨迹的转变、国家政治的变局以及民族危机的影响,都可能是重要的触因。但在30 年代,摄影界人士在国难深重的时代面前,针对摄影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功能展开的理念之争,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⑮的确,随着当时国家危机的日益加剧,通过艺术进行社会改造的观念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它当然也会影响到艺术家们的创作。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审美形态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传统社会的现代性转变,带来的不只是社会景观的变化,也使占视觉观看主流的艺术形式出现了转变,大肆出现的通俗画报取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绘画,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视觉产品,审美需求的主体也随之开始下移。同时,与“写意”的视觉艺术作品相比,“写真”的作品往往更容易与观者产生感情上的联结,对于那些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摄影家来说,选择纪实摄影是“投入社会洪流”的一个重要渠道。
当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新的摄影观念和实践行为随之出现,但无论如何,中国早期摄影实践中的纪实摄影探索都为中国摄影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
结语
纵观中国早期摄影实践者的艺术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联结摄影与绘画、现实的关系的路径——被推崇为中国古代艺术精华的传统文人画将现实生活抽象化,通过突破具体的“象”而探索无限的“道”;而摄影恰恰是一种致力于对“具象”进行再现的技艺,为了将摄影纳入到艺术的范畴中,早期的摄影家主动进行了“画意”探索,使摄影“美术化”,从而满足大众对其艺术性的想象;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审美形态的变化,摄影家开始对摄影本体语言进行探索,抛弃抽象的“道”,而在“具象”中发现艺术,并进而对纪实影像进行了审美意义的拓展。
如果我们将目光放眼西方摄影史,会发现其摄影艺术追求大体遵循了从表现到再现、再到表现和再现并存的实践路径,从画意摄影的尝试,到将艺术自觉带入他者影像、战地摄影及日常生活的再现,再到基于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的“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并举的路径。与西方摄影艺术的探索过程相比,同期的中国早期摄影显然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精致表现和纪实再现的艺术探索之中,并未展开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表现实践,这样的探讨和实践直到上世纪80 年代才进入更加深入的层面。
注释:
①刘半农:《半农谈影》,开明书店,1927 年版,第14-15 页。
②John Pultz:《摄影与人体》,李文吉译,远流,2012 年版,第84 页。
③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3 年第4 期。
④黄忏华:《美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页。
⑤胡志川:《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美学之争》,《中国摄影》1986 年第4 期。
⑥李建中、孙盼盼:《“艺”与Art:中西艺术观念的比较及会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9 期。
⑦宗炳、王微原著:《画山水序 叙画》,陈传席译解,吴焯校订,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版,第7 页。
⑧郎静山:《论集锦照相》,《上海艺术月刊》1942 年第3 期。
⑨刘半农:《半农谈影》,开明书店,1927年版,第17页。
⑩叶朗:《说意境》,《文艺研究》1998 年第1 期。
⑪刘半农:《半农谈影》,开明书店,1927 年版,第58-60 页。
⑫震球:《摄影与艺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季刊》1929 年第2 期。
⑬《摄影的三派》,《文华》1932 年第27 期。
⑭李媚:《三十年代的目光——庄学本影像的双重价值》,载于《庄学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年版。
⑮孙慨:《中国主流新闻摄影范式的拓殖者:张印泉》,载于《中国摄影大师》,赵迎新主编,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