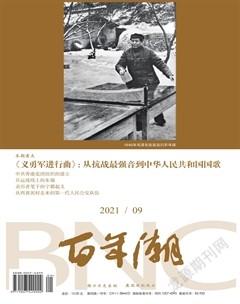我参与的中外政要保健医疗工作
黄宛 罗元生

黄宛
黄宛(1918—2010),我国著名心脏病内科学专家、医疗保健专家,现代心电图学奠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心内科原主任。黄宛一生对医学事业执着追求,无私奉献,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学成回国
1938年我收到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进入协和学习。协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严格求实的学风以及注重能力与实效的严师,都给我留下了良好而又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想来,我在尔后漫长的从医生涯中形成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无不与母校四年的教育有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门,我也中断了学业。1947年10月,在林可胜的帮助下,我申请到医药援华会的奖学金,来到了位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医学院深造。我选择的方向是心脏内科学方面,主要是心电图、心脏X线检查,还初步了解了心导管技术及血氧含量的测定技术。半年之后,我转到位于芝加哥的迈克瑞斯研究所学习。这是个专为犹太人办的研究机构,研究所有自己的实习医院和实验室,教授全都是美国知名度很高的医学专家。
1950年春,我感到该回国报效祖国,就写信与协和医学院联系。协和医学院当时正从四方招聘人才,充实师资队伍,接到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发出了聘书。张孝骞主任亲自给我来信:“你回来,中国同样有你发展的地方!”7月初,我购好从芝加哥直达天津大沽口的船票。由于船在太平洋沿岸许多港口不能停泊,这样原本近十天的航程,走了半个多月。船行至台湾后,允许上岸。船长说:“已经到台湾了,你可以趁机靠岸。”我说:“我不能去,我就是因为不愿意为国民党军队服务,才推迟两年出国。现在让我上岸,我宁愿随你们回美国也不去台湾。”后来几经辗转,我从香港经汉口回到北京。
重建协和心脏科
1950年8月,我到协和医院报到,张孝骞主任对我说:“协和的恢复和发展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新中国刚刚站起来,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她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就一头扎进了心电图室。
摆在我面前的是仅存的一台布满灰尘的心电图机,是1928年生产的仅供研究用的老式弦线性的。我首先清理这台机器,清理过程中发现这台心电图机的核心部分出现了故障,它的导丝断了,便与协和医院名誉院长方圻一起考虑把它装起来。这根仅有7μm(红血球的直径,肉眼仅在强光下能看其反射的光线)的导丝,要装在窄于1mm的缝隙中间,没有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是很难办到的。经过十多天的努力,终于装上了这根导丝,从而把心電图机恢复了起来。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我又尝试在3个导联旁边做了个盒子,试着把它改装成12个导联的新机器,没想到这一改造竟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协和不仅有了心电图机,而且能做12个导联的心电图。
从1951年开始,我连续在内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多导联心电图的诊断意义和使用方法,并积累一些临床资料。我意识到仅协和能做这样的心电图远远不行,我们要有一批掌握这门技术的专业人才,于是建议协和医学院举办全国性的学习班。就这样,从1951年春开始,协和开始在全国各大医院招收学员,每期五至六名,学时六周,对这些学员我都给予了耐心的指导。

阜外医院1959 年心电图班结业纪念留影,前排右三为黄宛
协和作为综合性医院仅仅有心电图是不行的,必须开展心导管技术诊疗,否则心脏病的诊断和治疗仍很落后。但当时,协和实验室仅有供示范用的F6和F7两支心导管。我在方圻和刘士珍的协助下,从废品仓库中找出了个可以测平均压的蒸汽锅上的表,为了简略地分析血氧又从血液组取得一组简单但难以操作的Scholander管子,就这样自1952年开始做右心导管。1952年至1955年间,就是凭着这两条导管,我为几十个人做了导管检查。这就是我在国内做右心导管检查的极原始的开端,直至1954年进口了英国的电血压计,1955年进口了法国的导管,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我在国外主要学习和研究心电生理等方面的知识,临床方面比较薄弱,而在协和担任大内科心脏学组长时,临床治疗的任务很重。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临床的担子挑起来。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严格的学习工作计划:每天上午在病房看病人、学临床,从实践中学习;下午在研究室做实验,进行心脏病研究;晚上看书,从8点一直到次日凌晨2点,学习6个小时,按照这个计划,我从32岁一直坚持到40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自1956年起,先是参与邓颖超大姐的保健,尔后又为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讲课。
1957年秋,总理得知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回到太原老家后突然患了心肌梗死,便立即指示我速赴太原为傅部长检查。飞机抵达太原后,我立即奔赴傅下榻的太原宾馆。到太原后,据保健医生讲,傅患的不是心肌梗死而是胃肠炎,理由是他服药后呕吐得很厉害。我向傅部长详细询问了病情,认为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很大,于是给太原市所有医院打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台心电图机。心电图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广泛心肌梗死,呕吐的原因不是胃肠病,而是服药不适引起的。于是我安排傅部长立即转院到太原市人民医院进行心脏诊治,治好傅部长后,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我参与的“医疗外交”
1965年初,时任医学科学院政委张之强同志找到我说:“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尚无学科带头人,他们向卫生部领导多次反映过,卫生部领导考虑再三,有调你过去的意思。”我认真地对张政委说,“既然领导认为我可以调过去,而且总医院又迫切需要,那我就去吧。”20世纪60年代总医院的条件很简陋,心内科病房是刚刚从内科系统中分离出来的。我到后担任一部副主任兼心内科主任。
到总医院后不久,“文革”爆发了。军医系统揪斗成风,我也被人盯上。年底,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到北京看病,住在玉泉山,总理派人通知我去玉泉山为胡志明诊疗。当时不明真相的我还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我听说胡主席是神经系统的病,与心脏上的关系不大,我去不大合适吧?”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动脑筋?北京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你都較熟悉,你去了之后将来协调会诊好办。”我看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不知说什么才好。到了玉泉山之后,我才明白,总理是在想办法保护我。
胡志明返回越南两个月后,医疗组自行解散。6月中旬,我回到了总医院心内科。不料这便开始了挨整的日子,我被邱的爪牙安排到京郊的大兴县去收割小麦,一直到第二年2月。这时,总理再次点名让我去给胡志明同志治病。见到总理,我心里特别高兴。总理话不多,只是对我说:“胡志明主席心脏情况很不好,我让你出趟差,到越南去,你思想上有什么负担没有?”我对总理说:“我犯了错误,批评还没结束,我怕我还会犯错误!”总理笑了笑,然后很严肃地说:“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事,你要正确对待,放心吧!”在总理的安排下,第二天我就抵达了越南。
我带领中国医护人员成功救治了胡志明,带功回国,到科里以后也就再没有人算我的老账了。此后,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心内科的全面建设上,想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我的病房里放了一张单人床,在加班加点不回家休息时使用,并把重要的病历都放在床边,随时进行查阅。
1970年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心脏情况不好,他的保健医生向他推荐了我。于是,总理又要求我去给霍查治疗。我迅速飞往阿尔巴尼亚。到了以后,我认真了解了霍查的病历,观察病情后发现,他的情况和胡志明的一模一样,是典型的“无Q波心肌梗死”。按照我的治疗方案实施后,霍查的病情有了十分明显的好转,可就在这时我却生病了,而且越来越严重,阿方于是让我回国。经检查,我患的是典型激素引起的出血性胃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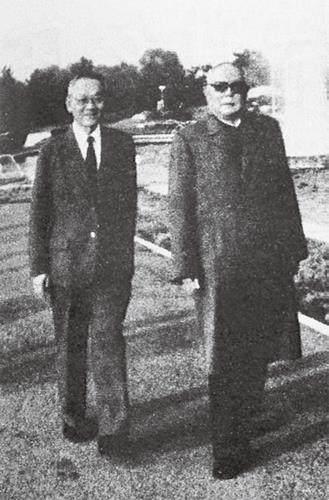
1986年黄宛与李先念在一起
1979年,越南领导人黄文欢因患肺结核,准备送往东德治疗。途经巴基斯坦时,他们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反映,希望能到中国医治。使馆人员把此情况报告中央后,决定让他到我们医院来。黄文欢住进总医院三部后,我们很快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对他的病情进行分析,诊断为肺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文欢的心脏不好,虽患肺癌,但做手术风险太大,趋向保守治疗。我则认为:黄患的是肺癌,手术风险的确很大,但这是当时最好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患有较明显的缺血性心脏病都被认为是做大手术的禁忌症。我反复分析,认为如果病人不马上实施手术,癌细胞很快就会扩散,这无异于宣布死刑。越南方面之所以改道来中国,是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信任,也是考验。于是,我决定请北京结核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一起会诊。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只有半数专家同意做手术,不同意手术的理由就是怕在手术中心脏出问题。为此,我当即表态说:“如果是因为怕心脏方面出问题而不进行手术,那么我可负全责,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包了!”这样一来,决定做手术的意见占了上风。
越南方面又让日本医学专家参与意见。日本派出的医疗队给出的意见和我一样,认为虽有心脏病,但必须而且能够手术。结果,手术进展顺利,肿瘤切除了,心脏也未出大问题。一连几天,我睡在病房进行观察,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就这样,我们的手术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黄文欢后来又生活工作了十多年,从而打破了当时肺癌患者活不过两年的说法,突破了心脏病患者做大手术的禁区。
(责任编辑 杨琳)
整理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副处长、政治协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