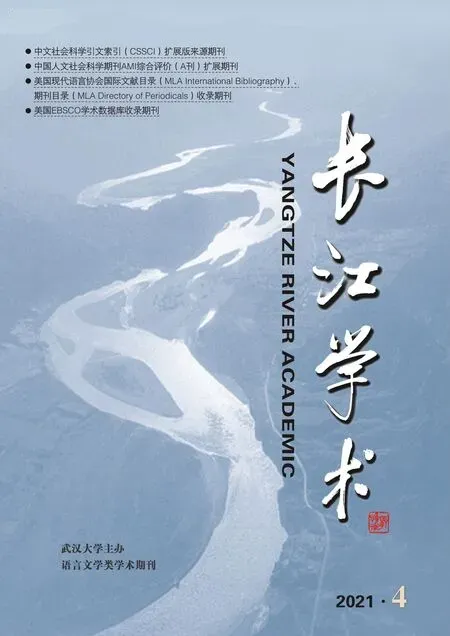回溯性建构与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指归
叶娟娟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引言:盖世太保-抚摸皮肤(Gestapo-geste à p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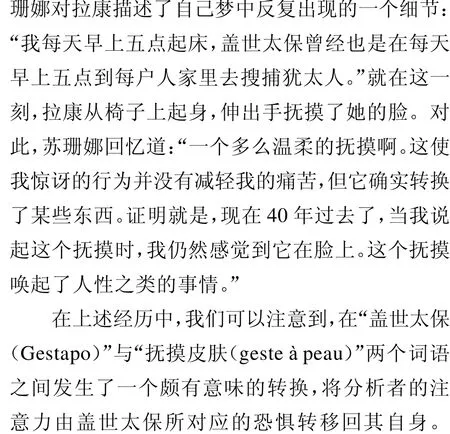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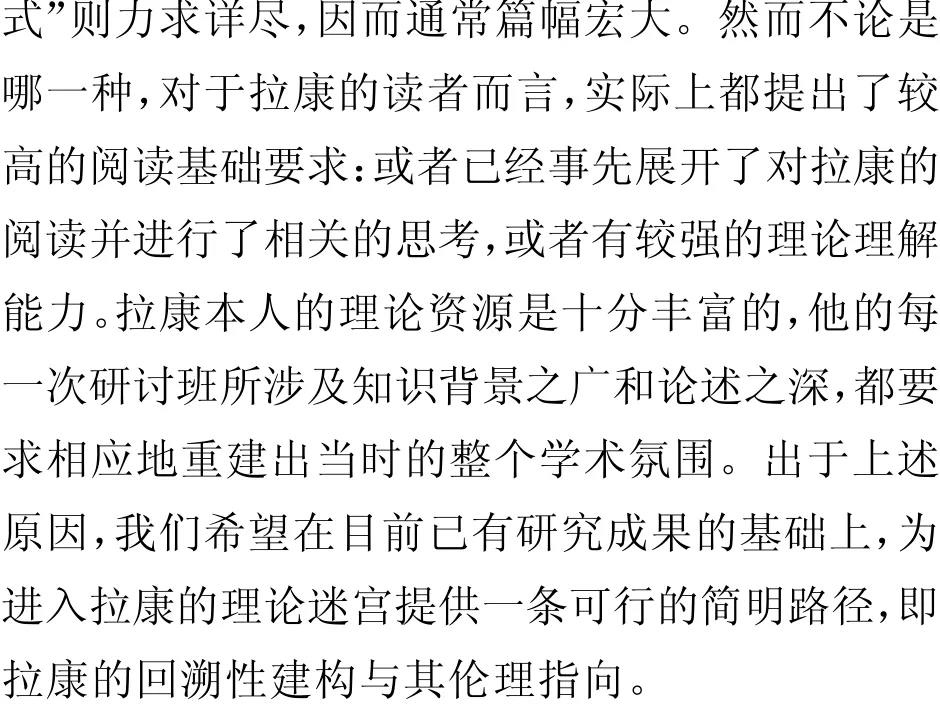
一、回到弗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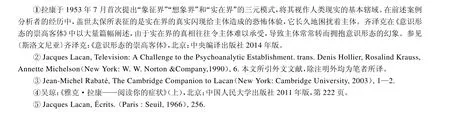



二、回望善的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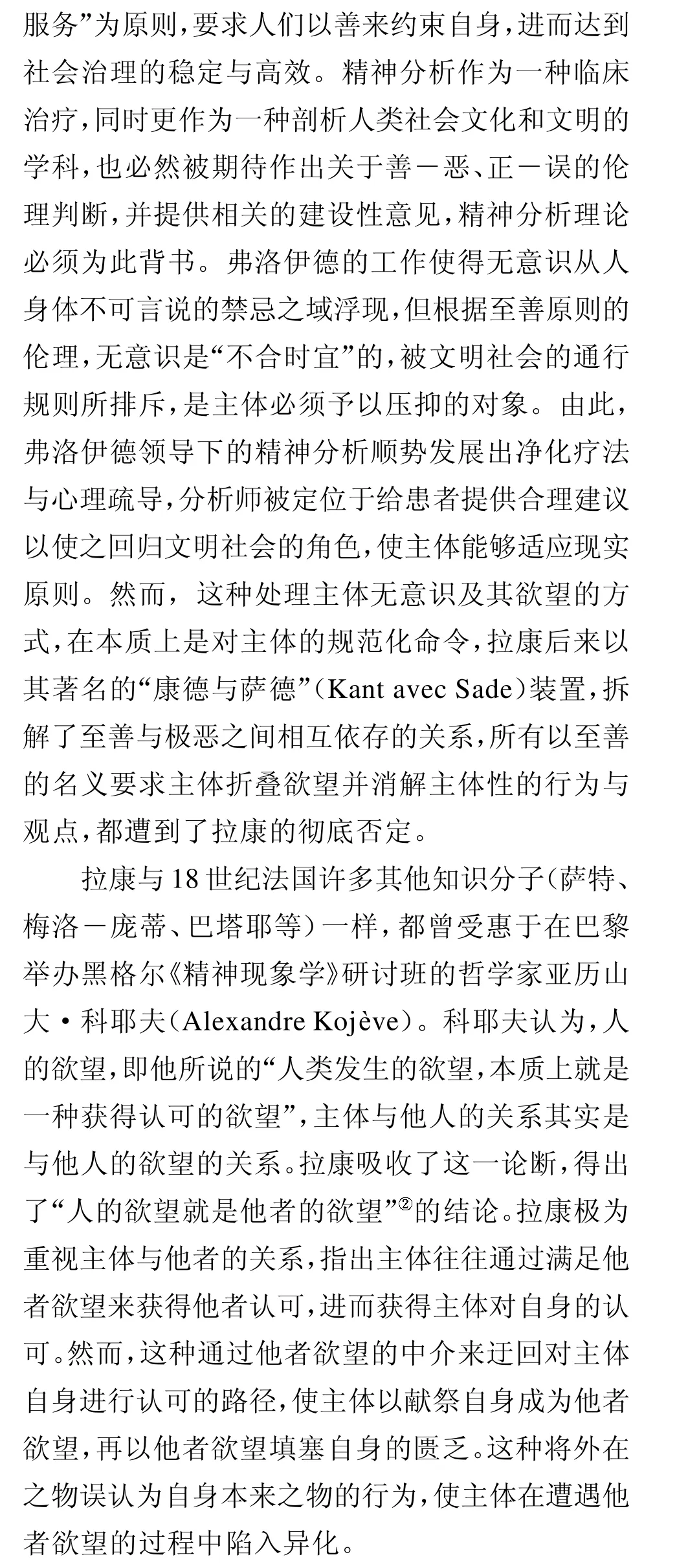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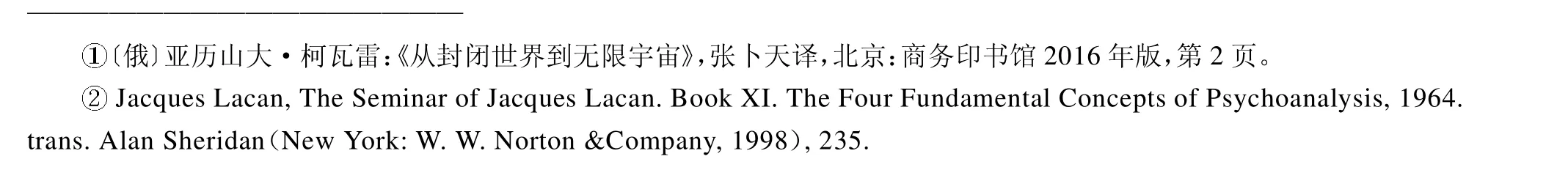
为从他者欲望的裹挟中析出主体的面貌,拉康分两个途径对他者欲望进行拆解:一是在精神分析大厦中架入语言学理论,指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建构的,以此阐释他者欲望对主体的植入过程;二是通过“康德与萨德”装置,展示了象征界如何以纯粹实践理性或意志的命令,即一种绝对强力的意志,以倒错的形式对主体施以萨德式淫秽主体的无节制之恶,拉康还以这一装置彻底瓦解了西方理性主体的自主自明神话。
拉康倒转了索绪尔的所指/能指公式,将其转换为S s
意谓能指在所指之上),以图示的形式强调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阻隔,表示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确立了能指的优先地位。按照拉康的观点,由于能指是不断滑动的,能指无法真正锚定所指,然而,正是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的词语裂缝中,实在界的真相往往得以突破符号秩序的边界而闪现,这也是后来齐泽克所阐发的“实在界的鬼脸”。在本文开篇所讲述的案例中,拉康正是利用能指的滑动这一特质,捕捉了掩藏在“实在界的鬼脸”之后的主体真实欲望,即,以“抚摸皮肤”为表象的指令,要求主体确认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拉康以“康德与萨德”装置对西方传统伦理所构想的自明主体进行了拆解。传统伦理以及弗洛伊德之后的自我心理学,都允诺主体在获致善与快乐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拉康表示这是一种幻象,是虚假的承诺,因为善与快乐都具有两重性,二者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悖论。善与恶是一体两面的,善的理念之倒转就是恶的意志。快乐达到一定限度后就会转变为痛苦,通过“欲望是法则的反面”,善以纯粹实践理性或意志的命令强加到主体身上,这与萨德式淫秽享乐主体互为镜像,这就是拉康所说的“萨德从后门溜进了康德的卧房”。拉康以原乐(Jousissance)作为支点,撬开了西方启蒙伦理至善的背面,揭示至善与极恶之间的同质性。由此,拉康要求人们警惕道德自身的悖论,因为其所暗含的善/恶之辩证,已经最有力和直观地呈现在当代以允诺未来幸福的名义而施行的政治之暴中,即,以至善为道德意志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杀戮都借由此法则,昭示道德强大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致命性的残酷,尤其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宣告了西方理性的全面溃败。为此,拉康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主体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三、回溯主体的个人史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学有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即人对幸福和至善的追求有其自然的目的和倾向,就如先有桌子的理念,后有匠人根据这一理念打造出完美的桌子,它们指向的是本体性的完善,或最理想的自我实现。因此,在传统伦理学观念中,主体的完美和谐与主体对幸福和至善的追求是同质的,它们在本体论意义上有其自然的根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基督教世界,“实在”与“虚构”还未出现对立,上帝与人及万物处于一个等级森严、和谐一体的封闭世界中,一切事物按照上帝的至高理念被赋予了自然本性。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封闭世界被瓦解为一个开放的无限宇宙,中心解体,至高之位不复存在,至善理念开始失效,现代性的伦理和价值体系必须为自身重新寻找新的根基。人类的生存环境从封闭世界置换为无限宇宙,意味着宇宙中心点与至善理念的彻底失落,宇宙不再以统一整体的形式运转,宇宙中的匮乏部分成为支撑宇宙存在的本质所在。匮乏部分成为实体意义上的空位,以悬置的无有状态赋予宇宙以无限性。



不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有自己关于世界统一图景的想象,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领域里,母婴同体就充当了这个统一图景的原初神话。主体从完满中永远失落的原初场景,在其他人类文明图景和阐释体系中也有相似的文化符号,如圣经故事中亚当



命名之时,由于主体尚未与象征界主动契合,这种他者欲望对主体的嵌入其实并不深刻,主体对于命名的认同是被动发生的,主体在后来的个人成长中仍可以对该命名进行拒斥,甚至依据象征界的法则对其进行擦除。镜像阶段主体对镜像的认同则较为复杂,主体在本质上也是被动的。通过他者和象征界对主体的询唤,主体在经历了原初的失落后,能够表现出对镜像进行主动认同的姿态,从而接受象征秩序即大他者对主体的统摄。
这里涉及拉康精神分析伦理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认同。主体在母婴同体时期的自我认同是依托于母体的,不论尚在母亲子宫里的胎儿或是刚出生的婴儿,在还未意识到自己与母亲身体的事实分离之前,婴儿对自我的认同表现在对母亲的持续依赖上,母亲就是自身的一部分。当婴儿开始观察镜中自己的反射形象时,父母或其他人会不断重复将镜像等同于婴儿的指认行为,对婴儿说:“看啊,这就是你!”在外界和他者的反复指示下,婴儿将镜像中的完整统一形象与自我进行对等联系,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不断重复和强化。然而,实际上,不同于镜中看起来和谐统一的整体形象,主体体验到的是自身的分裂感及对肢体的支配无力感,二者之间形成了冲突。拉康指出,镜像作为理想自我外在于主体的虚幻形象,与主体自身形成对立,对镜像的认同包含着对主体自身的否定,并对主体自身展开了竞争,这无疑造成主体对自身的额外消耗。当主体沉睡于自我的幻想中时,就迷失了主体本来之处,也渐失自己的本然状态。故而,主体应该穿越幻象,走出他者欲望的询唤,立定自身,承担主体的命运,这也是精神分析中主体的伦理责任所在。
四、他者的介入与主体的干预
在上述拉康所回溯的两个重要时刻所发生的主体认同,无一例外都涉及主体对他者欲望的处理。主体一出生就降临于象征秩序中,落入符号之网,以语言来言说使主体得以进入社会关系的构成,而主体的言说要求有听者的在场,听者充当了拉康意义上分析情境中的他者。他者的存在,使主体的言说具有了介入现实的可能,而介入现实,则是主体对自身存在进行的自我干预。


他者在拉康的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多面相概念,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涵义:大他者(Autre),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在象征界无处不在,统摄性地笼罩其中,以绝对强势的权威和意志要求主体臣服,遵守大他者的法与禁忌;小他者(autre),既是相对于主体的其他主体存在,又同时作为概念而独立于具体主体之外,亦如大他者是一种身份定义;更为重要的是拉康极为重视在精神分析关系中的他者,此时,他者可以是分析师,也可以是分析者,在更广泛的范畴内,他者可以是外在于主体的其他物之在场。
他者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二者是互证的概念,主体亦是他者的他者。拉康精神分析在恢复主体性的同时也重视他者的作用。主体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亦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是肃清他者欲望对于主体的异化,以使主体从他者欲望叠加的压力下挣脱出来,不向他者的欲望屈服;二是这一事实背后显示的是主体对于被认可的需求,主体通过满足他者欲望以期获得他者的认同,以此确证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因而,主体是始终与他者相缠绕的概念,此二者可以被视作一组“对子”概念,它们不能孤立存在。
我们始终要明确拉康的一个立场,其对符号化和大他者对主体作用的分析,并不是为了将符号置于主体存在的对立面。正如拉康高呼主体应直面自身的欲望,并不是号召主体要纵容自己的欲望。拉康反复要求主体警惕他者欲望对主体的异化,又极为重视主体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建立来观照自身。与拉康的回溯性建构始终指向主体的当下境况同质,拉康精神分析伦理所指向的也始终是主体的恢复。
拉康的精神分析要达到的临床效果是使主体直面自己,站回主体之位,接纳自身,而不是用如镜像般的统一整体幻象来对自我进行异化,因为对幻象的沉浸只会使主体在丧失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拉康虽然剖析他者欲望对主体的强制置入,以使主体能够拒绝他者欲望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也始终表示主体的存在需要他者的介入。他者的介入当然不是符号化社会下为主体提供自我心理学派的“矫正”观念,而是在认同主体的存在需要与他者形成互动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关系。以分析师为例,在一段精神分析经验中,分析师的角色排除了生活经验和大他者的暴力意志输入,提供主体在言说过程中与实在界的真实相遇的渠道。拉康的精神分析比之弗洛伊德更向前迈进的一步是使精神分析脱离了生物主义的桎梏,在文化研究层面具有了建立一门新的宇宙论的宏大格局。因而,在精神分析关系中,分析师与他者,作为分析者与主体的对子角色,可以替换为在主体日常经验中所相遇的其他介质,如文学与艺术。拉康表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原物(das Ding)的性质,可以物的形式使主体远离他者欲望的裹挟,填补主体的匮乏;又因为摆脱了语言和符号的暴力与意志,为主体提供了无的空间,供主体在此与自我相遇,以空无的形式提供了主体复位的可靠途径。这是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观对我们理解自身以及与文学艺术建立紧密联系的价值所在。
结语
回溯性建构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是根据现在来对过去作出新的理解,建构的立足点始终是主体的当下境况。拉康以回溯性建构的方法,回溯主体个人神话史的寓言式重要时刻,厘清了在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主体困厄处境的来源以及突围之法。拉康以同情的目光回溯主体的境遇,指出主体个人史笼罩在悲剧色彩之下,因而其精神分析的伦理永远指向主体。
拉康的这种以回溯性建构为方法论,始终坚持诉诸恢复主体性的伦理关切,深深影响着同时代及之后的大量思想家,例如巴迪欧注意到拉康通过回溯而厘清的主体是分裂的、匮乏的主体,正是这种主体支撑着真理的存在。巴迪欧承袭了拉康的“反哲学”立场,坚持对标准化的排斥、对伪善的追求幸福的排斥,坚持思考真理和知识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和齐泽克对拉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上新的活力与激进性。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主张“反俄狄浦斯”,将欲望视为生产性力量,实际上也未能超出拉康精神分析所探讨的命题范畴。
总体而言,通过定位回溯性建构作为方法论在拉康思想中的作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说在结构主义浪潮中,拉康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恢复主体性的人,也正是因此缘故,齐泽克坚决反对将拉康视作结构主义者。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不在于教人如何获得幸福快乐的善,它要求人必须从生命的悲剧向度中直面主体的命运。将主体的生命经验交付大他者、象征界的秩序与父法、想象界的幻象,都是对主体存在的盲目置换,只有主体确认自身的存在,直面主体的欲望,才能穿越我思与他者欲望编织的幻象,摆脱象征界与他者对其异化的根基。回溯性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从符号秩序的统治和掌控的企图中审视主体的当下境况,通过回溯将被自足的我思主体(幻象)排挤出去的主体移归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