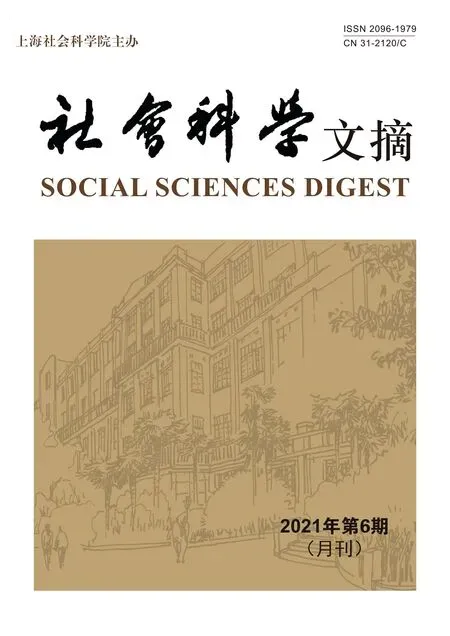集体型叙事中的女性声音
——对当代女作家非虚构书写的一种考察
文/孙桂荣
非虚构写作是建立在采访、调研、报道、考察等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纪实性文体类型,女性作家的创作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表述内容的研究(像乡土、历史、边地等),或代表性文本现象的个案解读(像针对梁鸿、李娟等人的非虚构之作)。从美学形态角度切入女性非虚构文学书写有别于女性小说等虚构文类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研究尚较为鲜见,本文试图阐释非虚构女性书写中集体型叙事中的女性声音问题。
集体型叙事与女性声音的理论联结
集体型叙事是相对于个人型叙事而言的形式种类。个人型叙事以个人化的“我”为叙述人,讲述自我参与其中的故事;集体型叙事的叙述人则是复数的群体,或化身为复数群体的代言人。这里的群体声音并非泛指一切群体的话语表达,而是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之声。在“沉默的大多数”群体即使有幸发声也往往被忽略、压制的情形下,多人共同发声的集体型叙述会产生单一的个人型言说难以比拟的强烈社会效果。只有借助群体性力量,“他/她们”的声音才能更清晰地被倾听到,是集体型叙事的伦理依据。
从价值上说,个人型叙事与集体型叙事均具有颠覆主流文化的现代性意义,但具体指向并不相同:个人型叙事从个人化视角、边缘化立场角度对居于主流位置的公共话语或官方话语造成一定的冲击和颠覆,针对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集体型叙事言说的同样是些无法化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声音,其以群体化、集束性出现的方式谋求位卑言轻的单个个人难以达到的话语力量。
因此,集体型叙事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复数化形式技巧,还与话语格局中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同为弱势群体发言这个角度与“女性声音”产生了某种内在联结。“女性声音”将叙事学视角的“声音”与性别视角的“女性”联系起来,意在通过叙述样态、言说方式、聆听方式等形式层面的文体考察并表达女性的权力诉求,以区别于以内容为主的传统性别分析视角,是女性主义主义叙事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苏珊·兰瑟曾言,“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女性声音”联系着美学形式与性别呼声的双重意涵,可以通过个人型叙事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集体型叙事体现出来,后者是居于“第二性”的女性话语借助集体的话语力量表达诉求的叙事样式。
将集体型叙事与非虚构写作相联系,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是建立在采访、调研、实地考察基础上的,采访、调研对象会牵涉到复数的多人,比写作者个人苦思冥想的虚构小说更容易关涉到“别人”的声音、群体的身影。如果说集体型叙事对虚构文类是一种可用、也可以不用的“备选”形式样态的话,其对非虚构来说可称之为“必选”项。至于将女性声音的视角纳入非虚构写作研究中来,则是为了修正目前研究中对其社会意识过分推崇而相对忽略其性别意识的倾向。笔者认为不少女作家的非虚构书写固然以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式彰显了不亚于男性写作的深广社会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的全然退场。女性批评者张莉曾言,“当这些写作者们试图书写一位女性眼中的‘世界’和‘现实’时……她们渴望个人的关注点能与‘社会关注点’衔接”。这种观点比起那些认为它们是无“我”、无“女”之作的研究要辩证一些。但“个人关注点”与“社会关注点”的衔接会落脚在哪里呢?笔者认为集体型叙事便是女性作家能够采取的一种连结个人与群体、女性与社会的有效文体样式。
“我”在场的集体型言说
不少非虚构女性写作采用了“我”在场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但这个“我”讲述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他/她们”的故事,“我”更多扮演一个采访者、见证人的角色,是化身为复数群体的代言人。让“我”在场,以亲历性、体验性的方式叙述芸芸众生的痛苦与欢乐,能够以拉近言说对象与读者距离的方式传达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意识,是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黄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丁燕《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等女性作家非虚构书写的一个共同特征,其最大程度地增强了叙述的现场感与真实感。
相对于言说对象直接现身说法或轮流发言的集体型叙事,这种以“我”为中介的集体型言说,会不会因为“我”的在场遮蔽或压抑了人物自己的声音?对此,学界是有争议的,研究者刘珽就曾委婉批评梁鸿的创作,“让人物或者一草一木来说话,比作者自己说更有说服力”,但笔者并不苟同。因为同一群体中不同叙述人轮番上场的叙述方式,不同叙述个体间的叙述内容与观点既可以相互支撑和补充,也有可能造成观点的分离甚至矛盾。有些“让人物自己来说话”的集体型写作就破坏了所言说声音的完整性、典型性。像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桑烨的《北京人》中,社会边缘人轮番上场充当叙述人,以口语化、个性化、地方化、风格化的方式传达出不同职业与身份的小人物生活。每个言说者被赋予了足够的话语权,未遭遇隐含作者的背后干预,但各章一比较,就会发现杂音太多。这使得这100位普通中国人的集体型叙事里有太多“众生喧哗”的嘈杂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和风格,像“万元户主”中因经济致富而气壮腰粗、文化涵养不高的言说便与其他章节中社会边缘人稍显悲哀落寞的独白差别较大。异质杂糅的群体型声音事实上难以增强话语权威,甚至会降低言说的公众效力。而“我”在场的集体型叙事经由女性叙述人的视点和中介所体现的群体声音则明显一致了许多,像《出梁庄记》中51个梁庄打工人的言说共同指向了农民工进城的漂泊与创伤,《女工记》中100个打工女共同指向机器流水线对女工的物质与精神吞噬。这种有着大体一致指向的多人声音聚合在一起的话语模式,以“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的方式,提升了边缘群体的社会关注度,显示出了集体型叙事的话语力量。
女性声音的集体型表达
非虚构关注的是一个群体共同面临的问题,言说对象往往有男有女,除非是专门针对女性群体,在内容上不会特别突出性别话题,女性写作者的自我性别感受往往是以某种无意识的方式潜隐于创作中的。像孙惠芬创作谈中所言,“听凭了写作中的直觉”。女作家选择设置携带自身经验、身份、趣味的“我”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叙述人,为性别无意识的流露提供了一定条件:一方面,通过讲述弱势群体的故事展示了并非自我的他人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我”的在场又公开保留了个人与女性的些许声音,将对他人世界的群体关注通过女性的口吻、视域表达出来。在人性关怀与女性关怀的双重烛照方面,集体型叙事作出了贡献。这在与同类男性写作的对比中体现得更明显些。
像同为描写工厂食堂的文字,丁燕《到东莞》书写的是个人主观感受的细节体验,其以“费劲”“唇焦舌燥”“漫长、暗哑的喉管”等直观的描述性词语形容难以下咽的食堂饭菜,画面感强,体现了女作家的细腻和敏感;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则是用复数人称“我们”叙述,以“食物”“食品”“粮食”“原料”“半成品”“成品”等概括性语词,体现出置身事外的距离感和抽象性,对言说对象(集体食堂)有着揶揄、调侃、反讽之情。从叙事学上说,丁燕采用的是与言说对象距离切近、召唤读者参与的“吸引型叙事”,设身处地从写作对象出发的女性色彩较为鲜明。萧相风的写作是一种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疏离型叙事”,表达叙述人对话语权威感的追求,更多体现出男性写作者的俯视性写作姿态。因此,二者尽管都是集体型叙事(前者是叙述人代女工发声的单言叙事,后者是以群体性“我们”为叙述人的共言叙事),但性别立场并不甚相同。
21世纪给女性写作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女性在关注大千世界的时候,并没有违心地自我遮蔽性别身份,而是融入了一定女性立场与视角,使看似中性化的集体型叙事包含了或隐或显的女性声音。其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以直接关注女性群体的方式表达的显性女性声音,像郑小琼《女工记》、丁燕《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工厂女孩》等关注的都是“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的女工群像,让被主流社会漠视与压抑的女工的声音集体性呈现出来;二是女性声音在并非专门关注女性群体的集体型叙事中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体现的。像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以作者自述的“性别无意识”方式对农村妇女自杀的故事格外关注。而梁鸿《中国在梁庄》中则有挥之不去的乡愁问题,与作品整体要表达的启蒙立场上的乡村现代性忧思之间甚至存在一定话语裂隙,被研究者张莉解读为“乡愁于《中国在梁庄》是一把双刃剑……这种乡愁也遮蔽了其他一些东西”。但笔者看来,乡愁这种个人化情感是与叙述人女性意识相关的。沃霍尔曾言,“作品中的性别策略源自作者一系列的修辞选择,无论这些选择是故意的还是无意识的”。女性视角的问题并不是作者避而不谈就可以规避的,尽管非虚构写作者已不再将性别作为主要元素,有些人甚至讳莫如深,但这并不等于说其性别姿态不在场。《中国在梁庄》的乡愁是第一人称女性叙述人感性情怀的自然流露,其冲破了作品副标题设置的“还原一个乡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的宏大叙事框架,回到了女性个人化情感的最深处。在男/女、理性/感性、群体/个人、农民/自我的话语向度中,后者并没有缺席,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悄悄存在,使得集体型叙事与女性话语的联系愈加丰富、复杂起来。
集体型叙事与女性需要的“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问题最初是由女作家张抗抗在1985年西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触及的是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的二元命题。女权与人权的二分法在当时的女性学界曾引发了一些后续论争。这些说法力求完整地观照女性有关人的困惑与性别的困惑的双重命题,但无形中暴露了女性/人性、小世界/大世界、内在世界/外部世界的二元思维,并有将女性对应于“小世界/内在世界”,而且是在价值上低于男性对应的“大世界/外部世界”的性别本质主义倾向,因此遭到了某些当时正全力拥抱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激进学人的批判。女性学者王绯提出的“女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之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是女作家与男作家站在文学的同一跑道上所创造的一种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抹杀女性性别特殊性的观点而备受争议。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论争主要就是围绕女性需要的这“两个世界”的内在关系而来的。
不过,经过强调“女人性”、以女性“小世界”的无限张扬颠覆男权文化的“大世界”的私人化写作之后,女性学界亦开始反思自身,普遍注重将社会性别(gender)“同社会身份的其他构成成分协调起来”,进行宽泛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非虚构写作内容上涉及三农、移民、拆迁、灾难、西部开发、南水北调、反腐倡廉等重大题材,形式上则以集体型叙事消解了个人化自传体叙事的单一与单薄,并囊括口述实录体、田野调查体、史料钩沉体、图文并茂体等各类样态,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跨文体写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学界关注的“大世界”传统中。从叙事基调上说,集体型叙事因为关注的是他者,发出的是群体性的声音,与21世纪以来研究界对女性写作“走出自我/身体,走向他者/社会”的主流呼吁是相一致的,也回应了西方女性学者西苏、斯皮瓦克等人在更深广层次上的社会性别言说。
从对外部社会“大世界”的眷顾到返回女性“小世界”的执着,再到重返“大世界”的勇气与能力,非虚构写作的集体型叙事似乎是走了一条女性话语的“否定之否定”之路。不过,经过20世纪后期思想解放与大规模的世界性学术思潮冲击之后,21世纪的文学环境已大为宽松,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也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两个世界”问题如此敏感和各执一端,叙事话语亦开始相对成熟和多元。一如本文上述所言,集体型叙事并不排斥个人话语与女性声音,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将女性对“大世界”的现代性忧思与对“小世界”的个人情怀联系起来,从而得以摆脱20世纪80年代“两个世界”论争时有意无意的各执一端思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纠结女性写作的性别/超性别、女性/人性、女权/人权、公共空间/私人生活的二元对立难题。我们可以把21世纪女作家的非虚构写作同女作家张辛欣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做一下对比。
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以《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最后的停泊地》等女性心理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采取的是第一人称日记体、内心独白体等个人型叙事方式,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伴随个性解放而来的女性主体性的上升,其个人性型叙事与女性情怀的无羁张扬,在当时看来有些激进和尖锐,受到了不少质疑和争议。1985年后,她突然推出了《北京人》《在路上》《寻找合适去死的剧中人》《去死》等。它们可称为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之作。其中,《北京人》每一章都是被采访人轮番登场的集体型言说,并基本放逐了写作者自身的女性个人声音。这当然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有着外界压力的因素在起作用。研究者金介甫曾说,“张辛欣转向新闻写作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一些人担心张辛欣正在‘退步’,甚至担心她对非虚构文体的运用,是对文学创造力的‘威胁’……内因受外部条件的严格限制使张辛欣转向新闻”。在彰显自我情怀与女性独立诉求受主流意识形态批评的苦闷与焦虑下,张辛欣通过《北京人》由自我“小世界”的挖掘转向了社会“大世界”的摹写,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文体探索,但对于文本中的女性声音来说却是一种无奈的遗憾,是女性写作在那个年代尚不自由的一种体现——不得不将其所需要的“两个世界”相割裂,在小说中展现女性情怀,而在口述实录体非虚构中彰显社会意识。
同样是非虚构创作、集体型叙事,同样是对女性“小世界”倾情泼墨(私人化写作)之后直面“大世界”的转向,21世纪以来的女性非虚构写作在延续了张辛欣的社会关怀意识、群体精神、时代参与感的同时,对其上述在“两个世界”之间各执一端的创作尴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化解和修复。如前所述,不管是以“我”作为采访人、见证人的在场性叙述的方式,还是多人围绕一个话题轮番讲述的共言方式,女性写作者的集体型言说均以某种或隐或显的方式流露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女性声音,尽管有时是与阶级、地域等其他社会关怀纠结在一起的,有些是在女性写作者自身习焉不察的不经意状态中完成的。不管怎样,集体型叙事昭示了女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绝非“去性别”的文类。作为女性书写的新的文体策略,其以性别在场的方式关注社会宏大命题,体现了女性写作在21世纪的新发展,也回应了新时代中国对有着“‘超性别和流性别’元素”、双性同体精神的“新阳刚”写作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