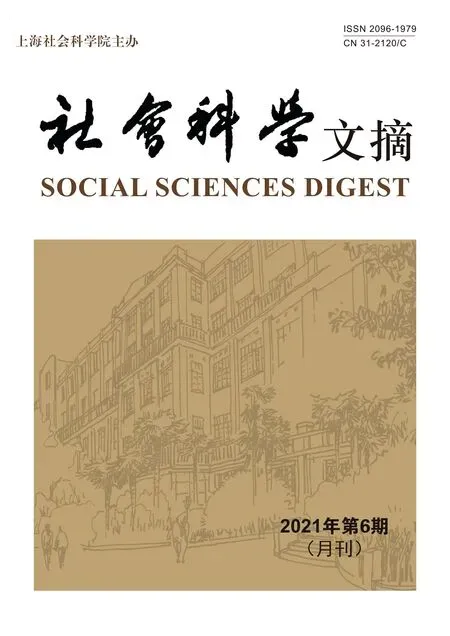“民族哲学”的概念辨析与“金岳霖悖论”的提示
——对伍雄武先生商榷文的回应
文/李河
伍雄武先生对我发表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的论文《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下文简称《民族哲学》)撰写的商榷文章(下文简称“商榷文”),全盘误解了笔者的文义,将我在文章中围绕“民族哲学”概念所梳理出的多种可能语义,错认为笔者本人的学术立场,并以此为依据指责笔者否定“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的理由,对此我不能不做出回应。
第一,商榷文认为,《民族哲学》“从各方面明确地否定民族哲学和哲学的民族性”,这是缺少引文依据的。即以该文标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而论,其关键词是“可以……谈论”,而不是“明确否定”,更不是“从各方面明确地否定”。
第二,伍先生何以会从《民族哲学》一文读出“否定民族哲学”的意思?或因他多年在国内的“民族哲学有无之争”中以“肯定派”自居,故而看到《民族哲学》的叙事与其不同,便认定我是个“否定派”,以为我的观点与他“正好相反”,是“对应的反题”。这恰恰表明,伍先生谈论“民族哲学”时过于执着“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预设立场,这就是我说伍先生执念过重的原因。
第三,那么对于“民族哲学”话题,除了执着“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写法,还有其他的吗?有的,这就是我在《民族哲学》一文中力行的“澄清概念”的写法,它强调依据文献和逻辑,将涉及“民族哲学或哲学的民族性”提法的可能含义逐个列出,一一辨明其利弊,以便“清楚明白地”使用概念。当然,要“澄清概念”,首先需要尽可能地“悬搁立场”而不是“预设立场”。“悬搁立场”并非不要立场,或者伪装成没有立场,而是说承诺立场应以澄清概念为前提,这正是《民族哲学》一文的方法论特点,也是我这篇回应文章的主旨。
笔者所论的“民族哲学”并非伍先生所谓“少数民族的哲学”
商榷文写道:“李河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哲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团结,即有负面的政治意义。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随后该文用大量篇幅阐述“国族哲学与民族哲学、国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令我大惑不解:我的文章根本没有论及少数民族问题,文章对我的批评从何而来呢?
伍先生的误解大概因为《民族哲学》一文的关键词是“民族哲学”,在他看来,谈“民族哲学”当然就是谈论“少数民族哲学”。我理解伍先生多年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哲学,因而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专业敏感,但他应该注意一个事实:我在《民族哲学》第一部分特意申明,文中“民族哲学”的英文对应词是national philosophy,其关注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本土哲学”,它不同于国内学界讨论的“少数民族哲学”,按照《民族哲学》第二部分对“民族”概念的辨析,“少数民族哲学”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ies of ethnic groups。
我为什么特意作此申明呢?就因为当时意识到这样的标题或许会引发误解。但我为什么又非要用“民族哲学”一词呢?盖因撰写《民族哲学》一文本来是为参加2018年8月17日召开的国际论坛,参会者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学者,论坛主题就是“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需要说明,这个主题不是杜撰的,近年从俄罗斯、原苏联中亚地区国家到东欧国家,从土耳其到非洲国家,“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都是个很热的话题。2017年到2019年,笔者在阿塞拜疆、越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调研座谈时多次听到人们谈论national philosophy,但热衷谈论的人大多缺乏反思和追问的哲学素养,他们不太在意对这个概念的可能语义和用法进行辨析澄清,其言辞背后更多涌动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激情。我意识到,“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在这些学者潜意识里代表着一种“伸张或回收思想主权”的意识,但我更认为,思想主权的回收只能靠基于透彻反思和追问的概念批判活动来实现,否则,回收的主权一定与思想无关。据此,我在2018年8月的论坛专门对“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一词进行澄清。——我想,这个过程大体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使用“民族哲学”(national philosophy)一词,又为什么会在文首特意强调此处的“民族哲学”并非指国内的“少数民族哲学”。
不能把“概念澄清”的文字混同于“立场承诺”的文字
毫无疑问,一个作者列出不同语义以及围绕这些语义的不同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该作者对这个观点究竟持赞同还是反对的立场,这本是毋须论证的常识。但这却是伍先生“全盘误解”《民族哲学》一文的根本原因。
《民族哲学》一文围绕“民族哲学”的语义进行梳理澄清,其基本句式是:“民族哲学”一词可能存在语义A、B、C……;如果接受语义A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如此这般的理论后果;如果接受语义B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如此这般的理论后果;……而商榷文表现出一种“偏好”,它将我列出的一些“负面语义”归结为我的立场,其基本句式是:李河文章提到了如此这般的观点,这(实质上)就是其文章的立场,这种立场是错误的。
譬如,笔者文章第三部分指出,“民族哲学”一词的“哲学”具有多种含义,为此笔者创新性地将西语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引入对“哲学”概念的解读:
(1)20世纪中叶前,哲学史家或哲学家多喜欢使用philosophy的单数形式语词,其原因或在于,无论人们自古对“哲学”有多少种差异性理解,但大多数哲学家坚信,哲学具有一种“使哲学成为哲学”的本质要素,正是这种要素意识使人们追问“哲学是什么/哲学不是什么?”笔者接下来指出,但是“单数形式的哲学观念”在思想史上会带来一种后果,即人们会像黑格尔、梯利那样把哲学史理解为中心论的或单线式发展的历史。
(2)到了20世纪中下叶,在“去逻格斯中心论+去欧洲中心论”的鼓舞下,人们日益喜欢谈论“复数形式的哲学”即philosophies,这种谈论有助于使哲学史叙事摆脱中心论和单线论模式,使人们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中谈论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比较哲学”。但这个视角也带来一些麻烦,人们会把太多的东西塞入“哲学”。如果说哲学当初曾是一种从宗教神话走出来的反思性概念批判活动,那么许多热衷谈论“复数形式哲学”的学者似乎又走上一条从哲学“倒退回”民族宗教和神话资源的道路。
伍先生是怎样看待笔者的辨析的呢?他以决然的口气把我为“单数形式哲学”画像的文字当成我承诺的立场。他说:“李河据此就认为,只有单数性名词所表达的概念,其内涵(含义)才概括对象的本质特征,才可以作为区分事物的逻辑根据。……李河就得出结论:在谈论民族哲学并辨析其是否为哲学时,作为根据与标准的,应当是西方哲学中的‘哲学’概念,特别是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概念。”类似断语尚有多处,而且都没有从我文章转述的直接引语。
任何读者只要浏览《民族哲学》一文关于“单/复数形式哲学”的相关论述就不难发现,伍先生作出上述系列断定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将语句的内容陈述当成了语句态度,将概念含义的描述当作特定立场的承诺!正是以这样的理解方式,伍先生还把我引述的弗雷格对“自然语言”缺陷的分析,硬安在我头上,指责我“贬低自然语言的价值”,对此我只能回应,“不敢掠人之美”。
“金岳霖问题”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还是个“两难问题”?
“金岳霖问题”是指金岳霖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读报告”里提出的两难问题,即先秦诸子学说到底“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一部“中国哲学史”,究竟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笔者在《民族哲学》第三部分将这些追问简化为两个陈述,即究竟是“X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X国”?进而,我循着前面关于“单/复数形式哲学”的讨论指出,凡坚持“单数形式哲学”观念的,大都会使用“哲学在X国”的表述,不会赞成“民族哲学”的说法;凡倡导“复数形式哲学”观念的,则多会义无反顾地使用“X国哲学”的表述,从而成为“民族哲学”说法的拥趸。我进一步观察到,这个“金岳霖问题”居然在波兰、乌克兰等国学者关于“民族哲学”的讨论中原封不动地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波兰有学者也在追问:“Polish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in Poland?”(波兰哲学还是哲学在波兰?)由此可证,这个两难问题不光为我国所独有,在当代世界也未过时。可以说,自“金岳霖问题”问世以来,国内如此深入讨论该难题的文字并不多见。
伍先生对我在“金岳霖问题”讨论中作出的贡献全然无视,他关注的依然只是“立场”。他说:“可见,李河先生在此欲借金岳霖对哲学史方法的论述,由否定‘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进而否定民族哲学。”“‘X国哲学’与‘哲学在X国’两用语的提出者确是金岳霖先生,但是,引述他的意见来否定哲学史中‘X国哲学’(民族哲学)的方法,则是对金先生的误读。”
伍先生批评我“误读”了金岳霖报告,因为他认为金岳霖是没有否定“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的,因而是没有否定所谓“民族哲学”的。这种解读在我看来相当可疑。因为“金岳霖问题”在我看来绝不是个“二选一”的“立场选择题”,即应该肯定还是否定“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的说法?它更是一种对理由的追问,即人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依据何种理由来谈论“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正是在这里,金岳霖发现谈论“X国哲学”(如“中国哲学”)存在着多个理由上的困难:
其一,这种谈论无论如何得“以欧洲的哲学为普遍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这种趋势不容易终止”,换句话说,以一种地缘性发生的传统作为标准,本身是个无奈的但又不得不的选择。
其二,既然立了这么个标准,那么欧洲以外国家是否存在哲学的追问就面临几种可能的答案,最极端的当然是“有”或“无”这两种断定。金岳霖说:“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的。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如果金岳霖先生是像伍先生断言的那样,对“X国哲学”的立场持肯定态度,那就意味着“X国哲学”(或者伍先生所说的“民族哲学”)在实质与形式上都与欧洲哲学问题无异,这个结论恐怕伍先生本人都不会同意。
其三,实际上,金岳霖先生真正感到难解的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如果一地一国的思想“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这里所谓的“困难”就是“两难”,即面对相较于“普遍哲学”而言是“有实无形”或“无实有形”的思想,断定它是哲学或它不是哲学都有同样的理由。为此,有学者把“金岳霖问题”称为“金岳霖悖论”。
从“悖论”角度审视“金岳霖问题”就不难发现,其最深刻的价值恐怕不在于要人们在“X国哲学”与“哲学在X国”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立场选择,而是刻画出不少欧洲以外国家的学者群体共同面临的“两难”处境,即在A、B两种答案中,选择哪一方都显得“似非而是”或“似是而非”。这也正是笔者文章不轻易作出单一立场承诺的根本原因。
“民族哲学”话题:后发国家的思想身份标志
现在的也是最后的问题是,我的文章难道只有概念澄清而没有立场承诺吗?我相信这一定是伍先生的疑问。对此我的回应是:第一,我的文章是有立场的,但与伍先生想象的立场迥然不同;第二,我的立场是建立在“澄清概念”基础上的,而不是相反。
先说说我的立场为何与伍先生的想象不同。
商榷文表明,伍先生心里仅存在“非有即无、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立场,比如围绕“民族哲学”概念,一定有赞成方和反对方;围绕“单/复数形式的哲学”观念,一定存在着单数派和复数派;围绕“X国哲学/哲学在X国”的争论,也一定有正反两方面的立场。概而言之,围绕“哲学”,一定有西方中心论或中国本位论的对立。因为他是“民族哲学”或“中国哲学”的赞成者,因而发现我关于“民族哲学”的谈法与他不同,自然就将我归入各种意义的“反方”观点。这是商榷文对我曲解的根本原因。
我的《民族哲学》第四部分是谈论立场的,那里的立场与伍先生替我选择的不同。这一部分的标题是“民族哲学:后发国家的思想身份标志”,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由于我们是有强烈发展意愿的后发国家,因此“外来/本土”“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开放性/自主性”等“两难问题”会在很长时期困扰着我们。它在哲学领域就体现为“‘中国哲学’vs‘哲学在中国’”之争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有哲学吗”这类质疑。这些问题之所以是“两难”,乃在于人们无论选择哪一方答案,都会面临一种吊诡的处境,即赞成它的理由与反对它的理由同样有力。类似情况在俄罗斯、日本同样存在,乃至在19世纪末的美国也曾存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新的证据:2019年9月21日—22日中山大学举办“第六届中日哲学论坛”,其主题是“哲学在东亚的接受、转化与发展”,会议多有《哲学在中亚的接受》《哲学是什么——在东亚重新思考其意义》等论文。这些证据再次表明,“‘X国哲学’vs‘哲学在X国’”以及由此衍生的“X国有哲学吗”一类问题,在“后发国家”(即使是后来已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成为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进而言之,我认为“金岳霖问题”或“金岳霖悖论”是对后发国家知识界面临的“两难处境”的准确表述。
最后,说说我对“金岳霖问题”的立场。我反对在缺乏清晰反思和追问的情况下,陷入“中/西哲学”“本土/外来哲学”的二元对立,陷入偏执一端的立场。在我看来,与其进行这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选择,不如“回到事情本身”,采取扬弃二元对立并“回归中道”的立场。这个“事情本身”或“中道”就是应把确立“反思的主体性”当作确立“哲学主体性”的先决条件,离开了清楚明白的反思和透彻到底的追问批判,仅只强调思想理论的地域属性,那或许是后发国家的常见的理论现象,但与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是不相干的。
我相信,有了反思和追问这样的“中道”,我们就有了哲学,“我们有哲学吗”就会是个多余的问题;没有这个“中道”,即使给自己的研究附加再多哲学的名头,依然不是哲学。一旦我们的致思强大到足以影响越来越广大的世界,“我们有哲学吗?”就会成为自然消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