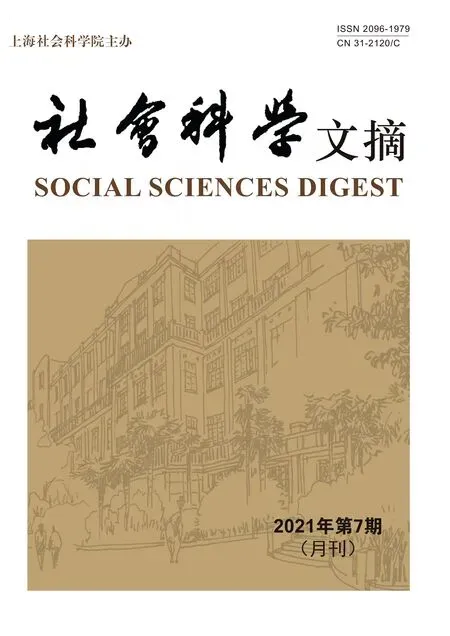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哲学中的“有”“无”观念比较
文/姚卫群
人与周围的事物在本质上是“有”还是“无”在古代是哲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都有探索这一问题的哲人。它实际也确是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不同地区的哲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有各自的见解。本文拟对三地这方面的主要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比较分析。
古代希腊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哲人很早就对自然现象和人自身的本质问题提出过一些看法。多数早期希腊哲人都认为事物是实有的。其中较著名的是泰利士、阿那克西美尼、毕泰戈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留基波、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
泰利士认为事物都源于水,“把水看成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提出自然界的基质是“气”,认为“气通过浓缩和稀释形成各种实体。毕泰戈拉派把“数”视为事物产生的源头,认为“从数产生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及一切形体。”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德谟克利特认为事物的基础是原子,“它们在宇宙中处于涡旋运动中,因此形成各种复合物。”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博学的思想家,在论及希腊早期哲人的思想时说:“那些早期的哲学研究者们,大都仅仅把物质性的本原当作万物的本原……。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幻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
主张本原说的希腊早期哲人认为这些本原是永恒存在的,不会有什么东西实际消灭,即事物不会化为“无”或“非存在”。这些哲人虽然没有直接论及“无”或“非存在”,但却是明确肯定事物是“有”或“存在”的。
古希腊哲人在论及“有”或“存在”的现象时实际也论及了“无”或“非存在”。如,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赫拉克利特在这里是从变化的角度谈“有”和“无”。说“有”是肯定存在着变化的过程;说“无”是否定有不变的东西,因为事物一直在变动,没有静止不动的事物。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认为,“有”不能真的产生于“无”。“无”中也不能真的产生“有”。这种观点否定了“无”与“有”的转变。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在讲述原子论时也论及了“存在”与“非存在”。他们认为,“存在”与“非存在”都是事物的表现形式,都是实在的。柏拉图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他的著名理论是“理念论”。他把事物“存在”的基础放在理念上,把“非存在”看作是“存在”的反面。理念是“存在”的基础,而分有理念的具体事物也具有依附于理念之上的实有。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亚里士多德把研究“有”的问题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某种形式的“有”。他说的“有”主要是“是”的意思,或“存在”的意思,而不是中文中说的“具有”或“拥有”的意思。而且这种“有”与事物的“实体”紧密相关。因为在说某一事物时一般都要问“是什么”,然后才有可能具体讨论这个东西的属性或状态等相关的问题。所谓“非有”或“无”实际也是涉及对某种“有”的事物存在的否定,而不是与“有”无关的。研究“有”及与其相关的“实体”成了哲学的根本问题。
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的哲学关注重点是在人伦问题或道德问题上,对自然现象或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也有,但主要集中在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成和关系问题上。至于事物的“有”“无”问题,有讨论,但涉及这一问题的中国古代哲人或学派并不多,有些还是受印度文化影响后出现的。
中国古籍中较早同时论及“有”“无”概念的是老子的《道德经》。该经第四十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说的“有”指有形象的事物;这里说的“无”指无形象的“道”。《道德经》的“无”不是指绝对的虚无,说的“有生于无”也不是指世间万物从绝对的虚无中产生出来。那么,世间事物不是从绝对虚无中产生,又是什么呢?《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说的“有物混成”实际上就是说在天地产生之前,有一种混沌状态。这种状态不能说是“无”,不是“无物”,而是一种没有分别的事物产生前的状态。也可以说就是“道”,“道”在这段引文中又被描述为是一种无形无相的宇宙产生前的状态。
庄周也是较早论及“有”“无”问题的哲人。他在《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周的这种论述也是认为事物的根本是“道”。但这“道”与一般的事物又不同。一般的事物有形有相,而“道”却无形无相。“道”虽无形无相,但却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对事物的产生和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庄周的这种“道”是形式上或形态上的“无”与实质上的“有”的有机结合。这是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种特定的“有”“无”观念。
魏晋时期的王弼也论及了“有”“无”问题。他在《老子》一章注中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停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王弼此处说的“无”不是指空无,而是指“道”。这从他的其他论述中也可看出来。如他在《老子》五十一章注中说:“道者,物之所由也。”王弼的这种思想基本上是承袭了古代老庄的主要观念。
王弼的“以无为本”的观念在魏晋时期也有人反对。如裴頠就是这样的人。裴頠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意思是说:绝对的“无”,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一开始的生,就是自己产生自己。自己产生自己,那么自己的体就是必然存在的。裴頠否定了王弼的“以无为本”思想,强调事物的存在是以“有”为根本的。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流派或宗派。在这之中,东晋时期的“六家七宗”在“有”“无”问题上的一些观念是引人瞩目的。其中的“本无”及“本无异”之说,论述的主要就是有中国特色较显著的“空”“有”观念。“本无”之说,认为“无在万化之前”,但又说“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此说具有佛教核心理念“性空”的特征,但其中的一些表述又有些将“空”实体化的倾向。“本无异”之说认为,“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此一观点与佛教大乘的主流思想中的对“空”的诠释完全不同,是用中国本土文化中原有的一些思想来解释印度大乘佛教核心理念的典型。隋唐之后,中国形成了一些佛教宗派。这些宗派虽然带有不少中国的特色,但理论的核心多依据印度形成的基本佛教教义。在“有”“无”问题上,一般都遵循印度佛教的缘起理论。这些宗派无论是偏于讲“无”,还是偏于讲“有”,其理论的基础都是“缘起”,因为从缘起论出发,既可以强调“空”,也可以强调“有”。
宋代及其后的中国思想界,在论述“有”“无”问题时常涉及 “气”“理”和“心”这几个概念。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太虚即气,则无无。”意思是,太虚就是气,因而无所谓无。这种理论否定“以无为本”的思想,认为有实在的气或太虚。程颢、程颐和朱熹都认为“理”是实在的,认为事物以“理”为根本。程颢在《遗书》卷十一中说:“万物皆有理,顺之者易,逆之者难。各循其理。” 在《遗书》卷十五中,他又说:“万物,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这实际也是将“理”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这三人讲的“理”都被视为是实有的,而万物都以这“理”为根本。宋代的陆九渊主张“心”为根本。他在《杂说》中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说也是一种实有论,把一切事物的基础放在“心”上。
古代印度
古印度哲人也有对“有”“无”问题的论述。在现存印度最早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中,就有相关内容。如《梨俱吠陀》中的《无有歌》中说:“那时,既无‘无’,亦无‘有’;既无空(气)亦无空(气)之外的天。什么被包含着?在何处?在谁的庇护之下?是否有深不可测的水?那时,既无死,亦无不死。无夜(与)昼的标记。太一靠自己的力量无风地呼吸。此外,无其它东西。最初,黑暗被黑暗所掩盖。这一切皆为无法辨别之水。生者为空虚所遮盖。太一通过炽热之力而产生。”
在这首赞歌中,世界最初被描述成一种混沌形态,是一种既没有“无”,也没有“有”的状态。但在这种状态中“太一”通过炽热之力而产生。因而,如果说世界最初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太一。太一是在无法区分“有”“无”的状态下产生的。这首赞歌是古印度最早明确提出“有”“无”概念的文献。
奥义书是在早期《吠陀》文献后产生的。它主要讨论的是关于“梵”与“我”的关系问题。所谓“梵”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所谓“我”指生命现象中的主体或众多我及其相关事物。奥义书强调“梵”是实有的,而“梵”之外的“我”(小我)是实无的。这种“有”“无”观念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哲学思想。在奥义书之后,古印度产生了不少哲学流派。正统派包括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非正统派包括顺世论、耆那教和佛教。
吠檀多派中影响最大的是“不二一元论”。这一分支认为,万有的根本是大我(梵),一切事物皆由大我幻现。大我或梵是实有的。而独立于梵之外的小我或现象界是人的无明或幻觉造成的,实际是“空无”的。数论派与瑜伽派都认为世间事物和人生现象是“自性”在“神我”作用后转变出来的,并认为这两个实体都是实在的,转变出了的现象最终也将回归自性。因而,这两派基本上是持实有观念的。胜论派侧重对自然现象的类别进行区分,正理派侧重探讨事物的推理和辩论规则问题。两派中都有“极微”(事物的最小单位)的理论,都认为极微是实在的,极微和合后生成的事物是实在的。因而,两派都是倾向于讲“有”的派别。弥曼差派强调吠陀言教的有效性,认为做祭祀能生实在的效果,因而也是侧重讲“有”的。顺世论是古印度的一个特立独行的派别。此派强调地、水、火、风这“四大”实有,其他的东西为“空无”。耆那教认为,实在的是解脱的灵魂或“命我”,而处在轮回中的灵魂或“命我”不能持久,最终是“空无”的。
佛教在产生时提出的理论与正统婆罗门教思想是相抵触的。佛教反对人生现象和世间事物中有一永恒的实体或主体,主张“缘起”的观念。这种缘起的观念对于佛教在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从缘起的理论出发,既可以认为事物是“实有”的,也可以认为事物是“空无”的。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是主张“实有”的。此部派的基本思路是:既然事物是缘起的,那么缘起的事物之体(诸缘)就不是“空无”,而是“实有”的。大乘佛教是主张“空无”的。这一点无论是从中观派还是从瑜伽行派的论述中都可以明显看出。中观派的代表人物龙树在《中论》卷第四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此派强调事物“性空”。瑜伽行派代表人物世亲在《唯识三十论颂》中说:“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这意思是说:一切事物都是识转变出来的,因而事物都是空无的。虽然瑜伽行派讲一切唯识,但这只是一种“方便说法”,是用来解构实有观念的。瑜伽行派最终也是否定“识”实有的。
比较分析
总之,古代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哲人都很早就对人与世界的本质问题提出了看法。其中既有认为“有”的观念,也有认为“无”的思想。比较起来,三地在这方面的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点。
古代中、希、印三地“有”“无”观念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无”概念的提出均可视为三地哲学思维明显提升的重要标志。在古印度,“有”“无”概念得到较明显的关注是在奥义书时期,此时古印度人的哲学思维表现活跃。在古希腊,“有”“无”概念受到人们重视,是这一国度的哲学思维有突出进展的时期。古代中国明确提出“有”“无”概念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有明显发展的时期。
第二,“有”“无”概念受到了三地的主要思想家或重要文献的重视。如古代中国的重要哲人老子和庄子是论述“有”“无”概念的主要代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论及这方面思想的著名哲人;古印度的奥义书和佛教的龙树是论述“有”“无”概念的主要代表。
第三,“有”“无”概念在三地许多哲人的论述话语中都是关联紧密的概念。如古印度《吠陀》中的《无有歌》将“有”与“无”概念对举;古希腊的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将“存在者”与“不存在者”相提并论;古代中国的王弼则说“凡有皆始于无”,将二者紧密关联在一起。
古代中、希、印三地“有”“无”观念的差别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古代希腊哲学将“有”的概念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视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古印度和中国哲学相对而言,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并未提到这样的高度。
第二,古印度哲学各派的理论中都涉及“有”“无”问题。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主要论述了“有”的意义,但从“无”联系到“有”的综合性论述不多,其他希腊哲人并非都对“有”“无”这组概念有一致的认知。古代中国哲人虽然很早就论及“有”“无”问题,但和印度哲学相比,对这一组概念的关注并未贯彻到各家各派。
第三,古代希腊哲人一般不把“有”“无”分割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强调二者中的一个产生另一个。古代中国则有“有生于无”或“从无出有”的说法。古代印度虽然有的派别论说事物的生成,但主流或影响大的派别倾向于否定有实在的“从无出有”。
综上所述,“有”“无”观念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东西方哲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从众多思想家在这方面提出的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哲学倾向,可以梳理出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古国在哲学上的发展脉络和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