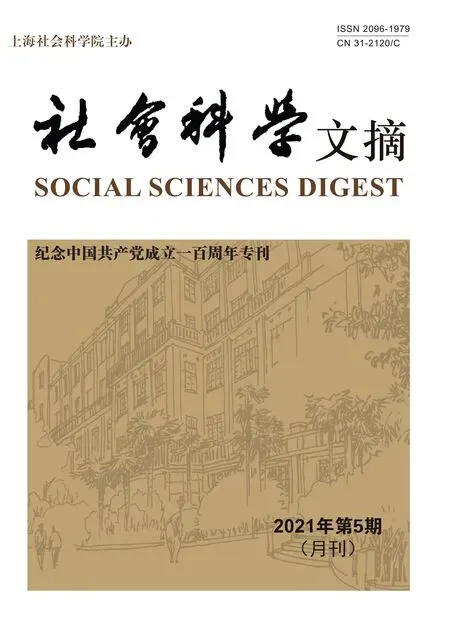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历史记忆与纪念
文/郭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作为一个经历风雨、创造历史的百年大党,诞辰纪念正是其光辉历程的最好见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自身诞辰的纪念,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7月1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事实上,就当时的认知而言,7月1日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而其作为党的正式诞生的纪念日却影响深远。因党创建历史的特殊性,加之距离当时已经相隔多年,革命战争年代又无暇顾及,难以保存相关档案材料,因此“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实际上正是党出于纪念需要而“发明的传统”,这被党的领导集体所认可并在党内达成共识,逐渐产生广泛影响。客观上,当时确定党的诞辰纪念需要有确切日期,但并未明确该日即党的实际成立日。建党纪念背后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多元景象,亲历者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也众说纷纭。改革开放后,不断有中共党史研究者试图揭开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之谜,以更好地服务于诞辰纪念,相关研究也成为纪念党的诞辰的重要方式。纪念日期或事件的选择只是因诞辰纪念需要作出的抉择,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具体、真实的历史事实,以及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党的诞辰纪念,理性对待党成立的相关记忆,可以实现党创建时的红船初心、责任使命与新时代党的新发展、新使命之间跨越历史的对话,将历史上的光辉灿烂不断引入当下,可以鼓舞人心,其意义非凡。
关于中共“一大”的早期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标志。因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大”代表们在会议召开时未能刻意留下这一伟大时刻的历史记忆,鲜有当时的历史资料存世,这造成了后来人们追溯“一大”召开具体日期时的困难。但实际上以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作为党的诞辰,正是党在革命斗争年代为了进行纪念而作出的选择,使党的诞辰纪念有“一大”记忆为凭借。
多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对“一大”的召开有不同回忆,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一大”的记忆叙述,应属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该文最先于1921年8—9月连载于《广东群报》,后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出版时间标为1921年7月1日,实际出版时间则在“一大”召开以后。因有避险因素的考量,文字颇隐晦,其中涉及时间的叙述有如下文字:“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当时陈公博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故到沪的时间至少在几天后,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毕竟距离不远,属于即时性回忆与叙述,所言较为可信。之所以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刻意记录下该重要历史时刻的具体日期,主要在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当事人于历史情境中尚没有如此意识。即便是陈公博即时性的回忆也未留下具体日期的任何痕迹,但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即中共“一大”召开于“七月十四日”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历程中,“一大”刚召开后的几年很少有人去回顾正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因此也没有留下太多关于“一大”的记忆。1929年的中共正面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相当复杂且困难的生存环境与政治局势,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党身份与地位,制定党的未来发展规划与目标。于是,历史记忆自然成为资鉴当下的重要资源。虽然这一时期开始有人回忆中共早期历史,但“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尚难确定,只能道出大致时间。无法确定日期的原因在于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党也在初步的成长过程之中,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这一问题。但诸多中共“一大”的参与者,却清晰地记得不少关于“一大”召开的细节与过程,此也符合人们进行记忆时存在的选择性记忆规律。随着时间流逝,记忆也越发模糊,但因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长壮大,人们逐渐意识到某些时间的象征意义及其重要性。不过,当时的回忆者似并没有将“一大”召开视为党的诞辰,诸人回忆皆“就事论事”,试图弄清并忆及“一大”召开日期及有关过程,也还没有将之作为党的诞辰纪念的明确意图。
“七一”诞辰纪念日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和纪念活动的举办,在党的创建之初即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等活动,借此宣扬劳工神圣,向普通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纪念活动视为政治宣传与动员的重要载体,但早期党较少举行与自身有关的纪念活动。直至 1930年才有南昌“八一”暴动纪念日等活动的操办,开始逐渐关注党自身重要事件的纪念,包括广州暴动、宁都暴动、“八一”暴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红色中华》创刊等。1933年,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更有力地调动苏区民众保卫根据地,实现“扩红”和筹款目标,中共隆重举行了“八一”纪念。该年“八一”纪念更是成为此后党相关纪念的样板。8月1日被当作“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习惯称之为“八一”节即建军节。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布文件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不宜再举行工农红军的建军纪念,但“在军队实现巨大历史任务转变之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加以凸显”,正是如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逐渐引起党的高度重视。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以集会形式纪念党的“诞辰”。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报告(即后来成文的著名的《论持久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这一重要命题,将之定在“七月一日”,并与抗战紧密联系。这为此后“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确立了记忆载体。最初毛泽东关于“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提法并未在党内引起共识,该年也没有官方文件将“七月一日”确定为建党纪念日。直至1939年“七一”前后,《新中华报》《抗敌报》《解放》《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铺天盖地发表关于中共建党的纪念文章,“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逐渐受到各方认可。当中共诞辰十九周年纪念来临之际,各方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已将中共成立纪念日定于“七一”,且似乎也意识到“七一”只是“成立”的象征符号,确立具体日期的目的是更好地进行纪念,更好地凸显纪念价值和意义,更好地记忆历史事件。
从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命题,经1939、1940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纪念活动开展建党纪念,到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对“七一”建党进行纪念,党的成立纪念日的确立和纪念活动的展开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该过程从党内核心领导的提议开始,逐渐得到党内的认同并以中央文件形式最终定型,出现了制度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确立和早期纪念活动的举行皆与抗日战争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通过纪念活动能更好地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更好地申明党的抗战路线和宗旨,以指导抗日战争。在“七一”建党纪念的过程中,也造就并深化了广大党员干部对“七一”建党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标志的历史印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逐渐得到各方认可。这生动地展现出一个纪念日的产生过程,“七一”从世俗时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最终被赋予神圣意义,成为象征时间。
“七一”纪念日的记忆追寻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定在“七一”,形成了以中共“一大”召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历史记忆。但中共“一大”召开的真实日期曾一度无法确定,“七一”只是象征性日期,“七一”纪念日的确定有因应抗日战争现实需要的意味,中国共产党官方也认可该节日使之颇具权威。虽然长期以来“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难以确定,但模糊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记忆并未影响到人们将“七一”视为“诞辰”的日子进行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回顾光辉历程的起点,希望弄清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于是追寻历史事实,开始广泛征集各方回忆。因为“七一”纪念逐渐影响到人们的回忆,并且记忆往往受当下环境影响,使不少人修改了他们的记忆。换言之,“七一”纪念日设置的目的和意义得以实现,它代表党诞生的记忆已深入人心,使不少人认为“七一”即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七一”被认定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董必武对此有较理性的认识,于是道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只是象征符号,既然“七一”已被赋予“诞辰”意义,那“不变也可以”,无意之间将各方关于“一大”的回忆提升至记忆理论层面进行认识。虽然记忆皆自认为真实,但往往受现实环境、个人情感等影响而存在移植、借用、建构乃至遗忘,根本上而言,记忆属于现实的产物。从当时诸多回忆而言,“七一”作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颇受质疑,但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共“诞辰”象征时间而存在。各方回忆中的疑惑显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活动的正常举行,中共诞辰记忆有了确切的表达方式,这也正是确定“七一”纪念日的意义所在。1950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共建党纪念,《人民日报》进行了广泛报道。新中国刚成立,中共即举行“七一”建党纪念,正表明对自身诞辰纪念的重视以及对“七一”建党纪念传统的重申。
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是一场特别隆重的活动,6月30日下午6时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共四万余人,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报告。对此,《人民日报》持续多日进行专题报道。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说:“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显然,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记忆对“七一”纪念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这些记忆更多停留于“私人领域”。
“诞辰”的确定与党史修改
长期以来,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一直存疑,没有资料能够提供确切证明。其实,早在1959年,董必武鉴别中央档案馆给他的几份文件中即已揭示出“7月23日”这一日期,只是较少为人注意,甚至有人觉得文件存在伪造嫌疑。直到1980年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才彻底解决该问题。据说,该研究成果还上报中共中央,得到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因“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还是决定不予改变。纪念往往属于象征表达,纪念时间与真实日期之间的误差也不难为人接受。
学者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叙述很早就较接近历史事实,李新、彭明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最早出版于1962年,其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叙述如下:“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不得不说这在当时属严谨且科学的表述,或许是受到1959年中央档案馆那几份文件的影响。198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分册)如此陈述:“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相对模糊的说法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也较为合理。随着相关史实的确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并且还专门用注释说明:“一大开幕日期是建国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八月一日或二日。在此以前,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规定七月一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七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该著述以注释形式较圆满回答和回应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问题。
通过各方论证,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的史实已获确定,后来各种党史表述均采纳了“7月23日”说法。虽说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已确定,但建党纪念日依旧为“七一”,纪念与记忆之间虽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纪念主要强调对象事物,只要对象事物并非虚构即可成立。记忆则往往强调事件的真实性,虽然有时距事实较远难以完全真实且经常被建构。同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实召开过,那该事件的存在即表明以中共“一大”纪念党的诞生是合理的,具体纪念日期则属次要问题。“七一”纪念的对象依旧是中共“诞辰”,并不存在因虚构而失去纪念对象的情况。此后至今,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均隆重举行,纪念话语虽发生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任务”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转变,但始终不离中国共产党追怀光辉历程、实现伟大使命这一根本宗旨。
结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记忆最开始并未与诞辰记忆有任何联系,但因时局发展等各方面需求,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到自身诞辰纪念的重要性,于是确定7月的第一日为建党纪念日。并且“七一”与“七七”产生连带效应,也是因应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七一”不仅用来宣传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也用来进行抗日战争动员和宣传。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及纪念活动的展开深刻影响到了当事人对中共“一大”的记忆。后来正式明确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后,建党纪念活动照例于“七一”举行,更凸显“七一”的象征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七一”建党纪念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记忆,而且每个时代皆体现出重要的精神引导。中共建党纪念日的创设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不能因日期有误而否认其地位。
中国共产党诞辰记忆包含相关历史人物的早期、晚期回忆,以及学者围绕回忆等资料的考证和讨论,但皆以探求历史的真确为目标。建党纪念在于阐发精神、鼓舞人心,更多地发挥政治宣传作用。纪念根植于记忆又影响到记忆,但是记忆与纪念皆围绕曾经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进行历史性追怀,铭记光辉历史时刻,从而将神圣过往不断接引到现实世界。记忆是人类传承历史和精神的一种方式,纪念则是人类传承与再创精神的一种表达。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风雨,不仅要正确认识党成立的历史,也要正确认识党的成立纪念,更应理性对待关于党诞生的相关记忆。今天我们仍要通过记忆追怀,不断强调和唤醒党的“初心”,将历史上的光辉神圣不断引入当下,鼓舞全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承担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