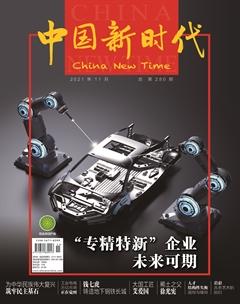稀土之父 徐光宪
宋小芹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徐光宪和他的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稀土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使我國的稀土分离技术和产业化水平跃居国际领先水平。
稀土是在冶金、军事、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领域广泛应用的一种重要元素,素有“工业维生素”之称。稀土在磁、光、电等性能上的优势明显,对改善产品性能、提高生产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到中国的稀土,我们要提到一位国际著名的化学家,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
徐光宪一生情系于祖国,根据国家的需要,4次转换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徐光宪和他的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稀土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使我国的稀土分离技术和产业化水平跃居国际领先水平。
坎坷求学路
1920年11月7日,徐光宪出生在浙江绍兴。徐光宪的父亲徐宜况早年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从事律师工作。他精通《九章算术》,爱好围棋,在徐光宪幼时便常常以“鸡兔同笼”问题和围棋启发他对数学的兴趣,培养他的逻辑思维。母亲陈氏教子甚严,自幼告诫他:“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之下,小学时的徐光宪就以勤奋刻苦著称乡里。
徐光宪十几岁的时候,徐家家道中落。徐光宪在父亲的影响下,抱着想要成为一名工程师的愿望,考入了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不久,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学校随之解散。1938年夏天,徐光宪转学至宁波高工,继续艰难的求学之路,吃、住、上课都在一座小寺庙里。靠着白天听课、晚上借路灯“秉烛夜读”的劲头,他啃完了几本大学英文教材;高工毕业后,他的旅费被骗,身无分文,只身来到上海。在大哥徐光宇的帮助下,他插班进入大同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就读,半年后又考入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
当时的交通大学一部在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教室上课,徐光宪和同学们挤在简陋的教室里解析艰涩的化学方程式,用残留下来的仪器做实验。在大学校园里,徐光宪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不知疲倦地充实自己。在大学的整整4年,徐光宪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回忆起特殊年代的大学生活,徐光宪说:“进上海交大时,是5:1的录取率,能考进交大的都是江浙一带名牌高中的优秀生,他们的基础都非常好。我是靠自学考进来的,所以一点都不敢懈怠。那时,在上数理化等基础课时,都是几个专业的学生同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数学的胡敦复先生、教物理的裘维裕先生和教化学的张我裁先生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他们上课全用英文讲授。每学期要大考一次、中考两次,每次中考又分为开卷考和闭卷考。在前两年中,每次大考总会有10%~20%的人留级,能够在交大顺利毕业实属不易。”
科学研究要胸怀祖国
大学毕业两年后,徐光宪参加并通过了当时全国各地区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的考试,并于1947年年底只身赴美。他先到圣路易斯城的华盛顿大学化工系学习,一个学期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暑期班试读,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校聘助教奖学金。
1951年3月,徐光宪凭借论文《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获得博士学位,从入学到获得博士学位,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当时他已经当选为美国Phi Lambda 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接连荣获两枚象征“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前途一片光明。
就在这时,大洋彼岸传来消息:抗美援朝爆发了。美国即将通过法案,要求全体留美学生加入美籍,不准回国。此时如果不加紧回国,那么就回不去了,但这时徐光宪的妻子高小霞的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高小霞的一句话坚定了丈夫回国的决心。她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为此,高小霞毅然放弃了博士学位,两人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毅然踏上了回国之路。
回国后,徐光宪夫妻俩双双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的科研条件跟国外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徐光宪却充满激情,并先后在量子化学、配位化学和核燃料化学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1951年,徐光宪为学生们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培养了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新北大成立后,徐光宪又负责主讲新开的物质结构课。“那时,人心很团结,能在工作中体会到共同的乐趣。”在那段时光中,徐光宪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学校新开‘物质结构课,没教材,教育部指定了四个人编写——唐敖庆、吴征铠、卢嘉锡,还有我。那时,同行们都管他们三个叫‘糖葫芦(谐音),所以我也常常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串‘糖葫芦。”徐光宪和三个朋友“隐居”青岛,从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书,夜以继日,每人每天写1万余字。结果最后这本共同编写的教材由于内容过多,被教育部选为参考书。
这本“讲义”,就是至今在学界仍享有盛誉的《物质结构》。它于1988年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化学一级学科领域获此殊荣的唯一教材,发行20余万册,影响十分深远。
改变稀土世界格局
“只有置身于稀土元素周期表和稀土4F轨道模型之间,徐先生才会怡然而坐。”了解徐光宪的人如是说。
徐光宪事业的巅峰,是跟稀土工业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素有“稀土王国”之称。但精练技术被当作“高级机密”掌握在少数外国制造商手中,对中国全面实施技术封锁,并试图通过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来获得长期利润。中国不得不高价进口稀土深加工产品,使我国长期处于资源无法合理利用的困境。
1972年,为改变我国稀土工业落后的面貌,徐光宪将研究方向转向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那时,稀土分离在全世界都是尚未解决的难题,对于徐光宪而言同样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只说了8个字,“祖国需要服从安排”。
“徐老师,您看萃取箱放这里行不行?”“徐老师,您看药剂混合后出现这种颜色是否合格?”“徐老师,这是刚才测得的数据,您看看。”……
40多年前包头的包钢有色金属三厂(现包钢稀土集团公司的前身)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稀土分离工艺的试验。忙碌的人群中依稀能见到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不时回应着周围工人们的提问,有条不紊地指导着试验工作的开展。这位工人们口中的“徐老师”,正是徐光宪。
“(镨钕)这两种元素比孪生兄弟还像,分离难度极大。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却长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我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再难也要上。”查阅资料时徐光宪发现,分离镨和钕的问题,国外学界也尚未很好解决。徐光宪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选择萃取法分离。
为了实现这次前无古人的尝试,他付出了百倍的辛劳与磨砺:住实验室、啃干面包,在北京和出产稀土的包头矿山之间来回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整整3年,徐光宪和他的团队终于取得突破。经过大量对比萃取剂,反复实验,徐光宪的团队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1974年9月-10月,通过新工艺流程的工业规模试验,徐光宪独创的稀土分离“三出口”工艺开始显示出威力。中国稀土分离从此告别了繁琐的“摇漏斗”,中国的稀土产业摆脱了“守着金饭碗要饭”的困境,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
1975年8月,第一次全国稀土会议在京召开。徐光宪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串级萃取理论,他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因为徐光宪团队的科研成果,中国出口了大量高纯稀土,占世界产量的80%以上。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冲击下,使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到30%~40%,打破了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对稀土的垄断。
2009年1月9日,近90岁高龄的徐光宪凭借在稀土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对于获奖,徐光宪显得非常谦虚:“这是诸多我曾经的学生和团队集体做出的成绩,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除了改变中国稀土工业的局面之外,徐光憲还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其中就有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徐光宪曾说,自己最大的安慰和自豪就是培养了一批能力和成就大大超过了自己的好学生,“例如在稀土串级萃取理论方面,严纯华带着他的博士生取消了‘恒定混合萃取比的假定,使之适用于江西重稀土元素的分离。在量子化学理论方面,黎乐民院士早已超过了我。在稀土光电功能材料方面,黄春辉院士取得了卓越成就……这让我感到高兴,假如学生不能超过先生,国家就不能进步。这不是谦虚的话,而是实事求是。”
作为教师,徐光宪上课从不迟到,他常说,讲课比天大。
“徐先生的敬业令我们汗颜。他教学几十年,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他总是要求我们在上讲台前,把准备在课堂上说的话想好,准备在黑板上写的字设计好,讲稿要预先印出来发给学生,但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其实这也是他给自己订的规矩啊。”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赵深回忆过去,感慨不已。
据学生们回忆,徐光宪授课细致认真,一口绍兴味的普通话,耐心细致地推导和解释问题。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几十年里,他先后讲过物理化学、物质结构、原子核物理导论、量子化学理论、原子核物理统计学、分子光谱理论等12门不同的课程。他说:“从学生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对我的讲课很满意,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自幼喜欢数理化,有科学报国的理想。这个理想终于能够逐步实现,对我而言非常幸福。”
此外,他还在编写教材上下了功夫,希望学生在学习完课程后,能够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因为意识到逻辑思维训练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都特别注重习题练习与训练,课前5分钟的习题测验,是他上课的特色。他希望学生做完习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除了传授知识之外,他对学生的关心也让人津津乐道。
20世纪70年代初,黎健夫妇的孩子得了脑瘫,一家人生活拮据。黎健是个稳重的人,这一切只是自己默默承受。徐光宪知道学生的困难后,每月用稿费接济这个贫困的家庭。某年正月初一清晨,黎健夫妇正陪着儿子吃饺子时,徐光宪敲门而入,手里提着烧鸡和八宝饭。给孩子派发红包后,徐光宪陪着他们一起吃饺子,欢笑声一直洋溢在北京西郊的小院里。
徐光宪的爱心,还涉及素不相识的人。《物质结构》一书完成后,徐光宪收到5000多元稿费,他把这些稿费全部捐给了北大技术物理系工会,让工会用来补助困难教职工。当时,5000多元是很大一笔钱,听到徐光宪“不要声张”的请求,工会的同志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2015年4月28日,徐光宪逝世,享年95岁。斯人已去,但徐光宪的话却被学生口耳相传:“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未来需要你们年轻人担负起来。”他会如同星空上闪耀的恒星一般,照亮新一代的中国人前行的道路,他的谆谆教诲,也会被所有人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