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操控下的中国早期电影产业
杨昆

电影于19世纪末在法国诞生,依靠商业放映走遍全球,第二年便同步传入中国,但其起步之艰难,运营之艰辛,却难以想象。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影业迎来发展热潮,离不开同时期金融市场的活跃与支持,包括明星、联华、电通等在内的最早一批中国电影公司,在学习各国企业管理经验、摸索企业资金运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电影金融的基本思路与独特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才有了20世纪初的“华莱坞”,才有了如今仍可回忆的“黄金时代”。
融资能力决定早期电影企业竞争力
从电影经济学来看,外部环境决定行业的资本流通,电影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才、技术、设备等电影基本生产要素的汇集,关系到电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创作方向。
20世纪初的世界电影市场中美国电影首屈一指,每年电影产业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光在制片业上的投资约2亿美元,年产800多部影片,占放映市场的60%-90%。摩根、洛克菲勒等华尔街资本大鳄利用各大电影制片公司自身扩张的融资需要,通过资本手段控制制片业。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使美国电影业成为可与汽车制造业、钢铁业、石油业、烟草业相比拟的重资本工业。
此阶段的中国电影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创作制片、技术升级、宣传放映等环节都亟需大量资金支持,但行业资本总量与美国电影业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政治、经济、战争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早期电影业常常陷入资金匮乏的境地。到1927年,全国电影公司的数量为历年之最,达到175家,电影院156家,到1930年,电影院增长至233家,可以容纳13万人,比1927年增加49.3%。但1931年开始我国金融环境急剧恶化,白银大量外流,民国政府颁布“禁银出口令”仍无济于事,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导致电影市场出现“资本荒”,资本呈现出严重的供需失调。时至1933年,上海小型電影公司只剩34家,两年后,仅存2家。1935年,华资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分行相继宣告歇业。上海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高达50万。电影公司资不抵债、裁员降薪,影片数量下降,大量公司陷入资金困顿而倒闭破产,“厦门影院原有八家,近受不景气影响,陆续关闭,仅存中华、思明两家”,“大连以前亦有影院三家,但今日亦已大非昔比。目前虽只有新世界影院一家,仍然无法维持,端午节后,业已关门大吉”,“澳门表面上虽极发达……而实际则皆外强中干,无利可图”。
电影业渐入“寒冬”。
为谋求行业发展,早期电影人的融资实践活动十分积极,融资方式多样化,最直接的莫过于从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取得的贷款。金融机构总是青睐大规模、实力雄厚、拥有一定自有设备的公司,但电影公司资产规模整体偏低,那些要靠租用设备、更需资金救厂的小公司,通常难以借到款项。资金最充足的天一公司1925年创立时为1万元资本,发展至1933年资产总额为50万元,明星公司也由最初的近万元资本增长至1929年的31.2万元。这与银行重点投资的动辄百万资本的面粉、棉纺织公司无法相比。但即便是大公司,对于银行高额的利息,也深感困难。实业家刘鸿生曾说,“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而且届期催还得很紧。”像刘鸿生这样拥有火柴、水泥、毛织等多个企业集团的大企业家尚对银行借款有如此感受,对刚刚起步的电影公司而言银行很少雪中送炭,更多的是雪上加霜。
在整个市场环境下,融资能力成为电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融资能力的本质在于企业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是由企业的资产规模、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发展潜力、资本结构、社会资源和社会声誉等因素综合构成。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电影产业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大、中、小型公司并存的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典型的“二八法则”。1922年至1937年间,全国影片公司约有175家。以1934年的国产影片数据为例,年生产数量排前十五名的制片公司,其生产总量为81部电影,共218602公尺,占全年国产影片数量的79.41%,长度总量的80.52%。产量最高的明星公司,一家出品量即占总数的22.55%。当年有电影长片出品的制片公司共36家,其中75%的公司全年只出品一部长片电影,资本相对薄弱。
刚刚起步的规模较小的电影公司融资极为困难。影片的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匮乏的小公司往往生产一两部影片就破产,当时行业中出现很多“一片公司”甚至是“零片公司”。这也反映出,当时的电影市场资本基本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这些公司的规模因资金的聚集而不断扩大,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和技术的汇集,优化了资源配置。特别是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或者本身经营不具备竞争优势时,债权融资所带来的财务压力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抵押(质押)贷款是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
实业发展依赖金融,电影业更是如此。电影企业的投资人或经营者中就有不少曾经的金融人士,天一公司的创办者邵醉翁曾经是中法振业银行行长,上海大世界经理黄楚九同时兼营日夜银行。
银行借款是债权融资最主要的方式,但20世纪初的电影业向银行融资十分困难。当时中国银行80%的贷款在丝业、棉纱和面粉三个行业。电影属于新型行业,投资风险较高,并不是银行青睐的投资对象。银行的贷款方式中以厂基地契、固定资产抵押的占44.36%,信用借款及贴现占16.01%,物料抵押及押汇占39.61%。作为轻资产的电影公司,厂基、机器等价值较高的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成为电影债权融资的主要方式。
电影公司的银行借款中,相比“在华之外国银行,资本既富,存息不过二厘,放息亦极低廉。一次贷放,一百万或二百万元,咄嗟并至,毫无难色”,我国银行资本存量、贷款利息等方面均难以和外资银行进行抗衡。1936年明星公司向交通银行的贷款利率为“常年玖厘每叁个月付息一次定期叁年”。因此,在电影公司的银行融资初期,向外资银行贷款显然是更为经济的选择。
明星公司是中国早期电影业最有影响的公司之一,银行借款一直是其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外部融资方式之一。以1930年为例,当年明星公司向各大银行还款付息的来往包括:东亚银行来往483.91元,道一银行来往6680.451元,泰昌钱庄来往1335.646元,津庄来往2647.95元,俱乐部693.129元,共计11841.086元,虽然总额并不多,但已经与多家金融机构保持联系。明星公司后来的发展越发离不开银行的支持。1931年11月,明星公司向美商汇众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将公司的30余亩土地地契作为抵押物,向汇众银行借款48万两,订期2年。5年后,公司财务陷入危机,汇众银行贷款项尚未还清,又举新债。1936年,明星公司将枫林桥厂基、机器、影片版权等资财为抵押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16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偿还前债。
另一业内翘楚联华影业公司亦向银行举债融资。该公司成立时虽以资本充足、资源丰富著称,但其创立实为几家公司合并而成,本身资本关系较为松散。当30年代上海爆发战争后,该公司经营模式的弊端就显露出来。同样遭受资本匮乏之限制,不得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融资。
几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依靠借款度过了一个个经济困难的时刻,但对于资本市场僧多粥少的现象,在当时属于投资风险大、收益不明确的新兴电影业,商业信用、社会关系等软信息是除企业资产外最为重要有效的融资来源。弱化资产抵押,提倡“信用”基础的思想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为电影公司的融资模式提供了借鉴。
当企业公布他们的银行借款信息时,也是对其他潜在债权人发出一个商业信用的暗示。这样的信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和公司价值。但倘若是一个不利于公司的信号,则会造成相反的结果。1936年,明星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未果。周剑云从中斡旋,江苏省政府陈果夫主席的亲笔发函,为明星公司与交通银行的贷款进行沟通。在当时紧张的资本环境及窘迫的公司境况下,这封政府官员的背书成为明星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关键,周剑云也因此提升了在明星的地位,成为公司核心人物。
明星公司向银行虽然成功取得融资,但加大了公司财务杠杆,背负起更重的债务。再加上外部社会环境和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明星公司后来在《民报》上发布了《革新宣言》,效仿欧洲电影公司的经营模式,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但其革新也未能挽救公司的命运,又举债银团,最终受控于资本。
电通公司向国华银行的借款也是采用“资产+信用”的融资模式。据张云乔回忆,电通公司在拍摄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时,由于资金短缺险些拍不下去,依靠银行借款勉强完成,“只是签订一纸书面契约即可。”但这样的信用也是与公司摄影机和录影机为抵押物的前提相融合的。
版权质押在中国早期电影融资中被较早应用。1936年,明星公司向交通银行进行的总额16万元的借款即采取“版权+资产”的融资模式。借款合同约定,在明星公司尚未还清借款期间,该公司所拍摄所有影片,由交通银行承接影片审查及相关手续办理,先行享有影片收益的分配权力,扣除每月应还本息额之后,再予明星公司进行支配。此项借款的质押物是借款期间公司出品的所有影片,其本质考量的是明星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而非特指某一部影片的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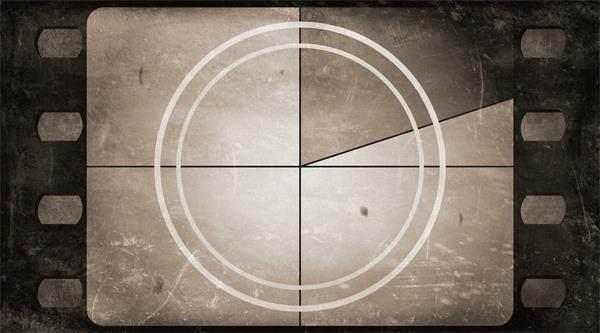
前期征信、后期风控为融资提供保障
随着当时电影融资业务的增多,投资者开始引入中介服务和中介机构,综合考量参与主体、交易规模及流程规范,全面加强事前事后的风险防控措施。
征信业务为早期电影信贷提供了中介服务。
征信业务是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基础,也是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的重要参考因素。征信所搜集掌握的大量企业信息,是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决策时重要的数据资源。1932年6月第一家华资征信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成立,打破了外商对商业信息的垄断。
中国征信所史无前例地对数家电影公司做了长期的、持续的征信调查,并将调查资料整理成报告或出版物,说明当时电影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目标,资本市场有電影公司的投资调查需求,现有的投资者或潜在的投资者愿意花钱去购买此类信息。以上海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关注电影市场,对电影制片、电影发行、电影器材等公司的营业情形、盈亏状况、财政状况、组织结构、主要人员、经理简介等信息做了详细的调查,其中不仅包括华资的几大电影公司,对外资公司也做了研究,同时出具英文报告供外资投资人参考。这样的信息获取是中国传统钱庄借贷、私人借款等融资模式的传承,建立在对借款人的资财实力、身份背景和社会关系信任的基础之上,具有人情社会下融资的典型特征。这和当今银行贷款、关系型融资流程中的个人信用调查有类似之处。从中国征信所最终提供的长达168页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持续经营的大型公司,往往具有两到三次的反复调查。

银行的风险控制和后期监管。
银行贷款风险防控除了前期的征信调查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在项目摄制过程中的生产流程监督和资金安全把控。当时银行采取专人负责监督项目整个生产制作过程,以保证电影投资人投资的电影产品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如期按预算完成交付。在明星公司和交通银行的贷款合同中,交通银行专门委派专员,负责稽核账目,管理质押物等。且“派员常川驻厂其薪金规定按月为国币肆拾元概由乙方(明星公司)负担其膳宿并由乙方供给之”。目的是要保证公司的资金用途,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财务账目是一个公司的核心信息,债权人的深层次介入,使得金融机构充分掌握债务人的,有助于保证资金的安全。
为保证债务人明星公司正常的制片活动,恢复其生产,交通银行每月先行垫付影片拍摄资金,对影片的主题内容有了更深层次的控制,合同中约定:……将由交通银行每片先行垫付制片费三万元,而每月预订摄制两片,则就是说交通银行每月须垫款六万元。——其条件则是以后明星影片收入概归交通银行管理,此项垫款,即于收入中陆续清还。因为,据说明星公司的出品,每一片的营业收入,可由四万元至五万元。此垫款的投资对象由公司变成了具体的影片,合同中明确了明星公司在规定时间内需要完成的影片数量和金额预算,保证债权人投资项目的完工时间和资金使用。
这样的融资模式显然会对投资方带来较大的资金风险:
其一,交通银行非专业人士,作为投资方,专业信息有限,对影片的经营与生产等信息有限,容易因为投资方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即明星公司比交通银行有更多关于影片成本、预期票房、发行渠道等方面信息,而明星公司又不需要对每一部影片的拍摄质量和经济效益承担风险。在经济学中,融资方可能会采取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从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其二,债务人制片时期和周期问题。该垫支融资形成的条件是明星公司每月拍摄两部影片,这是对公司制片的时期和数量的约定,也是债权人资金回流的保障。但自1936年6月融资之后,明星的生产效率远未达到预期水平。1936年6月至1937年4月的11个月时间里,该公司仅向电影检查委员会上报审查影片14部,与合同的约定相去甚远。显然这样的约定并没有更多的条款来担保,导致在后来明星公司未能如期完成工作量,公司陷入了更严重的财务危机。而未完工影片所带来的风险需要交通银行去承担。
其三,影片垫支资金的违约风险防控和资金性质不明晰。双方的约定是自此经营由明星公司收入陆续清还,即便是交通银行派财务人员常驻“明星”,监督其每日财务流水,但此举是事后监督行为。对于债务的偿还并没有在事前进行明确约定。该资金名称上为“垫付”,即债务融资,无论明星公司经营状况如何,都需要偿还本金利息。但此期间明星公司出品的一切影片均归交通银行管理运营,又具有股权融资的特点。且该垫款是专门针对交通银行预订的两部影片,但却需要明星公司的所有收入用来偿还,资金投入和回报的范围明显不同。导致后来交通银行按照每月6万元的资金投入,但明星公司并未按约定专款专用,而是将资金投入到其他影片的制作中,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项目融资和公司融资不同,它的特点是资金具有专项性、期限性和阶段性,即资金的流入流出较为简单明晰,应当是与项目密切相关。与项目无关的支出不能从该资金中列支。但显然从这笔借款合同以及后期双方的问题中并未有完善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融资模式没有解决制片公司的完工风险问题,事实上,明星公司在后期的经营过程中,确实未能如期履行影片摄制合约。交通银行的多次催促下,其订制的每月两部电影仍未能如期完工,明星公司却同时为新的债权人“星光影业社”开始拍摄影片。交通银行曾屡次与明星公司交涉,但却因没有更多的担保和惩罚条款,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也是在美国电影业后来形成完片担保制度中担保机构对项目制片完成的担保,银行只有接到完片担保公司出具的第三方保障背书,才会发放贷款。
民国电影公司向银行贷款是普遍采取的一种融资方式。资本与公司的博弈渗透进早期电影业,银行贷款条件苛刻,融资成本高,考量电影公司经营者的社会关系。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的电影公司,很难在与投资人的较量中占优势地位。形成了早期中国电影业中经营者、投资者、创作者间的“三权分立”关系。资本投资的目的在于最终对电影公司的控制,当年“北四行”之首的金城银行曾给上海大华戏院放款1万元,从银行记录中可见其放款目的,“先是发生放款关系,之后乘机收购企业股票或承购其发行的公司债,在此基础上再行扩大放款”。明星公司、联华公司最后也难逃被银团资本控制的命运。除此之外,资本还通过投资深入影响电影创作的主题内容及演员挑选,形成深度参与。南洋片商作为债权人,曾干涉影片《荒江女侠》的演员选择。交通银行作为贷款方,明确表示出对女演员胡蝶的青睐,将影片的演员选取与投资额直接挂钩。据夏衍回忆,1933年5-6月时,一次周剑云找我谈话,说自《铁板红泪录》《狂流》两部影片放映后,潘公展曾两次对他提出警告,若明星公司不改变作风,今后就不能得到银行贷款。明显可见资本在二者关系中的强势。
中國电影业融资模式的逐步成熟,是综合因素下中国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发展的成效,也是早期电影业成长的表现。资本给中国早期电影业中各个环节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为电影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加深了对行业的影响和控制,二者持续的较量是电影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规律。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早期电影业投融资研究(1905-1937)”(2020SJA0403)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