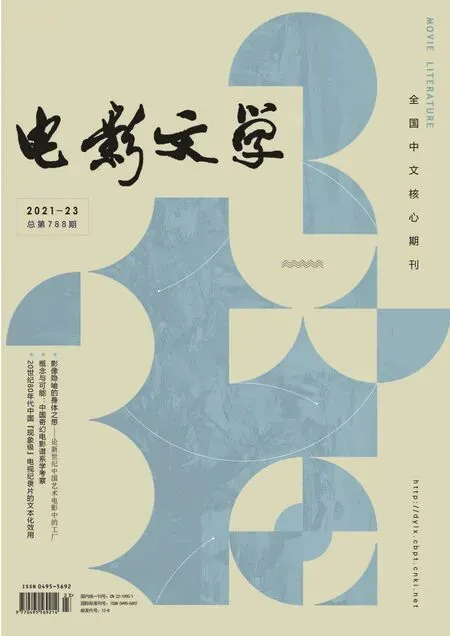瑞典早期电影的主流叙事与美学表达
宋雁蓉 杨穗益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
一、瑞典电影的诞生
瑞典历来有着重视民族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这使得电影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推广。1985年2月,爱迪生公司的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在斯德哥尔摩向公众进行展示。瑞典电影从放映之日起,很快就有意识地进入了主流文化的视野,从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电影,半年后的1896年6月28日,瑞典迎来了与电影的初次邂逅。瑞典首次的电影放映是由瑞典人罗伊克尔在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举办的放映活动,名为“巴黎人的电影”,在为期三个月的放映活动中,大约迎来了35000名观众,此时放映的影片均来自卢米埃尔兄弟所拍摄。
1896年11月30日,在瑞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斯德哥尔摩动物园的滑稽遭遇》(Komische
Begegnungim
Tiergartenzu
Stockholm
,1897)(又译:《醉汉在旧城里的争吵》)诞生,本片的导演是来自德国柏林的麦克斯·斯卡拉丹诺斯基(Max Skladanowsky,1863—1939),这部54秒的喜剧短片由两个镜头组成,记录了1896年在瑞典斯堪森(Skansen)入口处的滑稽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诞生之初,以《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单场景为主的短片中,本片由两个场景组接而成还是极为少见甚至是前卫的。1897年夏天,虽然在斯德哥尔摩的几个地方已经有了定期的影片放映活动,但直到1904年4月,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Kungsträdgården)旁才开设了第一家电影院——布兰奇电影院(Blanchs Movie Theatre)。这期间瑞典导演并没有大规模从事电影拍摄的实践活动,仅是陆陆续续地在各个城市修建影院,所放映的电影大多来源于法国,以及电影创作极度活跃的邻国——丹麦。国外资本逐渐注意到瑞典这块电影市场的处女地,法国、德国和英国商人相继来到瑞典从事活动影像的放映,早期工会组织和教堂也经常进行电影的放映,电影逐渐开始在瑞典的咖啡馆、游乐场、乡村等场所放映。
1905年8月,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影院公司(Handelsbolaget Kristianstads Biograf-Teater)注册成立,创办者是身为书店助理的古斯塔夫·比约克曼(Gustaf Björkman)以及自行车和缝纫机经销商尼尔斯·汉森·尼兰德(Nils Hansson Nylander),公司成立初期从事影像拍摄及后期制作业务。1905年9月5日,二人成立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第一家电影院在提沃利加坦(Tivoligatan)开业,这是一家由老旧的房间改建而成,能够容纳96名观众的影院。这段时间里,影院老板开始通过大量的广告吸引观众。
1907年2月16日,为了避免恶劣的竞争局面,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SvenskaBiografteaternAB)在克里斯蒂安斯塔德成立,创始人包括电影院老板尼尔斯·汉森·尼兰德(Nils Hansson Nylander)、银行家(Frans G.Wiberg),一位律师、一位药剂师。该公司的起始资金为15万瑞典克朗,在全国拥有19家电影院。因此,创始人的理念是为自己的电影院提供本公司制作的电影,即制作、发行、放映一体化。
1909年,查尔斯·麦格努森(Charles Magnusson)作为制片人加入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为早期瑞典电影学派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12年,瑞典电影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生产电影,公司从克里斯蒂安斯塔德搬迁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修建了电影摄影棚、电影实验室。查尔斯·麦格努森聘请了剧院工作的演员经纪人兼演员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其好友导演兼演员莫里兹·斯蒂勒作为公司导演。两人在1914—1921年短短七年时间,开创了早期瑞典电影学派的辉煌,这个时期的瑞典电影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默片的创作走向,这个时期的瑞典也被称为艺术电影的乐土。
在瑞典的20世纪头十年,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莫里兹·斯蒂勒主导的瑞典电影学派,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伯格曼电影对于电影艺术做了伟大贡献。一个国家的电影历经两次高峰时期,放眼世界也屈指可数,这背后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
二、瑞典电影学派的主流叙事
电影无疑是最适合呈现社会现实景象的艺术门类,柴伐蒂尼的长篇宣言中论及:“因为电影只有在它能提供它那个时代的事件和集体性悲剧的意义时,它才能够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段,一种人类和社会的通用语言。”
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795年所著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最早提出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宽泛庞杂的概念,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相对。“素朴的诗则为生活的景象所激动,它把我们带回到生活中去。”可见,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最容易贴近大众的。诚如钟惦棐先生所说,“电影不坚持现实主义,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电影现实主义的有无,将最终决定电影是否能够成为“最重要的艺术”。
首先,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将现实原封不动地机械照搬,而是需要创作者进行选择和加工,在基于现实客观性基础之上进行的二次加工;达到典型性的特征,实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创作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者的倾向性显得尤为重要,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是利用事实故事对于观众进行说教,而是在内容表达时,要自然地流露,创作者的观点越隐蔽,对艺术作品而言越好。在创作者对于现实问题进行反思的同时,这种表达的自然流露也被观众所接受,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完成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思和社会现状的揭示。
(一)瑞典学派的现实主义叙事开创
1913年,在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加入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的第二年,现实主义的创作与表现手段在《英格堡·霍尔姆》中已然显现,这部北欧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现实主义电影改编自尼尔斯·克洛克的舞台剧。
影片讲述的是斯文·霍尔姆和妻子英格堡·霍尔姆有着幸福的婚姻,丈夫患上严重的肺病后不久离世,由于英格堡缺乏管理经验,经营的店铺也随之倒闭,破产带来的贫穷,加之英格堡·霍尔姆生病,使她不得不来到济贫院,将三个孩子与其说是寄养不如说是“售卖”到有钱人的家庭。分别一段时间后,得知小女儿瓦尔堡·霍尔姆生病后英格堡不顾一切立马前往探望,之后又发现最小的儿子已经不认识自己,双重打击之下让英格堡精神失常。15年之后,作为海军的大儿子艾瑞克·霍尔姆通过早年的照片让母亲恢复理智。
《英格堡·霍尔姆》表现了斯约斯特洛姆对于瑞典现实社会的关切,尖锐有力地直击社会痛点——在20世纪初,瑞典当时的贫民法案其中的一个法律漏洞,可以使得投机者依据法规从贫穷的寡妇身边“购买”她的子女,电影敢于直面社会中不合理的济贫制度,并且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促使在20世纪初期的瑞典贫民法案的修改通过。这也是电影史上由于影片放映所引发民众广泛讨论,使得当局进行政策改革的首例影片。
从中可以发现,《英格堡·霍尔姆》对于瑞典社会状态和底层人群的关注,远早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于罗马社会百态的表现。本片也证实了电影不仅具有娱乐大众,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电影更是具有严肃的教化功能,身兼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甚至成为反映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百年过去,由我国青年导演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引发大众对于假药的广泛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针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改革。可见,瑞典电影学派的现实主义叙事依然对于当下现实主义作品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瑞典学派剧作中戏剧性张力构建
美国戏剧理论家乔治·贝克对于戏剧性的定义为:“以虚构人物的表演,通过感情渠道,使场内普通观众发生兴趣。”作为表现矛盾和冲突的美学手法,戏剧性一词涵盖广泛内容庞杂。简而言之可论述为演员在假定的故事情景之中,对于角色心理活动的外化表现。为了集中显现矛盾,戏剧性也常涵盖突发性、巧合与偶然等表现手段。
“早期瑞典电影的戏剧性往往是由斗争所激发的。”对于这种戏剧性背后的斗争,笔者做出以下概括:首先,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种人际斗争更具体地体现为人与父权的斗争。莫里兹·斯蒂勒的处女作《母亲与女儿》(Mor
och
dotter
,1912)就体现了这一点,虽然本片中父亲始终缺席,但母亲艾尔维拉和其女儿对拉男子乌尔的爱情被社会中的道德伦理这一无形的父权所驱散;《孩子》(Barnet
,1913)中,玛丽和乔治彼此相爱,但乔治被玛丽的父亲以缺乏安全感为由拆散了二人;讲述少女与父亲强烈争吵后的离家的《当爱情结束时》(N
är
k
ärleken
d
ödar
,1913)。《命运之子》(The
Son
of
Destiny
,1915)中,吉卜赛国王之女艾拉与异族男生子通婚,被国王驱逐出部落的故事。讲述对待感情不专一的富二代奥洛夫,爱上了女仆艾丽后与父亲起肢体冲突后离家出走的《红花之歌》(The
Song
of
the
Scarlet
Flower
,1919)。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导演的处女作《园丁》中被父亲拆散的年轻人幸福的爱情。充满幻想爬上“天梯”与已故的父辈、祖先沟通的《英格玛之子》(Sons
of
Ingmar
,1919)。可见瑞典电影学派对于父权社会的反抗意识,在20世纪头十年在电影中已有传达。其次,来自人与社会环境的斗争。比如《英格堡·霍尔姆》(Ingeborg
Holm
,1913)中漏洞百出的社会济贫制度对于单身母亲英格堡的迫害;《罢工》(Strejken
,1914)中贫穷的老人为了生计偷取了一些木头,却被当局判处多年的劳役;《塞尔日·维根》 (Terje
Vigen
,1917)中沧桑归来的维根发现妻女已故,内心的孤独寂寞与复仇愤怒外化为窗外的海浪击打着海边的礁石;《阿尔纳的宝藏》(Herr
Arnes
pengar
,1919),被大雪冰封的海面阻碍了通行,在等待交通复苏时,主角阿奇和艾尔丽莎相爱到最后的生死相隔;《最强》(Den
starkaste
,1929)中船长拉尔森和助手奥莱在海航和冰川里艰难的捕猎之旅;在《尤哈》(Johan
,1921)中,陌生的青年男子与马特里在小船上幽会,急湍的河流外化成道德卫士对有夫之妇的马特里进行道德审判等。最后,来自角色自我内心的斗争,如《走向幸福》(Erotikon
,1920)里陷入情感与伦理困境的教授利奥;《幽灵马车》(The
Phantom
Carriage
,1921)中回溯自己生前犯下的过错中得到基督之爱的拯救,实现了自我的救赎的大卫;《生死恋》里为了逃亡而无奈隐瞒自己已婚,有罪在身的流浪汉艾文德等。在斯约斯特洛姆和斯蒂勒涉足电影之前,两人便是经验丰富的戏剧演员和导演,深谙戏剧性之于故事情景的重要性,也得益于早年的戏剧经历,这让他们在电影创作时对于角色之间的矛盾关系把握、戏剧节奏的编排能够游刃有余。
(三)瑞典电影学派的剧作策略抉择
瑞典电影学派建立之初就表现出与文学作品的亲缘性,大量经典名片的剧本是由现成的文学著作改编而成,这在斯约斯特洛姆和斯蒂勒的电影代表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创作模式主要是电影公司和当时有名的作家签约或购买其著作的电影改编权,再由电影公司的职业编剧参与改编而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与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1858—1940)的合作,她的代表作《尼厄斯骑鹅旅行记》被称为与《安徒生童话》齐名的儿童文学。由于她的作品中有着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充满画面的想象力和平易而优美的语言风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成为瑞典第一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
斯约斯特洛姆导演的《暴风农场来的女孩》(1917)、《英格玛之子》(1919)、《幽灵马车》(1921);莫里兹·斯蒂勒导演的《阿尔纳的宝藏》(1919)、《古庄园》(1923)、《科斯塔·柏林的故事》(1924)均取材于塞尔玛·拉格洛芙的小说。
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对于优质文本的选择早已不局限于本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著作也被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搬上银幕。易卜生在1871年的诗作《塞尔日·维根》(Terje
Vigen
)被斯约斯特洛姆拍成同名电影;冰岛作家约翰·西古永松(Johann Sigurjonsson)的《生死恋》(Berg
-Ejvind
och
hans
hustru
,1918),丹麦作家赫尔曼·邦(Herman Bang)的小说《匕首》(The
Dager
,1916)和《迈克尔》(mikael
,1916)以及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2次的芬兰作家尤哈尼·阿霍(Juhani Aho)的小说《尤哈》也被斯蒂勒搬上银幕。把既有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既保证了电影文本的质量,又使得电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上映之后有潜在的受众群体,也符合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在少量的电影项目中投入大量的创作精力和制作资金以谋求精品的制片策略。
三、瑞典电影学派的美学表达
电影的叙事策略是电影艺术表现的基本手段之一,其中包括作为剧本形式的文本叙事以及影片呈现的空间叙事,后者不同于文学性的书写叙事,而主要指利用空间镜头和视听语言来增强电影的空间表现力,呈现电影所具有的独特审美特征和艺术魅力。
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莫里兹·斯蒂勒的影片有意识地对电影语言进行了诸多创造性的探索,开创了瑞典学派的诸多特征,与摄影师朱利斯·杨森(Julius Jaenzon)的合作使得他们成为最早进行实景拍摄的电影创作群体。纵观电影史,瑞典电影学派的创作者们并非将摄影机扛出摄影棚的第一人,自从早期的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大海》,稍晚一些的诸如埃德温·鲍特的《火车大劫案》都是最早一批户外拍摄的影片,户外实景仅成为故事发生场景的空间载体,相对于早期瑞典学派的实景拍摄,卢米埃尔兄弟、埃德温·鲍特等人的作品,呈现的却是无意识的选择。
瑞典电影人对于电影艺术高度敏感和艺术自觉,瑞典电影学派的先驱们在银幕上主动承担起建构瑞典民族风情和呈现自然景观的重任,突出瑞典电影人注重人与自然的人文素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影片中展现瑞典的地域特色,或波澜壮阔的大海,或是海边的巨石,或是代表宗法社会的古庄园,抑或冰天雪地的极夜现象,都构成了早期电影创作者表现的对象并纳入影片,参与故事表意。
在展现大自然原始之美的同时,将自然视为戏剧元素,视为电影中潜在的叙事动因,与演员一同参与叙事构成影片的意义序列,自然景观并不仅作为人物进行戏剧性表演的舞台背景而呈现,而是与人物的内心动机一同构成了推进影片叙事,强化人物内心矛盾的符号。
(一)自然景观的运用
“让自然景象在剧情中占据主要地位”。被称之为瑞典学派的主要表现手法。就自然景观的运用而言,早期的瑞典电影相较于美国影片呈现的西部荒凉外景、驿站和金矿区等外景是当时出于偶然和无意识的创作经验,“斯约斯特洛姆则一开始就有条不紊地应用同样的描写手法,并且怀有一个达到伟大艺术的计划”。萨杜尔更是引用莱昂·慕西纳克的话说:“瑞典人和兴盛时期(1916年)的美国人在电影中同样具有创造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有意识地这样做,而后者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的。”
从对早期电影史的梳理中会发现,瑞典电影学派并非最早将摄影机架到自然环境中去的,最早拍摄自然景观的影片要数卢米埃尔兄弟于18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卡普辛路14号的咖啡馆地下室里放映的短片《大海》(Baignade
en
mer
,1895),在早期默片中,自然景观仅仅作为和室内环境一样的空间承载意义,并不构成推动叙事发展和烘托人物内心的含义表述。比如《大海》中,海域的选择只是作为人群跳水动作的实现,自然环境并不在叙事层面上反作用于角色。而到了瑞典电影学派电影里,创作者有意识地将自然环境赋予了生命,既能承载故事的发生场域,又能随着角色内心波动产生变化。在《塞尔日·维根》《生死恋》《阿尔纳的宝藏》等瑞典电影学派代表作品中,自然景观不仅作为故事背景被呈现与讲述,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剧作功能,甚至已然成为电影中一个“缺席又在场”的角色所存在。景观与人物内心的情感起伏相呼应,呈现出原本需要角色表演才能体现的剧作功能。自然景观和象征原始宗法社会的庄园景色在摄影机的注视下,焕发出新鲜的活力,述说着北欧特有的地理风情和民族特色。
在《生死恋》(Berg
-Ejvind
och
hans
hustru
,1919)中,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的原始标题“Berg”一词在瑞典语中为“山峦”的意思,与主角艾文德(Ejvind)一词结合成“Berg-Ejvind”凸显出对于自然景观的重视程度几乎凌驾于角色之上。“斯约斯特洛姆所扮演的那个流浪汉,仿佛真是从这些山脉里产生出来似的。”在英国上映的版本则直接取名为“Eyvind of the Hills”。电影中呈现出自然中温泉、溪水、山峦等景观特点,男主角卡瑞(Kári)越狱之后,在荒野中用野外的天然温泉煮食物、喝溪水。这一系列的自然符号不仅解决角色在叙事逻辑上的求生问题,更在世界范围内展示了瑞典的地域特色,实现了北欧地域特色的推广和宣传。影片后半段,当村长率领官兵来山上抓捕艾文德和他的妻子哈拉(Halla)时,情急之下,哈拉将自己的孩子推下险峻的山崖,坠入河流中,急湍的河流被外化为角色恐惧。到了片尾,晚年的哈拉在无尽的懊悔中回想起以往的罪行,此时叠化的场景,孩子站在急湍的河流中,河流像恶魔一般击垮哈拉脆弱的内心,汹涌的水花使哈拉多年以来依然无法平静,最终选择离开住处,冻死荒野。就实景拍摄与棚内布景场景之间的转换而言,乔治·萨杜尔称:“天然外景和摄影棚布景之间全无一点破绽。”路易·德吕克也称本片:“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电影。”
《阿尔纳的宝藏》(Herr
Arnes
pengar
,1919),作为斯蒂勒电影生涯的高峰,风雪、冰山、被冰封住的船只等自然景观成为影片中主要的视觉元素。相对于同时期的格里菲斯,斯蒂勒的大场面不是恢宏激烈,充满澎湃活力的,而是肃穆且典雅的,在《阿尔纳的宝藏》电影中,六个身着白衣的抬棺者身后跟着几十个身穿黑衣的送葬人群,后景里是水面上被冰封住的船只,在寒雾中显得壮烈而又肃穆,同时又不乏美感。在三分法的构图规则之下,雪地占据画框的大部分,天空在大地的对比之下显得极为压抑,送行的人群身穿黑衣,在雪白的冰面的对比下显得格外耀眼。曲线的行走轨迹与三分法的构图呈现出节奏和线条上的动态呼应,既得益于朱利斯·杨森早年新闻摄影师对于纪实风景画面的偏爱,又得益于北欧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十分考究的构图策略在早期瑞典电影中已经掌握得相当娴熟。本片极大程度上体现了平稳克制又简洁的美学手法。片尾在冰天雪地里众人为艾尔丽莎抬棺送行的场景,深刻影响了弗里茨·朗的影片《尼伯龙根》片尾的送葬场面、《尼伯龙根2》的战斗场面以及谢尔盖·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1944)最后的送葬场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电影人大量吸取苏联的电影批评理论、电影创作、教学实践等方面的经验,用以指导我国的电影生产,深受苏联电影影响的“十七年电影”就能从中看到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等苏联电影人的影子,而溯其源头,便是斯蒂勒的电影——《阿尔纳的宝藏》。
(二)电影语言的创新
将视野放置在20世纪初期,纵观瑞典电影学派的代表作,厘清瑞典电影学派的视听语言策略后可见影片在视听语言的熟练与创新方面极具突破性。在1912年,斯约斯特洛姆导演了处女作《园丁》(Tr
ädg
årdsm
ästaren
,1912),这部23分钟的短片创作班底会聚了以后勃兴瑞典默片黄金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以此为原点来观照视听语言的创造性发展。诚然,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丹麦电影的强势发展,影响了邻国来自世界电影的追随,在《园丁》中,视听语言延承了邻国丹麦北欧电影公司的室内喜剧拍摄方式,室内戏段落往往选取一个固定式全景镜头呈现,加之字幕代替人物对话和具有提示故事动因的缘故,使得影片在镜头的运动和场面调度策略的方案选取上,未与影片中男主角赛德里克的归来的喜悦和无奈之下被父亲送走时的悲痛、与恋人罗丝分别后的不舍进行高度的贴合。影片从叙事上看,罗丝被赛德里克的父亲性侵、自己父亲的离世,被后来情人的家属抛弃,在整个社会环境的逼迫下,罗丝性情突变,最终精神失常。这是十分明显的两段式设计,以至于到了影片后半段对于罗丝的复归以及疯魔表现,没有在摄影方案和调度安排上结合人物转变有所调整,这也是最初视听语言乏善可陈的原因之一。
翌年,《英格堡·霍尔姆》这部被誉为瑞典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名片,也是历史上现实主义的扛鼎力作。片中的镜头语言已然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影像不仅作为单纯的剧情需要所呈现场景,更显现出人物之于环境、摄影机、观众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影片在第32分钟时,救济院外,英格堡·霍尔姆和孩子在相互拥抱之后送走孩子,为了不让孩子伤心,英格堡·霍尔姆趁孩子还没回头,迅速躲在救济院的屋檐下,时不时探头出来偷偷望着远去的孩子,随后难过晕倒。这个看似简单的场景中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表述方式:孩子回头始终看不见英格堡,英格堡对于远走的孩子时而看见时而担心被孩子看见,而摄影机也就是观众始终处于观看的视角,作为缺席的第三者注视着二者直接的看与被看。这个时长1分20秒的固定机位,在前景、中景、后景中各自承担着场景的剧情表述功能:这个镜头一开始,孩子的养母、孩子和英格堡三人从摄影的位置走向前景之处,开始离别前的告别;随后英格堡迅速躲在位于镜头中景之处的救济院屋檐下;孩子和养母逐渐走远,消失在远景的拐角处。
《英格堡·霍尔姆》中的精彩调度得益于维克多话剧导演的出身,以精致考究的场面调度构架出鲜明的纵深空间,角色一系列的动作在深焦摄影的场景中持续生产意义,搭配着克制的面部表情和较为夸张的戏剧化肢体动作,以缓慢稳定的节奏刻画英格堡·霍尔姆数十年不幸遭遇的鲜明人物形象。《公民凯恩》中的镜头调度策略和拍摄方式成为安德烈·巴赞景深镜头理论和长镜头理论的文本来源,在领先其27年的《英格堡·霍尔姆》中已然显现。
被誉为瑞典电影学派诞生的里程碑作品《塞尔日·维根》的视听语言和场面调度已经达到古典默片时期炉火纯青的地步,本片的拷贝卖遍整个欧洲、北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这就足以证明本片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故事改编自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9世纪的同名诗歌,讲述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封锁挪威和丹麦的航线,对于瑞典人民的封闭,使得水手塞尔日·维根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私食物,却在一次归家途中被英军抓捕,被关入英国监狱五年之久,出狱后发现妻子和女儿因为封锁饥饿致死。之后,维根在一次救援中遇到了当年拘役他的军官,但在抢走军官女儿的一瞬间,想到了自己已故的女儿,被感化后,在救人和复仇的挣扎之后,选择了解救军官一家。
影片采用插叙结构,在得知妻儿离世的悲痛和对被捕入狱前的幸福生活的回忆,以及最后解救军官一家释怀后的复归平静的形态的穿插对照之下,不同策略的视听方案进行对照呈现。影片开始时,是塞尔日·维根得知妻女死亡后心理大受打击,短短五年已经让之前年轻力壮又活力四射的维根变得落魄潦倒,胡须发白。身处中景的维根望着位于后景处窗外的海浪,巨浪汹涌击打着岸边的礁石,此时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单纯作为空间效果所呈现,更是外化了维根内心剧烈的悲痛和无处发泄的复仇之恨。
1917年的瑞典电影拍摄技法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室内的昏暗和室外明亮的反差表现出来的是剪影的拍摄手法,由于影片是白天所拍摄的,为了表现出时间的差异,在对于夜晚戏份儿处理,使用的是蓝色的滤镜染色。为了加强对比,在复仇被博爱所取代之后,巨浪复归平静,礁石不再遭受海浪的击打,维根挥手告别在船上远去的军官一家,在夕阳西下时,呈现一片祥和。最后镜头在余晖中转向妻儿坟前的十字架。除了对比的视听方案之外,在影片高潮的海面追逐戏也拍摄得十分考究,在极具观赏性、娱乐性的同时又不乏艺术上的突破。大部分场景将摄影置于大自然之中,在追逐戏的段落,摄影机被朱利斯·杨森(Julius Jaenzon)固定在各自的小船上,摄影机随着波浪中小船的起伏而呈现出身临其境的晃动感,让观众在紧张的钢琴曲和弦乐中强化代入感。镜头自身位置不动,随着海浪的起伏造成一种运动镜头的拍摄效果,这在当时以固定机位为主的默片时代尤为新鲜且极具活力。
维根在被英国海军发现后,双方开始进行追逐的较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年默片时期,摄影机常架置于地面,镜头相对地面而言静止,鲜见运动镜头。从英国海军从军舰上下来开始计算(00:24:20—00:28:13),不计黑场的提示字幕镜头,共有18个镜头,均在船上拍摄,相比摄影棚中的固定机位,本片让观众看到了运动镜头代入感的魅力所在,也从侧面佐证了斯约斯特洛姆对动作场面的把控。
电影《塞尔日·维根》在国际的巨大成功引起了瑞典影剧院影业公司的政策变革,公司不再大量制作那些默默无闻的影片,而是在几个电影项目中投入大量的创作精力和制作资金以谋求精品。如果说1950年的黑泽明的《罗生门》让西方观众感受到摄影机进入森林之中的惊喜,那么《塞尔日·维根》是摄影机有意识地进入自然最早的范例,在它之后对于自然景观的猎取,以环境推动影片的叙事,决定人物行为动机等策略安排都可以视作是《塞尔日·维根》遥远的回声。
《幽灵马车》上映于1921年1月1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酗酒者大卫被基督之爱拯救的故事。平安夜里,修女艾迪即将病逝,艾迪请求身边众人帮忙找到大卫,修女的两位好友开始分头寻找大卫,大卫的家里只有妻儿两人孤零零地在一起,另一个修女在街上找到了正在和流浪汉喝酒的大卫,大卫告诉众人一个传说,即在圣诞节零点死去的人,来年一整年将会成为死神的随从,并需要驾驶马车替死神收割灵魂。在众人的建议之下,大卫仍不肯前去探望艾迪,扭打之下,大卫被其中一个流浪汉用酒瓶失手砸死,此时刚好零点,死神来临,在接任死神之前,大卫需要为生前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电影通过对于大卫生前的所作所为进行闪回和插叙,逐渐让大卫意识到自己对于妻儿和艾迪的辜负,最后在与死神的对话中意识到艾迪用基督之爱对他的拯救后实现了自我救赎。电影大量采用了特殊照明、二次曝光技术、闪回插叙、平行剪辑等电影拍摄技法,在默片时期达到了电影技术和艺术上的双重高峰。
在电影二次曝光技术的使用上,斯约斯特洛姆显然晚于乔治·梅里爱,但与梅里爱式的室内片不同的是,斯约斯特洛姆将其安置在自然景观之中,当马车从急湍的海水击打着礁石的浪花里驶来时,那种自然和马车的运动呈现出来的动态之美和自然感受与传统室内剧的叠化效果截然不同。
本片对于死神的外化表现也让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从其中获得灵感,《幽灵马车》也成为伯格曼最爱的电影,而伯格曼又影响了无数的电影人,从师承的影响关系来看,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不愧被誉为“瑞典电影之父”。
结 语
早期的瑞典电影是在有意识地探索电影语言,以本土丰富的文学基底,向外展示出了一部又一部早期电影名片,电影人更是自觉担起电影对于大众的教化和推进社会进步的使命。在构建中国电影学派轰轰烈烈的当下学术界、国内电影市场日益磅礴、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井喷的今天,针对早期的瑞典电影黄金时代——瑞典电影学派发展及特征的阐述,希望对于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和研究提供一个可参照的观察视角,也希望为当下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宣扬中国的民族精神、地域特色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