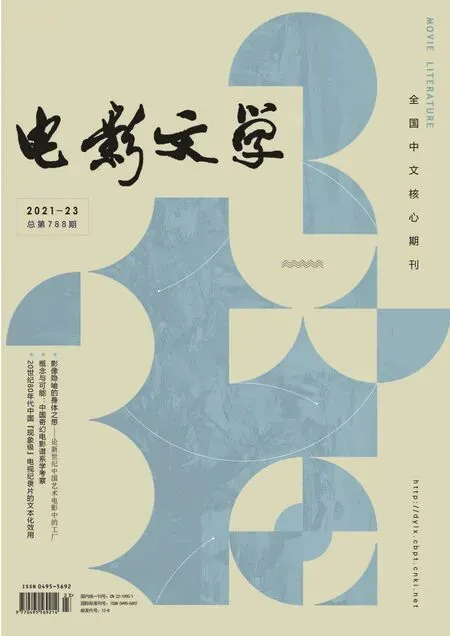凸显生态文明思想 讲好中国故事
——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
白 薇 王筱卉
(1.太原理工大学,山西 太原 030060;2.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
聚焦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三集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2021年3月12日开播,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青海省广电局牵头创作、上海广播电视纪录片李晓团队承制,也是国内主创人员独立拍摄制作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国家公园类自然生态类纪录片,已在央视纪录片频道及19 家上星频道、数十家地面频道、近百家新媒体平台播出,全面展现了青海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的建设成果。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由于高寒高海拔且严重缺氧,气候条件严酷,生态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极难恢复。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特别指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全面得到加强”。2015 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方案提出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成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为全国国家公园建设和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青海省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坚持保护优先、集约发展,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治理相结合,实现高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绿色发展和集约发展。《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就是展示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文明成果的一部纪录片。共分三集,每集50 分钟,分别讲述了黄河源头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修复、青藏高原高海拔的生态保护及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对自然和自然保护的感悟。主创团队跨越青海境内的三江源和祁连山两座国家公园和多个自然保护区,克服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历时一年完成拍摄。播出后在观众中反响热烈,开播一个月,多家卫视齐播,央视纪录频道罕见进行重播,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2610万,创造了我国近年来生态类纪录片的多项播出新纪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凸显,反映生态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纪录片出现了很多精品之作。但“众多精彩的中国生态文明故事还停留在实践层面,或用于检验西方生态主义理论的层面,没有提升至话语建构层面”。缺乏系统的话语体系支撑也造成了我国对外传播上陷入“失语”窘境。《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把我国生态文明思想潜移默化地蕴含在真实生动的纪录片中,构建出中国化的“草、海、峡、谷、冰、河”等自然符号,讲述了中国生态文明故事,着重表达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人与自然共同体的主张,在全球化的理念下凸显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自信。
一、平民化视角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是一种将个人经验和视野公开化的表达过程,能够拉近创作内容与观众的心理距离。《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采用自然纪录片常用的主导式作者叙事角度,适当加上了一些片中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片中的表达方式采用了平民化的视角,这种方式符合近年来我国生态纪录片发展趋势,即在“形式上,正在摆脱专题片式的说教模式,向故事化、系列化、类型化的方向发展;内容上,从纯自然元素展现进入精神文化生态构建;题材上,从国内走向国际”。片中随自然景观和动植物一起出现的不仅有科学家、专业人士,还有很多普通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的语言平和朴实,生活语言、甚至网民熟悉并乐于接受的网络语言随处可见。片中的科学家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感和学术表达的生涩,普通人看似平常的生活感悟里蕴藏着深刻的生态哲理。导演李晓说,这部纪录片里人物的讲话不是导演设计的台词,而是其中的人物实实在在自己说的。
(一)生活化表达体现科学知识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的生活美学,将审美艺术从康德的美学范畴进行了扩宽,提出对日常生活进行美的感受,将生活纳入美学范畴,为影视艺术内容的创作带来了启发。第一集《草海》中从事山地摄影25年的“青海湖鸟王”葛玉修看到公雪鸡兴奋地说:“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叫像软木塞一样,嚓嚓嚓嚓,一声比一声高,好像在说,这些母鸡都是我的。” 科学家将专业研究取得的成果或者给大众科普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传递给观众,昆虫科学家朱笑愚把搬运牛粪的粪金龟比喻成“草原上的铲屎官”,镜头里是粪金龟忙碌地搬运牛粪和远处走来的牧民,画外音说:“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很快会被牧人搬走。”有许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西藏齿突蟾,和平原上的蛙类不一样,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科学家讲述齿突蟾的适应性时则用比较的方式促进观众理解:“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那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齿突蟾,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慢一些,如果说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是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这些在观众看来从未见过的珍惜的动植物,通过专业的叙事者饶有兴趣的讲解,把科学理论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出来,不仅进行了科学普及,还传递着美和快乐,体现着大自然万物的神奇互动。
(二)故事化叙事蕴含生态哲学观
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既能让纪录片中的人物生动而具有人情味,又能将人物在叙事中置于变动之中,通过剧情内容来丰满人物,这样的故事化使得叙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作者的艺术表达。在《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中,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集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特有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以及表达方式,比如道家推崇的“道法自然”,尊重且顺应自然的法则;老子主张的“少私寡欲,知足知止”的生态消费观,庄子主张的“道生万物”观念和“万物平等”等观念融入创作中,这些穿越时空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不仅为我们提供精神力量,还提供了从古到今的实践智慧,滋养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话语自信。《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中的解说词、人物的语言就传递了这些传统生态哲学观。通过片中人物故事化叙事和情感投射巧妙地将人物的价值观体现出来,体现我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比如在第三集《峡·谷》中,医生达杰在做好严格防护挖取有毒的大戟后将没有用掉的根部重新埋回土里,因为“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生活,它不能跑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就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应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拿走的东西,也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辜负它的慷慨和善良”,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节制与感恩的态度。漂流船长扎西然丁在谈到漂流中的人和河流的关系时说:“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流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我的办法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体现了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不违拗自然的生态哲学。美术教师王芳芳说:“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休息心灵,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清醒,应该感恩,如此美的自然,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聚焦了现代人渴望融入自然、寻求心灵归宿的共情点。
不光语言,在片中人物在器材运用上也放弃了那些精密的科学仪器,代之以大众熟悉的器材。昆虫学家用一把张开的伞和灯光为昆虫开一场“夜间宴会”,吸引它们来做客,历史学家在野外用尺子丈量古老的岩画,同伴用手机进行记录,先锋派作家在湿地旁用身边的鹅卵石给小学生现场演示绘画的要领。这种平民化的表达方式把原本距离大众很远的科学家、历史学家、画家与大众距离拉近,符合全媒体时代大众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
二、生态叙事传播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影像是人们利用各种媒介对客观自然的一种主观描述,是把影像的精神价值与人的心理、情感需求相连,用来寄托美好生态愿景,以期让受众对生态环境更多地关注、思考的艺术形式。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突出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关系,主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把人、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看成是一个共同体,强调运用整体性、联系性及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解决生态问题。近年来,生态类纪录片摈弃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的利益作为最高权威的思维方式,尽可能地赋予生物与人类同等的尊严。《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很好地体现了生态叙事传播方法,突出人与自然共同体理念,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方式讲好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题材。该纪录片运用视听语言展示生态美感,以小见大地传递中国传统生态美学思想,宋家玲编著的《影视叙事学》从专业的视听分析角度指出了影响影视叙事节奏的六大要素:(1)被摄主体的运动速度或强度变化;(2)摄像机位置的变化;(3)摄影机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等;(4)景别的变化;(5)声音的配合;(6)镜头内部的速度变化。该片从构图到光线,从运镜到色彩,辅助故事,展现了在当地居住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与那些植物、动物、山川、河流的共生、共存关系。镜头配色和光影体现了极富诗意的生态美感,把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用一个个小故事形成生动的互文关系,润物无声地讲述了国家公园里的中国生态故事。
《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生动展现了国家公园内生命物种的多元形态和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选择题材方面体现了独创性,把生态纪录片注入新鲜内容,开掘了国家公园内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新的题材,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国家公园的生态美。在镜头语言方面,运用远景俯拍躺在广阔无垠草地上的大学生牧人达杰,站在苍茫的山巅远眺群山的历史学家,在高山峡谷中驾驶着橡皮艇与河流融为一体的漂流船长,用对比的手法把苍茫寥廓的自然之宏大和人类的渺小与微不足道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同古代山水传世名画中描述的天地万物之灵气在水墨之间融为一体,用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美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最形象的表达;而在描述生命物种多样性方面,则运用近景特写突出结伴而行攀岩走壁的高原精灵雪豹、姿势怪异地从滩涂爬到草地的高原珍惜两栖动物齿突蟾;用远红外高清镜头捕捉到珍惜野生动物荒漠猫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画面;运用延时拍摄法拍摄水下开花的云生毛茛,运用微距拍摄停在昆虫学家手指上的野生绢蝶。营造出无人区并不荒芜,而是随处可见生命的律动,用艺术化的手法表达了极限环境下高原动植物强大的生命张力。特别是在表现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上,多用平视视角拍摄,让原本弱小的高原植物或小动物有了与人类平等的关系。在中医达杰顺着大圆柏指引找到了一种能治疗刀伤的草药时,用仰拍的视角将其放大,而将人虚化为背景,赞扬了高原植物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生命的强大而奇异的力量。片中从一个个普通人平淡的讲述中体现生态资源永续的利用思想和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思想,以及生态保护对人们的反哺,体现了中华生态智慧。藏地中医达杰在看到被棕熊啃食过的蕨麻散落在一片狼藉的土地上,他小心地把保留有根系的蕨麻重新种到土里,希望再来的时候能够重新长出来,因为“自然界的东西不是人类独有的,共享不是一味地索取,及时地反馈是最好的感恩”。他在挖了一棵中药大戟之后小心地把周围的土填平,把草覆盖上去,“因为一场雨过后,草就会长回来”。牧民给孩子们讲故事中欺负小动物的孩子会被猫头鹰抓走,他看到附近有一个藏狐的窝,告诫孩子们放牧时不要打扰到它们。在环境恶劣的藏地,人类与动物建立起超越物种的亲密关系,体现了藏族的宗教信仰,也继承了中国传统中的生态智慧。
在听觉语言修辞方面,这部纪录片减弱背景音乐和解说的画外音,强化自然本真的生态之音,呈现出或平静安详,或寂寥空阔,或山雨欲来的氛围,用声音节奏营造纪录片情感氛围。正如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速度节奏如果用得正确,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正确的情感和体验;如果用得不正确,就会产生不正确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只能通过适当的速度节奏才能得到纠正。”在片中,山中的鸟声,峡谷里的风声,突如其来的雨变成落在草地上的冰雹声,牦牛吃草的咀嚼声,奔跑的马的呼吸声,小虫爬行在石头上的撞击声,随着一帧帧镜头徐徐展开,让人们听到久在城市里听不到的大自然最美的声音,与自然对话,让人们感到探头探脑的动物有着它们个人的史诗故事,每一株植物都有独特隐秘的生存法则,在山与水的交响中孕育出芸芸众生,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发展与平衡的关系都在镜头中呈现出来。就像片中昆虫学者说的:“在这里,人变成了客人,昆虫则成了草原的主人。”无论科技怎样发展,自然界中总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对自然保持敬畏,既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契合人类心灵深处的需求。导演李晓说:“拍摄国家公园符合现代人的内心需要,我们渴望蓝天,渴望绿色,渴望草原和森林。”这样的拍摄手法,从物理空间到精神世界,国家公园的含义,也在纪实影像中悄然发生了变化,展现了富有东方美学特色的纪录片意境之美。
三、人物言行体现中国生态文明特色
生态产品的文化价值应该“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自然精神,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承载着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精神,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目标”。作为一部系统介绍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自然生态类纪录片,应该如何在确保艺术性的同时,体现生态文明成果,达到宣传和教育目的,是创作人员孜孜以求的。据《青海日报》报道,青海省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准确把握牧民群众脱贫致富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关系,充分调动牧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截至目前,共有17211 名牧民转变身份成为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 元。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如何在片中体现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中国生态文明特色?如果能够从人文精神层面去观照本土自然景观资源和它对当地人产生的影响,必然会拓展纪录片呈现生态文明特色的方式,在教育宣传的同时显著地提升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主创团队抓住生态纪录片的特点,用小事件、小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和行为,达到了观照生态审美体验又避免说教议程设置,完成了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叙事主题,实现了艺术表达和宣传教育的目的同向同行的要求。
在片中,三江源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给当地人带来的福祉是从一个个小人物的神情和镜头语言中自然流露和表达的,在此,创作者对构图、特写等拍摄技巧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影视构图实际上是对被摄对象的一种安排和布置,好的构图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意念, 表现情节, 同时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 体现出创作者的美学素养。片中退耕还草后仍在高原牧场中的牧人扎西用刚剪下来的牦牛毛悠闲自得地在风景如画的草原上用传统的手工法织毛线,用晒干的牦牛粪煮水做饭,在自给自足,循环天然的西藏,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生活对扎西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必需,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但他们还是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它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它给的,如果离开几天,就会想它们,外面住不下去。”扎西眼里流露的是满满的幸福,他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不仅可以几百头牦牛为伴,而且“这里也成了国家公园”。此处镜头给了扎西面部的特写,摄像中的特写镜头是指用近距离拍摄的方法, 把人或物的局部加以强调, 起到放大局部的效果,造成强烈的视觉体验,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有对未来的担心和期许:“我们现在的放牧方式和以前不同了,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们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牧民卓玛加自从有了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身份后,就负责定期在楚玛尔河丈量河水变化,爬到冰舌上记录冰雪的变化,常年的生态监测让他发现:“国家公园里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虽然他以前也关心下雨和河流的变化,但现在他自豪地说,“这是我的责任”,因为“这河水连接的更多生命”。在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保护队员多杰作为“羊爸爸”喂养与母亲失散的十几头藏羚羊,他怕那头最小的羊受到其他大羊欺负,把它带回宿舍里睡觉,清晨几头小羊挤在多杰旁边抢着吸吮牛奶瓶,夕阳下两头藏羚羊依偎在“羊爸爸”头上,多杰给调皮的公羊取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宠爱地看着那些小羊从弱小慢慢长得强壮,明知它们长大后就会离开围栏回到草原,还是希望它们快点长得健壮、恢复野性的心理矛盾,看到自己亲手喂养照料的几头藏羚羊恢复野性跨出围栏与迁徙的羊群一起消失在茫茫草原的黯然神伤,都从镜头语言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这样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充满了人性的关怀,通过生活在本地的人们和外来的荒野探秘者记录、思考、探讨人的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传播生态和谐思想和生态文明成果的同时完成了生态纪录片不可推卸的教育引导责任。与自然纪录片相比, 生态纪录片不应满足于展现自然界的秀美风光与奇异物种, 而应该视野更广、题材更多样。生态纪录片应该具有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的视野和思维, 以再现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就像片中中医达杰所说:“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量做,尽早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这部片子的成功拍摄,本身也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唤起人们关注生态热爱自然的一种贡献。
近年来,本土题材资源的精品化创作已经日渐繁荣,深耕本地选题资源,投入一流团队,巨大制作资金和资源打造精品力作,巧用本土资源优势,凭借差异化策略,集中力量打造精品力作,已经成为我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热点。而描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也逐渐摆脱了西方生态主义的理论,代之以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在文化传播上更突出我们的话语体系。《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的播出,无疑给更多的人讲述了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故事,也必将通过向海外的传播,更好向世界讲述中国生态故事,传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