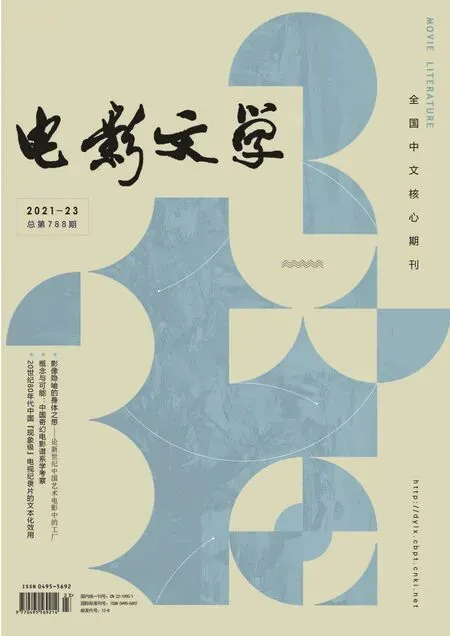线索、维度和形式:国产文化纪录片《胡同》的叙事模式建构
延保全 陈子瑄
(1.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2.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中国纪录片研究发展报告(2020)》指出,中国国产纪录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而文化社会纪录片作为其中之一,在近年广电总局和地方广电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并以中国特有的纪录片模式,在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阎昭导演的文化纪录片《胡同》是新阶段以影像记录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典型作品,它根据中国文化的特性建构了独特的叙事模式,以恰如其分地表达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审美心理和审美理想。《胡同》中这种叙事模式的创新性运用为中国文化的影像记录和本土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叙事线索:个体情怀和历史积淀的交织
纪录片《胡同》旨在以影像记录、保存和传播北京的胡同文化,而这种文化不仅是现象所显示出来的横向断面式的短暂现状,在其深层之下,胡同的性质与含义毋宁说是一种历史表征的符号、方式和历史沉淀的结果。但同时,“所有历史都是为当下人写的,为他们呈现一种东西。历史学家把这种东西叫作可利用的过去——这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自身的理解”。这种个体式的自我阐释与历史含义相结合,既是文化纪录片的要求,也是“胡同”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个体情怀与阐释是历史延续性成为可能的关键,而历史积淀又是个人文化生命感的基础和来源。可以说两者在“胡同文化”的体现和传承中相互交融,相互丰富,共同组成了文化所特有的真实性和生命力。
《胡同》的第一章《道路》即将视线聚焦在了承载文化的物质基础和物理空间之上。最早对“胡同”街制的记载见于元代,《析津志》有云:“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而元代的有些胡同甚至连名称都没有变,一直延续到今日。本片同样列举了《析津志》和其他一些记载胡同的古籍,诸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京师坊巷志稿》等,以期把握和强调胡同文化的古韵和其历史脉络的延续性。但制片人并没有一直执着于历史的追寻,而是继而随着时间的变迁寻找着新的轨迹和当下鲜活的生命感,正如片头所说:“时间在北京一刻不停。在北京许多地方,时间可以被看见,金瓦红砖、宏伟的宫殿和庙宇。但只有在一个地方,时间可以被触摸,虽少有记载,但它的一切却镌刻在人们心中。一扇门、一棵树、一种声音,来自遥远的过去,却依然触手可及。”这种“遥远的过去”和“触手可及”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是本片逻辑框架的聚焦,而此两点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正是“延绵”与“不变”,即剧中所说的“(胡同)经历时间的冲刷,撑起北京不变的轮廓”。
在简单介绍了历史古籍中的“胡同”之后,影片随即就将视线放在了现世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巷之中,并从个体角度寻找与历史相互勾连在一起又“触手可及”的真实情感。它并不是从冷冰冰的建筑房屋结构的视角去介绍街道,而是以典型的居民生活、生命情状作为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赋予物理空间以生命的真实。首章《道路》中以赵世龙的30年邮递生涯为视角,叙述了胡同道路对居民的特殊记忆和这些年来的人物变迁。以个人生命历程讲述胡同的外观外貌并从文化意义上贯联其前世与今生,如此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则得以展示。《韵律》篇以一段百年前的戏曲录音作为叙事开端,然后引出70多岁的京剧艺人王子成复现录音戏曲的故事,从廊房四条的韵律延述到如今胡同里悠扬的戏曲腔调,这种叙事逻辑将现代故事和历史记忆相连接并将其组成一条完整的脉络。《天地》章讲述净土胡同的金马派风筝传人吕铁成不断复原师父身前的风筝,但有一只仅存在师父想象中的风筝让他束手无策,最后清晨的鸟鸣激发了灵感,传统的艺术品又得以在高楼与胡同之间飞翔。通过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历史在不间断地延续,胡同文化也在时间的流逝中得以传承保存,“人们主观的‘触感’虽然各异,却总能从胡同客观的结构、环境、历史之中找到联系和依据”。正如剧中所说,这种文化叙事模式使我们“看到胡同被人忘记的那一面”。
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涉及广泛,包含众多,不一而足。但是在特定文化场域下,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及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维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生”也是“生活”,确切地说,它是“集体的,大群的生活”。一方面,《胡同》遵循着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通过典型表现整体;另一方面,在描述个人生活时,本片又注重这种生活中深沉的生命感受。如其片中人物邮递员赵世龙所说:“你要是在这儿生活了,甭说多,你就10年,你对它必须、肯定产生感情。梦里都是胡同,都是老街坊四邻。”于是,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而又被“别人忘记”的那一面被个体真实的生命感所唤醒。通过由古到今的纵向延伸,本片将个体情怀融于历史沉淀之中并置于社会整体观照下,使胡同的记录保持了文化意义的真实生命力。
二、叙事维度:形下具体和形上抽象的融合
纪录片在进行表现时,“通常会在特殊和普遍之间,在历史性的绝无仅有和一般性的司空见惯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如果没有普遍性的衬托,纪录片也许只是对某些特殊事件和特殊经验的简单记录;而全篇没有对特殊性的表现,纪录片将只是一些抽象、空洞的论述”。纪录片中所谓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其实就是形下与形上、具体与抽象之间不同维度的关系。如果说个人情怀和历史的交融是指纪录片文化历时性的关联与逻辑,那么形下与形上就是其叙事内容与元素的共时性维度关系。
形上与形下的结合很好地体现在《胡同》叙事维度中。《天地》一章讲述了金马派风筝艺人吕铁智、龙舟爱好者刘博以及蛐蛐爱好者刘云江的故事,以表现胡同中的自然气息和元素。但实际上,剧片的目的和实际效果不止于此。《天地》章集有句独白:“生活在灰瓦下的北京人,将自己的日子和身边的草木生灵结合在一起。这种日子与时节有关,与物候有关,与天地有关,与内心有关。”“天地”和内心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天地》实际上是要讲述胡同居民如何看待自我和自然、胡同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相关性思维观念,也即他们的“内心”。剧中刘博在自己故事的结尾说道:“比如在划船的某些瞬间,你把自己几乎是完全忘了,你是在天地的某一个地方,你就完全消融在里面。你在历史里的时候,在胡同的时候,更加容易有这种可能性。”这种“消融”既是对自然天地的回归,对人内心的回归,更是天人合一生命状态的绝佳体现。这种体验和感觉是抽象的,但正因如此,它又颇具深远感。而这种抽象又是本片在叙述完人物故事之后的总结,是对经验和经历上的提炼,更是利用形下的描绘追寻形上的含义,最后达到意义的彼岸。再如《规矩》一章,所谓“规矩”不仅是指胡同街巷地理的井井有条,更是在说胡同中的文化与其准则。纵横交错的胡同是北京城的脉搏,这些建筑的组合本身就具有严密的“规矩”,“西直门走水车,东直门走木车,朝阳门走粮车,每天定时启闭”,但同时这种井然有序的局面,“赋予了北京这座城市极具规范性的运转节奏。对秩序的尊重和坚持,充满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无论鸟瞰还是微观,无论一座建筑还是一个斗拱”。本章中以吉周复刻北京城建筑的故事开头,对北京胡同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感知进行表现,然后继以对胡同春联和纸马等礼仪风俗和规矩的讲述。但故事并没有以这些显现在外的形式或者视觉感知作为叙事结尾而是将维度进一步延伸到人的观念与内心,正如片中人物纸马艺人张阔所说,“通过这种仪式把这种文化、这种内涵深深埋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心里”的规则和准则才是《胡同》的文化叙事致力挖掘的重点。另外,本集独白评述道:“规则和秩序,最初是高高在上的教条。后来随着时间走入平民百姓,演变成了日常生活的规矩和习惯,又恰恰因为时间,被今天的我们遗忘。只有在胡同,依然留存并延续着这种独特的基因。”胡同所表现的规矩与规则不仅是形式的结构与秩序,更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生命状态和思维观念。可见,《胡同》努力在叙事维度上将真实具体的经验层和抽象的意义层相结合。如此,它在结构成完整叙事框架的同时,也兼顾了文化意义的深层次挖掘。
而这种编排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纪录片本身就具有文学的属性,“如果说艺术是用一种特殊的暗喻形式来表现人类意识的话,这种形式必须与一个生命的形式相类似”。而所谓“生命”正是艺术性上的意义。二是胡同作为本片的表现对象,其文化特质丰富复杂。胡同中的一些名居不仅被列为物质文化遗产,其间街坊里的传统艺术和风俗也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叫卖、老字号和毛猴工艺等。除此之外,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本身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和观念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正如《规矩》章所说,“规矩的含义多种多样,可以是成文的法则、约定俗成的风俗,甚至是对彼此承诺的看重”。而人的观念与思维并不具有直观性,而只能通过事件与行为来显现。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人”具有“群体”的意义,因为文化的意义不会生成于个体行为,它以群体普遍的生命方式而存在,而前者在文化意义上只能是后者的体现。如此,表现包括思维观念在内的群体性生命状态则成为本片叙事的必要,这也在文化表达方面决定了该片叙事维度的着力点在于如何处理个人和群体、形上和形下以及特殊和普遍的关系。以上种种原因使得《胡同》在记录文化时不得不从物质走向非物质,从形下走向形上,将个体所指向与埋藏在现象中的深层意蕴挖掘出来。但是形上的意蕴表达又离不开对有形物质的勾画,后者是前者的存在基础,或者说是其存在的部分原因。具体与抽象不能相互割裂。形式虽然注重于外在显现,但在普遍的遵守和阐释下,它也同样会产生超越视觉存在的意义。《胡同》的叙事不仅是在努力地从形下过渡至形上,而是致力于特殊与普遍的结合,并选取人物的典型事件与遭遇作为两种不同维度的叙事交融点,由小及大,由实至虚,以此达到叙事维度和框架的圆融完整。
三、叙事形式:写意手法与诗意表达的兼具
“毫无疑问,纪录片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而纪录片并不等同于记录本身。”一般来说,在“虚构”和“纪实”之间掌握平衡是纪录片需要遵循的规律。这是因为纪录片具有文学艺术形态的属性,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以它不仅是对现实的复刻,或者是对现实材料以影像的方式简单罗列,它在材料的背后体现着自己的主题观念。除此之外,《胡同》本身存在着形上和形下两种叙事维度,这也决定了本片需要一定的叙事形式来突破即视空间而进入更深的层次。而这种矛盾若想得以解决,则需要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写意”手法。尤其是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纪录片来说,利用写意手法达到根深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是绝佳的处理方法,也是平衡“虚构”与“纪实”的有效方式。
《胡同》中的写意随处可见。在影片开头,延时摄影、微距摄影就被运用到特写宏观建筑与细小景物上,并以哲学思辨的旁白话语引导观者进入预设的历史意蕴之中。而细节特写更是常见,尤其是在人物故事开头或结尾处,总是选取特定的表现对象做慢动作的镜头停留,以渲染气氛、暗喻意蕴。《胡同》每集中都会有故宫宫殿这一意象和胡同宅门交叉出现,这两种意象的交叠正是在显示一种文化的深沉感以及历史的绵延感。另外,音乐的运用也是《胡同》写意的一大特色。音乐不仅使电影作为视听艺术更加丰满,也能使电影叙事更加精彩。剧中的音乐在表现胡同外观、总结文化意蕴时多偏向运用中国传统的乐器,形成一种深沉的意境;在关联个人故事时,又偶尔以吉他等现代乐器引起追思和回忆。特写、意象和音乐的配合使得观者沉浸于纪录片整体的氛围中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纪录片的这种“写意”的确有着隐喻的意味和现象移情的特点:“艺术所能指涉的本质真实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于逻各斯的认知,一是使外在的现象成为符合心灵的表现。如果说前者是影像叙事的共性的话,那么后者则是纪录片叙事的隐喻优势。”实际上,《胡同》的写意系统与影视艺术常用的象征、隐喻以及选择强化信息的蒙太奇手法的确有所关联。但在中国本土文化的话语语境之下,毋宁说本片的写意更趋向于传统美学意蕴的追求。深入影片即可发现,《胡同》写意式虚构的主要目的就是创造属于中国美学范畴的“诗意”,而“中国美学的重心就是超越感性,而寻求生命的感悟。不是在经验的世界认识美,而是在超验的世界体会美”。文化的内涵是非物理性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这种把握超越的意识早根生于中国的传统之中,《周易》中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这种审美理想作为历史和社会心理而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胡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本身就回荡着古老而传统的旋律,体现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气韵,而电影的写意手法正是对这种诗意内核的美学把握。在象征和隐喻手法中存在具体的本体和喻体,但中国的“诗意”的超越意识并不会最终归结为具体事物,而是“不‘物于物’,与天地并生而融合,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而就中国美学的特点来看,审美境界就是一种人生境界。这就不仅是想象与虚构这么简单,而是历史蕴含、个人经验和人格结构的综合体。《天地》讲述了北京毛猴艺人孙怀忠的故事。在用毛猴艺术复现了北京胡同之后,他感慨道:“能走出北京,但走不出胡同。”而走不出的“胡同”正是影片叙事努力引导观者进入的“诗意”境地,一种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简单模式的领域。这种“领域”不仅是中国传统观念和审美思维历史沉淀的结果,更是社会心理在当下对“胡同”种种蕴含所做出的精神上的反应和思索。胡同的“诗意”就是这样一种直观、丰富并具有超越性的境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而中国故事从民族走向世界,必须在挖掘自身文化独特魅力的基础之上加以创新性表达,这是加强文化自信、建立文化强国的必要之举。实际上,关于胡同的影像记录自21世纪初就开始大量出现,诸如《北京的胡同》《北京胡同》《走遍胡同》和《史家胡同》等,但它们都仅是倾向于平铺直叙历史往事而淡化了对当下胡同面貌和风情的探索和深层次的挖掘。文化的关键在于传承传播,那么如何利用影视表现当下社会的文化传承,如何用符合现代审美心理的方式传播和在更深层次上讲述中国故事则是新阶段文化纪录片需要关注的问题。《胡同》串联个人经验和历史意蕴以强调历史的传承和延续,写意手法和诗意表达则是深层次表达文化蕴含和适应现代社会审美心理的需要。它为以影视手法展现中国社会文化、民间文化、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道路,更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优秀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