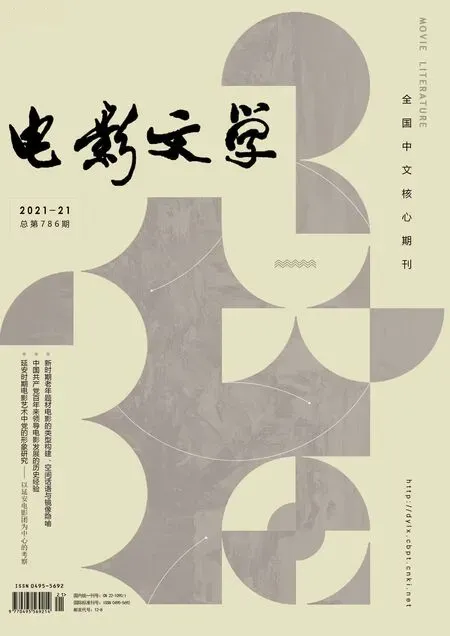论《荞麦疯长》的陌生化表达
张 璨
(淮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0)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想要“活成一部电影”的云荞,对舞蹈梦想执着追求的李麦,在平凡的日子里为兄弟和爱人背水一战的吴风。每个人都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异乡漂泊之路。导演徐展雄试图通过群像的方式记录一代人的青春,展现关于当代青年群体与故乡、都市、社会的融会与碰撞、阵痛与蜕变,《荞麦疯长》直击现实的内部,并通过陌生化的表达方式将其呈现。
一、主题表达的陌生化
(一)多主角的群像描绘
本片跳出了在大部分电影中围绕某一个特定主人公的经历来叙述的惯例,而是通过三个性格迥异又彼此关联的小人物将影片串联,正如电影结束时银幕上的字幕“愿所有爱与理想都御风生长”,导演徐展雄试图描绘的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追逐爱和理想的故事。《荞麦疯长》设定了三个典型性人物:天真烂漫、想要“活成一部电影”的云荞;对舞蹈梦想执着追求的李麦;在平凡的日子里为兄弟和爱人背水一战的吴风。可以说,三个主人公的设置都具其普遍性和典型性,是对万千面孔的提炼和加工,同时,选取多主角的群像描绘,又为影片增添了些许史诗的品质——为一代人的青春画像,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孤独,或热闹,但他们却又一样——似荞麦,适应性极强,生长周期短、生长速度快,它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孤傲的姿态,它努力向阳、汲取能量。
(二)陌生化的青春书写
近年来,国产电影对青春的书写一路高歌猛进,从2014年的《同桌的你》《小时代》《匆匆那年》到2015年的《左耳》《何以笙箫默》、2016年的 《致青春》《七月与安生》等影片,校园里的爱恨离愁、人际关系是此类电影的创作主体,而《荞麦疯长》则走了一条陌生化的路线。《荞麦疯长》将大量的剧情冲突放在了小镇和城市之间,通过三个来自小镇的年轻人,讲述“漂泊者”的生存状况以及探讨“为什么出发”的问题。
影片时间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此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全国各地人口开始急速流动,导演兼编剧的徐展雄,就出生于一座与上海隔海对望的小镇。他曾坦言,现如今,高铁和跨海大桥缩短了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却依然没有消弭一座核心都市和它的辐射乡镇之间的古怪联系。可以说,徐展雄将自身作为小镇青年的热血与迷惘作为了创作的母题,主人公云荞、李麦、吴风,都怀揣着一个都市梦,都向往着更高、更广阔的舞台,却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电影中有大量关于小镇的灰暗又潮湿的影像表达,小镇是嘈杂又死寂的,而都市的影像却极为模糊,它更像是一个梦想、一个符号、一颗灼热跳动的心脏。
故事一开头,云荞戴着耳机坐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幻想,百无聊赖的小镇生活让她在商场里的小偷小摸中寻找着刺激,她厌倦了小镇的一切:潮湿而灰暗的午夜场、蛮横无理的地痞流氓和那个了无生机的家。那一天,衣冠禽兽的姐夫在一个燥热的午后强暴了她,这无疑粉碎了她在小镇的最后一丝念想,她毅然决心出走!她爬上小镇那座高耸的钟楼,信誓旦旦地对那个爱着她的男孩说“要活得像一部电影”。而她的姐姐,在外求学后又顺理成章留在都市的姐姐,也并没有因此而跻身体面的都市生活。她在餐桌上展示着那对象征着都市欲望的“老凤祥”金耳饰,也不过是男友低价买来的假货,她周而复始地在广场上卖着刮刮奖,生活似一汪密不透风又永不会再起波澜的死水。
意气风发的云荞和她心爱的男孩离开了小镇,而在进发都市的途中,似乎又回到了鲁迅笔下那个遥远的拷问——《娜拉走后怎样》,小镇和都市,那条隐形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沟壑依然存在。
为舞蹈而生的李麦,在一个城市担任歌舞团领舞,舞台上的她希望将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在舞台上燃尽,然而一场意外,让她错失日本舞团的橄榄枝,也被迫离开了曾经的舞团。只身在城市打拼的她,只因电话那头父亲的一句“你妈的病需要用进口药”而不得不走向红尘,“别担心”“我很好”,只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小镇青年最能体会李麦口中这句灼热的回复。吴风则将漂泊感、无依感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几个关于吴风的特写镜头缄默而有深意:开水咸菜泡饭、小心地擦拭着小号、痴痴地透着玻璃凝望。透过这些特写镜头和远景镜头的切换,观众很容易感受到吴风在这个城市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他在都市的无根、漂泊无依诠释了他将兄弟情和心爱的女人视作己命。
剧末,导演徐展雄很巧妙地用人物群访再次展现了小镇青年在都市的生存影像,有北漂11年的厨师、穷困潦倒的实习生、蜗居在两三平方米逼仄空间的自媒体男孩……在这一系列小人物的或故事或自述中,我们感受到导演试图展现的小镇青年在都市中一面挣扎一面追梦的生存影像,他们一样体验着物质上的贫乏和回不去的故乡,他们忍受着漂泊的艰辛与无助,他们又一样——为了爱,为了理想,像荞麦一般,拼命扎根,拼命生长。
(三)异质空间的设定
异质空间的提法是来自福柯《关于异质空间》的论述,异质空间在国内也被译为“异乌托邦”,与乌托邦的单纯、美好相对,“异乌托邦”则将社会形态中最藏污纳垢的那一部分搬上银幕。《荞麦疯长》虽是以青春成长为母题,却没有将故事仅仅放置在校园或家庭的狭小场域中,而是把青年人的成长放到了更广阔的场域——社会的血雨腥风中、城与镇的交融与碰撞中,使得自我与现实的冲撞更加强烈,也增强了戏剧性处理,打破了过去青春电影题材中常见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儿女情长,而是转而探寻青年人离开校园后,在社会这个复杂的场域中的累累碰壁、无可奈何。
与温馨、安全的家庭空间相对,云荞的家是一个异质空间的设定,它本就支离破碎,又常常被母亲漠视,再加上龌龊的姐夫,压抑而死寂。云荞的男友也同样如此,他辛苦卖烧烤赚钱,却常常被父亲无理扇耳光,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温馨,同病相怜的两个人决心逃出小镇,逃离小镇,就意味着逃离愚昧、粗暴和冷漠;李麦生存的场域则充斥着权钱的压制和交易,透露着城市的秩序和规则。作为现代舞团的领舞,李麦年轻貌美、才艺出众,而当意外来临,他人却背弃信义,只留她独自面对,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听命于象征着权力的B司令,也不得不委身于年长的男人;而吴风,在兄长的教唆下,内心质朴、单纯的他却无法跳出黑社会成员的身份,独自去追寻自己的梦。《荞麦疯长》通过异质化的空间设定,让人重新审视一种以现实为映射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影片的批判性认知。
二、叙事策略的陌生化
《荞麦疯长》在叙事策略上也做了大胆尝试。正如前文所言,《荞麦疯长》力图描绘一代人的青春影像,在叙事上,也打破了惯用的线性叙事的方式,通过精心设计、剪辑的时空顺序以及略带魔幻色彩的场景,使三个人物的成长经历巧妙地勾连在一起,加强了故事的张力。
云荞和男友在逃离小镇的征途中,与李麦乘坐的车相撞,车祸致使两个人的命运就此发生了剧变。车祸后的云荞在医院醒来,四处寻找着男友,她焦急地呼喊着秦风的名字,此时画面一转,给了李麦因车祸受伤的右腿一个特写,进而开始了李麦车祸后的境遇叙述;吴风与云荞的联结也颇为巧妙,重情重义的吴风为了兄弟两肋插刀,在他与磁县这一帮小混混火拼时,碰巧云荞也回到这里准备要回被抢走的钱财,吴风无意中也帮了云荞。而在影片末尾,吴风决意去找B司令报仇时,恰巧遇到了来这里想用一首歌与城市告别的云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个人在灰暗摇晃的公交车上互诉衷肠,云荞说起了她离开故乡的初衷,画面随着云荞的叙述和回忆一点点从此刻剥离、流转、分割;吴风迷恋着楼对面舞蹈的李麦,哪怕李麦从未知道过他的存在,她似一束光,照进他混沌又泥泞的生活。所以,当她受到一点点玷污时,他不顾一切为她排除万难,当年迈的男人猝死在李麦家中,吴风悄悄为她收拾了残局。吴风倒在冰冷的泥潭中掩埋尸体时,镜头从冰雨淅沥的泥潭切换到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在窗边痴痴地看她跳舞的场景,看着她推开窗户向阳的面颊,对现实中无力抗争、深陷泥潭的吴风而言,李麦就是温暖而美好的象征。此刻与回忆交织,人物与人物之间微妙的连接,现实与虚幻的融汇,导演有意打破线性的表达方式,场景、时间、空间,刻意将其打碎、切换、重组,追求陌生化的叙事策略,将影片中的群像描绘串联,三个主人公虽命运各不相同,但通过导演的精心设计和联结,又凸显出同样的青春特质,似某种内在的宿命感——成长的过程中必经的阵痛和蜕变。
三、表现形式的陌生化
在《荞麦疯长》中,导演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没有局限在特写或主观镜头的切换或独白的形式,该片非常善于运用舞蹈元素,舞蹈与镜头语言、服装、音乐等表现形式的融汇让观众立体化地走进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舞蹈元素恰到好处地运用胜过了语言的表情达意,让该影片的表达更为震撼,更细腻也更具美的形式。影片开端,主人公李麦作为歌舞团的领舞,身着红衣,在一堆素净的白衣女孩中,她舞得最动人、最妩媚,这时的李麦意气风发,爱情与事业都像她的舞一样充满着生机;离开舞团后,去向B司令求职时,B司令要求李麦脱衣跳一段舞,为了生存,为了卧床的母亲,李麦没有丝毫犹豫,特写镜头放在了她腿上那道异常明显的伤疤上。此刻的李麦,翩跹而舞,舞得刚劲有力,她高昂的脸上,面无表情,观众再一次通过舞蹈的肢体语言,直观地感受到了主人公此刻境遇窘迫但仍充满着傲气;还有李麦的两次即兴舞蹈都极具象征意义,一次是面对男友无情的欺骗,当她得知这个男人骗走了她的钱和爱,她摘下已经梳理好的发簪,擦去用心涂抹的妆容,飞奔向舞台,此时观影人和台下的观众一样,屏住呼吸,所有的聚光灯都聚焦舞台上舞动的她,她将所有的委屈、不甘,都通过舞蹈的艺术形式呈现。另一次即兴舞蹈是在老男人毙命家中后,自己出逃。舞蹈是李麦的生命,舞蹈的画面无声地表达着李麦成长的阵痛、辛酸和无助,演员钟楚曦动作坚韧而洒脱,眼神悲伤却又坚定,但通过舞蹈表达出来的生命力量又是坚韧的、不屈的。《荞麦疯长》中舞蹈元素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舞蹈与主人公的命运连为一体,通过舞动的肢体语言和演员的面部神情,通过镜头的捕捉和剪辑交融出更强的表达力和视觉冲击力,影片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想象空间,带我们走进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尽管《荞麦疯长》作为徐展雄的第一部自编自导的作品,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人物的性格及情感处理上,抑或用力过猛“留白”不足等问题。但它没有刻意迎合当下的热点和潮流,而是尝试陌生化书写,通过三个典型性人物的群像描绘,勇于跳出线性叙述,大胆地融入了舞蹈元素,甚至带些许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已足以见长。《荞麦疯长》向我们展现了一群向着都市迈进的小镇青年的人物群像,探索了他们离开校园后,在夹缝中坚守着爱和理想,直击现实内部,可以说,《荞麦疯长》已开辟了自己的艺术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