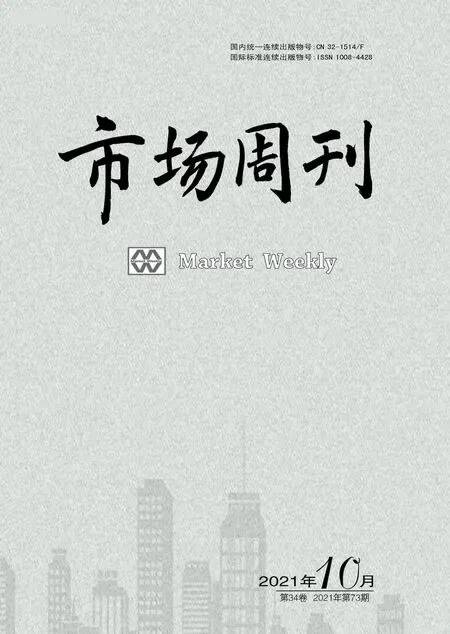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曾 玲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知识产权法起源于智力劳动成果社会性与私有性的冲突。 智力劳动成果具有社会性和私有性两种属性,任何一项智力劳动成果在进入公共领域之前,都是个人或者部分人智慧的结晶,为了保护人们不断创新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权利主体在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性使用权利以及限制他人随意使用的方式,对权利人的智力劳动成果进行保护。知识产权对权利的保护可以看作一种法定的垄断权,该权利是由知识产权法直接赋予权利人的。 在进入公共领域之后,这种 “垄断地位” 便消失了,该智力劳动成果便成为社会的共有财富,有助于社会各方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实现新的革新与发展。
知识产权成文法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私权利的重要性,在此后的世界市场中,为了追求个人私益的最大化,竞争手段不断升级,出现了具有强大市场控制力的垄断组织,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公权力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从而达到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目的。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知识产权法提供补充保护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立法背景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在人们过于追求个人利益、缺乏有效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出现的。 只是二者在对智力劳动成果的保护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知识产权从私法层面赋予权利人对自身智力劳动成果以绝对权从而保护个人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从公法层面以国家强制力为手段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调节市场竞争秩序,二者相互配合,共同达到促进公平竞争,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
“补充保护说” 是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的主流学说,其中有代表性观点认为 “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三座冰山,竞争法则是承载着冰山的海水” 。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原则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原则,这就决定了知识产权法本身的保护范围是有限的,对于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的内容,可以寻求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但是对于新兴出现的知识产权还未纳入保护范围的智力劳动成果、不满足条件未能获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智力劳动成果(例如 “北京烤鸭” ,其本身由于带有“北京” 字眼不满足注册成为商标的条件,但是并不能否认其本身所具有的追溯商品来源的功能)以及超过知识产权法保护期限的智力劳动成果,就只能寻求 “海水” 的保护,选择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冰山和海水的比喻生动地展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法进行补充保护的关系,对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空白的区域,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兜底保护,从而使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达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创新发展的目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相互制约
知识产权是一种正当的 “垄断” ,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反垄断法则是以规制垄断行为为立法目的的,二者之间相互制约,避免其中一方权利过限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对于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由反垄断法进行规制。 这一法条明确表明二者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援引知识产权法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例外,权利人根据知识产权法的授权对知识产品进行独占使用并且禁止、限制他人使用的行为,其实从行为结构看,符合反垄断法所规定的行业垄断行为,但是由于法律授权而得到豁免。 在市场竞争中,竞争实力强的一方会运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去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造成其他竞争者的损失。 在以知识产权为硬实力的当下,拥有知识产权就是一种竞争优势,知识产权赋予权利人在知识产权保护期内独占使用的权利就意味着其他的经营者对于相关权利的应用都必须经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对价,甚至连对价的定价权都掌握在权利人手中,这就使得知识产权的运用很有可能会超出权利边界,造成权利滥用。
任何权利都不能没有界限,但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因此只能由反垄断法进行规制。 反垄断法以国家强制力来制止运用知识产权谋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形成行业垄断的行为,可以看作公权对无限膨胀的私权的一种制约。 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对滥用知识产权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行为的调整,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
二、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补充保护主要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一般条款,即判断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但是一般性条款的不当适用很容易导致无限制的拓宽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在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交叉案件中,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保护的无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补充保护应当有所限制,否则其对智力劳动成果的过度保护将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例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著作权法对于 “游戏规则”的保护中,游戏规则属于思想范畴,而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也就是说,“游戏规则” 作为思想范畴的东西,属于著作权法排除保护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知识产品的保护不能破坏知识产权法本身的逻辑,对于知识产权法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 “游戏规则”,也不应当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否则会使得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产品通过规避专门法(即知识产权法),选择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方式扩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压缩公有领域的空间。
(二)向一般条款逃避
在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交叉问题时,首先应当考虑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穷尽了法律规则后,才能选择法律原则进行适用。 但是在实务中,法院面对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交叉问题,出现一种向一般条款逃避的现象,很多在未穷尽知识产权法对智力劳动成果的保护的前提下,优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一般性条款,架空了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品的保护,导致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本末倒置。
(三)保护标准难以统一
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主要依据是判断行为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公认的商业道德、商业惯例。 但是诚实信用原则本身的适用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就是说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保护标准,不能做到适用上的统一,以未定的标准来保护知识产权难免会导致权利保护的过度膨胀,损害到正常的交易秩序。
同时,公认的商业道德和商业惯例同诚实信用原则一样具有抽象性,尤其是商业惯例不仅具有抽象性,还具有地域性和时效性,在不同地域市场和时间节点都不同,这就会导致权利保护的标准出现地域差异,违背了法律的可预见性。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法拓展保护的边界如何确立
从上文得知,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对知识产权进行补充保护,从而拓展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也给新兴智力成果在被纳入知识产权法保护之前提供救济,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知识产品保护的界限应当如何界定,“额外因素法” 为之提供了新的确定思路。
额外因素法是指应当从具体个案中判断,一项智力劳动成果在受或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时,能否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能在知识产权立法政策之外的新因素出现时才能对之进行规制。 额外因素法在肯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智力劳动成果进行补充保护的同时,又对其补充保护的界限做出了合理限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体现出来。
额外因素法的运行要按照以下三个步骤。
(一)穷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正如前文所述,在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交叉案件中,存在很多向一般条款逃避的情形。 而反不正当竞争法要对知识产品进行补充保护的前提,应当是已经穷尽了知识产权法对该项智力成果的保护,即对于知识产权法已有相关条文进行规制的,应当优先适用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这就要求对于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案件的讨论首先应当在知识产权法的内在逻辑框架内进行,简单来说就是对于智力劳动成果的保护应当以知识产权法为主,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辅,从而避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或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
(二)是否符合知识产权法之立法政策
在穷尽了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后,还应当考察知识产权法对该问题的空白是立法疏漏还是有意排除。 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品的保护采用 “设权模式” ,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的 “行为规制模式” 存在根本区别,知识产权的取得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且具有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因此一项成果穷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都不能受到保护,存在两个原因,一是立法者有意将这项成果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即前文提到的 “著作权不保护思想,只保护思想的表达” ;另一原因在于法律本身存在滞后性和不周延性,不能穷尽所有需要保护的权利类型。 当个案中的成果属于后者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保护,当该成果与知识产权立法政策相悖时,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救济是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相悖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只能是补充保护,而不能在此之外创设不符合知识产权立法政策的权利保护类型。
(三)是否存在额外因素
当某项智力成果与知识产权立法政策相冲突时,应当谨慎对其进行考察,因为知识产权立法政策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哪些知识产权应当进行保护是从国家宏观角度予以考虑的,因此若不存在知识产权立法政策之外的新因素,则不能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对之进行补充保护,否则将会任意拓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比如在 “泰盛与暴风影音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中,被告暴风影音在其播放器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视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原告泰盛享有该影视作品的独家复制权和发行权,该案一审法院认定暴风影音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因在于 “暴风影音提供的在线播放业务会影响该影视作品的线下实体交易,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 但是从知识产权法框架内看,原告泰盛并不享有该影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不能作为适格原告提起诉讼,该案不存在知识产权立法政策之外的新因素,但是却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但是明显有悖于知识产权法所架构的著作权的权利保护体系,不适当地拓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
四、结语
综上,在选择适用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应当按照相应的步骤进行,只有在符合额外因素法适用的条件后,才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进行补充保护,要坚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以知识产权法为主,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辅,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才能避免实务中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滥用,合理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