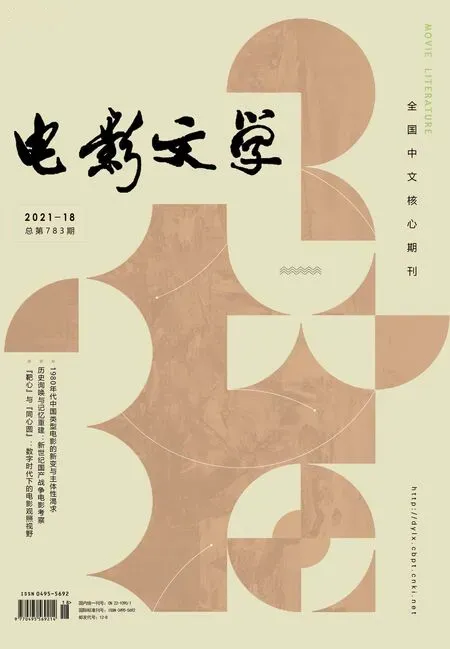电影《我的姐姐》中的多重叙事进程
赵世佳
(衡水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电影《我的姐姐》是新晋女导演殷若昕的一部口碑与票房均不错的作品。影片主体情节是一对夫妻因车祸丧生,他们有一个刚刚成年的未婚女儿,也就是本片的姐姐,她在医院当护士;还有一个需要养育的幼子,也就是本片的弟弟。因父母的过早离世,弟弟的养育问题就成了姐姐人生阶段的一个困境:选择传统的家庭血缘伦理还是自身生命的自由,两者只能选其一,但失去任意之一都或将成为人生的大遗憾。影片正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框架中搭建起来的,单从这个框架来说,该片算不得精彩,甚至可以说内容比较松散,很多情节是游离于主体框架之外的,但影片并没有给人枯燥乏味之感,它那种在沿着故事主线慢腾腾前行的过程中不断的旁敲侧击,给人产生了一种散文式的韵律,并且那些旁敲侧击并非没有意义,它们虽不能解决影片主线框架所提出的难题,却能与之纠缠在一起,从多重层次上影响主体人物的行动,并且在潜层形成与表面不同的含义,它们不断地形成主线叙事与辅线叙事的互动,不断地展现隐性进程对情节进程的补充或对立,不断地加深那种困境,使选择变得更加难。可以说,影片是在一个极其简单的结构框架中完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阐释,正是其简单的主线情节与丰富多元的辅线叙事和隐性进程的有机结合,使得影片成为一个具有多重叙事进程互动的韵律舞台。
一、情节进程中辅线情节对主线情节的渗透式影响
故事应该有完整统一的情节结构,但并不必须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的各个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如果把任何一部分挪动位置或删除掉,就会严重破坏它的完整性”。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是建立在戏剧实践之上的,那时的演出不允许在故事的主干上分离出细小的枝叶,而且它也容易得到心理认同,于是具有紧密组织的故事结构就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是,另外生发的枝叶情节就不是故事整体的有机部分了吗,旁敲侧击就真的会破坏主体情节的整体性结构吗?在一些文本中,如果枝叶情节与主干叙事发生了严重偏离,以至于难以找到两者之间的深层联系,这确实是值得否定的;但如果两者之间有着可察觉的深层联系,并且正是这种枝叶情节所形成的辅线叙事促成了主线框架中人物性格及行动选择等,那么这些枝叶情节就应该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看待辅线情节与主线情节的关系,主要还是看前者怎样服务后者:它可能使得主线故事表达含义变得更丰满、更多元,又使这些意义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结构框架之内。显然辅线情节与主线情节统一协调的叙事结构需要缜密的建构,可能并不多见,但影片《我的姐姐》正是一部这样的叙事作品,它的辅线情节不断地对主线情节进行渗透式的互动,使得略显单薄的主线框架也变得丰满起来。
失去父母,却又相对陌生的姐弟,被迫相处在一起。这个过程中,两人关系慢慢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冷漠逐渐变得热络起来。但即便如此,姐姐也一直面临着人生的自由或现实与家庭血缘伦理的选择。这样一个主线故事当然比较单薄,选择本身的意义也比较乏味,观众对它感受的鲜活性应该是短暂的。可以说影片是另寻其道,在主线故事上不断加载辅线叙事,给一个单薄的情节赋予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背景,使得每一个配角都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符号,也使得主体人物逐渐鲜活起来,其性格、行为都有了合理的来源;尽管背景意义偏离了主线叙事中那个选择,但决不能说两者之间失去了联系,它们以主体人物的性格及行动为纽带,并融合在一起:辅线叙事产生的意义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了主线叙事,但辅线的意义并没有失去其独立性,甚至给人造成了一种反客为主的假象。
一个重要的辅线意义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心魔,即那种对男孩的偏好。影片在其多个辅线中不断触碰这个“中国式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女儿的难以言说的委屈和伤痛”,观众很可能将此看作影片的主要立意,但必须指出,“重男轻女”并非故事要解决的问题,那个养与不养的问题并不涉及重男轻女,它只涉及一种自由与血缘的对立。因此辅线意义对主线意义并无直接干扰,但这些辅线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安然的选择,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姐姐行动的触点。最初姐姐对弟弟的冷漠并非没有原因,她从小便承受来自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偏见,父亲让她假装残疾以换取二胎指标,没有成功,于是遭到毒打;为了让她不再成为家里的负担,不经其同意改变其高考志愿,使其职业从医生变成护士等,可以说她正是那种重男轻女思想下的受害者,因此她对这种观念必须是极其愤恨的,进而也愤恨父母及弟弟,以至于与父母疏远,对弟弟陌生,父母离世后其对弟弟拒绝养育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
重男轻女的辅线并非安然一条,姑妈也是,姑妈为了弟弟——安然的父亲能够读书,放弃了自己的学习机会,同时负担安然父亲的开销,并且在安然遭受家庭嫌弃后,也代替弟弟担负起了养育安然的责任,虽然安然在姑妈家的成长过程并不顺利,成为表哥练拳的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在姑妈这条辅线中,安然属于间接受惠者,但这种受惠的最终根源并非姑妈,而是其同样作为弟弟的父亲。但当安然面临选择时,作为“好人”的姑妈已没有能力再让安然间接受惠,现实已不再允许她为弟弟承担责任,于是姑妈期望安然能像自己一样,作为一个理想的姐姐,随时牺牲自己。虽然安然并不认同姑妈牺牲自己的行为,但她作为受惠者,并没有显现出特别抗拒,倒是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温情,可能正是姑妈这条辅线成为安然与弟弟之间的润滑剂,使安然本已坚定的心动摇。但必须指出,这条辅线并没有实际影响安然与弟弟之间的关系,它似乎是仅仅表现给观众的,给观众造成一种改变安然的幻觉,但对于安然来说姑姑的一切是既在的事实,这条辅线在影片开始时就应该已经感动着安然了,但她不为所动。因此它的作用并非形成人物的行动动机,而是导致观众对姐姐的行为形成某种不愿意承认的期待倾向——姐姐也应该成为牺牲者。
另外,舅舅作为影片中的一个重要配角,他的很多行为属于主线叙事,他提出了自己有偿成为弟弟监护人的方案,尽管方案最终流产,但无论如何这对主线叙事来说都是一种突破,而且他也间接导致造成安然父母去世的车祸司机帮助安然替弟弟寻找新的父母。但舅舅本身确实存在一条辅线,即其失败的婚姻,以及女儿结婚也只能托安然帮自己随上份子钱。舅舅在这条辅线中影射的是一个失败得一塌糊涂,却又带有几分亲情的形象。由于这条辅线与几条重男轻女的辅线交叉在一起影响主线,观众很可能将其作为重男轻女的一个反例,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影片确实对重男轻女现象给予了呈现,观众很容易将舅舅阐释为对此现象的一种讽刺。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就很难确认这条辅线对主线故事的推动性。实际上这条辅线正暗含了家庭血缘的巨大作用,舅舅作为一个典型的失败人物,其与女儿的关系是破裂的,但亲情血缘犹在,舅舅送去的份子钱及托付安然用有纪念意义的相机给女儿拍摄照片,以及女儿的哭泣,其显示的都是遗失家庭血缘所造成的那种巨大的失落感。舅舅在安然父母坟地山下独自喝酒,也可以看作是寻找那种家庭血缘联系,从而弥补那种失落。这条辅线对家庭血缘的反映显然是重要的,因为安然面对的正是现实或自由与家庭血缘之间形成的矛盾。但同样必须指出,这种反映并不能在主线中真正影响安然的选择,它也只是在观众心中将家庭血缘的分量加重,在感觉上加大了安然做出最终抉择的难度。
可以说不管是与重男轻女相关的几条辅线,还是舅舅那条凸显家庭血缘的辅线,当它们与主线产生作用后,实际上都倾向于安然牺牲自我,戴上那个与家庭血缘联系的枷锁。假如影片仅仅如此,假如安然仅仅是放飞自我,那只能看作一种任性,其无端放弃传统的家庭血缘伦理于观众而言应该是难以接受的,安然将作为一个讽刺对象,但影片并没有将安然置于这样的境地。影片还有一些辅线,是从重男轻女的辅线中延伸出来的,但却对总体的感受倾向起了巨大的平衡作用。安然想当一名医生,由于父母的自私行为,只能做护士,她要实现自己的职业愿望就只能脱离目前的环境。这条辅线正是从现实的角度抗衡前面提到的几条辅线,它与主线之间的关系要更直接一些,它实际上构成了安然拒绝扶养弟弟的真正理由,可能正是为了强化这一理由,制造了安然与女医生之间的矛盾情节,并由安然男朋友之口道出了女医生家庭背景的强大,这几乎是切断了安然已有的生存之道,她只能辞职,逃离这个环境。影片反映安然现实的辅线并非仅仅一条,安然的婚姻问题实际同护士与医生的辅线非常相似,只不过它对主线的作用不够强大,影片在这条辅线上的发挥算是力道不足,或者是为了更突出那条与职业有关的辅线,进而降低了其作为主线的力道。
可以看出,整部影片一直将安然置于一种抉择的境地,如果仅仅这样向前发展,也就是姐弟之间关系的逐渐贴近,最终安然做出抉择;影片并非整体从这样一个稍显枯燥的过程入手,而是从各个角度产生相应的辅线,虽然这些辅线“不免具有偶然性,彼此之间见不出必然的互相因依关系”,但它们却共同渗透作用于与主线中的现实自由与家庭血缘伦理的对立之上,加大安然最终抉择的难度,也使得影片更有韵味。
二、隐性进程与情节进程间的互补式碰撞
如果说影片中辅线叙事与主线叙事结合,使得简单的故事主线得以向前顺利发展,人物行动的动机更加明确,进而形成一个饱满的叙事;那么影片的隐性进程则与情节进程在意义上形成了互补式的碰撞,使得影片阐释的含义更多元化,更能使观众产生碰撞式的思考。隐性进程是申丹教授提出的一个创新性的叙事进程概念,其与叙事进程中情节进程是并行的,它们“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两种相异的人物形象和两种互为对照的审美价值”,并且隐性进程在主题意义上可能与情节进程呈现“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但补充或颠覆性的意义并非在文本之外,它仍应符合修辞叙事的那种实用性,即“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只不过在那种双重阐释中,所谓的叙事目的将变得多元化,甚至矛盾化,但也正是这种多元化和矛盾化形成了故事中人物的行动,也形成了文本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可以说只有融合了隐形进程的意义,情节进程的阐释才可能完整。因此看待影片《我的姐姐》的意义,需要从人物及叙述的隐性进程中进行判断。
首先,影片情节中,安然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与其职业有关,从情节进程来看,其逃离目前处境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对其高考志愿的篡改,及自身的职业规划,大多数观众会感受到:这里存在着对护士职业的某种贬低,认为护士不如医生。这是安然想要逃离所处环境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如果仅靠传达这样一个负面概念,影响主线情节的进程,是不太合理的,它很可能引起观众的反感,但这种反感在实际观影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概念很容易被其他更明显的概念掩盖,它显然没有重男轻女、家庭血缘伦理等概念在影片中产生的情节意义强大,但影片确实存在与其相关的足够分量的情节,只不过它们与情节进程所传递的信息并不一致,因为它其实从更深层次上表露了护士在临床救治过程中并不比医生差,我们看到安然的一段精彩的抢救过程,她还及时纠正医生医嘱中的错误,护士起到了医疗救治中最后把关的作用。这样看来,安然逃离的似乎并不是这个职业,而是通常对这个职业的偏见。隐性进程在这里产生的含义与情节进程的含义是互补的,这其实使安然的逃离具有一定的反讽意义,使得主线情节表层所表达的那种对护士职业的贬低被消解了,随之消解的应该还有观众的反感吧。
再就是影片的情节进程讽刺的是那种重男轻女观念,顺带着对那种家庭血缘伦理的基础也形成了某种消解,因此从情节进程来看,只能看到人的现实自由与家庭血缘伦理之间的对立。但从隐性进程看,影片的隐含作者似乎一直对那种传统的家庭血缘伦理充满着敬意,或者说对那些女性的牺牲精神充满着敬意。影片在两个方面隐含着这种敬意。一方面是影片对姑妈的表现反映的,尽管影片的情节进程是对这种女性牺牲观念的批判,但影片中姑妈作为自愿戴上那个枷锁的形象却并非以一个牺牲者的形象来对待的。对于安然来说,她更多的是人生指路人,安然父母死后也是她主要操办他们的葬礼等。从内容上来说,她绝不是以一个女性牺牲者的形象出现的,她透露出的是精干、爽朗甚至有些霸气的感觉,其中还蕴含着深厚的情谊。安然离开前给姑妈深鞠的一躬可以看作对姑妈的感激,但于影片而言其实是对那些重男轻女家庭血缘伦理枷锁下勇于承受的女性的敬意。而且影片给姑妈的镜头大多是仰视的,无形中给这个形象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因此姑妈尽管在情节进程中应该是一个家庭血缘伦理的那种重男轻女枷锁下的牺牲者形象,但具体的影像内容实际上却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那种承受精神的赞扬,甚至隐隐地对以安然为代表的那种对传统家庭伦理承受精神的缺失表达了某种慨叹。另一方面,则是安然在逃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影片开始安然拒绝扶养弟弟的态度看上去是决绝的,并且随着情节进程的不断向前发展,情节进程中的辅线也为观众交代了这种决绝的原因,其实在这种原因面前,安然拒绝承担责任的心理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影片在交代安然拒绝原因的过程中,却使安然表现出巨大的痛苦感,仿佛随着真相的揭露,这种拒绝对于其自身而言成为一种原罪。在影片的后期,安然在客厅里对着父母的照片哭泣,字面的意思是想得到父母的承认,但父母已逝,其与父母之间的纽带就只剩下唯一的弟弟,其实这也是在隐性进程中再一次呈现出家庭血缘伦理在安然那里仍然有着强大的作用力,以至于安然想要斩断这种观念的束缚需要承担极大的精神痛苦。并且观众不仅在安然身上看到了这种痛苦,舅舅与其女儿之间也有着相似的痛苦,这也从辅线情节的隐性进程中表现了家庭血缘伦理的强大。
从现实角度看,安然面临着自身职业的自由愿望与承担家庭血缘伦理责任的对立:在愿望中表现了两种差异性的职业,似乎护士是一种与临床医生不对等的低等职业;在责任中把重男轻女与这种责任相关联,似乎是将这种责任置于一种接受批判的位置。但是,这样解读情节的意义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很明显,影片情节中人物的行为以及叙述过程中的隐性进程显露出了不同的意义,只有同时掌握了情节进程与隐性进程的意义,才算是完整地掌握影片的意义,尽管两种意义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这更能显示出文本意义的辩证统一性。
可以说,影片《我的姐姐》主线情节简单,表层意义也比较单一,但影片在情节进程中,将比较复杂的辅线情节与主线情节结合起来,尽管辅线情节在意义和线索上都具有独立性,却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着人物的行动动机,也影响了观众对情节的期待倾向;另外其叙事的隐性进程一方面修正了情节进程中可能会引起观众反感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与情节进程似乎矛盾的观念。那么也正是这种较复杂的辅线与简单主线的融合,隐性进程与情节进程的矛盾统一,才使得影片的意义更加完整,才使得影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