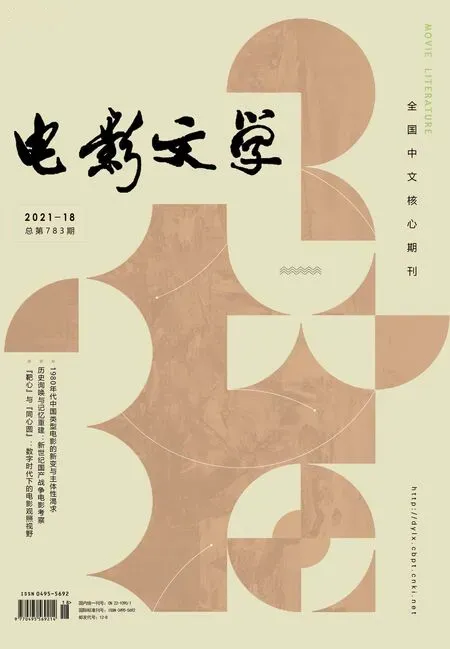论周晓文八十年代的类型电影实践
李思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站在21世纪的坐标轴上回看中国电影历史,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个让人无比怀念的黄金时代——十年浩劫已经结束,改革开放正在进行,思想解放和启蒙几乎成为整个80年代的主导话语,伤痕文艺、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兴起、退场与延续,也对电影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这种社会巨变和文化思潮为底色应运而生的新电影自然呈现出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面貌。无论是第四代导演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追求与在电影本体论意义上对“电影就是电影”的坚持;或是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对影像美学的探索与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都因其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和辉煌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20世纪80年代绝不是一个仅有艺术片探索的年代。文化上的精英话语之外,还有经济制度开始转变、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趋势不容忽视,以及这一趋势下与市场和大众更为契合的商业电影的实践和发展。
必须厘清的是“商业片”“娱乐片”“类型片”三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商业化”一词被视作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连接遭到批判,然而进行一种面向市场、面向观众的电影实践又是如此之迫切,这迫使当时的电影人对“商业电影”概念进行了一种策略性的改述,着重强调电影的愉悦功能的“娱乐片”便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对商业电影一种约定俗称的称谓”。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当政治经济环境逐渐转变,“娱乐片”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逐渐被“商业电影”的说法所取代。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当下,要发展商业片/娱乐片,“类型片”所蕴含的核心旨趣和艺术规律都几乎是一门必修课。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商业片/娱乐片,都可归为类型片。或者说,“类型”是抵达“商业”和“娱乐”的一种重要方法。
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电影史书写,都将重心放在第四代、第五代的艺术电影探索和成就上,却很容易忽视与观众联结更为密切的娱乐片发展。以周晓文为例,在本就不多的关于周晓文的学术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艺术片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人们似乎已经淡忘,是20世纪80年代的“疯狂系列”使他声名鹊起,是对类型的探索和对艺术与娱乐的巧妙平衡使他成为一名“叫好又叫座”的导演。历史的错位体现在:即使周晓文对娱乐片的探索、类型化的尝试大获成功,但真正使他进入主流电影史书写的作品却还是东方奇观式的艺术片《二嫫》。这种错位并非偶例,它饱含了复杂的政治历史因素。当体制改革滞后于时代需求,当电影的商业化探索超越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准备空间,那些夹缝中的探索者注定要在错位中长久等待。
今天,当中国电影开始高度市场化、类型化,当重写电影史的呼声不断高涨,或许正该是我们重返历史现场,重新认识和评估那些一度被电影史所忽略、遮蔽和遗忘的20世纪80年代电影实践的时刻。本文意在以周晓文导演的“疯狂系列”电影为切入点,探析作品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阐述周晓文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的类型电影实践对中国电影史的特殊意义,以及对当下电影创作的启发。
一、“疯狂系列”产生的电影语境
所谓“疯狂系列”,指的是周晓文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两部影片:1987年的《最后的疯狂》与1988年的《疯狂的代价》。《最后的疯狂》于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疯狂的代价》也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的4项提名与金鸡奖的最佳剪辑。
这两部影片在当时不仅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更是在评论界、理论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89年前后,《当代电影》编辑部召开了《疯狂的代价》座谈会,杨远婴、李奕明、贾磊磊、钟立、尹鸿、戴锦华、张卫、李迅、李陀等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各自对该片的看法和解读,尽管解读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都对《疯狂的代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专家学者们在这一会议上的发言被整理成文,发表在《当代电影》1989年第二期上,不仅如此,同期另有两篇文章补充着关于周晓文其人及其作品的信息,包括编剧芦苇对合作者周晓文的回忆和介绍以及柴晓峰与周晓文本人的对谈记录。这些足以表明学界对周晓文和“疯狂系列”的巨大热情和兴趣。那么,“疯狂系列”究竟诞生于何种电影环境中?它做出了哪些新的突破?为何获得如此巨大的反响?它对当时的中国影坛又有何特殊意义?这都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对“疯狂系列”所处的电影大环境的探析同时也是寻找其大获成功的外部原因的过程。《最后的疯狂》上映的1987年,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一方面,长期被认为是电影的主流的艺术片成就突出,从第四代起就以西方电影理论滋养创作的中国艺术片在此阶段开始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张艺谋和陈凯歌在1987年分别凭借《红高粱》和《孩子王》入围戛纳和柏林电影节,中国电影终于再次出现在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版图中,并因浓郁的民族色彩让世界发出一声惊叹。不仅如此,艺术探索还在向前推进,1987年黄健中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将这种形式的探索发挥到极致,但同时,这种更先锋、前卫、实验性的电影也让艺术片离观众越来越远;另一方面,观众流失的现实问题如此之迫切,一场旨在加强电影娱乐性的理论大讨论呼之欲出——1987年,《当代电影》杂志连续三期刊登了《对话:娱乐片》,从理论层面发起了对娱乐片的大讨论。更重要的是,随着各制片厂创作人员加入讨论,大家对目前中国娱乐片的发展状况和如何借助类型发展娱乐片等问题的认识更加深了一步,多篇讨论类型电影的理论研究文章也陆续推出。在理论的滋养和引导下,1987年各个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大批以娱乐为目的的影片,如《金镖黄天霸》《翡翠麻将》《黄河大侠》《东陵大盗》《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等片,一些知名导演如吴贻弓、滕文骥、黄蜀芹、张艺谋等纷纷加入娱乐片的探索,实践对理论的“追随”让娱乐片风头更盛。到了1988年,“包括武打样式、惊险样式、歌舞样式等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达80部,占全年故事片总产量的60%以上”。“疯狂系列”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一个即普通又特殊的样本。
称其普通,是因为“疯狂系列”的两部影片与同时期的众多娱乐片一样,为长期匮乏娱乐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渴望娱乐性的电影观众带来了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但同时它又是特殊的、突破的样本,这在于它对当时娱乐片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突破性的解决并尝试为中国电影寻找一条新路径。
二、一个突破的样本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娱乐片创作风潮看似热闹非凡,但实则存在诸多明显的问题。一是创作者们“轻视娱乐片”的态度。当时正逢艺术电影在海外崭露头角,大部分人依然以影像探索和艺术表达为荣。而对娱乐片的探索大多是被迫的、非自觉的。娱乐片的地位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二是创作者们“不会拍娱乐片”的窘境。早在1985年,李陀就在与陈荒煤的通信中指出:电影观众的减少和上座率的降低并不仅是因为艺术探索片的出现,而且市场上也并非没有以娱乐为目标的影片,这些娱乐片之所以无法吸引观众,是因为创作者们还没有把握娱乐片的艺术创作规律,反倒盲目自信,认为“哄观众高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长期以来,特殊的制片体制使得电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对观众的远离和对所谓“类型”创作经验的不屑使得当时的娱乐片多是单纯娱乐元素的堆砌,产生了许多杂耍式电影。或是将清末民初的民间奇侠故事与功夫打斗场景融合,或是展现一次危机/案件的解决过程,将日常生活中鲜能见到的大场面或惊险体验铺陈开来。总之,娱乐片总体呈现出简单、俗套、猎奇的特征。正如当时的学者所概括的:“一时之间,主创人员几乎涉猎了娱乐片的所有题材:凶杀、警匪、情爱、武打、劫机、行窃,诸如此类。但观众依然不爱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创作还没有真正进入娱乐片的形态范畴,还没有找到完整、娴熟的娱乐片的叙述方式。而只是一味地靠改变影片所涉及的表现题材来招徕观众。”在这种情况下,周晓文的创作实践展现出一种可贵的突破。
(一)高度自觉的娱乐和受众意识
周晓文的突破首先在于其高度自觉的重视观众、追求娱乐的意识。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探索片、艺术片占据大部分注意的时代。不仅如此,中国电影还有一种从郑正秋起就有的肩负社会人心的教化传统。20世纪80年代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精英话语的确立也使得文艺一度被放置在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的境地。虽然在经济压力下,有很多导演去拍娱乐片,但那大都是一种无奈之举或是权宜之计。周晓文倒也并不能算一个完全的例外,他在创作思考中坦言,“《最后的疯狂》是1987年西影派给我的‘赚钱’任务,我接的时候并非十分情愿”。但是,周晓文在创作初期就展现出的对观赏性、娱乐性的重视以及与对观众心理的研究是高度自觉的——“《最后的疯狂》充分考虑了观赏性、娱乐性,研究了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节奏、兴奋该如何安排、气氛该如何营造等”,在叙事上也力求清楚明白,绝不含糊,以免让观众摸不到头脑;对创作者与观众的关系这一问题,他认为“导演不是观众的教育者,而是观众的好朋友”。当被问到对电影在社会上的教化作用与如何用电影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周晓文坦言“不知道”,并进一步谈道:“我知道的,是电影界首先应该教化教化自身才好……我实在不配说什么教化,也拍不了这种片子。”即使在想表现人的精神焦虑的《疯狂的代价》一片中,也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因素,不忘“一味地搞得很沉沉,就会失去很多观众”。可以说,获得观众并留住观众,这一点几乎是周晓文前期创作中的重中之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此,即使他也有作为“电影的作者”想表达的艺术的一面,也只能在娱乐观众、为观众所接受这一范畴中“戴着镣铐跳舞”,这或许与他的第一部影片的遭遇有关,但这种对观众感受的认真对待和对娱乐观众的高度自觉,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显得格外宝贵。
(二)新路径的自觉追求
与同期娱乐片表现出的单薄苍白相比,周晓文的突破还体现在自觉去追求一种艺术与娱乐的结合上,自觉地去深化娱乐片的精神内涵。
虽说《最后的疯狂》与《疯狂的代价》都是娱乐性影片,并且是具备较为成熟的类型意识的娱乐性影片。但同时,脱胎于体制内,长期受第四、五代导演审美品格影响的编剧和导演又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电影的艺术追求。这看似矛盾,却正是当时的评论理论界针对当下中国电影现实问题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也是周晓文努力去实践的“新路径”。
这并非笔者臆断。周晓文在《最后的疯狂》拍摄完毕后,曾在访谈中提到:“当今电影界、理论界对艺术片和商业片产生着严格的档次分界。提到娱乐片往往认为比较粗俗,胡编乱造。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我曾倡议过:要拆掉娱乐片与艺术片间的这堵墙。有人看过《疯狂的代价》之后曾说,这部影片不伦不类,导演不懂什么是电影。我是这样想的:把艺术片与娱乐片二者综合一下,拍出一部自觉的反类型电影。”这里的“反类型”,所指应是“艺术片”“娱乐片”这些电影界严格区分的“类型”。周晓文认为,当时的中国电影不具备拍摄纯娱乐片的经济条件,“与其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搞小打小闹的东西,还不如在影片中增加人物命运深刻塑造、强烈的时代氛围和社会风貌的展现等内容来拍娱乐片”。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有诸多现实因素的考虑,但周晓文对一种新的电影发展路径的探索是高度自觉的。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也体现出这种融合的倾向:“我希望我拍的影片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使观众达到一般层次上的审美愉悦。同时在我的影片中也能更多地追求,表现艺术家对社会、人生、伦理等方面的深层思考。”在这条类型意识与精英话语结合,娱乐元素与艺术品位交融的“新路径”中,周晓文迈出了令各方都颇为满意的一步。
(三)类型的方法与艺术的借取
这种艺术与娱乐结合的新路径主要依赖两个方面,一是类型化的叙事表达;二是艺术的借取,也即对人的书写。
对影片类型化的自觉追求在“疯狂系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以《最后的疯狂》为例,追逐的悬念在一开始就被抛出,配合音乐与平静的都市、海景交叉,有股吸引人心的力量;片名出现后,紧接着的就是黑暗中的飙车戏码和激烈的警匪争斗。可以说,导演在开场就将城市空间、警匪、汽车和枪支、追逐与暴力等警匪片固有模式中的元素统统抛出,兼顾到观众的感官刺激与剧情需求上的悬念铺设。在《最后的疯狂》中,商场中宋泽的逃跑被错认、刘福泽欲杀宋泽却被宋泽以颇具暴力美学意味的方式反杀、宋泽对三位女孩的控制和失控、结尾部分列车中的“业余演员”与何磊的配合以及众人在“戏中戏”中与宋泽的博弈,最后宋泽与何磊的身体对抗和爆炸景观等,在镜头的运动和影片的氛围上都最大限度地体现着紧张的追逐与激烈的力量对抗,而这正是警匪片、惊险片所必备的元素。
在人物的塑造和主题上,《最后的疯狂》也如一般的警匪片模式那样展示了一个“叛逆”却正义感十足的警察和一个复杂多变、势均力敌的对手,并对观众完成了一次善之中心的宽慰——虽然过程曲折艰难,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法律终将战胜邪恶,善和正义终将到来。当然,我们今天来看,这些探索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是对叙事和节奏的把握上影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许多地方徒有意识却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回看起来总有些“浪费”之感,但这是历史背景和条件所决定的,无须苛责。
对人的热爱和书写是周晓文作品中绝对的主题,而这一特质正是他联通类型、娱乐和艺术的关键。他曾说自己拍电影的座右铭是“要热爱人,并且公正”,也自我小结道:“统观我的几部片子,我一直对普通人的命运比较感兴趣。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影观众中普通人居多,那么,银幕上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易使广大观众产生共鸣。”这既是站在观众的角度,也是站在艺术的角度,无论是娱乐片、类型片还是艺术片,引起人的共鸣永远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在娱乐片的讨论中,除了将娱乐片的兴起和发展放置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讨论,还有学者将娱乐片的必要性与新时期人的复归联系在一起,在新时期的电影中,尤其是第四代的电影中,对人的主题的发掘,对人的命运和价值的重新书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另一方面,“娱乐片是以其自身形式来表达了人的主题,对人性的最基本要求来进行一种沟通、对话……娱乐片是面对着更完整的人”。
周晓文正是通过对人的绝对突出在类型片的范畴中打下自己的文化烙印的。《最后的疯狂》中,何磊与宋泽一警一匪,一正一邪,导演却将二人设计成年龄、身世、经历等各方面颇为相似的两个人,在细腻的笔触中勾画出两个有血有肉、矛盾又真实的人物形象,正义的警察也有撬门“偷”材料的“劣迹”,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也有柔软的瞬间,就连列车上的乘客,也有又怂又勇的平凡人的高光时刻。何磊与宋泽的“双生”设定和对准每一个角色的镜头让影片的细节和现实感得以丰富,这使影片脱离娱乐片外还有很大的解读空间。《疯狂的代价》中更是如此,当导演更进一步把镜头对准人的心理状态,当熟悉的双生设定再次出现,当导演在犯罪、惊险的故事之外展示了一个广阔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影片再次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有人从中看到了“工业化进程中城市生活的文化命题”,有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电影文本,有人“觉其微弱地流露出‘雌雄同体’的文本意向”……对人的关注是周晓文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90年代当他“回归”到艺术片的创作,这一特质依然没有改变——在《二嫫》这一影片背后,他不是关心90年代经济关系变化,而是“关心经济关系变化后,权力关系也跟着变化条件下的中国人”;对权力、对个人性格的塑造这一话题,他所感兴趣的是“拥有权力的人,失去权力的人,拥有财富的人,拥有欲望的人”,他坚定“我只对人感兴趣。我的出发点不是用人来揭示社会,而是用社会信息来揭示人”。
三、类型化道路:超越、中断与续接
作为娱乐片风潮中的产物,周晓文的“疯狂系列”与同时代的娱乐片一样对改善中国电影娱乐性匮乏的局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个突破的样本,周晓文又因其对类型的自觉追求和对艺术片的借取,探索出一条艺术与娱乐融合的发展道路,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新路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丰富了“类型化”在当时中国娱乐片发展中的内涵。
他曾在创作谈中提到,《疯狂的代价》中,为了“写人”、为了让观众产生“落空”,他“产生了反类型的愿望”,“反类型必然会让人觉得唐突,觉得期待落空。这个不怕,今天的反类型可能明天就会成为类型,然后又出现有志之士来反它,电影的类型总会越来越丰富”。周晓文对类型的超越是双层意义上的,一方面《最后的疯狂》超越了过去一些国产惊险片“迷恋于编织曲折离奇的情节,将情节置于人物之上,将人物仅仅当作惊险情节演进的手段,因而满足于叙述案例或交代故事,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的局限。另一方面,在《疯狂的代价》的结尾,当青青把罪犯踢下塔楼、当她从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当兰兰对着因为自己而犯罪的姐姐吹了一个大泡泡时,周晓文也完成了对《最后的疯狂》的超越,甚至是对《最后的疯狂》所代表着的一类惊险片的超越。这既令人惊喜又令人担忧,在中国电影还处于类型片初探的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导演有了超越类型的意识并开始实践。虽然在当时,类型的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大部分导演还不具备在类型框架内“讲好故事”的能力,这一超越或许是“过于超前”“不合时宜”的,但其意义依然是重大的、值得被书写的。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整体趋势是去政治化,体制内的导演在艺术探索的同时需要娱乐和类型的元素来留住观众,所以娱乐与类型得以凸显其价值,才使得周晓文艺术与娱乐相结合的“新路径”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影坛马上迎来了90年代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创作的回归,尽管在主旋律电影中,观赏性的要求被明确提出,但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依然是第一位的。这种政策的导向也影响到了周晓文的创作,虽然他本人一直不喜“娱乐片”与“艺术片”的区分,但是当他在90年代出现《黑山路》《二嫫》等第五代式的作品时,这种明显的创作转向无形中也构成了一种自我背叛。“疯狂系列”之后,周晓文的创作可谓一路坎坷,《九夏》中途夭折,《黑山路》生不逢时,直到1994年的作品《二嫫》才为周晓文赢得了斐然的国际荣誉和载入电影史的通行证,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开辟出来的“新路径”探索的中断。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寻找这一路径的历史渊源。若是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坐标上去寻找周晓文所探索的这条道路,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一种独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内在精神承继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传统——在“雅与俗、城与乡、外来的与本土的、电影艺术家主体审美意识与市民观众圈艺术趣味之间寻找平衡”,而这恰好也是“在力求使影片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与照顾到几亿普通观众的接受水平之间”倾注心血的周晓文导演所不断尝试的。三四十年代,电影的艺术与商品的两重特性,迫使艺术家们不断调节“电影文本内思想成分、形式功能和商业效应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周晓文也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需要兼顾影片的娱乐价值和艺术品质。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改善电影一味娱乐而无内涵的状况是以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到电影界为转机的,文学性的介入为电影注入新的力量,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周晓文则完成了一个置换,是政治本位电影体制内孕育出的兼具艺术探索精神的知识分子自觉把商业的、类型的思维引入到电影中,借此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
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否需要续接这一度被继承又被“中断”的路径呢?笔者认为,不仅可以,而且非常迫切。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电影格局依然没有超出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范畴,然而无论是艺术探索片还是商业类型片,创作氛围和整体水平都未及过去辉煌——艺术片成为鲜为人知的“小众”电影;而仍将类型化作为重要的艺术方法和市场策略的商业片却往往只剩“商业”,而鲜有内化类型艺术规律的精品出现。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抛出的关于电影发展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对类型电影的艺术规律依然学习得不够,商业电影的品质依然亟待提高,我们更未完全建立类型化的评价标准和观赏意识,自觉在商业与艺术中寻找平衡的电影也是凤毛麟角。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当电影市场逐渐规范、观众审美逐渐成长,当呼唤电影艺术性回归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许多商业片为了提升质量做出了很多尝试,如在文艺片与商业片中寻找微妙结合点的《芳华》,在类型的框架中讲述一个现实主义故事的《我不是药神》,又如主旋律电影主动寻求与类型模式合作的《红海行动》等一批引起广泛讨论的影片……但就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国电影市场总体而言,“烂片”的产出率远高于“好片”,而这些“烂片”仅作为商品都尚未达到合格标准,更妄谈艺术品质。
在这种状况下,或许我们更能发现在当下重提周晓文的意义所在:其一,如果要拍观众喜闻乐见的类型片,那便去研究、遵循其内在的艺术规律;其二,即便是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影片,也要加入自己的“思想”,丰富影片的精神内涵,尽力在娱乐与艺术中寻求平衡。周晓文在20世纪80年代便说,“惊险片也需要探索精神”,这样朴实的道理在今天依然值得倾听。尤其是在电影导演思想苍白贫乏,仅仅关注票房,一味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一不小心就走向媚俗的当下。正如沈义贞教授强调的:无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的导演,都要承担精神探索的任务,所有一切在电影史上留下杰作的、不同类别的导演,都起码是思想者,“无论是摒弃低级趣味抑或是迎合审美期待,没有思想的高度与精神的探索是无从谈起的”。周晓文的意义也在于此——关于如何在中国语境之下学习、熟练和超越类型,如何在类型的框架内承载更多的文化意义,周晓文的“疯狂系列”或许可以为当下的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一种参考思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各种探索并进的年代,那时有人在不断探索艺术的边界,同时又有人在“雅俗共赏”的层次上孜孜不倦,无论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都在现有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下创造了卓越的成就,那种在争论与商榷中不断修正、重建的电影生态和自由宽广的电影精神空间值得我们深思。学者陈墨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娱乐片风潮时感慨:“80年代虽然很多东西很幼稚,包括娱乐性影片也非常不成熟,但是它确实给中国电影故事的复苏打下了一些基础,并且给类型片的探索也做了很好的铺垫,建立一个理论最基本的支点,然后再往前走就好了。可惜80年代结束得太匆忙,有一些事没有完成。不过世事如棋,新世纪又走到这上面来,隔空接力。”今天,我们重读周晓文在20世纪80年代的类型电影实践,我们回到历史去寻找那些曾被遗忘的影片和影人,重估他们的价值与意义,是对更加开放、自由的文化环境和创作氛围的一种呼唤,更是一种殷切的期盼,期盼未来的中国电影能够有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