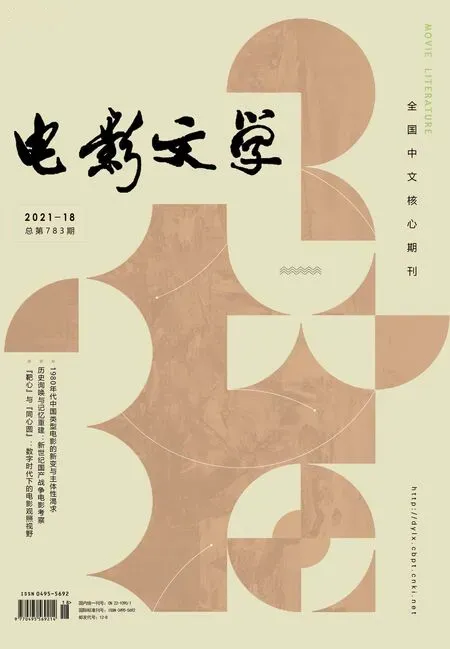张猛电影:底层人物的生存镜像
麻 敏
(湖南女子学院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在当代青年导演中,张猛表现出了某种坚守特质,这包括了对地域、对特定人群,以及对现实主义美学的坚守。在张猛的“东北三部曲”(《耳朵大有福》《钢的琴》《胜利》)等作品中,他让观众看到了一幅幅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诱发着人们进行关于真善美和道德理想的思考。当中国电影处于全球化语境中,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为娱乐诉求和商业逻辑所支配时,张猛的这种坚守无疑是极为难得的,他对底层人物生活的深刻反映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张猛的底层创作沿革
1975年出生的张猛,能够在“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中始终对底层题材保持专注,这一艺术取向的形成并非偶然。应该承认的是,家庭因素的影响使得张猛早早就拥有了一种底层视角。出生于辽宁铁岭的张猛,其父亲正是导演张惠中。张惠中所导演的电影,如《男妇女主任》《冰峪沟》以及电视剧《大年初一》等,无不是有关现实生活、表述底层经验的作品。如反映东北农民生活的《男妇女主任》充满笑料,却又具有深层意味。电影的基调是乐观的,却也隐晦地表达了对基层官僚体制和形式主义,以及普通民众缺陷的讽刺。可以说,张猛的创作,正发轫于父亲始终扎根于东北的,将草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艺术化的一系列作品。
在谈及张猛电影的底层创作沿革时,我们并不能忽视小品在其中的艺术源流意义。和父亲编导了如《红高粱模特队》《三鞭子》等小品一样,张猛也一度积极地投身于小品的创作,与小品演员们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所编写的小品《功夫》和《说事儿》曾连续两年获得春晚小品类节目一等奖。与小品的接触也影响了他的电影创作思路,即从未遗忘锐利审视弱势群体的生活,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功夫》中三个骗子的诈骗行径等)给予反思,但同时,又高度注重电影的喜剧性,避免只是对苦难或丑恶进行简单叠加。
最后,张猛的执导筒之路,正是从底层叙事这个方向开辟的。张猛先后于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这期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如《偷自行车的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张猛也将自己追求的电影风格称为新现实主义,但由于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于底层生活的表现过于“赤裸裸”和惨烈,张猛有意识地要寻找底层的快乐与温情。在北电的电影文学研修班进修期间,张猛就拍摄了长达117分钟的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在手持DV中,张猛追踪了身边一位绰号“王大耳朵”的叔叔退休之后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可谓奠定了张猛之后聚焦底层的基础。完成进修后的张猛,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他的第一部登上院线的电影作品,正是改写成剧情片的、细腻表现了小人物的凄凉与温暖的《耳朵大有福》。这部电影在社会观察与人性发掘上的亮点,让张猛获得了上海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自此之后,张猛的视点便鲜有“上移”,始终关注着底层的人与事。
二、多面向的底层生活观照
从内容上来看,张猛在电影中对底层生活进行了一种多面向的观照。在他的镜头中,不同身份、拥有不同困境的小人物纷纷浮现,让观众看到他们的底层经验。
(一)经济困顿
对于底层人物而言,其最为明显的特质便是所占有的物质微乎其微,所拥有的各类资源都极为匮乏,以至于其不得不为日常生活而奔波劳苦。如在背景为20世纪90年代东北国企改制的《钢的琴》中,下岗工人陈桂林在失去工作的同时,家庭也面临分崩离析。前妻小菊与一个贩卖假药的、经济地位显然要优越于陈桂林的奸商再婚,想争夺女儿小元的抚养权。陈桂林无法提供给女儿一台真正的钢琴,使得女儿在家还要在画的黑白键上练习,这使得他产生了自己做一台钢琴将爱女留在身边的念头。而随着这项庞大工程招揽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余下岗工人困顿的经济条件也一一展示在观众面前,人们靠在简易房里开理发店、杀猪、开锁等维持生计,还有人刚买的猪肉便被偷走。人处于一种充满挫折、沦落和蹉跎的生存状态中。又如在《耳朵大有福》中,底层人对于生活风浪几乎毫无抵御力的状况被展现无遗。离开火车修理工这一岗位的王抗美自己疾病缠身,老伴也生病住院。为了省钱而拿走退休联欢会上的橘子,在去医院看望完老伴后便用给老伴的残汤剩水泡一块一的泡面充饥,以“我这里啥都有”婉拒网吧老板让他买包榨菜的建议。“耳朵大有福”成为一种讽刺。而电影中的底层者显然不止他一个。如当王抗美催促抽奖人给他找钱时说的是“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做饭呢”,对方说的是“你这要是假钱,我老婆就没饭了”。简短的对话完成了一次世俗写真。人物的挣扎是令人心酸的,而他们的坚韧又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二)身心苦难
而在收入微薄之外,人物因身心而饱尝的苦难也是张猛表现的对象。“身体是生命感受与生命存在的家园,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体现,身体的健康完整、生命的存续乃是自然和社会赋予一个人最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身体的受难、残缺、死亡却在底层叙事中频频出现,喻指着底层群体基本生存权利被无情剥夺。”如在《阳台上》中,22岁的张英雄在丧父之后不仅经济困窘,成为在上海流离失所的上海人,他还有着属于自己身体的束缚,那便是他在结识沈重后才意识到的同性性取向,然而沈重却有女友并和女友在张英雄视为自己秘密基地的“东方皇帝号”上亲热。而电影中的陆珊珊则作为一个智力障碍者,同样因为身心的限制在社会竞争中居于绝对弱势。她无法保护自己,让自己成为张英雄窥探而嫌弃的对象,被其他人骂“神经病”,甚至被父亲陆志强安排与别人假结婚,下巴上的创可贴暗示了她还受到肉体上的损害。她是比张英雄这一弱者还要孱弱的人,残缺的心智让她无法拥有安全、尊严与自由。
(三)行为失范
在生存条件的局促逼仄下,人们就有可能出现价值观的扭曲与行为的失范,如在《阳台上》中,从东北来到上海的社会青年沈重就一度将自己沾染的不良习气传给张英雄,在沈重的教唆下,张英雄偷过一个外地人的钱包,甚至产生了“搞了陆志强的女儿”的想法,几乎彻底堕落。尽管在电影的最后,张英雄放弃了杀死陆志强和强暴陆珊珊的念头,但他依然生活在无能无助、无所依靠、无所作为的境地中。而行为的失范又加剧了他们生存的坎坷。如在《胜利》中,陈胜利原本是黑帮老大,在被判入狱10年后,已经几乎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在想靠开幼儿园走正道谋生后,昔日被他挑断脚筋的娇哥又上门寻仇。类似的还有如《钢的琴》中涉嫌销赃的季哥,偷琴未遂、因为争风吃醋又和人大打出手的陈桂林,赌博的胖头等。行为失范只会让原本就身处底层者进一步远离社会的发展成果和权力中心,进一步边缘化。
三、有意味的底层镜像呈现
而在叙事的高度真实化基础上,是形式的高度戏剧化,在小品编撰中浸淫多年的张猛以各种方式对人物的生活进行加工,完成了一种导演介入、处理痕迹鲜明的底层镜像呈现。这既是张猛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突破,也是他有别于同样擅长用影像见证底层生活,但追求一种原生态纪实审美的娄烨、贾樟柯等导演之处。
首先是隐喻的运用。张猛电影中,“隐喻场面的安排调度既实现了叙事任务,又折射出诗意光辉”。例如在《钢的琴》的开场中,天空阴沉,细雨迷蒙,陈桂林组织的婚丧乐队正在为一场十分滑稽的葬礼表演,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的字样。而灵堂就摆在工厂的墙边,张猛有意将贯穿全片的两座高耸的冷却塔也纳入镜头。这便是一处十分明显的隐喻。电影中悼念的“母亲”正是这座即将被拆除的工厂,而陈桂林等人到中年的下岗工人们则正如失去母亲庇护的孩子一样彷徨无措,但还要用《步步高》音乐来“让老人加快步伐吧”。也正是因为不知人生的方向在何处,才会使得众多工友都投入到了陈桂林造钢琴的计划中来,他们没有挽留女儿的动力,认认真真地参与造琴完全是因为他们留恋“工人”身份和在工厂劳作的氛围。
其次是超现实画面的设计。在对题材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把握上,张猛往往又故意加入了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内容。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即“对现实抑或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猜测,抑或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否定”。如在《山上有棵圣诞树》中,在艰辛生活和日渐淡漠的夫妻关系的摧残下,海波分裂为一个强悍风光、胆大妄为的“黑道老大”自己和一个胆小懦弱的鱼贩子自己,而前者将后者杀死。这种幻象实际上是底层者对脱离困境的一种臆想。又如在《钢的琴》中,在表现造钢琴过程时,观众们看到男人们在轨道上用各种乐器演奏着激情澎湃而又荒腔走板的斗牛曲,而淑娴等女性则身穿红色大摆的舞裙翩翩起舞,所有人都面容肃穆。伴随着激昂的舞蹈,炉火通红,钢琴雏形渐渐出现。这一幕无疑是超现实的,是荒诞不经的,但也正是一种对现实富有诗意的猜测(这其实是淑娴等人与工人身份作别的内心活动)和否定(能在废墟中发挥才智造出钢琴的工人们却遭遇下岗,这本身就是荒谬的)。
最后则是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如前所述,张猛极为注重电影的喜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保证电影的娱乐功能而纵容电影滑向“滑稽戏”。张猛选择的是对观众既定审美经验的巧妙偏离,完成一种情绪丰盈的、神来之笔式的黑色幽默。如在《大耳朵有福》中,一张被写了“周杰伦三年二班”的一元人民币反复出场并总是被特写呈现,从网吧老板流入王抗美手里,再从王抗美手中流向算命者,结果在48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又从抽奖人那里回到了王抗美的手中。一张破旧且被人性涂鸦的小面值钞票得到了迅速流通,底层人斤斤计较的生活面目可见一斑。又如《钢的琴》中陈桂林对淑娴说:“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啊,陈桂林,就是希望我能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结果没甲了,成夹生了。”在葬礼演奏《三套车》时,画外音(死者儿子)表示:“这曲子听着太痛苦了,老人听着这曲子步伐得多沉重啊?”淑娴抢话:“知道了,叫老人加快步伐吧。”陈桂林问:“走那么快去哪儿啊?”淑娴搪塞:“你管他去哪儿呢。”而就在喜庆的乐曲中,孝子们开始大放悲声,杂耍艺人开始表演吐火和脑袋开酒瓶,让观众哭笑不得。这些突兀的设定其实是既辛辣,又包含怜悯的。一言以蔽之,张猛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再现底层者的生活,这无疑是艺术对现实议题(阶级失落、人尊严的摇摇欲坠等)的一种有力回应。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人物,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求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可以说,张猛电影的底层叙事发轫于父辈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成长于对小品、纪录片等的尝试,最终成型于“东北三部曲”等作品。在对下岗工人、底层市民、残障人士、双性恋者、罪犯等人生存困境的展现中,张猛表达了他对这些弱势者的深切关注。并且,张猛通过隐喻、超现实画面和黑色幽默等,完成了对生活的提炼和变形,为观众营造了过目难忘的底层生存镜像。张猛电影鲜明的现实指向,以及饶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其实正是一种知识分子责任感和对艺术不懈追求的体现,这无疑是值得中国电影人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