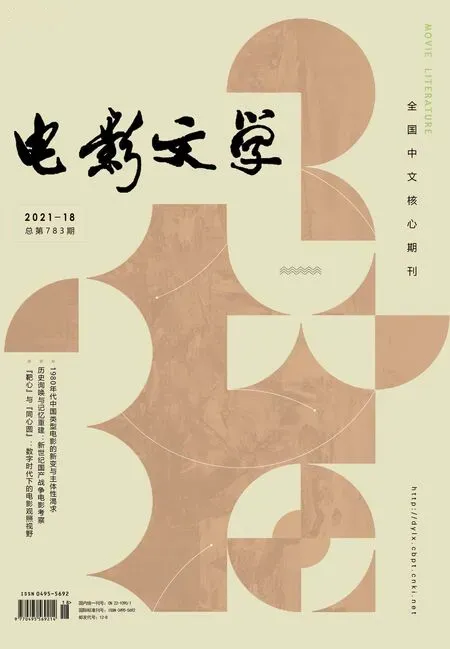论克拉考尔的电影救赎观
颜汇成 刘思雨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齐泽克·克拉考尔所著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复原》中的“复原”一词在英语释意中蕴含着救赎的含义。在论著的最后一章其就电影的救赎潜能做出阐释,其指出,电影的目标是解决现代性社会所带来的人的抽象化、孤独化与单向度思考倾向的问题,以此弥合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裂隙,获得自我救赎。针对克拉考尔在此提出的救赎观,诸多文章在论述时,从现代性困境出发,解析其救赎的原因与目的,并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入手,分析其选择电影媒介作为救赎中介的原因。但克拉考尔为何要在大众文化之中选择电影作为实现个体救赎的媒介,其理论中“复原”一词与救赎之间有何关联,通过物质现实的复原是否能达到其所期望的救赎目标等问题却并未得到思考应答。其次,电影理论史上针对克拉考尔电影写实主义理论,有诸多的认为其理论僵硬、机械化的批评,如尼克·布朗就曾指出“克拉考尔的这种写实理论是反戏剧、反象征、反实验、反文学、反绘画的”;宝琳·凯尔也“自鸣得意地将作者揶揄为德国迂腐学究,开启了对这本书长期而多样的批判性评价的历史”。但正如罗伯特·斯坦姆所言,不能因为巴赞的写实主义理论相较于克拉考尔更具有开阔包容性,就把克拉考尔仅仅视为一位“天真的写实主义者”来对待。事实上,在克拉考尔对电影写实主义理论及其救赎潜能的论述中,我们能发现,克拉考尔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中潜在性的哲学立场,即他将电影作为有机生命体加以思考的视角。本文即是以克拉考尔电影著作《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复原》为研究对象,结合米莲姆·汉森对克拉考尔学术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克拉考尔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出发,阐释其为何在大众文化中选择电影这一媒介作为救赎中介的原因,思考复原与救赎之间的关联意蕴,从电影本性认知层面对其电影理论进行再思考,并在对比克拉考尔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理论的区别中,进一步阐释其电影写实主义理论认知自我与世界的意义。
一、电影救赎的方式:物质现实的复原
克拉考尔的电影写实主义观念生发于他对摄影的思考与阐释之中,在《论摄影》《摄影小史》中,克拉考尔便指出,摄影媒介的出现不仅使被呈现物完整地被复制、呈现成为可能,并且可以使主体用以物为中心的观念认知世界,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复原》中,克拉考尔将对摄影的理论认知延伸到电影之中,强调电影的特性则在于摄影技术能完整复制外部物质世界,“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明显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从摄影媒介到电影媒介,对外部的复原呈现是其媒介的特性,外部物质是其表达的核心。然而,克拉考尔所注重的外部复原并不是对外部表征的再现,而是对外部物质中所蕴含的经验、映像的再现。“一个电影镜头,无论它在内容选择上何等精当,必须原封保留未经加工的物质现象的多种含义”,并且“它们的再现化范围是超过物理世界之外的,由于它们不停地引起心理—物理的对应,它们暗示出一个可以恰切地称之为‘生活’的现实”。质言之,重要的不是外部物质的再现,而是外部物质所传达出的经验真实。对克拉考尔而言,对外部物质经验再现的重视使消逝的、不被主流认可的意识形态再现成为可能,同时也弥合着受众与现实经验之间的裂隙。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克拉考尔十分推崇棍棒喜剧,在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理论中,棍棒喜剧以人与物的核心冲突使身体与物质之间建立联系,也进而使观众与物质建立感知。其次,其以偶然性决定人物的机遇、命运的剧情特征也使其具有打破资本主义一体化倾向的力量。
对电影媒介中摄影特性的强调与对外部物质经验再现的重视使克拉考尔将“未经搬演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无穷无尽,含义模糊的生活流”“揭示正常条件下看不见的东西”特性迎合为电影表现题材的座上宾,将“追赶”“舞蹈”“发生中的活动”视为电影表现最上乘的题材。因为对克拉考尔而言,电影重要的不是叙事性的情节建构,而是表现外部物质经验的空间建构,以此保证外部物质经验的纯净以及其与个体的直接性连接。对于克拉考尔而言,魏玛时期的大量影像作品已然表明:主流叙事电影在面对资本主义文化所产生的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遮蔽立场,并且其主要目标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因而重要的不是叙事情节,而是影像中的“洁净状态”,即以不包含任何主观印记的方式去展示外部世界,以此使我们“觉察到聚集在物质的微观结构中的巨大能量”。这也是为何,克拉考尔认为先锋派电影中反对叙事、注重以外部物质表达内在经验的特性是具有写实主义倾向的。
“洁净状态”空间的建构与外部物质经验的传达是影像需要完成的复原任务,而受众在其中则应站在旁观者视角的位置,感知影像对外部世界复原所带来的力量。对于克拉考尔而言,一方面,旁观者视角强调个体站在事物之外感知事物从而在世界之中确立自身位置的特性与其所认可的电影写实主义理论具有先天的亲缘性,因而其与巴赞在这一层面具有一致性。对于巴赞而言,“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激起我的眷恋”,对于克拉考尔而言,重要的也是“电影的目的是使激动的目击者一变而为清醒的旁观者”。但另一方面,其与巴赞有着深刻的对立:巴赞更加注重现象学的经验感知,使受众在旁观中纯粹地感知外部世界。而克拉考尔则注重影像除了要使受众旁观世界,还要使其“正视‘事物的盲目的进程’”,使“观众为拍出来的画面的现实性质所震动,便不由自主地对它们发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作为写实主义者的克拉考尔反而与形式主义者爱森斯坦立场一致,他们都非常重视观众主体性的生成。但二者又有所不同的是,爱森斯坦是选取诸如杂耍蒙太奇一类的具有高度刺激性的景观内部的冲突手法来使受众获得自主性,而克拉考尔则是选取使外部世界经验陌生化的方式。也因此克拉考尔十分强调偶然性、生活流以及街道电影中的漫游属性并将“戏剧性叙事和剧场化的场面调度为前提的电影驱逐到‘非电影’中”。
对“洁净状态”空间的建构、使外部物质世界经验陌生化以及观众主体性生成的强调构成了克拉考尔电影写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这些理论核心的主旨则指向克拉考尔想通过电影达到的在现代性困境之下救赎个体的目标。对于克拉考尔而言,电影复原的方式是通过建构“洁净状态”的电影空间,将其作为承载物质陌生化经验的容器,使受众在对其旁观的过程中感知到生活中真实的、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异质性经验,并由此生成主体性思维,打破现代性困境下单向度的思考模式,以此实现自我救赎。此种理论设想一方面认识到电影作为窗户/镜像/梦境对世界的再现意义与能给予受众的精神反思力量,但另一方面,并未认知到主体不仅是自我生成建构的,也是由“结构中的位置所建构的”。毕竟,“没有一个主体是在社会形态之外,或社会化过程之外”。主体在自我生成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与既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克拉考尔所认为的受众的旁观者视角即可使受众生成反思性,甚至反抗性经验的观点,则是忽视了实践的功用。其并未认识到只有使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真正参与、融合进社会实践之中才能生发出真正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异质性经验,才能达到他所期许的反思现代性、弥合个体与外部世界裂隙从而获得自我救赎的目标。毕竟,“任何经验都是人类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作用既影响了人,又改变了物”。因此,克拉考尔试图通过电影对外部世界的复原达到救赎目的的理论设想虽在逻辑上自洽,但在实践层面却具有乌托邦的意味。
二、“转向摄影是历史孤注一掷的赌博”:电影作为救赎中介的原因
通过对克拉考尔写实主义理论的梳理,可以看出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理论中复原与救赎的深刻关联性,即复原是通往救赎的媒介道路,而救赎是现实复原的理想目标。但克拉考尔选择电影作为实现其救赎目标的中介,还与其思考视觉经验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影像与记忆的关系以及影像内部因过去、现在、未来的并置而蕴含的对抗力量的问题有关。
对于克拉考尔而言,面对现代性症候,在宗教精神式微的年代想从内部精神角度寻求解决之法是徒劳的,因而其认为无论是舍勒的“自然神学”,马丁·布伯的“相遇哲学”对话原则,还是罗森茨威格与布伯对犹太教《圣经》的重译等理论工作,不仅无法解决当下社会的精神困境,反而可能引发新的价值混乱等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宗教与精神领域中的徘徊会让人们回避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任务……当他们想要去往现实之时,恰恰忽视了真实存在的外部世界。”克拉考尔所主张的价值重构并不在宗教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而是在大众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也因此他主张像拾荒者一样拾起日常生活中的碎片来分析、解决现代性问题。在对大众文化的观察之中,他拾起了电影这一媒介碎片。然而,问题的关键不是他选择电影这一媒介所获得的理论洞见,而是为何是电影,而非其他更为成熟的大众文化媒介成为他通往救赎道路的桥梁?
克拉考尔在1924年至1933年的魏玛写作时期,就已开始意识到现代性社会中视觉经验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他指出,福特生产管理技术将年轻的女性身体与性经验结构相勾连,并物化为一种视觉表征经验。此种视觉表征经验一方面加剧了工业化时代对身体、意识的规训,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此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性别秩序、技术伦理的焦虑。其次,是大众装饰所带来的连续的迷醉式图景,以及“踢乐女孩”将其身体化为几何式图形的表演,以此创造的对身体文化的观看仪式。这两种视觉感官经验都使受众流于碎片性思考,丧失主体性。因此,视觉经验已成为现代性工业社会规训个体,消除个体独立思考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对于克拉考尔而言,要解决现代性问题则要转向视觉经验,而在对视觉经验的观察中,其体察到摄影技术的重要性。
克拉考尔对于摄影媒介的关注思考,其核心在影像与记忆的关系之上。在“世界本身已经呈现为一张‘摄影的面孔’”的时代,摄影是留存历史记忆,保留当下的意识形态与未来意识形态潜在性缝隙并使人的意识获得与自然、历史对峙能力的重要媒介。“摄影虽然与自然的盲目复制有着共谋关系,但也‘挑起了各个场域的决定性对峙’,因为它的内在疏离效应破坏了主导性宣传的表面连贯性。”对于克拉考尔而言,个体在面对摄影留下的影像时,不同的认识经验可在此碰撞,从而使个体思维在此反省、再生,而电影继承并发展了摄影媒介的这一特性,完美契合了克拉考尔试图通过影像所达到的文化效果。
“历史经验为影像所获,而影像本身则充满了历史”,电影影像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复制使过去、现在、未来得以对话,克拉考尔在此基础上想要建立的是基于影像对外部物质世界复原而搭建的历史档案库,以保存个体记忆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经验。在影像所表现的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丧失与自然、社会纽带、宗教信仰的关联性,也因官方意识形态借由影像力量对外部世界做出的界限规定而日益遁入单向度思考之中。因而,克拉考尔认为,只有同样运用影像,并通过对现实世界碎片化景观的复原才能与之对抗。在对世界外部陌生化经验的感知之中对抗宏大叙事;在官方历史档案库之外保留一份私人感知经验;在不附带意识形态的纯粹物质经验之中对抗已然“成立”的书写。也是在此基础上,否定辩证的历史观才成为可能。所以转向摄影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孤注一掷的赌博”。
电影媒介契合着克拉考尔想通过影像达到的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建立异质性经验从而将个体从抽象化思考中解救出来的救赎目的。而在对电影救赎的设想中,一方面,克拉考尔希望银幕影像成为“美杜莎的脑袋”,即通过影像对外部世界的复原再现使人直面恐惧之物,由此使个体在面对陌生化、异质性的物质时产生主体性思维。另一方面,克拉考尔还希望借由影像的视觉特性构筑“人类大家庭”,使其在“反映和肯定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实际的和解精神的主题”之中勾连世界各国的情感,由此建造影像的“巴别塔”。在对救赎中介选择与电影作为其中介得以救赎的设想论述中,既体现出克拉考尔的人文主义视角,同时也潜在性地表明着克拉考尔并非只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进行认知的思想观念。
三、克拉考尔电影理论的本体论阐释:电影作为有机生命体
纵观电影理论史,在20世纪60年代宏大理论建立之前,电影理论的研究一直围绕着电影是不是一门艺术、电影艺术体现在何处以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关系进行讨论。自米特里所创建的电影符号学诞生之后,电影理论则进入与社会、政治、性别的广阔议题相联系的宏大理论时期。电影研究的主题也从“电影作为艺术”转变至“电影作为语言”“电影作为文化”。发展至德勒兹,电影则作为思维开始显现其意义。德勒兹将电影划分为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将电影视为“影像的物自体”,即电影可通过本身的存在生成思维与意义。运动—影像在个体面对世界冲击所产生的主体行动中凸显,而当个体在面对冲击无法做出有效回应时,行动危机也由此产生,只好借助于回忆机制介入以寻找解决之法,而当回忆中的潜在影像与实际影像不断交叠而产生回环时,时间—晶体由此应运而生。在此,潜在与实在、解构与建构同时存在,并不断地结晶、溶解,在这种流变不息中,处于永恒变动的“非有机生命”在此意义上生成,电影也在此挣脱运动—影像的精密控制,时间—影像便在此凸显。德勒兹打破了人与电影之间的主客体视角,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认知电影之于世界的意义与电影媒介自身的特性。在此,电影自身实现着通向康德所言的不可知的“物自体”通道的作用。而克拉考尔的电影救赎观在本体论的层面,同德勒兹一样,深刻体察到电影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的本质。
在克拉考尔的论述中,这种电影本体论主要显现于两个层面。首先,是克拉考尔在其理论中所强调的以物为中心的观点。克拉考尔认为,个体精神的救赎是通过对外部物质经验的重回而达成,此种以外部物质为中心再现世界从而连接主体的“复原”设想,与德勒兹电影理论中突破以人为中心视角来认知电影的理论观念相一致。其次,克拉考尔对“救赎”一词的理解与阐释,坐落于对人精神的回归之上。质言之,将人自身放置在世界之外从而直面世界的本真样貌;将自我与思维交付给电影这一精神自动装置,从而使个体的内在性解放出来,以此弥合主体—客体、心灵—身体的分裂。在此,克拉考尔将电影视为精神自动装置来代替宗教以来的至高主体——上帝,以此使个体逃出形而上学的孤独,弥合个体与外部自然的裂隙,使个体感知到人类无法认知的“物自体”,由此摒弃无法感知的、非连贯性的“虚空”并真正触碰到世界的本真经验。在此,克拉考尔已经潜在性地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在场于世界而又超越自然逻辑、语言、材料的媒介形式,电影可以通过自身的生命彰显外部世界。
将电影作为生命体自身显现世界的认知观点与近代哲学以来,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转向现象学让“世界自身显现”的经验感知的认知模式转向有所关联。而在电影本性的认知与将电影视为有机生命体的思维模式关联上,我们也更能理解克拉考尔所认知到的电影救赎力量,即电影可通过自身的生命再现外部物质的本真意义,因而作为主体的创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利用摄影机对世界进行复原再现。
四、电影写实主义理论的救赎力量
面对与传统社会大分裂的现代性社会,克拉考尔以强调主体量化、以商业性为首要诉求、受众单向度接受的大众文化为出发点,生发出写实主义理论,期望受众在对世界的旁观中,反向瞥向自身,以此生成积极性主体,对抗单向度思考模式。但从大众文化观入手,也造成了积极性主体的难以生成。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主体的量化与商业性的本源诉求,有悖于克拉考尔写实主义理论中反对单向度思考与机械化生活方式的观点;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强调个体单向度接受的特点也致使克拉考尔认同受众的旁观者视角,而忽略了实践的作用,因而无法使主体与社会实践结合,也因此无法产生克拉考尔所期待的积极的主体。与之相对的是生发于群众文化立场上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群众文化所强调的实践性、美育性、社会效益诉求,使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更为强调个体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者视角,并从典型化出发“生产偶像”,即在公共领域中创造具有导向力量,号召群众进入拼搏场域的个体,而不是从消费主义出发,创造注重于消费行为的生活方式的呈现,索取、占有文化资源的“消费偶像”。
也是在此基础上,克拉考尔所想达到的从现实出发,生成积极性主体的救赎诉求,无法在从大众文化出发的理论实践中落地生根。克拉考尔所倡导的积极性主体要在强调主体与艺术客体的交互性作用、艺术对主体的美育性作用、艺术对社会效益的重视作用的群众文化观中才能得以生成。而这也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强调要从群众文化出发,以使电影为人民大众服务,创造出“典型化”人物、“典型化”叙事从而召唤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因。
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与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理论因从不同的受众观出发,所以在电影的艺术观念、电影实践层面有不同的论断。但抛开观念的异质性,便会发现,两种写实主义都从其内部显示出了写实主义之于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力量。克拉考尔的写实主义理论更为注重电影与形而上的宗教之间的连接,认为电影作为充当上帝主体的精神自动装置,在面对主体时显现自身,以此进发救赎潜能。而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从形而下的社会层面出发,凸显电影连接主体与当下社会形势的意义,在对主体的询唤之中迸发力量。两种写实主义从不同的层面出发,使个体认识到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激励我们去反思我自己在空间—时间中的本体论处境”,并以此使个体在面对他者的世界之时产生自我意识,毕竟,“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质言之,自我意识在认识到他者之时才得以产生,个体只有在看见他者之时才能反向瞥向自身。也是在此意义上,两种写实主义理论虽然理论根基、理论诉求有所差异,但都有着期许这个世界更为美好的愿望,也都蕴含着使个体回归本源、回归理想世界的救赎力量,而这也是电影写实主义理论最本真、最本质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