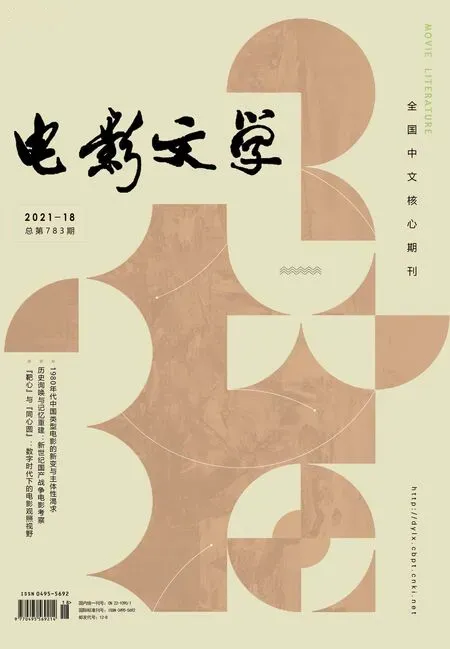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靶心”与“同心圆”:数字时代下的电影观照视野
吴晓钟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一、“靶心”:电影的本体价值
电影理论曾经历经典到现代、“本体”研究到“主体”研究的转向。实际上,经典电影理论与电影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数字时代的媒介环境对于电影本体的冲击,使其更具重返的价值。譬如,在《电影作为艺术》中,爱因汉姆不仅追问“电影是什么”,还提出“电影应当是什么”。爱因汉姆强调逾越事物外观的机械复制,巴赞则忠于机械复制本身。以下,不妨重温巴赞对某些电影技术的理论意见,从中推断他将如何看待数字时代下的电影。
摄影作为电影再现手法的“靶心”,最早受到正面的挑战。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强调影像的自然属性:“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然而它毕竟产生于被摄物的本体,影像就是这件被摄物。”于是,他认为影像是本体意义的规约,后长期被视为经典电影美学的奠基。数字时代的影像既可人为炮制而不依赖于被摄物,连摄影机都可以取消,令其美学与哲学的基础岌岌可危。巴赞认为电影是一种通过化学手段自动呈现出来的自然的艺术,随着赛璐珞胶片的消失,此条件已然不成立。由此而引发的论争,围绕着数字影像与指涉物是否存在物理联系而展开。数字影像以芯片捕捉,再数码转化为影像,因而认为数字影像不具“索引性”。“索引性”一词最早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提出:“索引符号”(即与指示物具有存在性关联的符号)。电影的魔力不再是摄影机记录下的不可复制的艺术灵韵,数字摄影将再现转化为呈现与创造,这种“数字本体论”是对“摄影影像本体论”的威胁。实际上,“摄影影像本体论”较“索引论”更为复杂。我们判别影像,不仅仅基于“索引性”,更在于主观上认同影像与被摄物足具相似性。“真实感知并不是真实的确证,它对现实生活的指涉,不取决于客观的检验,而取决于感知和内心经验的暗合。”摄影不为解释被摄物,而是被摄物的再创作,摄影本身是一种丰富的世界,本就不限于事实的附庸。数字技术并没有颠覆摄影最本质的艺术形式,数字影像的可塑性与传统摄影并不相左。数字摄影仍基于光学的几何原理,传统摄影的“真实感”“电影感”仍是数字摄影的美学目标与试金石。两者的区别在于技术,但在画面的呈现上彼此仍存在融合或共处的可能。由是,数字虚拟的影像也许在“索引性”上是虚构的,但在感知接受中无疑是真实的。影像与其指涉物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数字影像呈现仿真的拟像,但作用于真实。因此,数字摄影仍是摄影,摄影仍是电影的“靶心”。
电影院是另一个面临冲击的本体领域。影院空间是唯一在“物质”上尚未被彻底改变的“靶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重创、对人类身心的创伤以及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都对全球影院造成极大的冲击,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也许更是长期而持续性的。一方面,便捷的网络平台正“撕裂”银幕,让电影的传播实现多屏化与分众化的趋势,使影院电影的存在遭遇冲击,疫情更加剧了这一冲击的力度;另一方面,影院电影也不甘示弱,众多导演投身于新技术与大银幕的结合,试图重建影院电影的美学优势。一直以来,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均是围绕于、定位于影院空间而存在的,电影需要影院的“现象学”空间。从胶片到数码、2K到8K、24帧到120帧、2D到3D、单声道到杜比音效,都是影院电影迈向巴赞之“完整电影”的努力,强化着自身的影院属性。让-路易·博德里曾指斥影院为现代的柏拉图洞穴,人们被绑缚于意识形态的枷锁中凝神于阴影。实际上,观众是自愿付费进入的,他们主动且相信那个公共空间的允诺——一种仪式化的功能,公共空间内共享心理氛围的共情效应。影院空间不仅有宏大的影像,有环绕的声音质感,有黑漆漆的大厅,有彼此陌生又共存的公众的在场,更有不可忽视的“前体验”,即入影院前出行的经验。概言之,“看电影”是从生活的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可以说,基于完整的电影经验的角度而言,电影的“影院性”仍是电影独特的“靶心”。在确保疫情防控与人民安全的基础上,影院依然为观众所需要。
综上,借助于经典的本体理论,我们可以发掘,虽然数字技术取消了胶片、改变了摄影技术、冲击了电影放映,但摄影、影院作为电影之“靶心”的地位与价值并未改变。即便在后疫情时代,电影院仍是电影的“底线”。当然,电影之“靶心”的本体范畴并不限于这两点,还包括此本体基础上所诞生的电影艺术的经典作品、美学、历史与理论等,本文不做展开。
二、“同心圆”:突破边界的实验
数字时代下,电影的“同心圆”可谓层出不穷。笔者认为,电影之“同心圆”是由“靶心”向外延展的探索与实验,自身显示出的新特征亦不尽相同,试图以多样的方式开拓电影的可能,推进电影更周全的未来定义。后疫情时代的电影危机,影院、影视公司的破产危机,客观上敦促了革新的必要性。促使业界反思电影业态,开拓电影产业链延长的思路,拓展电影的发展空间,或许也是电影转型升级的时机。“同心圆”既涵盖着电影独特的性质,也涵盖着非传统电影特有的性质,亦即某种电影的未来样态——或将重构电影的生产、发行、消费等基本逻辑,酝酿着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变革。下文以四种“同心圆”为对象,对其显示出的新特性给予归纳与把握。
(一)屏幕:日常化的“同心圆”
数字技术重塑了电影文化的局面,电影之大众艺术王座的位置受到冲击,需要与计算机、视频、游戏、电视与虚拟现实等同场竞技。于是,一种有着日常化趋势的“同心圆”出现,迈出银幕的边界而走入大众的屏幕。数字时代的电影经由网络平台的传播,观众得以在屏幕上任意储存、操作、处置电影,导致制作者失却设想电影与观众联结的方式。以往影院电影在专业化的创作者与观众间有着明晰的界限,随着观看边界的延伸,观众化身为电影的使用者、消费者、用户,甚至文本生产者,在数字信息的高速公路上肆意驰骋。“从接受的观点来看,观众娱乐、思索、暂停与修改他们有关银幕影像与声音的假设”。这种观影模式民主化、日常化的解放,打破了影院观影的机制,人与电影的关系亦得以拉近。如学者陈晓云所言:“未来的‘电影’或者更为宽泛的‘影像’,会更大程度地跃出‘艺术’的范畴,而进入更带普遍性和日常性的传播和交往领域……”
一般而言,“网络电影”涵盖两种概念:一种是在影院播放也在网络播放的传统电影;另一种是专门为网络放映而制作的电影。后者最初的形态是微电影,是互联网视频产业与电影产业的结合物,受众的视听要求较低,理念的不同导致作品的不同。而关于前者的争论则沸沸扬扬,从国际电影节出台的各种针对网络电影的不同规定,其态度便可管窥:“就奥斯卡和戛纳的态度而言,其认为网络电影与院线电影还存在较大的差别,他们的行为是为了保护院线电影,而从威尼斯电影节的态度来看,其认为网络电影也是电影的一种形式,与院线电影同样属于电影的范畴,二者不应该被分别对待。”笔者所讨论的正是前者,着重强调的是屏幕播放的不同经验。从观影经验来看,屏幕观影处于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小尺寸的屏幕与普通的音效不利于沉浸效果,外界的干扰与打断是不可避免的,暂停、快退、快进等操控阻止了观影的连续性,意识始终是警觉而日常态的。这是将互联网媒介的特点引入电影媒介中,观众从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屏幕里选择一种来看电影、使用电影。因此,这种非线性、无拘束的电影“同心圆”,是一种电影为成为日常所需的努力,更在后疫情时代充分显示其价值,疫情期间其傲人的市场收益便可见一斑。随着“宅生存”成为广大观众的普遍日常,观众的消费习惯与审美观点产生新变,互联网与电影的关系将越发紧密。
(二)媒体:再媒介化的“同心圆”
从“媒介考古学”的观点来看,“每一次主要的转向和变革(‘电影之死’),其背后的深层动因皆在于媒介本身的形态和特征的转变”。数字时代的“电影之死”,不过是又一次技术变革的修辞,再次呈现逾越本体的趋势,以“同心圆”的方式自觉从熟悉的媒介领域向外游离,达到电影的再媒介化。桌面电影、监控电影、数据库电影、游戏电影、引擎电影、弹幕电影……这些新形态的电影来自于数字媒介的融合力量,媒介性的膨胀突破电影媒体的边界。数字媒介“再媒介化”的时候,更多地注入了自身的媒介逻辑,尤其对电影的观看有着强劲的改造力,进而导致文本的分化。在实验精神的引领下,媒介的形式升格为被叙之事本身。
“桌面电影”的出现,正是以电脑桌面为叙事内容的典型范例。桌面电影讲述人类的电脑操作行为,镜头由电脑桌面的录屏构成,以作为网络的生存模式与视听经验的模拟。媒介性的凸显改变了放映的平台,只有电脑桌面最适合桌面电影的播放。在熟悉的软件操作与信息弹窗中,叙事者以内聚集的方法化身桌面的“代理人”,观众不自觉地代入自己的电脑桌面,因为现实与虚拟至少在屏幕形象上已无差异。这种膨胀显示出镜语的美学颠覆,它取消了电影的摄影机运动、场面调度等传统语言。“监控电影”同样是突破媒介壁垒的影像实践。无孔不入的监控让现实世界成了无边无际的摄影棚,电子眼化身为电影眼,超媒介的环境促成世界的电影化。它不再生产影像,转而直接提取监控媒介的信息,监控影像的挪用被赋予新的可能与意义。关于媒介边界的探索,出现得更早且走得更远的当属“数据库电影”,“它指计算机可以为电影提供庞大的素材数据库,电影可以不必依赖摄影和现实,运用计算机的各类软件和数据库就能自动生成一部电影。这种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影的制作模式,它意味着电影与现实渐远,与数码渐近”。“软件”更成了“数据库电影”的灵魂归宿。在此一层面上,媒体已反身统御电影,进而成为一种“靶心”之外的“同心圆”。
(三)感知:信息化的“同心圆”
与数字更亲近的时代,现实与虚拟虚实难辨,新的影像美学给予反馈,一种逾越传统电影感知边界的“同心圆”应运而生。动画试图取代实景,120帧试图取代24帧,空间蒙太奇试图取代时间蒙太奇……“新的视听技术并非停留在机械层面的发明,而是在互联网环境重新挖掘影像的信息性,赋予电影新的功能——从原有视听的感官,扩大为新的感性扩展和视听习惯。”数字时代的影像是纯粹的代码,组成画格的是数字,电影成了数字编码的视频。随着影像空间的多维化,银幕、屏幕、VR等转化为信息流动的平台,观影的感知成为信息的处理,多层次的信息流要求观众调动自身去行动与体验。
帧速率,作为电影技术中未曾动摇的另一根基,如今也在进化。4K、3D、120P放映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实现了120帧下的细节如此精确的银幕时空。然而观影的反馈不甚理想,技术的实现已然超越常人的日常感知经验。清晰度、流畅度的提高,使优缺点的信息均被放大,日常感知所无法看到的细部带来了观影的不适。“VR电影”的出现是更具超前性的实验。景框,作为电影感知中对限制的提醒,是爱因汉姆所认为的“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基石。VR对限制提出挑战,致力于消除现实知觉与观影知觉的区别。从景框电影到全景电影,成为一种主动的感知与整全的观看。固然,VR有利于人们的身体与思维吸取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不同的认知模式,发掘未知的生存经验,预告生活所可能塑造出的样子,从而在信息化的认知时空中建立人与世界的全新关系。但是,若要真正实现VR与电影的结合,前提是必须塑造一种让大脑相信的感觉。“消弭虚拟和现实界限的终极裁判是人的大脑,也就是人的精神,它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体验……”一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开拓的具身思想:“身体本身在世界中,正如心脏在肌体中……我可以在思想中俯视寓所,想象寓所,或在纸上画出寓所的平面图,但假若不通过身体的体验,我就不可能理解物体的统一性。”此意义上说,如果“VR电影”能实现观众的身体、知觉与虚拟信息世界的统一,那么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是有可能消散的。观众可能成为电影的一部分,电影也可能成为个体的独一无二的电影。然而目前的技术水平是远不理想的,各种头戴目镜设备仍有生理性的干扰,距离过近的屏幕也容易引起不适,“VR电影”的感知方式仍须实验。总之,这些探索试图在信息化的认知时空中建立人与世界的全新关系,将逾越传统观影的感知边界,成为一种信息化的“同心圆”。
(四)叙事:互动化的“同心圆”
为了与观众加强交流互动,出现了叙事者自降身位的现象,显示出一种互动化的“同心圆”。既往,传统电影对互动性的介入始终抱持抵抗的态度,因互动的介入将干扰电影的内在连贯与目的性导向。在“网络电影”“弹幕电影”中已浮现互动的身影,诸如对手中的电影进行操控或弹幕等,但均不作为深层的互动,观众并不能操控电影的叙事走向。“VR电影”或将真正突破叙事的边界,让观众参与叙事并推动情节的发展。叙事的走向将成为导演、电影、观众三方合作的产物,形成互动化、游戏化、浸入式的叙事新特征。技术的实现提供叙事空前的泛空间化的前景,塑造出边框消弭的浸入式的时空。“所谓的‘浸入’,并不是浸入一个已经完成的结构,而是说结构根据浸入者而发生改变。”观众可以第一次浸入电影的时空,不仅要移动眼球、移动全身,还要以具身体验为目标,创造交互的叙事场景。从浸入、在场到具身,实现赛博电影世界的全方位包裹。于是,虚拟世界的互动性置于前景,故事的讲述则退居后景,叙事的边界趋于模糊。
由于后疫情时代常态化的隔离需求,安全的交流、互动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诉求。而游戏本身便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后疫情之下游戏产业的突飞猛进,足见这种诉求的迫切度。实际上,这种浸入式、互动化的“叙事模式”在“游戏电影”“网络作品”中已有运用。“游戏电影”作为全新的媒介体验,从在场至在线,是一种以跨媒介协同、粉丝文化为前提的新型媒介景观。奈飞出品的互动式“网络作品”,更呈现一种试图颠覆电影的文化立场。当然,在奈飞的《黑镜:潘达斯奈基》中出现的互动叙事并不纯粹,各种可能的叙事选择都是事先预设在内的叙事线索,实质依然是一种布设好一切的叙事艺术。目前的探索而言,互动和叙事依然存有美学的分野,互动和沉浸的天然矛盾也尚未自洽,在原创性、视听语言、美学追求与目标价值方面仍是模糊的。总之,叙事的互动化作品应视为一种新的“同心圆”来看待。
三、观照电影的视野拓展
如果说电影的“靶心”是影院、摄影等本体范畴内未被推翻的核心,那么电影的“同心圆”则是电影为突破边界所应运而生的各种实验。“同心圆”涉及的方面包括了屏幕、媒体、感知与叙事,这些技术的实现、形式的变化与美学的颠覆已跃出“靶心”的边界,成为融合新媒介特性的“同心圆”。进而,如果我们将“靶心”与“同心圆”这样一组概念及其关系纳入观照电影的视野中,将有益于我们开拓数字时代之下的电影视野,有益于把握“电影是什么”与“电影将是什么”的本体追问。下文将在电影与“后电影”、美学与媒介、“靶心”与“同心圆”的坐标之上展开思考。
首先,从电影与“后电影”的坐标观之。表面上,数字技术将电影研究推向“后电影”的时代,冲击了电影媒介的物理结构以及本体论的合法性。但“后电影”的有关理论却始终围绕着媒介的特殊性和本体论展开,包括各种电影影像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其实重新把电影的本体召唤回了学科的中心。可以预见的是,新、旧媒介间的互动只会更加复杂而深入。也许短期内,电影理论、电影研究将不追求一种普遍的逻辑,沿着“后电影”有关研究的路径,暂时转向多元化、碎片化的电影样态研究,同时出现更多元的跨学科的理论对话。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电影”研究始终与电影研究持存着连接的可能,而非绝对的断裂。因此,如果说电影仍然是电影研究的“靶心”,那么“后电影”研究亦可视为电影研究的“同心圆”。
其次,从美学与媒介的坐标观之。要定义一种媒介的艺术可能性,必将视美学为第一的原则来作为其本体论的基础。相对于“靶心”,“同心圆”发展的愈演愈烈,让媒介属性获得统摄性的地位,其审美属性自然不会波澜不惊。媒介技术本身并不美,作用于人以后才有了审美。大可不必局限于“唯媒介”的物质逻辑,而应基于如何创新地运用媒介,从效果的意愿上升至美学的目标。因此,需要以不同的媒介眼光来看待“同心圆”。作为数字时代的媒介景观,其边界往往是模糊而仍然可变的。技术作为心智的外化,终究为了人而服务。在专研媒介的基础上,需要把观点转换为适合于媒介的形式,把不必要的因素剔除,从而找到自身最恰当的美学。因而,“同心圆”从“靶心”向外,推进未来电影作为媒介的更周全的定义,必须适应它所区别于“靶心”的新角色。
最后,从“靶心”与“同心圆”的坐标中观照电影,需要持有开放的视野。让·爱泼斯坦曾提出“纯电影”的概念,一种不受其他艺术“污染”的电影。巴赞则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纯电影”,但存在“非纯电影”,即电影艺术的本体是不断对外界吸收的。因为电影艺术综合了多种艺术的特点,本就是一门具备“非纯”艺术特性的艺术。阿兰·巴迪欧也提出“绝对不纯”的概念,但不仅仅是巴赞意义上的综合,更针对时间、各种艺术、非艺术形式、道德等多方面的综合。概言之,电影无须摈弃一切不是纯粹电影的“同心圆”,无须放弃接近其他灵感的权利。“靶心”与“同心圆”虽有着一定的区别,前者是行业,后者是全新的、有待发展的媒介形态。但前者引导后者的发展,后者则推动前者的变革。后疫情时代的行业危机将加速这场变革,但后者不会取代前者,两者将共存而互补。因此,两者既应当以相对独立的节奏发展,又值得相互沟通与彼此激发,这将有益于形成良性的电影生态圈。亦如学者李道新所言:“只有放弃对电影本身的纯粹性或本质性的执念,努力跨越学科的界限,在各种知识话语及情思体验之间会合梳通,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与未来发生在科技、媒介和文化、电影等领域的巨大变化。”换言之,当下及未来的电影只有在话语的层面上放宽定义,才有可能再次激活自身的可能性,推进电影的疫后新发展。
结 语
“靶心”与“同心圆”的电影观照,不妨理解为针对电影终结论的一种回应。电影的尊严仍然在于它所引起的持续期待,在于观众与电影人着迷般地探寻着电影所未呈现完尽的一切。援引巴赞的存在主义式的回应:“电影的存在先于它的本质。”巴赞未曾停止追问,也未曾期望得到终极答案:“电影确实还没有发明出来呢!”与其说是教条,莫若说是态度,从“电影是什么”到“什么将是电影”,引导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开阔的电影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