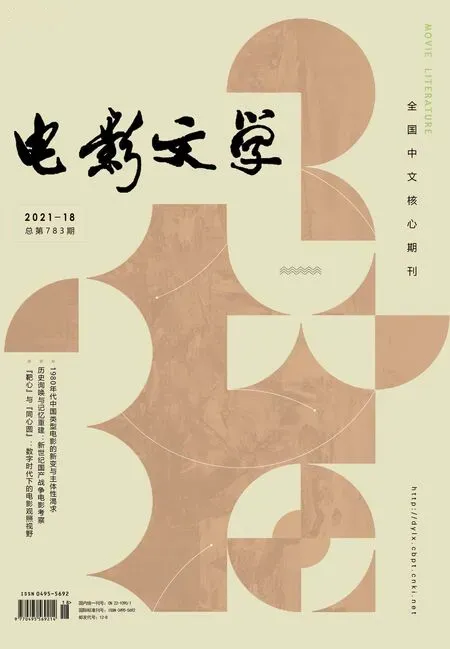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抗日神剧”从何而来?
——中国电影史角度的抗战电影源流与发展
王若璇 袁庆丰
(1.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2.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在过去的十年中,“抗日神剧”不仅是影视剧的热播题材之一,而且成为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专有名词。它通常“指代的是一类带有娱乐性和神化色彩的、表现抗日战争历史的电视剧,集中出现于2011年前后的荧屏并活跃至今,作为一个被归类的定义大约于2013年前后出现于互联网并很快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学界的批评,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从文化逻辑的角度而言,抗日题材影视剧的出现符合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的意愿、怀念民族英雄的情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从该题材衍生出的“抗日神剧”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与电影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渊源:从左翼电影到升级换代版的国防电影
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而言,2010年以来“抗日神剧”的出现不是偶然,它的发展脉络要从电影诞生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说起。中国电影诞生自1905年,而有关抗日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32年的左翼电影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有新旧之分,这是学术界的公论。“新电影”出现之前,所有的中国电影都属于“旧电影”,即为旧市民电影。而“新电影”除了左翼电影,还有新市民电影、国粹电影,以及左翼电影的升级换代版国防电影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抗战电影。其中,左翼电影的一个主题便是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这也是左翼电影较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中日两国从军事摩擦、军事对峙再到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左翼电影是最早反映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形态。
九一八事变之后左翼电影应运而生,但彼时民国政府不允许电影中公开出现涉及抗日的内容,因此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共识便是影片中所谓的“敌军”“敌人”等角色都是对日本侵略者的隐喻。例如,孙瑜在1932年编导的《野玫瑰》(无声片)中加入了号召爱国青年参加义勇军的片段,这便是对抗日救亡主题的隐晦表现。1933年的左翼电影《小玩意》(无声片)中,作为小商贩女主人公对民众发出呼吁和号召就是:“敌人打起来了,中国人要觉醒。敌人侵略过来了,我们要觉醒,我们要反抗。”这一情节也是为了启蒙观众的抗战意识。1933年的影片《恶邻》(无声片)以一个寓言故事隐喻了九一八事变,男主人公黄华仁的“东邻”黄猷一家凶横霸道,经常寻衅滋事,暗指中国的东北三省被“东邻”日本侵占。1934年的左翼电影《大路》(配音片),正面表现敌军和汉奸对国防公路的破坏以及中国民众的英勇牺牲。总体而言,在早期中国电影的话语体系中,抗日主题在左翼电影诞生的1932年就已经出现。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发动了吞并我国华北五省的进攻。1935年12月9日,首先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界人民中,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火焰,一致要求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初,中国电影界发起了国防电影运动,国防电影运动以鼓吹民族解放、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就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而言,国防电影有1936年的《狼山喋血记》《浪淘沙》《壮志凌云》;1937年的《春到人间》《青年进行曲》《联华交响曲》。国防电影贯穿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题,例如,影片《狼山喋血记》在国民政府的绥靖政策下以寓言的方式呼吁抗日,故事发生在被狼群侵扰的某个北方村落,因村民瞻前顾后以至于豺狼肆无忌惮,村民最终决定团结一致起来打狼,观众完全能够明了其中的内涵。《壮志凌云》的故事发生在东北地区,两个毗邻的村庄虽然过去有矛盾,但面对土匪敌人的攻击,两村最终联合起来抗击敌人,取得了胜利。《浪淘沙》中警探老章与嫌犯阿龙一同流落荒岛,两人明白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在岛上生存,本片以隐喻的形式阐明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青年进行曲》则讲述了华北奸商协助侵略者,爱国青年诛杀汉奸、破坏敌人军粮供应的故事,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抗日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中日军事摩擦的加剧,国防电影对抗日话题的涉及也越来越明显,《春到人间》中已经出现了中国正规军队的形象以及鲜明的旗帜、帽徽等政府军元素;由8个短片组成的《联华交响曲》,其中5个短片是抗日题材。
总之,1932年出现的左翼电影,其主题包含了两个指向——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压迫弱势群体;同时,左翼电影反映的阶级矛盾通常是通过弱势群体的暴力斗争得以解决的,具有启蒙性、革命性和宣传性。1936年兴起的国防电影运动是左翼电影的升级换代版,左翼电影的阶级性被弱化,民族矛盾得以提升和强化,民族解放战争思想得以发扬,其启蒙性、暴力性即反抗性和宣传性均被纳入国防电影体系当中。
二、雏形:抗战电影的基本面貌与特征转化
“抗日神剧”真正的雏形是抗战电影。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面反对日本侵略、呼吁民众抗日的抗战电影应运而生,并且不再受到民国政府的约束。从此,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一同进入地缘政治的格局,即国统区、沦陷区与上海“孤岛”。就现存影片来看,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即国统区的电影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由战前国防电影转化而来的抗战电影。
据统计,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到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香港一共出品了61部国防电影和抗战电影,“占同时期香港电影总产量的13%”。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有3部:即1938年启明影业公司出品的《游击进行曲》、1939年新世纪影片公司出品的《万众一心》以及1939年大地影业公司出品的《孤岛天堂》。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一共出品了19部电影,全部是表现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抗战电影。其中,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只有3部,均由位于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即1940年摄制的《塞上风云》《东亚之光》,1943年摄制的《日本间谍》。这些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证明,一方面,抗战电影继承了从左翼电影到国防电影转化而来的斗争模式与反侵略、反压迫的宣传性;另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全面转移为中日民族矛盾。就国统区的电影面貌而言,抗战电影是其唯一的表现形态。
不过,现今“抗日神剧”中单调猥琐、丑陋狰狞的汉奸与日本士兵形象并非来源于抗战电影,相反,《游击进行曲》与《万众一心》塑造出了有特色、立体化的汉奸与日本士兵角色。“抗日神剧”中愚蠢自大的“日本鬼子”被呈现出人性化的、有正义感的一面。譬如,《游击进行曲》中的日本共产党员被设定为反对战争、颇有正义感的士兵,并与作为男主人公的游击队员里应外合,最终与中国军民一同获得最后胜利;更有意思的是,汉奸居然是被日本士兵打死的。《万众一心》中的汉奸张沛,出场时是一位相貌堂堂的青年才俊,如此正面的外在形象使观众难以料到他居然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此外,1940年的《东亚之光》以被俘日军的觉醒和悔悟为题材,以日军战俘的视角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不仁之举,以宏观的战时视野展示了日军凶残及被欺骗的另一面。该片中“参加演出的是政治部所属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三十多个觉悟了的日军士兵,收容所给战俘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和政治思想教育,从而使他们逐步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
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正面战场,在敌后与沦陷区中暗杀敌伪组织也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电影中不乏对敌后斗争的展现,这无疑为抗日题材影视剧提供了正面战场以外的视角。有组织的暗杀、特务与谍报活动等具有传奇性的题材与元素被后来的“抗日神剧”全面吸收并赋予猎奇的色彩。譬如,作为香港出品的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对敌后的现实情形做出了即时反映,呈现了爱国青年有计划、有组织的暗杀行动。他们的活动得到了流亡的舞女、贫苦市民、卖报小孩的支持,反映了底层平民与爱国青年共同抗日的民族大义。《日本间谍》从外国间谍范斯伯的视角,呈现了日军在“满洲”沦陷区榨取人民钱财的罪恶勾当;同时,抗日义勇军则以正规军的形象出现,发挥了鼓舞人心的巨大宣传作用。反映蒙古族与汉族联合抗日的《塞上风云》,则较为完美地展示了地域性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抗日景象。
其次,从艺术表现模式上看,左翼电影、国防电影与抗战电影是一脉相承的,如二元对立的矛盾形式、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等,都是基本的元素配置。在内涵层面,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潜移默化的理念宣传以及抗日救国的主题也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抗日神剧”与它们之间的文化逻辑也表现在以上特征的继承和发扬之上。抗战全面爆发前,由于官方的限制,左翼电影与国防电影无法正面表现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真实情景。而抗战全面爆发后,8年间国统区出品的抗战电影一共只有19部。由此可见,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中,抗战电影的数量有限,而且对抗日战争的艺术表述大部分还是一种意向性的描述,总体上缺乏对中国军民在抗战期间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不畏牺牲的爱国情怀的全景式的、更为深入的传达与颂扬。
三、流变:1949年以来“抗日神剧”的形成脉络
如果说抗战电影是“抗日神剧”在题材选择与呈现角度等方面的雏形,那么“十七年”时期的抗日题材电影则为“抗日神剧”的出现和流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隐患。1949年之后中国的“十七年”电影和“文革”电影,尤其是“红色经典电影”,几乎全盘继承了从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再到抗战电影的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基因,并形成隔代遗传。其主要特征是反强权的革命立场、阶级对立的思维模式与暴力斗争的叙事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电影一方面坚持了中国优秀的民族文艺传统并从中汲取了营养,体现了时代感。但另一方面,它确实存在诸多问题。譬如仅就“十七年”电影而言,意识形态至上的原则致使电影的艺术生命力匮乏,人物形象单一化。呈现出更强的政治化特征,工农兵形象统摄银幕,表现工人、农民、解放军的英雄事迹的电影所占的比重相当之大。“十七年”电影强调对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度颂扬,由此造成了模式化与概念化的艺术形式,“假大空”与“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由此诞生。1962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地雷战》中,日军中队长中野、小队长龟田以及汉奸等反面角色在人物塑造上模式化,外貌狰狞、猥琐、无能。影片即将结束时,中野在民兵的攻势下,居然头晕眼花,将“镇妖石”看作一颗“巨大的地雷”,眼前浮现出“侵略者之墓”的场景,以至于他仓皇之下踩中地雷而身亡,这一桥段的设计客观上无疑是过分地矮化了日本军官。1965年,同样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地道战》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平原的军民以挖掘地道来打击日军的作战方式。在这一点上,《地道战》吸收了抗战电影对战争宏观维度的关注,呈现了另类战场的军民斗争情形。然而,影片却塑造出了从内在到外形均是愚蠢的、丑陋的单调反面角色,如汉奸司令汤丙会与日本陆军队长山田等。影片中,日军在进入地道后,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两名手持枪支的日本士兵在没有负伤的情况下居然轻而易举地向一位同样持枪的女村民投降,这似乎与常识相悖。由此,“十七年”电影中的战争题材影片基于二元对立的敌我冲突模式对反面角色进行了过分的丑化与矮化。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僵化的艺术模式发展到了极端,为日后抗日题材剧的弊病和“抗日神剧”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意识形态至上的“十七年”电影模式在中国大陆的影视剧中已经被边缘化,而娱乐化的影视思想与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借助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电视、流行歌曲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对大陆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哺。80年代的抗日题材电影中,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与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保留了严肃而悲壮的抗日主题。但到了新世纪,2000年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与2004年冯小宁执导的《举起手来》都将抗日题材进行了喜剧化与荒诞化的处理,对“日本鬼子”的丑化与戏谑成为两部电影的喜剧元素。由此,抗日题材影视剧的悲壮感被逐渐解构,喜剧化趋势也从此被打开。
我国的电视剧产业历经了1978年至1992年的转型期与1992年至2003年的形成期。在2003年至2012年间,电视剧实现了升级与高速发展,以资本和新媒体为代表的各种力量涌入电视剧行业,全方位推动了电视剧的产业升级。同时,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也伴随着“泛娱乐化”的现象,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提出的观点,电视的普及与产业的繁荣“使得一切事物诸如新闻、宗教、政治、教育都以娱乐的方式来展现;媒介的变化不仅改变了话语结构,更使得人们在电视的统治下成为娱乐的附庸”。在此背景下,抗日这一严肃题材也难以避免地被“泛娱乐化”裹挟。“抗日神剧”汲取了此前同题材电影中过度丑化的反面角色塑造模式,同时加入了对抗日英雄过分“神化”的元素,以促成所谓传奇式的情节,达到娱乐观众、博人眼球的效果。2005年上映的电视剧《铁道游击队》中便出现了抗日英雄可以“飞檐走壁”“骑自行车上火车”等荒诞的情节。此时,抗日题材电视剧被“神化”的现象已初见端倪。
“抗日神剧”的“井喷”现象出现在2011年前后,“据统计,2012年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200多部,其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70部;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在产量也节节高升的同时,“抗日神剧”的情节也越来越荒诞,“不少抗日剧的细节将残酷的战争进行了游戏化的处理,把严肃的抗战史变成了玩闹的把戏”。“手撕鬼子”的情节便出现在2010年出品的电视剧《抗日奇侠》中。2011年出品的《飞虎神鹰》中,侦察英雄燕双鹰不仅可以在任何地方神出鬼没,更能飞檐走壁,以一敌十,轻松消灭敌方多名狙击手。同年出品的《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孙成海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向空中投掷一枚手榴弹,却能将日军的一架飞机击落。2012年堪称“抗日神剧元年”,本年度播出的抗日剧中神化我军、丑化敌军的情节不胜枚举,例如《枪神传奇》中的男主角居然可以使手枪射出的子弹在空中转弯并击中敌人,以此来展示枪法之神;《敌后便衣队传奇》中的“爆破王”马洛这一角色不仅可以制造出“包子雷”,还有西红柿、黄瓜、胡萝卜、辣椒等“蔬菜雷”;《利箭行动》中的男主角李剑可以单枪匹马地打垮十几个佩有步枪的敌人,从枪林弹雨中毫发无损地穿梭,并通过冷兵器飞刀全歼敌人;《箭在弦上》将冷兵器与巾帼抗日元素相结合,剧中角色徐二航被日军围攻,因寡不敌众而惨遭日军侮辱,但她却如有神助般地拾起地上的弓箭逐一将佩枪的敌人消灭……诸如此类的情节不一而足。由此,早期抗战电影中所具备的历史真实性、现实性与反思性在现今的“抗日神剧”中消失殆尽。
结 语
总体而言,“十七年”时期的抗日题材电影延续了从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再到抗战电影中二元对立的敌我或阶级模式、革命宣传意识与暴力斗争元素,并在意识形态至上的环境中初步形成了“抗日神剧”中过分丑化日军形象的手法。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中国影视逐渐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中国电视剧在新世纪之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同时,抗日题材电视剧在汲取了《鬼子来了》《举起手来》等影片对抗日主题的喜剧化处理之后,在“泛娱乐化”的潮流下,衍生出了“抗日神剧”。从文化逻辑的角度而言,“抗日神剧”的泛滥有其存在的土壤与发展的依据,但是过度的传奇化情节与游戏化场面不仅使该题材丧失了艺术格调,更是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以娱乐的形式消解了抗日战争这段残酷历史的严肃性与悲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