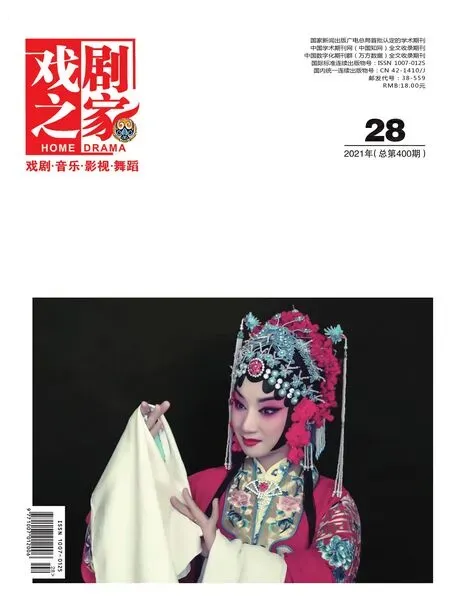《罗生门》中的他者叙事
李静宜,邓斯博
(江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56)
《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拍摄的一部影片。该片在1950 年8 月26 日上映,并荣获第12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以及第24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10 部影片”之一。导演黑泽明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喜欢在创作时从某一哲理观念出发进行构思,有时也会改编剧本,以达到自己的创作意图。
电影情节主要取自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电影以天灾不断、战乱连绵的平安朝代为背景,讲述了一起武士被杀的惨案。在电影中,三位当事人向审判长讲述了不同版本的案发经过。剧情内容简单,但复杂的叙事产生了许多谜团。不同的叙述者讲述相同的案发经过,但他们在讲述事实时都有所隐瞒。这种所谓的真相也隐射了世道人心的混乱,真实地阐释了人性的弱点。绝妙的叙事艺术,开放式的结局造就了电影《罗生门》的经典地位,也成就了导演黑泽明的美名。他凭借反传统的视听语言,反映传统文化的崩解带来的信任危机。他对人性及人类未来的思考,着实有股震慑人心的力量。
一、独特的叙述视角
电影《罗生门》不仅再现了原著的故事内容,而且还安排了第三者的叙事设计。情节模式对观众的理解起“延迟、阻隔、干扰和制造悬疑”等作用,使电影更具魅力。在小说里,存在着“当事人”多襄丸、武士和真砂的三角关系。电影里新出现的杂役,使旧有的三角关系被打破,“旁观者”樵夫、行脚僧、杂役建立了新的三角关系。两个层次的情节模式使电影叙事朝平衡化方向发展。
黑泽明为《罗生门》的故事设置了一条主线:行脚僧、樵夫、杂役三人在躲雨时谈到怪事,里面的四段故事都围绕武士死亡事件展开。樵夫自言自语地抱怨“不懂,简直不懂。”行脚僧和杂役追问,引出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故事。他说:“三天前,我上山砍柴,发现了一个树枝上挂着女人的斗笠,不远处还有武士的尸体,我就急急忙忙就近报了官。”然后,樵夫将自己听到的供词一一复述。接下来,电影场景切换到衙门口,多襄丸、真砂、武士、樵夫四个人证词不一,不知道谁在撒谎。行脚僧相信了樵夫讲的话,但前后的矛盾引来了杂役的怀疑。他只好说出自己的目击经过:多襄丸在凌辱真砂后,又请求她的原谅,并表示愿意改邪归正。真砂感到耻辱,就暗示两人决斗来决定她的命运。武士怕死不愿决斗,还羞辱真砂。多襄丸害怕有危险,也想放弃真砂。真砂见状,挑唆两人决斗。二人只好比武,但两人剑术一般,过了很久,多襄丸刚好刺死了武士。
故事的主线是顺叙,但行脚僧与樵夫对过去的回忆又是倒叙。导演通过这种打乱时间顺序,不断将描述中的过去渗入现在的手法,使影片脉络清晰。在破庙这个叙述空间下,两个层次的叙事,清晰地展现了电影内部的叙事结构。超叙述层次主要通过樵夫之口复述整个事件。樵夫是事件的旁观者,更是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话有穿针引线的作用。影片的两条时间线,也就是樵夫的回忆和四人的证词,相互作用,推动了影片的后续发展。影片结尾又返回到樵夫,将首尾呼应起来。三人的谈话内容看上去是关于真相的评论,但樵夫和行脚僧在复述故事时,也加入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正如佐藤忠男所说,“樵夫这段叙说,并非为了把真相搞得更加复杂,而是为了弹劾和揭发呈堂的三份当事人的供词里的谎言。”行脚僧、樵夫和杂役为这套话语提供了三个视角,他们构成了影片的主体部分,构成了故事的时间和空间,也揭示人物内心。除了直接的叙事之外,叙事中的评论也是其结构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引导观众,帮助其理解电影背后的隐含意义。樵夫、行脚僧和杂役三个叙述者是剧中的人物,也是三个符号,他们代表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这也暗含了作者对人类本性的反思,对人生和死亡的深刻思考。
二、对人性黑暗真相的震惊
通过樵夫对案件的叙述,影片转换到当事人论述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在这种叙述中仍然不断穿插出现。在影片中,黑泽明反复让樵夫的叙述中断,并加入三人对案件的讨论和对世道人心的感叹。在电影《罗生门》中,樵夫被设定成了核心人物,他作为第三方,目击了整个事件,同时也是凶案的重要参与者。四个主要叙事段落都采用他的视角,在他的复述中展开。赵毅衡曾说:“特定叙述角度把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他没有直接谋害人命,却与罪犯相差无几——他贪图小便宜,偷偷拔下了武士尸体上的精美匕首。在盗得匕首后,求生的本能和窘迫的生活处境使他在官府面前说了谎。他本性良善,却没有摆脱人性见利忘义的弱点。当他看见其他三人说谎时,还是天真地表示极大的不理解和愤慨。这既揭示了人性本身的复杂和鄙陋,又隐含了黑泽明对自身的怀疑,极具讽刺效果。在影片最后,樵夫最终说出真相并收养弃婴,承担了一个“希望”的未来。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和他一样,终将在矛盾与彷徨之后,去拯救那些可珍视的东西。黑泽明希望引导观众关注人性,关注如何摒弃人性中恶的一面,重建道德的信心和希望。
行脚僧是一个传统的人道主义者,他多愁善感且悲天悯人。除了哀叹“世道人心,简直就没法让人相信了”,却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举动。他希望人们善良、世界充满爱与美好,却听到了这样可怕的故事。他感觉这样的现实像地狱一样恐怖,几乎对人性失去了信心。在影片中,行脚僧哀叹了六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的开头,避雨的樵夫、行脚僧和杂役讨论这桩怪事,行脚僧感叹:“战争、地震、暴风、火灾、饥荒、瘟疫,年复一年,除了灾祸还是灾祸,强盗每晚都会来突袭我们,我已经看到过很多男人就像昆虫一般被杀掉;但即便这样,我也从未听说过如此可怕的事情。对,非常可怕,这一次,我可能会最终丧失对人类灵魂的信心。这比强盗、瘟疫、饥荒、火灾和战争都要糟糕。”他震惊于人们的自私与丑恶。最后一次是真相被揭穿时,三人都陷入沉默,是对现实的沉默,也是对人心的悲哀。此时,突然传来婴儿的哭声,婴儿预示着新的希望。杂役剥下婴儿的衣服,樵夫骂他是恶鬼。杂役不服气地提起樵夫偷拿武士短刀这件事,迫使樵夫承认自己也很贪婪。樵夫打算悔改,收养这个孩子,于是想从行脚僧手中接过婴儿。可行脚僧已经对人类失望至极,以为樵夫要剥掉婴儿的贴身衣服,所以严厉地斥责他。樵夫说,自己想收养这个孩子。行脚僧感到有些欣慰:“我很感激你,多亏了你,我想我可以继续保持对人类的信心了。”雨过天晴,阳光照在樵夫身上,樵夫抱着婴儿往夕阳深处走去。
最后出现的婴儿,给地狱般的罗生门增添了一丝生机,但杂役剥走婴儿的衣服又反映出人性的复杂与黑暗。最终,行脚僧相信了樵夫收养弃婴的善举,“并引导观众更多地关注人性,关注如何扬弃人性中恶的一面,走向光明的未来”。
三、重获对人性的希望和信心
影片以倒叙蒙太奇的手法,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探讨人性的善与恶,人是否可以相信,客观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樵夫和行脚僧都是第三方视角的见证人员,没有参与到案件本身。多人物叙事的非连续性,使故事在某些环节断裂,又在某些地方连接,真相更是扑朔迷离。在纷乱如麻的叙述中,主体间的关系捉摸不定,观众跟着陷入沉思。每结束一段叙事,樵夫、行脚僧、杂役都会分享自己的见解。他们讨论的内容远超过对凶手的猜测和对故事的评论。这种时间的延伸和构思的精巧,体现在“一个杀人故事怎样被讲述”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主题:如何看待杀人故事被讲述。影片通过死亡展现了黑泽明对人的理解:人如何在利益中反省自身,战胜非理性的欲望,完成自我救赎。在这个意义上,樵夫才是罗生门真正的主角。风雨是起点,回归人性是终点。
电影通过樵夫和行脚僧对多角色证词的转述,塑造人物多样化的性格,保证叙事结构的多元化,在激起观众强烈兴趣的同时,也保证了结局的未知性。《罗生门》结尾是开放式的。故事的内容简单,情节却很离奇;出场人物很少,内涵却很深刻。电影在虚无、怀疑和崩溃的背景下,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表现了反人性观和反社会观。但结尾的人性化转折也给予观众希望,赞扬道德将复兴,人道主义会一直存在。
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该电影保留了小说多角度的叙述技巧,替每个人的自我叙述找到框架……内容来自于《竹林中》,框架来自于《罗生门》”。“《罗生门》结合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情节,采用一种多重平行叙述的独特手法,讲述了竹林中的死亡事件,每个人物的独白都是整个事件的碎片,经过人的自私本性的折射,这些独白本身是不可靠的。同样的道理,转述这些独白的叙述者本身也是不可靠的。”
死亡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每个角色谈论的也都是死亡,甚至去世的武士也通过女巫来阐述自己被杀的经历。尽管如此,观众也不能判断谁是凶手,谁在骗人。电影最终也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死亡使人性的渺小与可悲暴露在夏日的阳光下,也赋予死亡本身更深刻的哲理内涵,这也是黑泽明的用意所在。影片的主题涉及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对于死亡的认识。这部影片在日本电影甚至是世界电影中,都是一部不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