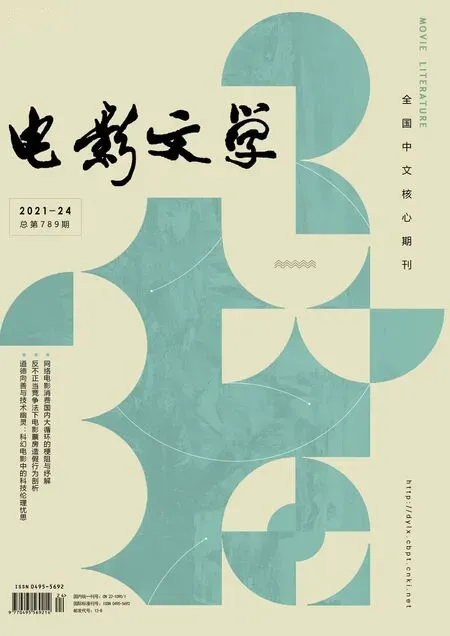从革命到后革命:新主流电影《1921》的情感结构
李冰雁
(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革命历史题材片一直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类型,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模式的成熟,融合政治性、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新主流大片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和票房,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起着积极作用。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片,《1921》(黄建新,2021)将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共一大进行合乎“美的规律”的影像表达,上映4天票房破3亿元,不少网友表示“被触动到了”。导演黄建新在访谈中提到,《1921》通过创造“感性的氛围”,激活观众的“潜意识”,是一种高于共鸣共情的审美体验。李道新在论文中指出,这种“潜意识对位”以及“激活潜意识”达到“通天下一气”的效果,“开启/延续了一种整体思维的中国电影新模式”。赵卫防认为,《1921》将“叙事的宏大性和日常性结合、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化描绘、国际化视野的拓展”以及“新颖的电影语言”等方面实现对以往建党题材影视剧的超越。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1921》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表达激活了观众的“集体无意识”,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其叙事模式及影像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后革命”时代,主流电影如何将过去历史精神和当下社会文化进行对话,活化抽象的理论,唤醒不同时代观影者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崇高感,以一种当代年轻人能够接受的“后电影”形式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不妨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唯物主义”中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即认为“情感结构”有助于将社会关系模式识别为历史表达模式,它旨在阐明人们在特定历史时刻对事件和情况的协调反应网络。对威廉斯来说,过去总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阅读现在,一种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的方式。简言之,“情感结构”有助于实现当下与过去的理解与对话,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以《1921》为例,考察新主流电影如何在“后革命”语境下塑造“革命式”情感结构,使历史、记忆与审美经验在银幕上合而为一,获得中青年观众的情感认同,从而使革命精神在当代得到传承和延续。
一、从物理时空到精神时空的跨界叙事
新主流电影集商业性、艺术性和历史性为一体,往往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增强戏剧性,提高影像的表现力。有鉴于此,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如何把握限度和意识就显得格外重要。毕竟,在短短两小时内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扫描容易流于碎片化叙事。例如,同样为献礼片的“建国三部曲”,即《建国大业》(韩三平,2009)、《建党伟业》(韩三平,2011)、《建军大业》(刘伟强,2017)对历史采用“全景式”扫描,由于人物过多、历史事件繁杂,导致叙事主线不够突出;枝蔓太多冲淡了主题。尤其是许多重要事件以旁白的形式介绍,没有最大化地实现影像叙事的功能。
跟以往的新主流电影相比,《1921》从叙事和影像方面都实现了一定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将电影还给电影”。影片充分利用“影像的力量”深刻展示了一批青年志士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探索,对革命道路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例如,影片开场透过狱中陈独秀眼睛的大特写插入一段蒙太奇组合段落,每个画面和细节都透着“想象的能指”:飞机盘旋下,一群人在故宫落荒而逃,鸦片战争爆发,直观地展现出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内忧外患的情景;接着展现李大钊与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再到他生命中各个瞬间的闪回片段,表明一代人寻求救国救亡道路的艰难历程。影片尾声,陈独秀再次入狱,此时的他在铁窗前怒吼,与片头构成叙事呼应。重大历史事件以蒙太奇形式切入,使时代成为“背景”,人物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命运遭际就具有主观能动性,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凸显。
《1921》另一个著名蒙太奇段落是青年毛泽东奔跑的场景。在毛泽东的视点中,法租界里的法国国庆庆典流光溢彩;此时从花园里的视角切入,俯视镜头下是一群被拒之于门外的中国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两个视点切换,两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使观众与毛泽东共感共情,一种屈辱和愤慨油然而生。随后,毛泽东冲出人群,以一种夸张的大步伐一路奔跑,背景以一种广角旋转镜头呈现出租界商业街灯火通明、高楼林立,暗示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对比,中国落后就要挨打。此时插入毛泽东的回忆段落,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在湖南乡下反抗父亲出走。父亲,象征封建家长制;出走,意味着与强权和旧势力的决裂。这场“奔跑”蒙太奇使影像具有丰富的情感指向,尽管有艺术化的虚构和渲染,但其传达的情感结构唤起当下观众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正如电影海报所言“一百年,正青春”,“奔跑”既服务了电影叙事主题,又有多重意义指向: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人肩负着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重任;另一方面,预示着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征程,奔向崭新的世界。
《1921》的叙事场景游走于不同时空,除了讲述北京、上海、广州等早期共产党成员组织(参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上海工人罢工运动外,还交织着两条副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摆脱欧洲反共势力和租界密探的监视;日本特务对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捕。副线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剧情,还与主线构成互文性叙事。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有了“人民”意识,罢工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诞生的过程,罢工运动从侧面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不仅行得通,而且必将取得胜利。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并没有美化革命,而是指出革命必定要经历艰苦卓绝、流血牺牲。例如,李大钊在北京被处以绞刑,镜头切换到罢工运动现场,黑白画面中成千上万的工人整齐肃穆,鸦雀无声,仿佛隔空为革命烈士默哀;接着画面出现色彩,一面面红色旗帜凸显出来,人声沸腾。这种虚构性的诗意表达预示着经过革命者的浴血奋战,民智得到开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电影中,地理空间成为指涉具体之物的空间,通过不同空间的排列组合产生新的所指。就叙事模式而言,《1921》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际的跨界叙事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精神时空”,即时代大形势下个体对人生道路的共同抉择。在共同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信念的引领下,碎片化的历史片段得到具有向心力的黏合,独立的物理时空组合成符合历史逻辑性的精神时空,从而实现叙事功能。精神时空一方面在叙事层面标记历史记忆,使抽象的文化变得具体可感;另一方面,通过同一个物理时空打通现当代精神时空,形成共同的情感结构,使当下观众对历史人物产生同情和理解。
从电影语言层面来看,由于场面调度和剪辑的选择,使具有历史指向性的物理空间从“过去”转化为“现在”,将不确定的、抽象的“历史”变得清晰、稳定,可观可感。地理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下和历史联结的纽带,从而唤醒人们潜意识深处的文化乡愁。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在新媒介时代,各种媒介以不同的形式重构民族意识,激起人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主流电影较好地发挥影像叙事的长处,能够以一种当代人接受的方式讲述历史,使当下与历史的情感结构相通,从而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二、革命、青春与电影类型的表达
新主流电影在讲述革命历史的过程中融入青春、爱情、悬疑等元素,沟通了从“革命”到“后革命”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在威廉斯看来,“情感结构”是历史上某个时期出现的特定思维方式,它出现在政策和法规的官方话语、对官方话语的大众反应及其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挪用之间的差距。也正如此,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通过或显或隐的细节就能管窥全豹,交织着多元的历史叙事。《1921》将恢宏的历史背景以蒙太奇形式穿插讲述,通过留白手法展现历史细节,还原人物相对真实的思想和性情,使当下观众易于理解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行为和选择。例如,影片通过简约的对白描摹了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等青年形象,以对话和蒙太奇画面呈现刘仁静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同时也刻画了他们年轻好玩的一面,对大上海充满好奇;而李公博、周佛海则偕女眷流连上海的繁华世界,两人都中途退出会议,为他们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伏笔。这些场景和细节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刻画出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并对他们此后革命道路的选择提供人性化阐释。这些历史叙事结合了正史和野史、真实和想象,将宏大的历史简约为生活细节,从而贴近观众的现实生活和真实性情。
在新主流电影中,革命的宏大叙事往往与个体的情感叙事有效缝合在一起,从而使革命情感结构与个体情感结构实现同一性。例如,《悬崖之上》(张艺谋,2021)中“乌特拉”行动以牺牲革命者的生命为代价而取得成功,最终烈士的遗孤被送回母亲身边,大雪消停,黎明的曙光到来。同样,在《1921》中,李达和王会悟、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几乎与建党事业同步:受进步思想影响的男女青年一边组建小家,一边宣传革命思想,筹备中共一大会议;随着一大顺利召开,他们的小家也迎来爱情的结晶,也预示着革命终将取得硕果。在影片尾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也令人动容,在杨开慧牺牲的那一刻,镜头插入两人雨中送别的场景,暗含着革命与爱情、信念与理想合而为一。
《1921》在对革命历史的讲述中,将家国情怀、革命理想与个体经验、人类的普遍情感联结在一起,使革命历史的情感结构与现代情感结构一致。威廉斯认为,“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尤其是对文化的描述,人们习惯于用过去的经验来表现。文化的形成关键是如何将经验直接或规范地转化,这涉及将过去不断运动的特质投射到当代活动中。在文化不断被评估、被建设的流动过程中,文化的生产过程不断在官方话语/明确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经验之间取得动态平衡。”简言之,文化是在历史沉淀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投射了当下的观念和文化。事实上,将革命置于现代性语境下,摒弃假大空的宏大叙事,沿用“主旋律+”的叙事模式是新主流电影的特色,从最早“主旋律+爱情”的《黄河绝恋》(冯小刚,1999)、《红色恋人》(叶大鹰,1999)、《云水谣》(尹力,2016)到“主旋律+悬疑”的《风声》(高群书,2009)、《悬崖之上》再到“主旋律+动作”的《湄公河行动》(林超贤,2016)、《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以及将革命变成全明星视觉盛宴的“建国三部曲”等。爱情、悬疑、动作等是各种类型电影的基本元素,新主流电影吸收各种电影类型的特点,在丰富电影叙事性的同时提高审美性,同时引进众多一线明星参与演出,实现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1921》也在电影类型方面进行创新性表达。影片突破以往主流大片人物脸谱化的弱点,以丰富饱满的细节、立体的人物形象还原历史现场,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加入冒险、动作、谍战、爱情等各种类型元素。例如,在租界中发生的那场追捕戏,巧妙地利用汽车和公交车作为道具,镜头快速切换,剪辑流畅,悬疑、动作、节奏和紧张气氛都得到恰当处理,呈现出电影商业性的一面。多元化的电影类型表达既是电影叙事的内在要求,也满足观众的观影期待,使观众与电影文本进行深入的参与和互动。毕竟,每一种类型电影都有相应的形式和契合的主题,每一种类型都释放出新的叙事能量,开拓新的可能性。作为商业性的电影,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片,融合其他类型的形式和风格,在符合历史逻辑的视野下讲述新的故事,带给观众新的体验,满足人们对电影的娱乐性需求。
情感结构是否能得到成功唤醒还与代际有一定关系。正如韦勒克、沃伦所说,“在某些历史时期,文学的变化无疑是受一批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所影响的,如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或浪漫主义运动等都是明显的例子。”简言之,青年一代对社会或文化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推动作用,他们对同为青年人的行为更感同身受。同样,我们可以看到,《1921》起用黄轩、刘昊然、倪妮、王仁君等50余位优秀青年演员,凸显“青春力量”,力求演员和历史人物的神似和形似,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同时也符合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的史实。青年演员的加盟再次呼应“一百年正青春”的主题,也容易引起青年观众的情感共鸣。新主流电影以多元的类型表达重述革命、历史和青春记忆,以现代性叙事使传统故事呈现出与当代人共通的情感结构。
三、后革命时代的情感认同
近年来,新主流影视剧一度火热“破圈”,接受者从中老年群体扩大到青年人,赢得票房口碑双丰收,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战狼2》《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2019)分别以56亿元、36亿元、31亿元占据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10位。在电视剧方面,继《大江大河2》(李雪,2020)、《山海情》(孔笙,2021)等主旋律电视剧获得高收视率后,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张永新,2021)还不停被年轻观众“催更”,并登上微博热搜,在豆瓣上超过36万人打出9.3高分(满分10分)。
在毛尖看来,主旋律影视剧“破圈”的文化逻辑在于“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从来没有形成对立或对抗关系,基本是平行而动,而当代的情况则更加特殊了。这些年以B站网友为代表的年轻人,反而是主旋律的护旗手”。那么,当代年轻人为何成为主旋律的“护旗手”?新主流影视剧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显影了当代中国怎样的情感和文化指向?王杰曾以《刺客聂隐娘》《战狼2》的社会反应为例,指出中国当代时尚的基本情感结构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的“双螺旋结构”,它在某种层面上是将“过去”理想化并且具有面向未来的情感和价值指向。“双螺旋”结构指出中国当代情感结构的复杂面向,既有赓续传统文化、延续革命精神的一面,也是审美现代性的表征。然而,将“过去”理想化并不能真正打动人心。正如20世纪50—70年代从“红色经典”到“革命样板戏”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的人生历程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时代和社会赋予他们神性的光环,与当下主流文化始终“隔”了一层。纵观近年来的新主流影视剧,可以发现在大写的历史下,小写的“人性”得到凸显,在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值得被铭记。例如,《集结号》(冯小刚,2007)、《八佰》(管虎,2020)等战争片,场面恢宏、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展现出历史人物由于种种“偶然”所带来令人唏嘘的下场。他们和任何时代的普通人一样,在历史的舞台上沉浮,渺小、脆弱甚至不由自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新主流影视剧展现了时代激流中人物的人生轨迹,投射出现代性伦理,包括国与家、集体与个人和历史的偶然等关系。在银幕上,一个世纪前和我们同样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动荡的年代同样遭遇对人生道路选择的彷徨、对理想和信念的苦苦探索、对前途的悲观和焦虑。他们也有青春叛逆期,也要应对伴侣的不理解,也有革命道路上遭受挫折的痛苦和牺牲。在《1921》里,青年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以对封建家长的反叛开始;王会悟埋怨李达干革命还要自己垫钱;陈独秀多次入狱,将《新青年》编辑部撤退到广州,还四处讨要教育经费。最终,李大钊上了绞刑台、杨开慧被枪决、何叔衡跳崖、邓恩铭遭受酷刑等。在《革命者》(徐展雄,2021)中,经过流血的惨痛教训,李大钊明白了光有主义和理想还不够,革命需要真枪实弹,否则只是读书人无谓的牺牲。革命不再是诗情画意,不再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是随时可能的流血和牺牲。更难得的是,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会有结果,是否值得,是否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希望,但他们仍然坚持下来。
更进一步看,受“996”“007”“内卷”“躺平”不断刺激的当代年轻人,他们被新主流影视剧所召唤的情感结构还在于对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单向街》英文版导言所提及:“本雅明作品经常出现的隐喻,如地图和图表,记忆和梦想,迷宫和拱廊,狭景和全景,都唤起一种独特的城市幻象,唤起一种独特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银幕上的“历史”被赋予现实与虚构的双重隐喻,讲述了一个乌托邦、一种乡愁,从而照见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换言之,新主流影视剧以一种当代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叙述过去的经验,其呈现的历史空间、精神空间乃至历史叙事中所出现的真实与表象、回忆与梦想与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结构相通。通过情感认同,唤醒一代人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对沉淀在旧时空的感情,以及植根于其中的对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激情与失败的可能。
不容忽视的是,情感结构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将当下与历史情感结构的融通,不仅需要对过去情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还需要审美主体的主动介入。新主流影视剧之所以能受到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很大程度上跟这些作品丰富的审美内涵有关。从叙事层面上看,独特的叙事视角、符合历史的叙事逻辑、饱满的历史细节、立体的人物形象都是亮点。从电影语言层面上看,由具有表演功力的演员担纲,加上精细的场面调度、多样化的镜头语言、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视觉元素,造就了年轻观众易于接受新主流影视剧类型模式。
综上所述,新主流影视剧在情感结构和类型表达等方面的创新和突破,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影像表现力。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媒介即讯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将历史和经验影像化,消除历史文本的“固化”,使历史记忆缝合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预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