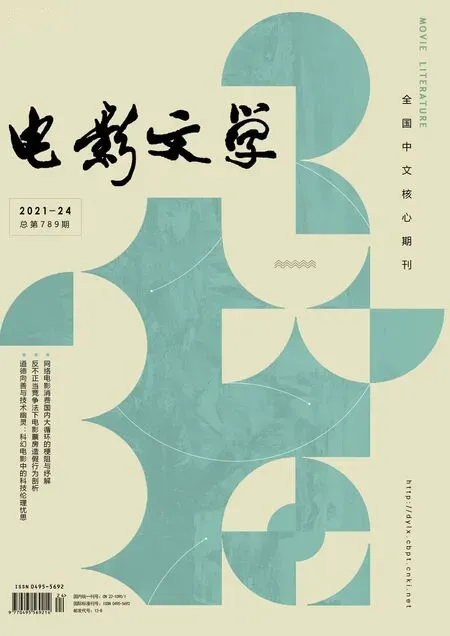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再媒介化叙事
林 茜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广汉 618307)
钱钟书在《七缀集》中谈论诗画关系时提到:“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正是因为诗、画这种跳出本位的企图才催生了新的艺术媒介:诗画作品。其实,不仅是诗歌、文字、图画,其他的艺术品也欲打破原有媒介的限制、束缚,彰显出其他媒介的特质。因而,艺术的“出位之思”其实是一个跨媒介问题。相反,诗画作品对诗歌“言志”、图画“表意”的挪用、融合则是再媒介化的过程。再媒介化(Remediation)是媒介传播领域的一个术语。丹麦的传播学家克劳斯·布鲁·延森(Klaus Bruhn Jensen)认为,再媒介化“通常指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美国大卫·博尔特(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新(Richard Grusin)在其合著的《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体》一书中也提出在融媒体的当今,“没有任何媒介可以独立运作并在分离和净化的空间建立自己的文化意义,因为它必须和其他媒介建立或尊重、或挑战的关系。”因此,再媒介化叙事成为数字化时代艺术再现的必然趋势。它要求新媒介创作者秉承尊重、竞争的态度从旧媒介中汲取部分形式、内容、理论特征、意识形态等进行再叙事,从而使新旧两种媒介相得益彰。
戏曲电影是对电影、戏曲进行再媒介化的“混合媒介”,它“处于戏曲与电影的双重艺术形态之间,属于‘复线性’的类型片,同时受到二者的影响。”其叙事自然继承了两种艺术媒介的特质。其实,电影和戏曲的媒介融合由来已久: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是一部戏曲电影,第一部彩色电影是梅艳芳主演的京剧电影《生死恨》。电影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纪实的艺术形式;而戏曲则恰巧相反,强调的是写意的虚。早期的戏曲电影偏重于记录功能,因此大多是戏曲纪录片类型。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更多的作品开始尝试通过再媒介化叙事来缓解两种艺术媒介的矛盾,从而扩大戏曲电影的影响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粤剧有着兼收并蓄的胸怀。近年来,广东粤剧院在戏曲振兴和曲艺传承的大背景下,诞生了不少创新进取的好作品。2021年5月上映的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就成为今年的“出圈”之作。其终极预告一经放出便冲上了热搜,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正片口碑也不负众望,打破了2000万元的票房大关。那么,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作为戏曲电影的分支,是如何进行再媒介化叙事的?又是怎样通过再媒介化叙事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技、戏曲之虚和电影之实进行美学融合的呢?
一、内容创作的再媒介化叙事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对民间传说《白蛇传》的再媒介化叙事是通过同名粤剧实现的。首先,粤剧通过再媒介化叙事,从民间传说《白蛇传》中获得了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和粤剧的抒情特质相结合,使用了以情叙事的折子戏形式。然后,粤剧电影《白蛇传·情》采取了电影媒介更为紧凑的叙事,并结合“微相表演”对粤剧进行了改编,塑造出有情之人。由于对旧媒介的充分尊重,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将民间传说、粤剧、电影三种媒介的不连续性减到最小,从而达到旧瓶装新酒的效果。
(一)以情叙事
“尊重和挑战原有媒介是再媒介化叙事的重要原则。”《白蛇传》是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主角白素贞敢爱敢恨、不畏强权,勇于追求真爱,深受大众喜爱。在清朝,随着报恩、盗仙草、断桥、状元救母等情节的加入,白蛇被塑造为既坚定又温柔的女性形象,代表“为追求自由幸福爱情生活,和封建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进步女性”。因此,不管是粤剧还是粤剧电影,这一人物形象都得以保存。但原有传说因其时代价值,凸显的是白素贞对强权的反抗,《白蛇传·情》则结合了粤剧的抒情功能,以一个“情”字的改编去着重塑造白素贞对爱的坚贞不渝。因此,在叙事上,《白蛇传·情》运用了折子戏的方法,把整幕剧分成序幕、钟情、惊情、求情、伤情、续情、尾声七部分。然而在粤剧电影的再媒介叙事中,则需要考虑电影媒介的基本艺术特征——节奏。节奏“指单位时间内矛盾冲突的密度所营造的或快或慢的叙事风格。它体现着导演的创作意图,影响着观众的情感与情绪。”不同于电影,粤剧是具备“‘四功五法’: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和手、眼、身、法、步的传统表演艺术”。为了符合电影叙事的特征,又尊重粤剧的程式化表演,《白蛇传·情》从两个多小时的舞台演出缩减为100分钟左右的银幕呈现。反观其创作过程,不难发现再媒介化叙事过程中,影片抛弃了一些不适宜的戏曲特色,比如繁复的唱词和缓慢的叙事,并凸显了电影中的人物冲突。首先,该片在叙事上删除了求情和续情两部分,改为序幕、钟情、惊情、伤情和尾声的五幕折子戏形式,因而叙事节奏更加明快;其次,影片将水漫金山作为冲突激化的高潮场景,借助数字技术集中展现了白素贞、小青与法海、十八罗汉的武斗,营造出叙事张力十足却不失粤剧韵味的叙事。
(二)以情塑人
“以情叙事”的同时还得“以情塑人”。许仙这一角色在众多版本中都是胆小懦弱的扁平人物。为了充分挖掘和阐释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再媒介化叙事后,许仙形象变得更为立体,且有情有义,他对白素贞的真情流露也颇为感人。在拼命冲出结界不得的情形下,他更发出“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妖亦人”的感叹。除去主角,《白蛇传·情》的配角再媒介化塑造也凸显了片名中的“情”字。在白素贞盗取灵芝一幕中,她虽不惜与守药仙童动武,但却仍在危急时刻救下跌落山崖的鹿仙。鹿仙知恩图报,在鹤仙即将斩杀白素贞时劝她逃走,然而白素贞不仅不逃,反而决定一家三口共赴黄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最终两名仙童将灵芝赠予白素贞。与此情节类似,关押许仙的小和尚也被许仙的真情打动而私放他与白素贞团聚。就连法海也未惩戒私放许仙的小僧,反而在他身上看到了仁爱之心。在以往版本的《白蛇传》中,这些角色均是缺乏情感的纸片工具人,粤剧的再媒介化叙事,使他们成为有血有肉的“有情人”。
“有情人”的塑造还依托于电影的“微相表演”。在戏曲表演中,由于舞台和观众的距离,演员除了会将动作和表情刻意夸张放大外,也会借助千变万化、图案各异的脸谱来便于观众区分角色。但电影拍摄不同,在特写镜头下,“微相表演”可以捕捉到任何细微的人物情绪,从而放大戏曲的脸谱艺术。“微相表演”指的是用长焦特写镜头对人物心灵的穿透和流露,这对演员的心理表演有很大考验。在电影《白蛇传·情》中,用“微相表演”捕捉粤剧演员的脸谱正是一种适宜的再媒介化叙事手法。影片中,白素贞的扮演者曾小敏对眼神传情的拿捏就非常精准,她的表演既保留了粤剧的脸谱特征,又体现了电影的真情实感。那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如焦急、担忧、愤怒、无奈、绝望、痛苦得到了自然连贯的转换和流露。尤其是她被十八罗汉丢出门外时定格的怒目镜头,写满了不甘与绝望,极大地渲染了打斗场景的悲壮。如同巴拉兹·贝拉所言,“我们能在电影孤立的特写里,通过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看到即使是目光最敏锐的谈话对方也难以洞察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微相表演”的电影叙事,配合韵美悠长、低回婉转的粤剧唱腔,在演员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尽显角色的喜怒哀乐,因而发挥出戏曲艺术的抒情功能,将千古流传的《白蛇传》讲出了当代新意。正如博尔特和格鲁新所言:“再媒介化不是一种谱系化的演进,因而能使两种媒介的不连续性最小化。”
二、艺术表现形式的再媒介化叙事
双重逻辑是再媒介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即时性(真实体验)和超媒介化。博尔特和格鲁新指出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承诺提供更为即时、真实的体验来改革之前的媒介,因此即时性使新媒介变得更为透明。但与此同时,这种承诺又不可避免地提醒人们旧媒介的存在,这便导致了超媒介性。它使人们意识到感官接触的一切皆为旧媒介的再现。艺术表现方面,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叙事符合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通过对电影、粤剧、舞蹈、武术、绘画等多媒介的融合,影片呈现出“融舞于武”“融技于艺”“融画于影”的感官盛宴。这种再媒介化叙事手法置观众于虚拟现实的即时性中,使粤剧电影这一新媒介变得透明,从而引发观众共情。与此同时,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叙事又随时彰显着原有媒介的存在,因而很好地传播了粤剧、绘画等媒介的艺术美。
(一)融舞于武
王国维曾给戏曲下过这样的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可见,歌舞不仅是戏曲内容,也是其叙事方式。王国维说的歌舞其实是戏曲程式化表演:唱、念、做、打的一部分。粤剧中的“打”即武打,它包括舞水袖、玩扇子、耍棍挥棒、舞刀弄枪等形式。电影《白蛇传·情》中白素贞同十八罗汉的精彩武斗是该片再媒介化叙事最为出彩的部分。白素贞的扮演者曾小敏是国家一级演员,她能文能武、身手不凡,对于水袖的使用更是得心应手。水袖是演员肢体与情感的延展,它“行云流水”般的美感不仅是技能的体现,更是中国古典舞气韵和神采的展现。片中,白素贞用水袖左右上下的舞动、旋转、抛洒,卷小佛灯为武器和十八罗汉相斗,腾挪跌宕,激荡人心。长达三米的水袖如蛇,更把她的怨恨、悲情,以及对许仙矢志不渝的真情全部释放出来。白素贞“以身带袖,袖身相合”的表演使这场水袖打戏不仅保留了粤剧的舞蹈美,更用演员的“打”使人物内心情感外显于行。
戏曲讲究表演的连贯性,而电影则是以镜头为单位进行叙事。《生死恨》导演费穆总结出“长镜头、慢动作”的戏曲电影叙事美学风格,认为这是“塑造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物关系,以及制造场景气氛的重要手段。”长镜头用于写实,而慢动作则用于写虚。这样一来,便能形成电影和戏曲虚实相生的艺术美。在这一段中,导演先是在一个较长的单位镜头下,完整地展现了白素贞用双剑和十八罗汉武斗的场景,用“真刀真枪”体现这种短兵相接的急迫感,然后用慢动作展现她抵挡十八罗汉棍棒的动作瞬间,凸显救夫的艰难。同理,大量的升格镜头则用来表现水袖击打在罗汉身上以柔克刚的力量感。与此同时,演员翻转跳跃的程式化动作又将场面舞蹈化、诗意化,因而更好地烘托了人物情绪。大量近景和特写镜头则采取蒙太奇的叙事手法从许仙和白素贞声泪俱下的面部表情来展现二人被强迫分离的悲怆感。白素贞屡战屡败,最终被十八罗汉阻挡于门外。此处慢镜头聚焦白素贞被击打出门外,水袖直抛,满眼凄凉不甘的刹那,再使用俯拍镜头,特写了她摔倒于地,瞬间三米水袖横甩摊地的静止画面。与此同时,背景音乐戛然而止,戏剧性留白叙事加入,拉近了观众与演员的距离,从而将白素贞救夫不得的决绝与视死如归的悲壮渲染至极致。由此可见,再媒介化叙事下的舞蹈化武打动作,能放大并延长演员程式化的“打”戏,让观众体验到逼真、震撼的临场感。这种临场感即真实的即时性。武舞交融的再媒介化叙事集舞蹈、武术、戏曲、电影媒介之优,既保留了武术和舞蹈的优美感、流畅感,凸显出粤剧演员的技艺和身段,又结合了电影语言的叙事技术,将技巧与艺术相融,从而使观众在即时性中达到了以情动人的共情效果,感人至深。
(二)融技于艺
巴赞曾断言:“摄影和电影将一劳永逸地满足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痴迷。”然而,他的结论是错的,这两种视觉技术并没有满足人类文化对即时性和真实性的渴望。现代影视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图形(CG)已成为这种愿望的最新表达。CG技术其实是人们对真实生活的再媒介化。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团队利用大量且高质量的CG特效对水漫金山进行了再媒介化叙事。粤剧中这一段高潮是演员的踢枪表演。但电影叙事不同,利用镜头剪辑和CG特效可以展示各种恢宏场面。该部分便是将事先拍好的演员程式化表演,如抛水袖、转圈、抛剑等动作和海浪的特效镜头进行合成,从而呈现出水袖抛洒激起海浪袭向法海的壮观场面,大大增加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
成功的再媒介化叙事须遵从双重逻辑。精湛的CG技术的确如实呈现出排山倒海的惊涛骇浪,满足观众对即时性和真实性的追求,但也同时消解了粤剧本身的写意美,那如何弥补?该片的再媒介化叙事借力CG,也回归CG,通过对画面的修饰以达到二者的平衡,保留粤剧电影的超媒介性。该片美术指导李金辉指出,水漫金山“借鉴北宋山水画的风格,调子不悲伤,但更为低沉”。画面中,白素珍施法的水袖、海浪为白色,湖水和金山寺的建筑则为黑灰色。白、灰、黑三色融在一起,如一幅跃然纸上的传统水墨画。法海在海浪中的还击也如同传统神话中的大鹏金翅鸟,使用禅杖则如蘸汁的毛笔于水中润开。降低光影反差,水墨风格的特效镜头把写意内敛的宋代画感展现出来,带给观众古风传统意境的体验,从而尽力保留了粤剧的写意美。最后,影片中宏大的交响乐背景和电影4K全景声的呈现方式在国画风中置观众于大浪逼近的危机感里,将现代科技融于东方艺术的意蕴中。由此看来,宋画媒介、CG特效和数字技术的加入不仅解决了现实摄影无法企及的困难,还进而展示出一种壮阔奇幻的叙事场景。
融技于艺的另一处例子是白素贞和许仙二人初见后不舍分离的场景。粤剧唱词委婉,歌词优美,“落花风中翩,舞尽相思意,烟雨帘前袅,牵就缠绵丝……”此时,随着歌声和人物心情,影片画面也开始自由变换,呈现出“绿湖粉花轻落,灵鸟彩蝶飞舞,小鱼碧波游弋”的唯美意境。所谓“心之所道,景之所到”。伴随人物的唱词,CG画面从花好月圆的荷塘月色切换到茂林深篁的竹林漫步,再到浩瀚宇宙的斗转星移,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时光流逝之感与粤剧唱词之美。与此同时,写意空间的自由组合还拓展了人物的心灵空间,并悄然加快了电影叙事节奏。从雕栏前素衣执手的浓情厮守过渡到洞房花烛的交杯酒,蒙太奇手段的使用讲述了白素贞和许仙从相识到相爱的整个过程。正如《白蛇传·情》导演张险峰所言:“要想平衡‘写意’与‘写实’的关系,必须把现实主义的手法和表现主义的手法相结合;必须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必须打破戏曲舞台的场景叙事,以使叙事空间更具张力与想象力。”再媒介化不是取缔旧媒介,而是在尊重的原则里进行挑战。在此过程中,新旧媒介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融技于艺,才能虚实相生。
(三)融画于影
再媒介化除了“对媒介的再媒介化”“临摹现实”两种方式以外,还包括“对旧媒介的革新”。戏曲中,演员走一圈“圆场”意味着叙事空间的改变;骑马、登船、下轿等无实物场景则通过虚拟的身段来展示;而唱腔与打戏则通过歌词及动作来直接或间接地叙述人物情感。这便是戏曲舞台的假定性,需要“景随人移,人随景动”。但在电影中,镜头叙事赋予了戏曲电影新的审美。例如,舞台剧“钟情”这一幕是通过演员的唱词配以身段的表演得以呈现的。改编为电影后,镜头如同摄像机能捕捉即时性的瞬间动作,再结合CG背景打造如诗的画面。例如:拉近的镜头通过一个面部特写捕捉到白素贞羞怯的嫣然以及许仙对她一见钟情的心动瞬间。镜头的拉远则展现伞下二人的四目凝望和推伞的细微动作,使得演员的优美身段在缥缈如画的西湖美景中如定格的瞬间照片,显得更加和谐婉转。下一刻,镜头又切换至断桥下嬉戏的双鱼与二人的倒影,由人及景,寓情于景,烘托出脉脉含情、缠绵旖旎的“钟情”画面。镜头剪辑叙事不仅在忽虚忽实、忽隐忽现中使二人初见钟情的心理活动外显于形,还将画内“情”和画外“景”交织在一起,达到融画于影、融情于景的作用。
戏曲作为我国艺术美学的代表,十分注重意境。正如《周易》中所言,“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意境是建立在意象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象。它与意象之不同,在于它‘空灵’。意象重在实,意境重在虚。”通过可感观的形象来阐述思想和情意,影片中的荷花意象便是一个好例子。从频频出现的满池盛荷再到尾声的寒塘残荷,荷花贯穿全片,对应着白素贞的情感变化。相遇之初,莲荷带珠笑,水波映轻舟,盛开的荷花象征着纯洁忠贞,映射着白素贞对人间真情的向往和“钟情”的喜悦。然而人间走一遭,她却经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胆追求真爱,却遇重重阻隔。景因情生,大雪纷飞的池塘最后只剩下衰败的荷根,烘托出白素贞“情之所至,一往情深”的悲怆。为创作意境,该片剧组还做出了大量的再媒介化叙事探索:全片从宋元山水画、江南水镇、明清园林等媒介中吸收灵感设计出了210张国画做场景图。考究日本瓷器的颜色绘制法海袈裟;模仿敦煌壁画塑造东方人飞天的感觉;使用汝窑中常用的“豆青”色铺陈故事开端……加以泼墨、晕染、实物、CG特效的再媒介化,最终,《白蛇传·情》才得以打破戏曲舞台和电影摄影棚的限制,使全片呈现出唯美的山水画即视感。影片的画面造型“不浓艳庞杂,构图、色彩、线条融入了宋代绘画风格简约、留白、含蓄之气韵,注入东方美学意境,配以优美音乐,与传统戏曲的精髓十分吻合。”例如“断桥残雪”这场戏便是借用留白手法来降低色彩饱和度,从而凸显出“伤情”的凄美氛围。可以说,《白蛇传·情》的再媒介化叙事已经完全跳脱出电影和戏曲这两个旧媒介,而是在更广阔的艺术媒介中找寻灵感,以期达到融画于影、情景交融的效果。
戏曲电影虽为电影,但一定是在充分保留戏曲艺术魅力之上进行再媒介化叙事,才能在追求创新和发展的同时,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所言:“对戏曲和电影而言,要博弈不要冲突,要从题材和内容出发,找到最合适的艺术呈现。”《白蛇传·情》在内容创作上,对民间传说《白蛇传》进行再媒介化叙事,注入粤剧媒介的抒情功能,以情叙事;并借助电影媒介的“微相表演”塑有情之人。艺术表现方面,影片符合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集电影多变的镜头语言和“立象尽意”的戏曲手法为一体,通过对电影、粤剧、舞蹈、武术、CG、绘画等多媒介的融合呈现出“融舞于武”“融技于艺”“融画于影”的感官盛宴。与此同时,新媒介的透明性也提醒了观众旧媒介的存在,从而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尤其是粤剧的艺术美。
戏曲电影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在创作过程中,不能仅把电影作为记录手段而忽视其艺术创造功能,新时代的戏曲发展也需要不断吐故纳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通过再媒介化叙事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技、戏曲之虚和电影之实相融,为观众呈现出余音绕梁、美轮美奂的观影体验,不仅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达空间,还为古老的粤剧注入了当代生机。作为新的“混合媒介”,虽然该片也面临诸多质疑,如戏曲表演程式的革新减色了粤剧原本的韵味等,但其再媒介化叙事手法却可圈可点,值得后续戏曲电影继续学习和探索。戏曲电影若能用好再媒介化叙事,将戏曲、电影、数字技术、文学作品、诗画等媒介进行有效融合,去芜存菁,发挥出艺术相融相通的感染力,定能讲好具有传统文化精髓和美学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