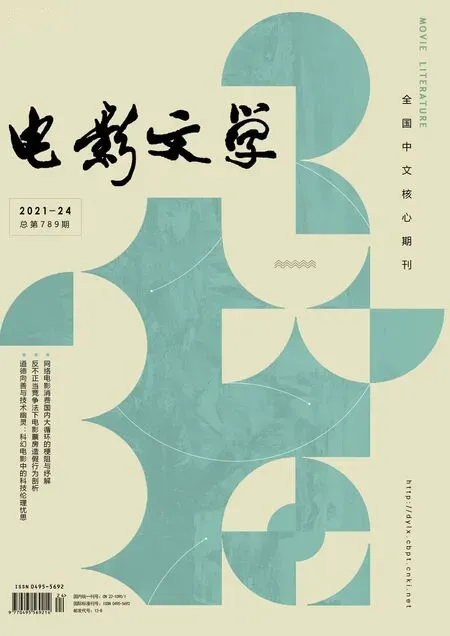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白蛇传·情》:粤剧审美的时代化
赵 茜
(1.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8;2.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北京 100007)
戏曲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媒介融合快速发展的语境下,如何更好地创新传播理念和策略,是一直为学界所热议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戏曲电影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将戏曲艺术与电影技术相结合,经过百余年的碰撞与交融,为戏曲艺术的跨媒介传播提供了探讨方向。由珠江电影集团与广东粤剧院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上映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电影将“戏”与“影”深度融合,既凸显了戏曲艺术的写意之美,又赋予其现代化的叙事方法,更加贴合当代艺术审美体验。
一、作为心灵碰撞的戏曲电影
《白蛇传》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以其为故事蓝本创作的戏曲作品不胜枚举,其中粤剧《白蛇传》就是经典剧目之一。经典粤剧《白蛇传》的故事情节相对传统,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为了更好地让戏曲艺术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进一步扩大受众群体,广东粤剧院对这一剧目进行了创新改编,精准提取“情”作为切入点,串联故事线索。新编剧目《白蛇传·情》设置了“钟情”“惊情”“求情”“伤情”“续情”及尾声“未了情”六部分,着重体现了故事的情感内核。电影便是基于这一版本的剧目内容进行影视化创作,在视听语言的呈现下人物情感表达更加细腻。
电影是视觉的艺术,也是感情的艺术。《白蛇传·情》很好地把“情”贯穿始终,完成了一次现实与传说、电影与戏曲的跨时空对话。白素贞修炼千年幻化人形,到人间寻找许仙再续兰因前缘,开场便让白素贞表达了自己对情感的期许,“人间好在有情有爱亦有家”“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寻寻觅觅中与许仙断桥相遇,以两人相互“钟情”为开始。两人成婚后,恩爱有加。白素贞最大的心愿“就是与许郎做长久夫妻”,并不顾自己的千年修行为许仙孕有一子。法海坚守职责本分,前来告诫白素贞:“妖与人不同界,不许胡来。你迷爱痴弃仙道,严惩无例外。你若再流连忘返,必降祸灾”。时逢人间端阳佳节,白素贞明知雄黄酒会让自己显现蛇形,仍甘愿为情郎三饮雄黄,不料许仙“惊情”而亡。为救活许仙,白素贞只身前往昆仑“求情”,取灵芝仙草以救许仙之命。白素贞与看守灵芝仙草的仙童一番争抢,仙童也被白素贞的一片痴情所感动,“都说人间有情痴,谁料你这蛇儿比人更痴”,说罢便将灵芝仙草赐予她。白素贞求回的灵芝仙草虽救了许仙的命,却未能唤回他吓破的胆,许仙找法海指点迷津,听信了法海的话忘情皈佛,随同法海进了金山寺,这一举动着实让白素贞“伤情”。在她看来,许仙应与自己一样坚定与痴情。白素贞寻夫一路追到金山寺,不惜与十八罗汉对抗、水漫金山也要救出许仙。许仙看着白素贞为救自己拼尽全力,幡然醒悟,一语道出电影的核心观点,“人若无情不如妖,只要有情妖亦人”,许仙用真情感化看守他的小师父,逃出金山寺。白素贞功力不敌法海,可身伤也掩不住心伤。逃出金山寺的许仙与白素贞再相见,苦苦哀求白素贞原谅自己,并将真情娓娓道来,白素贞决定与许仙“续情”相守。白素贞触犯天条,却因痴情保住性命,被佛祖收入雷峰塔再修千年,许仙践行自己的诺言,在雷峰塔外与她相伴,继续这“未了情”。
可以说,电影不仅讲述了“情”的故事,也很好地塑造了“有情人”。白素贞虽为蛇妖,却自始至终为真情付出;法海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人物,也仅仅是站在身份职责的角度劝阻白素贞和许仙相爱,使其形象相较之前更加柔和,体现了仁者之心;许仙最终认清真情,甘愿守在雷峰塔边,陪伴心爱之人的举动,为这一段存有遗憾的“情”留下些许欣慰。通过转变故事主题基点和人物形象刻画重点,削弱了传统剧目中包含的阶级性和斗争性,用更多笔墨生动描绘人世间的真挚情感,以及排除万难追求爱情的果敢和坚毅,更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电影所表达的情爱之忠贞、美好,能够满足当下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爱情的想象。“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通过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1]85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电影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影像方式记录、叙述、表达日常生活和情感。同时,电影也是当下最普遍、最流行且最容易接受的艺术样式,能够跨国别、跨地域、跨年龄层,实现多维度传播。电影在创作传播的过程中,其所包含的历史、社会、生活、人物和情感等,为创作者与接受者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也为不同国家地区了解中国文化建构了想象空间。就艺术的社会属性而言,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交流活动。“艺术作品是最为恰当与有力的帮助个人分享生活的艺术的手段”,“正是通过交流,艺术变成了无可比拟的指导工具”,创作者通过艺术作品将个人或大众生活经验转化为审美感受,而接受者又将人生体验、个人情感与所感知到的信息融合一体,引发情感共鸣,从而形成了共同参与的传播效果。这种“温润心灵、启迪心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才能够建立在情感共鸣和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进行艺术传播,打破时间、地域界限,更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白蛇传·情》在精准把握情感尺度的基础上,使创作者与接受者完成了一次心灵碰撞。同时,在对传统剧目传播进行解构和重塑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潜力。
二、跨媒介审美的时代
19世纪末电影的诞生,使戏曲艺术有了一个亦敌亦友的“同行伙伴”。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完成以来,就奠定了电影与戏曲的关系,学术界、艺术界关于“将影就戏”与“将戏就影”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前者主张电影要适应戏曲艺术本体,在符合戏曲表演的逻辑下进行叙事;而后者则强调戏曲电影要打破舞台表演的框架,将叙事逻辑、情节表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传统美学得到现代性的延展。
早期的戏曲电影,仅仅是对戏曲艺术的一种跨媒介记录。当时的戏曲电影,只是单纯地对舞台现场进行影像再现,而无法实现思想提升和视觉突破。随着现代电影技术的发展,分镜头的设计、叙事节点的剪辑、动态细节的捕捉等运用到戏曲电影的摄制之中,使其从“看上去很真”变为了“看上去很美”。戏曲艺术浓墨重彩的舞台特点,正通过影像充分地表达出来。
“白蛇传”的故事最早定型于明代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第28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经过评话、说书的演绎,到嘉庆十四(1809)年,出现了苏州弹词《义妖传》。从那时起,白蛇就已不再是蛇妖,而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对爱情忠贞、令人同情的女性代表,而金山寺住持法海也逐渐成为可憎的反面形象,使得宿世冤孽、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观念变得淡薄无力。“白蛇传”的故事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部儒释道合一的具有教化色彩的作品。
千百年来,“白蛇传”的故事不断被改编为话本、戏曲、小说、歌剧、舞剧、电视剧、电影,足见神话故事想象空间的巨大。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壮丽奇幻场景、鲜明人物形象的设计,往往以高度的想象力为基础,体现着人、兽、神的复合性,技能和法术都超出了自然规律。戏曲舞台并不能完美地将其展现出来,而电影总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通过观看和参与来体现其优越性。从这方面来说,电影显现出其与人性、生命、情感、理想以及想象力的共谋,其高度的假定性对于表现虚拟世界和人物具有天然的优势,并且为现代观众所喜爱。
对戏曲电影来说,如果不能从视觉上吸引观众,那么它极可能是失败的,更谈不上生命力。因此,从舞台剧到电影的变化不仅是制作上的更新,更是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对电影视觉愉悦性的特殊要求。视觉画面呈现所带来的愉悦效果是先于故事表达和情感再现的,也可以理解为电影镜头具备的视觉冲击力,是其独特的美学表征。从舞台呈现到电影银幕的粤剧《白蛇传·情》,为观众摄制了一幅幅绝美的水墨画,山水桥屋、茂林修竹,这些优美的图像,不仅营造了视觉美感,更烘托出白素贞与许仙相遇、相识、相爱的美好场景。
当然,电影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视觉优势,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描述的一样,电影是一往无前的,它不允许停顿歇息,所以给观众带来了一种“震惊式”的体验。戏曲电影《白蛇传·情》也有着明显的景观化倾向,如白素贞和小青在人形与蛇妖之间的变身表现得更加游刃有余;白素贞去昆仑求取灵芝仙草,可以看到雪山图景,白素贞、鹤鹿仙童腾云驾雾;救许仙出金山寺一幕,白素贞与十八罗汉打斗的场景,融合了戏曲程式化武打动作、水袖舞和电影特效,白素贞和小青联手水漫金山寺的场面,在与法海斗法的几个回合中营造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有趣的是,戏曲电影《白蛇传·情》一方面做足了“电影感”;一方面又没有放弃戏曲艺术原本就有的“写意感”,从场景设计、拍摄技巧,到画面构图、后期制作,处处可见跨媒介审美的重要体现。整部影片以中国水墨画式的风格为基调,每一处都宛如宋代绘画的水墨丹青,崔巍嵯峨的云峰、波光潋滟的湖海和花团锦簇的林间小路,还有满目琳琅的灯笼、复古典雅的油纸伞和轻巧灵活的竹筏,让人身临其境。同时,影片对断桥相遇、昆仑山打斗、水漫金山寺等场景的设计,都利用了淡墨晕染、动静结合的表现方式,给观众营造了一种强烈的现场参与感。
众所周知,“黑屋观影效应”将观众注意力强行集中在电影银幕上,电影中的音乐有助于构建情节的叙事空间和情感空间。不同的音调、节奏和旋律代表了不同的故事情节变化和情感表达。电影音乐通过快节奏和强烈的情感营造出一种“黑屋观影效果”,而观众正感受着电影所带来的视听乐趣。这种强烈的视听效果和体验,正是电影的媒介的重要特征。
戏曲电影《白蛇传·情》在音效设计上,也体现了现代性的审美追求。相比舞台现场只有锣鼓等器乐的单调伴奏,影片的音乐风格极具特色,先进的多媒体制作将二胡、月琴等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洋乐器融合在一起,将清新雅致的古典音乐、厚重的西洋音乐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在保留传统粤剧唱腔的基础上,影片还增加了粤剧小调、流行乐曲改编,如片尾“圆我的愿,心事千年,只等你遇见。……为了他,求仙草;为了他,漫金山;为了他,舍生死;为了他,我愿塔里再困千年。”词曲优美通俗、概括出整个故事,表达了以“情”为重的心声。
三、戏曲电影的突围
21世纪以来,尽管戏曲电影努力在互联网、新媒体上下功夫,但还是收效甚微。近年来,国家对戏曲艺术、戏曲电影非常重视,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对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纵观这几年的戏曲电影,票房超过百万元的屈指可数,究其原因还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戏曲艺术的程式,缺乏电影的视觉冲击感。
随着电影和戏曲这两种艺术形式在传播关系上的强弱进行了对调,电影由被同化的一方变为了主体,戏曲也开始作为一种元素被置入电影之中。此番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成功“出圈”,让我们看到戏曲人和电影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高小健曾在《中国戏曲电影史》中给戏曲电影做出定义,“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特有的类型之一,专以中国戏曲表演为对象,倾力展示中国独特的戏曲艺术魅力、记录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大师的艺术成就和优秀的中国戏曲剧目、弘扬中国悠久的民族戏剧传统”。随着时代发展,学界对于戏曲电影的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进行深入探索与阐释。戏曲电影不仅是跨媒介记录,而且戏曲艺术的传统性与电影艺术的现代性融合度越来越高,既能够保留戏曲艺术的写意手法,坚守民族艺术的精华,又能够运用电影艺术的写实再现,用镜头讲故事。
笔者以为,戏曲电影这一类型片不再是因为谁迁就谁而存在,而是更好地展现二者独特的艺术之美,有效解决戏曲艺术程式性、虚拟性与电影艺术技术性、写实性相结合的问题。因此,戏曲电影要在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平衡点探索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根植优秀戏曲作品的电影化表达
戏曲电影首先是对优秀戏曲作品的选择和再度创作。戏曲艺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追求,熔铸着人们对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蕴含着民族和时代精神。戏曲电影在选取改编作品时,应当注重思想内涵表达和美学价值体现,使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让戏曲电影真正转化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2009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境)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力。此前,粤剧代表剧目《传奇状元伦文叙》《柳毅奇缘》等均创作拍摄了电影版本,获得广泛好评,也为《白蛇传·情》的创作拍摄积累了经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戏曲电影是艺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有力抓手。一方面,用电影表现戏曲故事,使得电影这一“舶来品”与最具民族特点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处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的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就需要善用适合现代生活的传播手段和方式,“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二)创新戏曲电影的表现手法
戏曲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在题材选择、唱腔设计、镜头语言等方面探索适合现代审美的创作风格和表演手法。20世纪50年代,邵氏黄梅调电影不仅在香港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也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不可忽略的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在黄梅戏的基础上,对唱腔和曲调进行了“在地性”调整。当下,戏曲电影创作亦是如此。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将戏曲艺术独具特色的“打戏”融入武术和舞蹈动作,但又不失戏曲艺术程式化的美感,相应地增强了视觉感受力。同时,电影技术手段的运用为戏曲这一舞台艺术提供了大屏幕的无限可能。正是这种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观赏性的影片,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据统计,戏曲电影《白蛇传·情》近六成的观众年龄在30岁以下,足以证明创新的重要性。
(三)拓展市场化发展空间
戏曲电影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产物,应在坚持艺术本体的基础上顺应市场发展,达到艺术性与市场性相统一的目的。根据猫眼票房统计,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票房为2136.8万元,一跃成为戏曲电影票房之最。一方面,电影在创作和宣传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市场化探索和努力;另一方面,电影能够在主题内容、视觉呈现上抓住观众,用专业的、高质量的作品扩大欣赏群体。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生存与发展态势。戏曲电影的传播途径不仅是院线播放,也应进一步用好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采用适合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推动中国故事、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在电影工业体系逐渐形成的今天,戏曲电影的创作传播始终面临着巨大挑战,并不断督促其作为文化消费品进行改革创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成功为戏曲艺术与电影技术的融合提供了一种成功范式,并为传统艺术的延续性发展做出了尝试性突围。但我们不应过分乐观,应该认识到在未来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中,中国戏曲电影还需要继续探索其叙事风格和表现方式,创作出更多展示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情感的作品,自觉承担起对外传播的使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