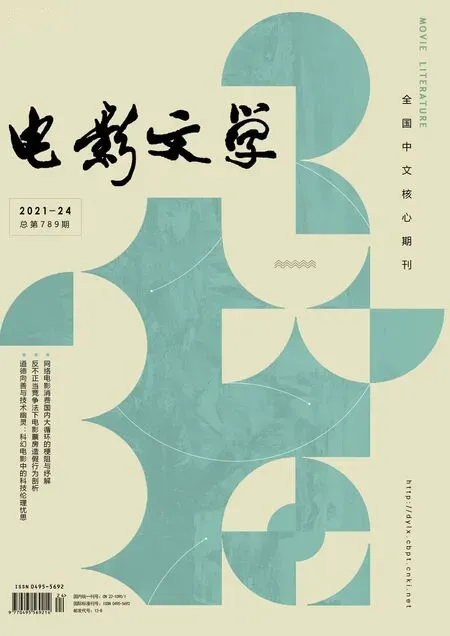观念为先、人伦叙事与作者追求
——评影片《刺杀小说家》
刘 好 袁智忠
(1.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术学院,重庆 401524;2.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一、观念为先:新奇幻电影的工业化突破
电影《刺杀小说家》讲述了现实世界与小说家笔下异世界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故事。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路阳就已经开始预想影片中会涉及的奇观视效,以及实现这种视效的拍摄方法和后期特效制作的方向。为了构建出独特且奇幻的小说异世界,影片采用“面部捕捉”“虚拟拍摄”等高科技创作方式,这也是首部大规模使用“虚拟拍摄”的工业化国产影片,并且在叙事上用更具特色的结构变型实现电影观念和电影实践上的创新,以此创作出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新奇幻电影。《刺杀小说家》的“先行”观念即是在这样的故事文本中反向刺激了“新”奇幻电影的工业化概念,实现突破。
工业化标准之“新”。“我们实现了一套全新的标准化工业流程,为之后的中国电影特效制作提供了经验,同时要让观众看到我们做的东西不输好莱坞”,导演路阳说。想要摆脱国产奇幻特效的刻板“五毛”印象,必须以“鉴”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这就需要创作者在制作的过程中权衡试错的成本,吃透受众的观影心理,呈现遵循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作品。于是,作者使命注定让《刺杀小说家》自带“先行”性,其显著的特点即是“后期前置化”,对于此概念的研究早期多是在纪录片领域,但是随着数字技术在影视创作流程中的全面介入,传统意义上的“后期制作”不仅是“最后工序”,而且在电影创作中从概念上围绕着“视觉性”来展开创意,这也是新奇幻电影中的“神化”魅力。而在导演路阳的手中,一个自由发挥的异世界场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东方影像奇观。大部分中国奇幻类型电影的“东方美学”塑造方式,都旨在基于对中国古代地缘文化认知中的异域地理风貌和异人神兽之塑造,故事选择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作为异世界的基底,营造一个在东方故事框架里的东方美学,烛龙坊街道、大殿门、白翰坊坊门等场景充满了中国古建筑的设计风格,塑造具有辨识度的东方视觉奇观;红甲武士一身中国红战袍,打斗设计震撼有力,展示中国功夫之精华;赤发鬼终极对抗的山顶花园,在四面佛像的包围下,揭示中国传统观念的正义与邪恶。在创作前期,导演的脑海中已经前置化地具象了这一叙事场景,将场景的磅礴、视效的精湛革新与观众的观影情绪相连接,导演路阳做足功课,在预期中实现影片的工业化流程,并在影片宣传中吸引流量,渲染口碑。这一切都是在视觉数字技术的前提下,实现新奇幻电影工业标准的转换,也为中国故事披上了符合东方审美的“外衣”。奇幻是游走在现实与架空世界的充分发挥空间,虚无的奇幻世界与现实社会语境又存在一种悖论,《刺杀小说家》真诚且不至于炫技的另一个关键即是在叙事结构上的创新。
叙事结构之“新”。在工业化电影的叙事突破中,《刺杀小说家》展现了两维时空,一个幻想中的奇幻世界,一个幻想中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世界发生在赛博朋克风的山水重庆,纠结与疑惑在狭窄老旧的下半城展开,潮湿的气候和刻意的色温带来了浓重的末世氛围。一个城市的影像风格建构着其独有的文化空间和人文感受,借助山城重庆特有的空间感和气候,制造出压抑和忧伤的氛围。《刺杀小说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铺陈,影片以这个世界充斥着“变种人”为故事的基础,用“买凶杀人”为由引出小说人物的命运与李沐的命运产生的关联,在诱惑下合理地将主人公关宁带入圈套。在此背景下,展开了精彩的图书馆激战,即使是违背现实逻辑制造的动作奇观,“电人”拥有特异功能,他的搭档在注射某种药剂后变得体能惊人,以一敌百,导演大过异能动作片瘾。值得思考的是,虽然创作者为观众铺设了故事背景,但为什么观众会将一切合理化,对基于现实时空中的异能荒诞设计少有质疑呢?那是因为另一个更为天马行空的小说空间穿插叙事,现实与小说时空的叙事在短时间内没有充分的逻辑关系,也未像普通叙事方法一样将两个空间形成自然的向心力,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小说时空中路空文笔下的“皇都”世界的人物遭遇与现实世界的人物遭遇渐渐重叠,让受众随着叙事的清晰陷入观影的沉浸感中,让两条线索逐渐回归到主旨逻辑线中。这样看来,《刺杀小说家》以一个先入为主的主线线索展开叙事,但实际意图却是“分裂”的,小说中的幻想世界,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宣泄窗口,则占据了更大的篇幅,“现实世界”作为整部电影情节的真正根基,却成为对幻想世界的一种补充。路阳说道:“《刺杀小说家》的故事更自由,没有现实主义语境的限制,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更自由的方式去进行故事的创作。”路阳导演在叙事上给自己搭建了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舞台,用不局限于时空或类型的方式将一切犯罪、善恶、荒诞的叙事交由奇幻的时空,一方面巧妙规避尺度问题,另一方面借以“幻象”抒发作为学院派出身的电影导演难以摆脱的使命感和社会人伦的思考。
二、人伦叙事:影像叙事的内向化表达
2021年春节贺岁档七部影片中均把握住了贺岁心理,在团圆之际满足受众娱情同构与小确幸憧憬的需求,大打亲情牌、喜剧牌、明星牌,影片《你好,李焕英》接档排片大卖40亿元票房正是最好的例证。《刺杀小说家》综合票房稳居贺岁档第三,其营销定位是影片主创们的一次博弈,影片以平稳而又内敛的方式参与竞争,不至于埋没在“娱乐至上”的排片列表,其策略即是故事原本构架具有情感内核,与看似注重书写“以情动人”的作品不同,而是通过对艺术手段的调用来铺设实现,将影片改造成为“走心”的视觉作品,实现美学追求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初衷。在此意义上,与其说创作者对当下影视类型进行了思考和改版,不如说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对人伦关系有所思考和感悟,并进行内向化的叙事。这样的内向化叙事不是偶然,而是代际导演的创作共识,在中国电影的观念、制片规模、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发生巨变的当今,所涌现出来的一批兼顾“票房+口碑”的新力量导演,其共性即是在“体制性”和“作者性”的天平上找到平衡点,并用作品表达作者思考。“外向化的情节中,人物命运多受客观环境驱使,而内向化叙事中,人物命运更受到人物内心环境的驱使,新生代电影更注重人物心理典型而不是外部环境的典型。”
“人伦”为儒家理论,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对“五伦”有所阐释:“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刺杀小说家》中内向化的人伦叙事是贯穿始终的,最突出的即是“人伦”中“父女之情”的书写,也是整部影片情感逻辑合理化的“基石”——寻子。影片的开头,一个女孩子的三声“爸爸”画外音,不仅喊应了梦境中的关宁,也巩固了受众的观影预设,一个父/子、梦境/现实的故事将娓娓道来。有关“寻子”牵涉了两个对比人物,李沐身边精神力量很强的反派女性屠灵,坚持不懈一直找寻女儿小橘子的关宁。其一,关宁寻子秉承“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的信念,关宁的内在动力是通过对比视域进而强化的,回忆视域中多个与妻女的温馨画面,透过门缝在温暖的色温下女儿和妈妈唱着“小橘子”之歌,有关成长的“小确幸”歌词:长高高、红烧肉、糖醋里脊……加上小孩的爽朗笑声,同时也强化了受众的寻子欲望;相比较现实视域中的邋遢落魄、暴力与误会,足以展现主人公寻子的心切和失子的悔恨。导演路阳巧妙地运用听觉记忆埋下了关键线索,在小说世界中女儿“吹响笛子”,父亲化身红甲武士对抗赤发鬼;现实世界中关宁用一首来自鸟山明《阿拉蕾》片尾曲的歌谣将小橘子的模糊样貌唱具体,实现寻子成功的大圆满结局。其二,屠灵在李沐的错误引导下,固化地以为把孩子弄丢/抛弃孩子即是一种不负责任,自己在没有得到“爱”的成长环境下,扭曲的思维被强化,但是当她见证了关宁对寻找女儿的坚持,并且也亲自解开了刺杀小说家之谜,内心的仇恨逐渐冰释瓦解。对比下的“父女”人伦叙事中,父亲与女儿的关系就像是“一段旋律”似的相连接,是“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途中也许有很多阻碍和误会,但是唤回亲情的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而寻子中的父爱表达也形成了辐射圈,关宁与屠灵的共同成长则是“感化”与“被感化”的关系。人伦叙事中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影片的价值内核,即在寻亲之路上找到“坚持”和“信任”的意义,也找到在抵抗实力悬殊的“大魔王”时的方法。至于屠灵的情感和解,导演采用了开放的表现方法,不对成年形象加以道德评价,但该形象在故事中“由恶变善”的成长,也许已经让她对父母的恨意得以冲淡。《刺杀小说家》中“寻子”人伦关系的对比表达实现了影片的主题抒发——“只要相信,就能实现”。正如路阳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向化目标:“做后期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很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一年大家都不容易,都在想办法度过这一年,可能《刺杀小说家》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有意义。”这也是导演在“后疫情”时代创作语境下的生命感悟。
《刺杀小说家》工业化“亮剑”的同时,并未丢失内容表达,尤其是有关人伦叙事的情感表达,情感的饱满度与视觉的冲击性两者相得益彰,良性互动,合力呈现一部具有观众缘的作品。戏剧美学观中阐释内向化叙事的目的是“越来越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观照人心的艺术方式,不仅是剧作家们用来映射外部世界的一面镜子”。导演路阳在《刺杀小说家》中将情感内核放置故事的基底,在受众完成外向化视效享受之后,回味的却是关于主题的思考,让人共情的是一种基于强烈主体意识的自我对话,当然,还有旋律“小呀小橘子……”
三、作者追求:理性写实的趣味书写
随着数字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短视频行业的泛滥,观众逐步地养成了碎片化阅读的习惯,让观众放下手机,在影院里用近100分钟来欣赏一个故事,这就需要电影讲述者尽显十八般武艺,用情节、视效、流量等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院线排片也给观众许多的选择,受众在做选择的时候,善于将影片粗略分类:喜剧的、感人的、高概念的、有明星的……以一种固有的审美期待看电影。在观看《刺杀小说家》时受众原本的审美期待的是视觉特效的盛宴和叙事的巧妙,但在影片推向高潮时,影厅里不缺笑声,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趣味书写一方面是创作初衷与贺岁档的和解,另一方面就是属于导演的理性叛逆。
将冲突“戏谑化”。在奇幻世界中,一个名叫“赤发鬼”的邪神凭着精神与信仰的煽动引发各方彼此的残杀与征讨,在底层互害的背景下路空文深陷其中,随着叙事线索的重合,路空文与小橘子遭遇危险,宵禁来临时,两个单薄的个体暴露在外,被红甲武士在街道上追逐穿梭的桥段中,异能人自带音效地营造一种“无敌”即视感,这样的处理神似导演温子仁《海王》中意大利屋顶跑酷,破坏王和手无寸铁的小人物展开博弈,破坏王具有开挂能力横冲直撞,用暴力清除眼前阻碍,升格拍摄冲出房顶有《金刚》穿梭丛林的即视感,力量十足,而小人物不同,赤手空拳地在合作中巧妙地化险为夷,展现团结和机智;决战“赤发鬼”的山顶花园,月光的照射下,面对三头六臂的“大魔王”无计可施,荒诞即是在“只要相信,就能实现”之后,用导演扎克·施耐德《美少女特工队》、佐藤顺一《美少女战士》的双时空叙事与高概念的日本动画动作进行设计处理,童年的记忆告诉我们,在月光剪影前喊出“代表月亮消灭你”时,美少女就是正义的化身,正义终将打败邪恶。在故事的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导演没有遵照传统的方式,例如用爱感化、编写巧合或是加以援军等,而是用趣味书写的方式将情节推进,尽管有些荒诞,但是将其摆入早已铺垫好的剧情当中,让逻辑合理,这样的突破是用实际行动宣告华语流行电影步入了一个更加“年轻”、更加“快餐”的时代,导演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精准受众的投放与集体大众娱乐。也许,这样的表达是作者的理性思考,面对“大魔王”时,观众也心知肚明要拔下眉眼中的刀才能取得胜利;但面对力大无穷的邪恶势力,脑洞大开的导演没有让对战人物变成势均力敌的实力对战,落入“英雄式”的超能固化形象塑造,而是巧用“戏谑”表达电影主题,为终将取得胜利的正义之战找到娱乐点。其实面对生活,也可以如此。
将影像“游戏化”。如果从电影类型化的角度对《刺杀小说家》进行分析,影片在文本建构层面,就着手思考如何将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相结合,于是影片通过情节的合理架构,融合不同类型与戏剧性元素——武侠、悬疑、奇幻,甚至动漫、游戏等进行呈现。路阳说道:“《刺杀小说家》中当然有一些游戏化的特质,实际上现在很多主题游戏,尤其是3A游戏(Triple A Game:高投入,长周期,高消耗的游戏),有非常具有电影感的镜头设计。”《刺杀小说家》中的影像“游戏化”过程是受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带入的。对照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体验环节,可以归纳为:领取任务(主人公关宁领取了刺杀小说家路空文的任务)、收集道具(发现自己的梦境和路空文小说的联系,揭露李沐买凶杀人的真相)、学习技能(掌握异能,也是对抗大魔王的基础)、闯关并打大BOSS(在小说世界中合力智取赤发鬼)、游戏通关(寻女成功,圆满结局)。采用了游戏化的叙事方式,通过在影片中设计游戏引导主角参与游戏完成任务,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影像“游戏化”的进阶方式是符合观众心理预期的,观看影片的过程更可以想象成为一场游戏“直播”,增加参与感,观众可以在了解规则的基础上与剧情共情,确实是一种大胆而有效的尝试。在游戏逻辑相似的基础上,影片的特效也充分地考虑到了游戏“动漫化”,在赤发鬼的神座殿上,舞美设计是出奇的磅礴,衬托出路空文和小橘子的渺小,制造出奇幻感和游戏感;人物在小说空间中的形象、化妆、打斗动作、武器等都具有科技感和设计感;营造的游戏空间成为电影的双重空间,为观众提供了新的空间想象。“《刺杀小说家》中有一些漫画的意识,也有游戏镜头设计的意识,但它又不是独立于电影叙事之外的。我们会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让他们变成电影的方式。”路阳说。游戏感与漫画感增加了影片的元素,让影片更具有可看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将元素融合拍摄成为以叙事和情感为基础的电影。影像“游戏化”的处理表现了新力量导演在创作过程当中的理性叛逆,也是同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的观众之间生命体验的共情。
从整个2021年春节贺岁档的热议来看,7部贺岁影片给“后疫情”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维,具有传统电影所不具有的新特点、新叙事模式和新观影体验。《刺杀小说家》既是突破者、创作者在拥抱工业化数字技术革新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平衡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并以作品说话,带领观众享受视觉盛宴。更可贵的是,在急剧转型的社会变革中,创作者能与自己对话,绽放出内向化的艺术个性,给作品以更深刻的价值。在新锐导演的眼中,观众不再是观看者,而是电影表达的参与者,共同实现电影的社会人伦关怀。这一点,很路阳。